|
劉文典(公元1889~1958年),中國文學史家,字淑稚,原名文聰,安徽合肥人。1919年赴日本求學,1916年回國,歷任北京大學教授、安徽大學校長、清華大學國文系主任。1938年到昆明,先后在西南聯大、云南大學任教,為九三學社成員。終生從事古籍校勘及古代文學研究和教學,著作有《淮南鴻烈解》、《莊子補正》、《三余雜記》等。
劉文典的怪與狂
劉文典怪。
有學生描寫清華時期的劉氏:“‘以貌取人,失之子羽',這句笑好像特別是為我們劉先生而設的……劉先生憔悴得可怕——看呵,四角式的平頭罩上寸把長的轉發,消瘦的臉安著一對沒有精神的眼睛,兩顴高聳,雙頰深入;長頭高兮如望空之肌膚瘦黃兮似辟谷之老衲……狀貌如此,聲音呢?……既尖銳又無力,初如饑鼠兮終如寒猿……”到了西南聯大任教時期,又有學生回憶劉氏上課前,先由校役提一壺茶,外帶一根兩尺來長的竹制的旱煙袋。他講到得意處,就一邊吸著旱煙一邊解說文章中的精義,不理會下課鈴響。或稱劉“儼如《世說新語》中的魏晉人物”。
劉氏還性格滑稽,善談笑,嘗自稱叫“貍豆鳥”;此因“貍”、“劉”古讀通;“叔”者豆子也;“鳥”則為“鴉”乃“雅”之異體(劉文典字“叔雅”)。這種自謔,令人噴飯,與道貌岸然者異,故“學生們就敢于跟他開點善意的玩笑”(學生回憶)。
怪之甚者,是劉文典請陳寅恪出“國文”試題,陳出上聯“孫行者”以覓下聯,劉氏也不以為然,許之,結果考糊了很多考生,一時傳為新聞。
劉文典又狂。
劉原籍合肥,可對于皖系軍閥段琪現常攻擊之,往往詈及父母,令人不能記述。
長安徽大學期間,為了學生鬧風潮一事,劉與前來視察的蔣介石起爭執,被拘,后經蔡元培等力保,方“即日離皖”以了事。事后,劉之師章太炎特贈聯一副以贊之,聯曰:“養生未羨嵇中散,疾惡首扒彌正平。”
劉治《莊子》,作《莊子補正》,嘗謂:“古今懂莊子者,唯二人半而已。”劉曾講元遺山、吳梅村詩,講完稱:“這兩位詩人,尤其是梅村的詩,比我高不了幾分。”自負如此。
還有一次,劉在聯大躲日機突襲之警報,遇一從事白話文創作的同事,當場斥之:“你跑什么警報?我跑因我是‘國寶'”。其人要評教授,劉勃然大怒,道:“陳寅恪是真正的教授,月薪該拿四百,我該拿四十,朱自清只能拿四元,可他,我不會給四毛錢!”
劉文典之怪之狂,當不是無本的。倘腹中空空,又怪且狂,乃一“瘋子”。劉氏豈是瘋子!考其涵養與行藏,既學問淵博又思想進步愛國。
關于前者,有胡適之、陳寅恪評價為證:胡為其《淮南鴻烈集解》作序云:“叔雅治此書,最精嚴有法。”陳為其《莊子補正》作序云:“先生之書之刊布,蓋為一匡當世之學風,而示人以準則,豈僅供治《莊子》者所必讀而已哉!”學生對劉氏的反映是:“先生于經史百家,無所不學,講課莊諧具出,妙趣橫生。”“他教勻們《圓圓曲》、《萬古愁》兩篇文字時,把明末清初的事如數家珍般一一說給我們聽,并且在黑板上列舉了很多典故。像這樣博涉群書而又能駕馭者,豈是時下讀兩卷小書便以學者自命的小鬼們所能同日而語的!”
至于后者,不妨簡述一下其生平。劉少時在安慶讀書,得到陳獨秀、劉師培的賞識,18歲入同盟會。東渡日本即師事章太炎。辛亥革命后一年回國,在上海與于右任、邵力子辦《民立報》。袁世凱為復辟謀刺宋教仁,宋遇害時劉因隨陪在側也遭槍傷。后又任孫中山秘書處秘書。洪憲的袁皇帝死,劉回國到北大任教,其間為《新青年》編輯,曾掩護過陳獨秀的出逃(羅章龍說)。由北大而安大(安徽大學)即發生沖突蔣介石事。遂回北大,復去清華。抗戰事起,劉失去愛子。“公私涂炭,堯都舜壤,何期?”又輾轉來昆明的西南聯大,不失大節。后留云大,共和國成立,劉即戒去“阿芙蓉癖”,是一級教授,以教書為天職,樂育天下英才。綜觀劉之一生,誠“與時共進”,非冥頑僵化之輩。
學問淵博,思想進步愛國,乃“大人”也。大人不失赤子之真,故其無虛飾、不矯情,其狂其怪,不亦劉氏赤子之真的表現乎?!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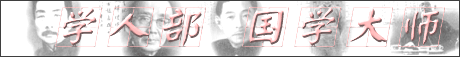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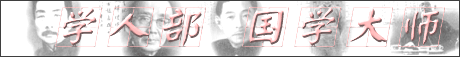

mailto:guoxue@guoxue.com
![]() 010-68900123
010-68900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