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學在中國的建立和發展,是二十世紀中國學術界最為重要的成就之一,對歷史研究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它的誕生,有賴于兩個條件:一是傳統金石學的發達;二是西方考古學理論和方法的傳入。(注:參見張光直:《考古學與中國歷史》,收入《考古學的歷史·理論·實踐》,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再加上一大批中國學者的共同努力,才使得考古學這門新興學科得以在中國建立并迅速發展壯大。傅斯年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位代表人物。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東聊城人。早在北京大學讀書期間,他就積極參加五四新文化運動,創辦《新潮》雜志,宣揚“民主”、“科學”等西方新思想、新學理,名震一時。1920年初啟程赴英國、德國留學,初攻實驗心理學,后治哲學,兼讀歷史、數學、物理學、語言學、人類學、比較考古學等科。1921年底回國,受聘擔任中山大學教授,兼文學學長及國文、歷史兩系主任,后受命籌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任所長一職長達三十余年,直到去世為止。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持了中國考古史上多次重大發掘,如安陽殷墟、城子崖等。抗日戰爭期間,該所繼續在西南、西北等地從事考古活動,并在整理、研究考古發掘物方面也做出了巨大的成就,為建立科學的考古學蓽路藍縷。傅斯年倡導的“近年的歷史學就是史料學”,即是建立在考古學迅速發展的基礎之上的。此外,他廣延人才、培植新秀,為考古學的薪火相傳嘔心瀝血,體現了一代學者對考古學的關心與重視。本文主要探討傅斯年在考古實踐,即他任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期間對考古學的發展所作的推進作用,以及他在考古學理論和方法上的特殊貢獻,借以說明中國考古學的發展并不是一帆風順,而是歷盡曲折,經過眾多學者長期不懈、共同奮斗的結果。
一、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國考古學的發皇地
“傅斯年在學術上的最大貢獻,恐怕應在于他創辦并主持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注:楊志玖語。轉引自《傅斯年與歷史語言研究所》,《文史知識》,1999年第5期。)1949年以前,該所是從事田野工作最多的單位,舉其犖犖者即有:1928-1937年在安陽殷墟的十五次發掘;與山東、河南兩省地方政府分別組成古跡研究會,發掘了山東城子崖和兩城鎮遺址,河南浚縣辛村衛國基地,汲縣山彪鎮和輝縣琉璃閣東周墓地以及永城造律臺等遺址。抗戰爆發后,時局動蕩,中國東南半壁河山淪入日本之手。該所仍在大后方堅持考古發掘不輟,先后組成幾支考察團,發掘了云南大理、蒼洱地區的古代遺址,四川彭山漢代崖墓及成都前蜀王建墓,又在河西走廓和關中地區進行調查發掘,獲得了大量的考古資料,在中國考古學史上寫下了輝煌的一頁。下面僅以安陽殷墟的發掘和研究為中心,說明歷史語言研究所為中國考古學的發展所作的巨大貢獻。
傅斯年1928年4月受命籌建歷史語言研究所,他所擬定的工作計劃包括范圍相當廣泛,共列有九組:文籍考訂、史料征集、考古人類及民物、比較藝術,以上屬歷史范圍;漢語、西南語、中央亞細亞語、語言學,以上為語言范圍。后在正式成立時合并為三組:(注:歷史語言研究所在1934年增設人類學,(第四組),1946年又設立北平圖書史料整理處。)歷史學、考古學和語言學,分別聘請陳寅恪、李濟、趙元任為各組主任。從先前把考古學納入歷史范圍,到將其與歷史學、語言學并列,視為一門獨立學科,體現了傅斯年對考古學的重視,代表了世界考古學發展的趨勢。
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后,傅斯年聘任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系博士畢業生、山西西陰村史前遺址發掘主持人李濟領導考古組,并提出了“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作為考古組的口號。當時的傅斯年,剛過三十,年富力強、精神飽滿、意氣風發,渾身充滿活力,不但具有雄厚的國學根柢,對于歐洲近代發展的歷史、語言、心理、哲學都有精深的認識,“是了解現代考古學和科學技術的少有的幾個天才人物之一”。(注:李濟:《安陽一殷商古都發現、發掘、復原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因此,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伊始,便開始了震驚國內外學術界的安陽殷墟發掘。
有學者認為,仰韶村、周口店的發掘標志著中國考古學的誕生,以重建古史為目標的殷墟發掘為中國考古學的發展。(注:參見張忠培:《關于中國考古學的過去、現在、未來的思考》,《傳統文化與現代化》,1999年第1期。)事實上,仰韶村、周口店的考古發掘和研究均是由外國人主持的,主要采用的是古生物學、地質學、體質人類學等自然科學的方法。因此,從嚴格意義上說,由中國人自己主持的大規模、有目的、科學的考古發掘應是安陽殷墟,并以此為契機,揭開了中國考古學及其相關學科研究的序幕。主持安陽殷墟發掘的單位即是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作為所長的傅斯年,在這次發掘中表現了卓越的組織能力和高超的科學發掘技術。
早在李濟就任考古組主任之前,傅斯年便派董作賓赴安陽進行初步調查,并做了第一次試掘,取得了豐碩的收獲。初戰告捷,令人鼓舞。傅斯年之所以選擇安陽殷墟,是基于“安陽之殷墟,于三十年前出現所謂龜甲之字者。此種材料至海寧王國維先生手中,成極重大之發明。但古學知識,又不僅在于文字。無文字之器物,亦是研究要件。地下情形之知識,乃為近代考古學所最要求者。若僅為取得文字而從事發掘,所得者一,所損者千。……此次初步試探,指示吾人向何處工作,及地下所含無限知識,實不在文字也”。(注:傅斯年:《本所發掘安陽殷墟之經過》載《國立中央研究院十七年度報告》,收入《傅斯年全集》第四冊,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年。)從中可以看出傅斯年對考古學的理解很徹底全面。因此,李濟到任后,便立即主持了第二次發掘。比起第一次來說,這次發掘更符合近代考古學的標準,除系統地記錄和登記發掘出的每件遺物的準確出土地點、時間、周圍堆積物情況和層次之外,還要求每個參加發掘的工作人員堅持寫下個人觀察到的及田野工作中發生的情況的日記,因而第二次發掘的成果更為顯著。此后,在傅斯年的全盤統籌之下,考古組排除種種困難。這些困難既有經濟上的資金不足,又有政治上與地方政府的矛盾。傅斯年總是想方設法加以克服,保證了殷墟發掘工作的順利進行。
隨著考古發掘規模的不斷擴大,歷史語言研究所的考古活動吸引了一批從國外留學歸來的專業考古人才,如梁思永及后來加入的吳金鼎、夏鼐、馮漢驥等。此外,大量的考古實踐也培養了一群中國自己的考古學家,包括董作賓、郭寶鈞、劉耀(尹達)、胡厚宣、高去尋、石璋如等。他們具有豐富的知識和經驗,為中國考古學的發展奠定了人才基礎。
安陽殷墟發掘共進行了十五次,不僅是中國學術界的一次壯舉,在世界考古學史上也是為數不多的重要考古發掘之一。國家學術界對其成就給予高度評價,認為它是可與十九世紀希臘特洛伊(Troy)古城的發掘和二十世紀初克里特島諸薩斯(Crete Knossos)青銅文化遺址的發現相媲美的重大事件。可惜,1937年,由于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安陽發掘活動被迫中斷。
安陽殷墟的發掘在考古學上的重要意義,按照李濟的說法,“有三點特別值得申述:第一,科學的發掘證明了甲骨文字的真實性。這一點的重要常為一般對甲骨文字有興趣的人所不注意,但實富有邏輯的意義。因為在殷墟發掘以前,甲骨文字的真實性是假定的。就是沒有章太炎的質疑,(注:章太炎:《國故論衡·理惑論》“近有掊得龜甲骨,文如鳥蟲,又與彝器小異。其人蓋欺世豫賈之徒,國土可鬻,何有文字?而一二貿儒信以為質,斯亦通人之蔽。”)科學的歷史學家也不能把它當著頭等的材料看待。有了史語所的發掘,這批材料的真實性才能明了,由此甲骨文的史料價值程度也大加提高。此后,就是最善疑的史學家也不敢抹殺這批材料。章炳麟晚年偷讀甲骨文,是他自己的門人傳出來的;第二,甲骨文雖是真實的文字,但傳世的甲骨文卻是真假難分。在殷墟發掘以前,最有經驗的藏家也是常常受騙的。有了發掘的資料,才得到辨別真假的標準;第三,與甲骨文同時,無文字的器物出土后,不但充實了史學家對于殷商文化知識的內容,同時也為史學及古器物學建立了一個堅強的據點,由此可以把那豐富的但是散漫的史前遺存推進一個有時間先后的秩序與行列。”(注:李濟:《傅孟真先生領導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幾個基本觀念及幾種重要工作的回顧》,收入《感舊錄》,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3年。)殷墟多年發掘的結果,得到了一批承上啟下,具有連鎖性的考古資料,將中國的信史向上推進了數百年,把史前的文化與歷史的文化作了強有力的聯系,為世界所矚目,引起各國考古學者,如伯希和(Paul·Pelliot)、高本漢(Kartgren·Bendhand)、梅原未治等人的極大關注,伯希和就曾于1935年親臨安陽發掘現場參觀。張光直也強調了安陽發掘在中國考古學史和歷史研究中的重要性,“一方面是由于殷墟是中國考古學史上頭一個用現代科學方法作長期發掘的遺址,所以在殷墟發掘過程中考古學者所經驗出來的心得,對以后本世紀考古工作者思想和研究的習慣,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影響。另一方面,由于殷墟是目前中國歷史上最早的一個有文字記錄的考古遺址,它對于中國史前和歷史時期間的關系的了解上,便發生了承先啟后的作用”。(注:張光直:《安陽·序》,收入《考古人類學隨筆》,三聯書店,1999年。)可以說,殷墟的發掘及甲骨文的發現,開辟了中國學術研究的新紀元。
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后,安陽殷墟的發掘活動匆忙結束,從此開始了漫長而艱難的流亡之路。歷史語言研究所有21萬冊圖書,大半屬于文史方面,另外還有一大批考古發掘物和金石拓片,轉移起來非常不易,而其幾次播遷,先南京、歷長沙、昆明,最后定居在四川南溪縣的李莊。此外,傅斯年把存在南京的出版品,全部裝箱,派員押運到香港,交與商務印書館,存在九龍倉庫中。可惜,這部分珍貴的資料在日本侵占港九時,全部被炸毀了,這是一筆無法彌補的損失。參加殷墟發掘的考古人員遂轉入對安陽發掘物的研究。李濟負責對安陽陶器的裝飾和器形進行詳細的研究,董作賓在胡厚宣的協助下繼續潛心研究甲骨文,梁思永初步審核侯家莊的發掘記錄。這些學者之所以能夠靜心從事研究工作,與傅斯年的支持與幫助是分不開的。
戰時的重慶,物價飛騰,經濟十分拮據,生活尚成問題,更不用說進行調查發掘和出版學術專著了。傅斯年總是想盡一切辦法,盡量派人到云南大理、西北各地和四川本省參加各種學術調查和發掘活動。如大理南詔文化遺址的發現、四川彭山東漢崖墓的挖掘,都達到了很高的科學水平。同時,他還千方百計將學者的研究成果出版。在經費相當緊張的情況下,歷史語言研究所先后出版了一批學術精品,其中包括陳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趙元任等編輯的《湖北方言調查報告》、勞干的《居延漢簡考釋》、董作賓的《殷歷譜》等歷史、語言、考古人類學的研究成果。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董作賓所撰著的《殷歷譜》。
董作賓在《殷歷譜》中大量使用把甲骨卜辭按占卜日期排列起來進行綜合研究的排譜方法,從卜辭中整理出商王按嚴格規定的日程逐個祭祀先王、先妣的所謂“五種祀典”制度。這種根據甲骨卜辭所反映的禮制等方面的情況進行研究的方法,揭示出了甲骨卜辭中一些需要加以解釋的重要現象,對于甲骨文的斷代研究和禮制等方面的研究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傅斯年慧眼識英才,多次勸勉督促董作賓寫印《殷歷譜》,并親自籌劃印刷出版事宜。董作賓回憶道:“傅孟真先生曾殷殷見詢,此書其若干字,印若干頁,需若干紙,曷早為之計,物價且飛漲也。”(注:董作賓:《殷歷譜·自序》,收入《董作賓先生全集》,臺灣藝文印書館,1977年。)在傅斯年的催促和關注下,董作賓歷時十年,數易其稿,終于在1945年完成了《殷歷譜》,并手寫石印出版。傅斯年為這部不朽的巨著撰寫了序言。高度評價了董氏的學術成就,指出董作賓在歷法研究中廣泛應用新技術,并用現代天文學關于日月食的記錄加以檢驗,澄清了商朝統治時期的順序。最后他寫道:“必評論此書之全,則有先決之條件:其人必通習甲骨如彥堂(董作賓字彥堂);其人必默識歷法如彥堂,必下幾年工夫”。(注:傅斯年:《殷歷譜·序》,載《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1945年。)就《殷歷譜》的學術價值而言,這種評價是絲毫不過份的。
傅斯年領導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對安陽殷墟的發掘和研究,極大地推動了中國考古學的發展。對此,鄧廣銘有極中肯的評述:“可以說,中國沒有個傅斯年,就沒有二三十年代的安陽殷墟發掘;沒有當初的殷墟發掘,今天的考古學完全是另一個樣子”。(注:鄧廣銘:《回憶我的老師傅斯年先生》,收入《傅斯年》,山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
二、傅斯年的考古學理論和方法
傅斯年不僅在考古實踐上有突出貢獻,在考古學理論和方法上也有卓越的建樹。他在德國留學期間,正值蘭克(Ranke'L'von)派史學觀點盛行之際。蘭克學派的主要理論是提倡“科學的史學”,深信史學可以而且必須客觀化,其中不能摻入一絲一毫個人的主觀見解。在蘭克看來,史學最后可以發展到和生物學、地質學同樣高度的科學性,落到實踐的層面,則是借重語言學的知識從事考證,以史料學為史學在史料范圍的擴大和考訂的精密方面。傅斯年在德國柏林大學期間,在主修哲學的同時,廣泛涉獵其他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尤精于科學方法論。他受到兩種科學空氣的影響:一是近代物理學,如愛因斯坦相對論,普朗克的量子論;二是德國歷來引以為榮的語言文字比較考據學。在這種學術氛圍的熏陶下,傅斯年成了蘭克學派在中國的積極倡導者。他在中山大學和顧頡剛一起創立語言歷史研究所,在《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周刊》第一集第一期的發刊詞中就明確提出:“所以我們正可承受了現代研究學問的最恰當的方法,來開辟這些方面的新世界。語言、歷史學也正和其他的自然科學同手段,所差的只是一個分工”。(注:均轉引自傅樂成:《傅孟真先生年譜》,傳記文學出版社。)關于研究宗旨,他又做了明確的說明:“我們要實地搜羅材料,到民眾中尋方言,到古文化的遺址去發掘,到各種的人間社會去采風問俗,建設許多的新學問。”。(注:均轉引自傅樂成:《傅孟真先生年譜》,傳記文學出版社。)這無異是傅斯年史料學思想的宣言書,蘭克學派的影響已初見端倪。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的結尾處,更可以明顯地地看出來:“一,把些傳統成自造的‘仁義禮智'和其他主觀,同歷史學和語言學混在一起的人,絕對不是我們的同志;二,要把歷史學、語言學建設得和生物學、地質學等同樣,乃是我們的同志;三,我們要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注:收入《傅斯年選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這確是蘭克學派歷史主義的基本見解。在《史料與史學》發刊詞中,他再次重“申史學只是史料學”“這一思想:”此中皆史學論文,而名之曰‘史料與史學'者,亦自有說。本所同人之治史學,不以空論為學問,亦不以‘史觀'為急圖,乃純就史料以探史實也。史料有之,則可鉤稽有此知識。史料所無,則不敢臆測,亦不敢比附成式。此在中國固為司馬光以至錢大昕之治史方法。在西洋,亦為軟克(蘭克)、莫母森(Mommson)之著史立點。”。(注:原載《中研院史語所集刊》外編第二種,《史料與史學》,1945年。)傅斯年提倡的科學的史學,是乾嘉考據和蘭克實證主義二者的總匯。誠如臺灣學者趙天儀所作的評價:“(傅斯年)把史學當作跟自然科學、經驗科學一樣,是實事求是,腳踏實地的態度,以確切的方法、材料和證據來從事研究的功夫,不能不說是把中國的學問,尤其是史學等部門,從國故的故紙堆中引到更廣大的田野工作上,而獲得更真實、更有意義的結果”。(注:見《傅斯年思想綱要》,收入《中國前途的探索者:中國思想家》第八輯,臺灣巨人出版社,1978年。)
傅斯年“近年的歷史學就是史料學”中的史料一詞包涵的范圍極廣,在《史料與史學》的發刊詞中所列的名目中,除了傳統意義上的文獻古籍之外,還包括田野考古報告(如《安陽發掘報告》)、中國考古報告(已出《城子崖》、《殷墟文字匯編》二種),以及人類學集刊、中國人類學報告等考古人類學方面的原始資料。歷史語言研究所從創立到1948年遷往臺灣,共出版了大量歷史、考古人類學、語言研究考著和論文,其中尤以考古一項的成就最為突出。除在《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中刊載的考古學論文外,還出版了《安陽發掘報告》(1-4冊)、《中國考古學報告(1-4冊)、《城子崖》等發掘資料。在一定程度上,傅斯年提出的史料范圍就含有方法論的意義。無獨有偶,李濟曾發起編寫一套《中國上古史》,在《再談中國上古史的重建問題》一文中,他系統地說明了編撰這部書的一些基本想法,列舉了編寫上古史所需要的七種材料:第一種是與“人類原始”有關的材料;第二種是與研究東亞地形有關的科學資料,包括地質學、氣象學、古生物學各科研究成果;第三是用考古方法發掘出來的“人類的文化遺址”;第四是體質人類學;第五是“狹義”的考古發掘出來的屬于有文字記錄時期的資料;第六是民族學家所研究的對象;第七是“歷代傳下來的秦朝以前的記錄”。(注:原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33本,1962年,收入《考古瑣談》,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兩相比較,不難發現兩人的共通之處,頗有異曲同工之妙。傅斯年的這種建立在考古發掘資料之上的史料學思想,為新史學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如前所述,傅斯年精于科學的方法論,曾著有《史學方法導論》。他主張用盡可用的材料,聯系所有可以聯系的工具,把各個材料的內涵,各種材料間的關系講透徹。這里所說的工具即是方法。1929年,他應邀作《考古學的新方法》的演講。在報告中,傅斯年批評中國考古學家還是用舊方法整理發掘物,即“用文字作基本,就一物一物的研究。文字以外,所得的非常之少”。而西方考古學新方法則是“以世界文化眼光去觀察,以人類文化作標準,故能得整個的文化意義”。考古學離不開人類學和民族學,要注意人體測量,根據比較的方法來推測當時人類的身高及其變化。研究年代學有比較和絕對的兩種方法,用來推定發掘物的年代。他并以安陽殷墟發掘為例,著重談了地層學方法在考古學中的作用。(注:參見《考古學的新方法》,收入《傅斯年選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傅斯年所講的考古學新方法,并不是傳統金石學家所推崇的文字訓詁、名物考訂、音韻等項,而是西方考古學中使用的地層學、年代學、人類學、民族學等新方法,這在總體上為中國考古學的發展指明了方向。
歷史語言考據學是蘭克學派的基本精神,其精益求精,嚴肅謹嚴的方法與乾嘉考據大師所用的方法很多方面相一致。因此,傅斯年把蘭克史學中應用歷史語言學批判考訂史料的實證主義同乾嘉考據學兩派融匯起來,構成“科學的史學”的基礎。應當說明的是,傅斯年所援引的僅是蘭克學派的部分觀點,其他如蘭克的思想和宗教信仰則鮮言之。二三十年代,正值中西學術交流融合最活躍的時期,西方各種研究方法紛紛被介紹到中國學術界,如胡適宣揚的實驗主義,何炳松翻譯魯濱遜(J·H·Robinson)的《新史學》等。傅斯年受到嚴謹治學精神的訓練,提倡先從專題入手,搜集、考訂史料,經過排比之后,再以樸實無華的語言敘述出來。這種風格與考古學所要求的科學性正相吻合,也是新史學得以建立的關鍵所在。傅斯年對中國文化有很深的造詣,學問廣博,經史子集,無不涉獵,在繼承傳統文化精華的基礎上,吸收西方先進的理論和方法,正是傅斯年視野開闊的集中體現。他以歷史語言研究所為大本營,在中國建筑“科學的東方學正統”時,清醒地意識到中西學術交融的發展趨勢:“此日學術之進步,甚賴國際間之合作、影響與競爭,各學皆然,舊學亦未能除外。國人如愿此后文史學之光大,固應在戰勝外國人之心而努力赴之,亦應借鑒于西方漢學之特長。此非自貶,實目廣也”。(注:傅斯年:《論伯希和教授》,收入《傅斯年全集》第七冊。)處在世界學術潮流影響下的中國考古學,更不能抱殘過守闕,固步自封,而要采納新方法,引入新理論,方能開拓考古學的美好明天。
三、余論
傅斯年對考古學的發展是全力支持和嚴格要求相結合的。他非常愛才,但又要求很高,態度很苛。比如對田野考古發掘報告的撰寫,他便有一清楚的標準:“‘過猶不及'的教訓,在就物質推論時,尤當記著。把設定當作證明,把設想當作假定,把遠若無關變作近若有關,把事實未允許決定的事付之聚訟,都不足以增進新知識,即不足以促成所關學科之進展,所以,作者‘多聞闕疑,慎言其余'。……寫近代考古學的報告尤當如此”。(注:見《城子崖·序》,收入《傅斯年選集》。)事實證明,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的田野發掘報告及研究論文著作,盡管由于條件所限,印刷粗糙,但都是高水平的杰作,至今仍是研究者的必備參考書。
作為一名教育家,傅斯年為考古學的發展延納人才,獎掖后進,使中國科學的考古學得以循序前進,不斷發展壯大。以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為中心,吸引了一大批考古學的精英人才。李濟、梁思永、董作賓、石璋如、夏鼐……可以說,傅斯年領導的這一學術研究團體,是中國考古學的中堅。李濟回憶道:“我個人認為,若不是傅先生提倡考古,我的考古工作也許就中斷了”。(注:李濟:《創辦史語所與安陽考古工作的貢獻》,收入《傅斯年》,學林出版社,1991年。)1948年底,歷史語言研究所遷往臺灣,傅斯年所長兼任國立臺灣大學校長,即在臺大文學院創立考古人類學系,培養考古人才。教授陣容來自歷史語言研究所的第三組(考古學)和第四組(人類學)。講授的課程有:考古人類學導論(李濟)、中國古文字學(董作賓)、民族學、中國民族志(芮逸夫)、中國考古學(高去尋)、體質人類學(楊希枚)、民俗學(陳紹馨)、田野考古方法實習(石璋如)、民族調查方法實習(凌純聲)……可謂極一時之選。李濟、董作賓、芮逸夫、凌純聲等都是中國考古人類學的先驅者。在他們的精心教授下,臺灣大學培養了一批考古人類學人才,有的在國際學術界也享有盛譽,如張光直、許倬云、宋文熏、李亦園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傅斯年“在短短的兩年中,為臺大樹立了優良的學風,并為臺灣的學術研究立下了不拔的根基”。(注:李亦園:《永懷師恩—記受恩于傅斯年先生的一件往事》,收入《人類的視野》,上海文藝出版社,1996年。)傅斯年這種對考古人才的吸納與培養,與其倡導考古學的理念相輔相成;使得中國考古學薪火相傳,不斷走向成熟。最后,借用張光直的一段話作為本文的總結:“三四十年代的歷史語言研究所是一個人才薈聚的寶庫。所長傅斯年先生雄才大略,學問眼光好,又有政治力量和手腕。他以‘拔尖主義'的原則,遍采全國各大學文史系畢業的年輕菁英學者,把他們收集所里,專門集中精力作研究工作。所以三四十年代被他拔尖入所的學者多半是絕頂聰明,讀書有成,性情淳樸、了無機心的書生。……高去尋、勞干、丁聲樹、張政烺、陳槃、董同和、嚴耕望等先生都可為代表。這批人才的儲集,可以說是傅斯年先生對中國史學上最大的貢獻”。(注:張光直:《懷念高去尋先生》,收入《考古人類學隨筆》,三聯書店,1999年。)
刊《山東社會科學》2000年第3期,頁75-79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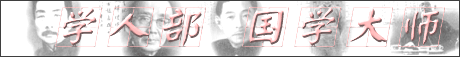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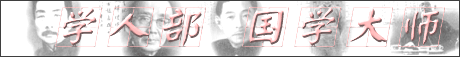

mailto:guoxue@guoxue.com
![]() 010-68900123
010-68900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