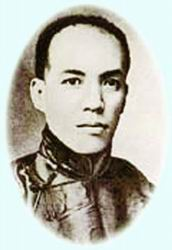 |
| 梁啟超(1873——1929) |
現代史學家中包括“二陳”在內的一批大師巨子,所涉獵和所建樹的史學實際上也可以視作文化史學。所謂文化史學,是指著者不僅試圖復原歷史的結構,而且苦心追尋我華夏民族文化傳承的血脈,負一種文化托命的職責。
史學在中國自有不間斷的傳統,由傳統史學轉變為現代史學,應是順理成章之事。然而向傳統史學置疑容易,提出史學的新概念、真正建立新史學,殊非易事。
現代史學開創者:梁啟超、胡適
已故經學史家周予同先生,在1941年寫的《五十年來中國之新史學》一文中,有如下的論述:“學術思想的轉變,仍有待于憑借,亦即憑借于固有的文化遺產。當時,國內的文化仍未脫經學的羈絆,而國外輸入的科學又僅限于物質文明;所以學術思想雖有心轉變,轉變的路線仍無法脫離二千年來經典中心的宗派。”(見朱維錚編《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第517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事實確是如此。單是新史學與經今文學的關系有所厘清,已是困難重重。按周予同的說法,晚清治史諸家中,崔適、夏曾佑都是經今文學兼及史學。只有梁啟超是逐漸擺脫了今文學的羈絆,走上了新史學的道路。
就此點而言,任公先生對現代史學的貢獻可謂大矣。而現代史學中的學術史一目,也是任公先生開其端的,《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三書,就是他研究學術史的代表作,至今還經常被學者所引用。誠如梁之好友林志鈞所說:“知任公者,則知其為學雖數變,而固有其緊密自守者在,即百年不離于史是矣。”(林志鈞:《飲冰室合集序》,中華書局1989年版《飲冰室合集》第一冊,第3頁)但梁之史學,前期和后期的旨趣不盡相同。1901至1902年寫作《中國史敘論》和《新史學》的梁啟超,對傳統史學的態度甚為決絕,他總結出舊史學的“四蔽”(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知有陳跡而不知有今務;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二病”(能鋪敘而不能別裁;能因襲而不能創作)、“三難”(難讀,難別擇,無感觸),摧毀力極大。后來寫《清代學術概論》、《歷史研究法》和《歷史研究法補編》,則表現出對傳統史學不無會意冥心之處。但不論前期還是后期,梁之史學都有氣象宏闊、重視歷史整體、重視史學研究的量化、重視科際整合的特點。他把中國歷史分為三個階段:從黃帝到秦統一,為上世史,稱作“中國之中國”;秦統一至乾隆末年,為中世史,稱作“亞洲之中國”;乾隆末年至晚清,為近世史,稱作“世界之中國”(梁啟超:《中國史敘論》,《飲冰室合集》第一冊,文集之六,第11至12頁)。這是一種著眼于大歷史的分期方法,頗能反映中國歷史演化的過程。
胡適的史學在梁的基礎上又有所跨越,《白話文學史》、《中國哲學史大綱》,在專史方面已是開新建設的史學了。但胡適實驗的多,完成的少,他的作用主要在得風氣之先和對史學研究的“科學方法”的提倡。二十年代興起的古史辨學派,除了受康有為所代表的晚清今文學的影響,與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直接“從周宣王以后講起”有很大關系。顧頡剛在《古史辨》第一冊的自序里寫道:“第二年,改請胡適之先生來教。‘他是一個美國新回來的留學生,如何能到北京大學里來講中國的東西?'許多同學都這樣懷疑,我也未能免俗。他來了,他不管以前的課業,重編講義,開頭一章是‘中國哲學結胎的時代',用《詩經》作時代的說明,丟開唐禹夏商,竟從周宣王以后講起。這一改,把我們一班人充滿著三皇五帝的腦筋,驟然作一個重大的打擊,駭得一堂中舌撟而不能下。”(《古史辨》第一冊,第36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所以當1923年顧頡剛在《讀書雜志》上發表《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提出著名的“層累造成說”,胡適給予支持;而錢玄同和傅斯年也作有力的回應,疑古思潮遂掀起波瀾。顧的“層累造成說”包括三方面的意思:
第一,“時代愈后,傳說的古史期愈長”。如這封信里說的,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時有堯舜,到戰國時有黃帝神農,到秦有三皇,到漢以后有盤古等。第二,可以說明“時代愈后,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時只是一個“無為而治”的圣君,到堯典就成了一個“齊家而后國治”的圣人,到孟子時就成了一個孝子的模范了。第三,我們在這上既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確的狀況,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傳說中的最早的狀況。我們即不能知道東周時的東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戰國時的東周史;我們即不能知道夏商時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東周時的夏商史。(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載《古史辨》第一冊第60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這些觀點他想在一篇叫做《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的文章中論述,文章未及寫,先在致錢玄同的信里講了出來。倍受爭議的禹大約是“蜥蜴之類”的一條“有足蹂地”的蟲,就是此信中的名句。
顧的這封信在學術界引起巨大的震撼。他后來回憶起這段往事時說:“信一發表,竟成了轟炸中國古史的一個原子彈。連我自己也想不到竟收著了這樣巨大的戰果,各方面讀些古書的人都受到了這個問題的刺激。因為在中國人的頭腦里向來受著‘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的定型的教育,忽然聽到沒有盤古,也沒有三皇、五帝,于是大家不禁嘩然起來。”(顧頡剛:《我是怎樣編寫古史辨的》,載《古史辨》第一冊第17至18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讀書雜志》系胡適主辦,因為顧的這封信展開了一場歷時八九個月的大討論,直到1924年年初方告一段落。而1926年出版的《古史辨》第一冊,則是對這場討論的總結,顧頡剛寫了一篇六萬余言的長序,“古史辨”作為學派因之而誕生。
當時與“古史辨派”相對立的是釋古派和考古派。也有的概括為“泥古派”或“信古派”,指起而與顧頡剛、錢玄同論爭的柳詒徵等文化史家,影響不是很大,且用“泥古”或“信古”字樣概括他們的觀點似不夠準確,可暫置不論。考古派首功當然是羅、王、郭、董“四堂”(羅振玉號雪堂、王國維號觀堂、郭沫若號鼎堂、董作賓號彥堂),還有李濟、夏鼐等。當然考古者大都也釋古。董的《殷歷譜》和《甲骨文斷代研究例》、郭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和《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李濟的《中國民族的形成》和《安陽》等,均堪稱古文字與古史研究的典范之作。釋古派可以王國維和陳寅恪為代表。如果認為梁啟超提出的多,系統建設少;王、陳的特點,是承繼的多,開辟的也多。
最具現代性的史學家:陳寅恪
特別是陳寅恪的史學,是最具現代性和最有發明意義的中國現代史學的重鎮。
他治史的特點,一是在史識上追求通識通解;二是在史觀上格外重視種族與文化的關系,強調文化高于種族;三是在史料的運用上,窮搜旁通,極大地擴大了史料的使用范圍;四是在史法上,以詩文證史、借傳修史,使中國傳統的文史之學達致貫通無阻的境界;五是考證古史而能做到古典和今典雙重證發,古典之中注入今情,給枯繁的考證學以活的生命;六是對包括異域文字在內的治史工具的掌握,并世鮮有與其比肩者;七是融會貫徹全篇的深沉強烈的歷史興亡感;八是史著之文體熔史才、詩筆、議論于一爐。他治史的貢獻,主要表現在對“中國境內之古外族遺文”的釋證、對佛教經典不同文本的比勘對照、對各種宗教影響于華夏人士生平藝事的考證、對隋唐政治制度文化淵源的研究、對晉唐詩人創作所作的歷史與文化的箋證、對明清易代所激發的民族精神的傳寫等等。而所有這些方面,他都有創辟勝解。他治史的精神,則是“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是他學術思想的力量源泉,也可以稱作陳氏之“史魂”。1929年陳寅恪所作《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寫道:“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唯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金明館叢稿二編》第218頁)《柳如是別傳》之緣起部分也有如下的話:“雖然,披尋錢柳之篇什于殘缺毀禁之余,往往窺見其孤懷遺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夫三戶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辭,即發自當日之士大夫,猶應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別傳》上冊第4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又陸健東著《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披露的1953年12月1日陳寅恪“對科學院的答復”,尤集中闡述了寅恪先生的這一學術精神。《答復》中寫道:“我的思想,我的主張完全見于我所寫的王國維紀念碑中。王國維死后,學生劉節等請我撰文紀念。當時正值國民黨統一時,立碑時間有年月可查。在當時,清華校長是羅家倫,是二陳(CC)派去的,眾所周知。我當時是清華研究院導師,認為王國維是近世學術界最主要的人物,故撰文來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學問的人。特別是研究史學的人。我認為研究學術,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獨立的精神。所以我說‘士子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于俗諦之桎梏'。‘俗諦'在當時即指三民主義而言。必須脫掉‘俗諦之桎梏',真理才能發揮,受‘俗諦之桎梏',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學說有無錯誤,這是可以商量的,我對于王國維即是如此。王國維的學說中,也有錯的,如關于蒙古史上的一些問題,我認為就可以商量。我的學說也有錯誤,也可以商量,個人間的爭吵不必芥蒂。我、你都應該如此。我寫王國維詩,中間罵了梁任公,給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為芥蒂。我對胡適也罵過。但對于獨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認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說‘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認為王國維之死,不關與羅振玉的恩怨,不關滿清之滅亡,其一死乃以見獨立自由之意志。獨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須爭的,且須以生死力爭。正如詞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賢所同殉之精義,其豈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見該書第111至112頁,三聯書店1995年版)
陳垣與陳寅恪并稱“史學二陳”。陳垣的專精在目錄、校勘、史諱、年表的研究,并兼擅詞章之學;史源學一目,是他的創造;治史的顯績則集中在宗教研究和元史研究。從繼承的史學傳統來說,清代史家趙壹、錢曉徵對他的影響最大。所以陳寅恪評贊其史學之貢獻時說:“近二十年來,國人內感民族文化之衰退,外受世界思潮之激蕩,其論史之作,漸能脫除清代經師之舊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學之真諦,而新會陳援庵先生之書,尤為中外學人所推服。蓋先生之精思博識,吾國學者,自錢曉徵以來,未之有也。”(陳寅恪:《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序》,《金明館叢稿二編》第219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版)但陳垣五十年代以后世潮潤及己身,沒有再寫出重要的著述。陳寅恪則挺拔不動,愈到晚年愈見其著述風骨。尤其1953年至1963年積十載之功撰寫的八十萬言的《柳如是別傳》,是他一生之中最重要的著述,是我國現代文史考證的典范,是“借傳修史”的明清文化痛史的杰構,置諸20世紀的史林文苑,其博雅通識和學思之密,鮮有出其右者。
現代史學家中包括“二陳”在內的一批大師巨子,所涉獵和所建樹的史學實際上也可以視作文化史學。所謂文化史學,是指著者不僅試圖復原歷史的結構,而且苦心追尋我華夏民族文化傳承的血脈,負一種文化托命的職責。
文化史學集大成者:錢穆
文化史學的集大成者是錢賓四先生。
賓四是錢穆的字,無錫人,自學名家。始任教于無錫、廈門、蘇州等地的中學,1930年起北上京華,執教鞭于燕大、北大、清華、師大等高等學府。錢之著述,早期以《先秦諸子系年》、《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國史大綱》為代表。治國史而以學術流變為基底,直承儒統,獨立開辟,不倚傍前賢時雋,是錢氏史學的特點。其抗戰時期在西南聯大撰寫的《國史大綱》,特地提出應把“我國家民族、已往文化演進之真相,明白示人,為一般有志認識中國已往政治社會文化思想種種演變者所必要之智識”,作為修撰新通史的必備條件;并昭示國人樹立一種信念,即對“本國已往歷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錢穆:《國史大綱》修訂本上冊“引論”第7頁,及卷前“凡讀本書請先具下列諸信念”第1頁,香港商務印書館1989年版)。他強調:“歷史與文化就是一個民族精神的表現。所以沒有歷史,沒有文化,也不可能有民族之成立與存在。如是我們可以說,研究歷史,就是研究此歷史背后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的。”(錢穆:《中國歷史精神》第7頁,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76年初版)錢穆晚期的代表著作是《朱子新學案》,其價值在重新整合理學和儒學的關系,把援釋入儒的宋學,收納回歸到儒、釋、道合流統貫的傳統學術思想的長河中去。國學大師之名,章太炎之后,唯錢穆當之無愧。
中國現代學術之史學一門最見實績,真可以說是人才濟濟,碩果豐盈。梁、王、胡、顧和二陳、錢穆之外,張蔭麟、郭沫若、范文讕、翦伯贊、呂振羽,都是具通史之才的史學大師。郭的恣肆、范的淹博、翦的明通、呂的簡要,為學界所共道。就中張蔭麟的史學天才尤值得注意。雖然他只活了37歲,留下的史學著作最重要的竟是一部沒有最后完成的《中國史綱》(只有上古部分)。
史學天才:張蔭麟、陳夢家
張蔭麟,自號素癡,1905年生于廣東的東莞,十六歲考入清華學堂,十八歲發表《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說質疑》于《學衡》雜志,批評梁啟超而得到梁啟超的激賞。1929年赴美國斯坦福大學研習哲學和社會學,四年后回國,任教于清華,兼授哲學、歷史兩系的課程。他試圖把哲學和藝術與史學融合在一起,提出要用感情、生命、神采來從事歷史寫作。他說:
史學應為科學歟?抑藝術歟?曰,兼之。斯言也,多數積學之專門史家聞之,必且嗤笑。然專門家之嗤笑,不盡足懾也。世人恒以文筆優雅,為述史之要技。專門家則否之。然歷史之為藝術,固有超乎文筆之上矣。今以歷史與小說較,所異者何在?夫人皆知在其所表現之境界一為虛一為實也。然此異點,遂足擯歷史于藝術范圍之外矣乎?寫神仙之圖畫,藝術也。寫生寫真,毫發畢肖之圖畫,亦藝術也。小說與歷史之同者,表現有感情,有生命,有神采之境界,此則藝術之事也。惟以歷史所表現者為真境,故其資料必有待于科學的搜集與整理。然僅有資料,雖極精確,亦不成史。即要經科學的綜合,亦不成史,何也?以感情、生命、神采,有待于直觀的認取,與藝術的表現也。(張蔭麟:《論歷史學之過去與未來》,《張蔭麟先生文集》下冊第1059頁,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84年初版)
他認為正確充備的資料和忠實的藝術表現,是理想的歷史寫作的兩個必要條件。他自己的史著和論文,把他的這一史學寫作理想變成了現實。謂予不信,請試讀《中國史綱》以及《明清之際西學輸入中國考略》和《北宋四子的生活與思想》等專書和論文,你無法不被他的“忠實的藝術表現”所感染。你甚至可能忘記了是在讀史,而以為是在閱讀文學家撰寫的饒有興味的歷史故事,但他那不摻雜繁引詳注的歷史敘述,又可以做到無一字無來歷,無一事無出處。
包括梁任公、賀麟、吳晗在內的熟悉他的學界人物,無一例外地稱賞他為不可多得的史學天才。熊十力說:“張蔭麟先生,史學家也,亦哲學家也。其宏博之思,蘊諸中而尚未及闡發者,吾固無從深悉。然其為學,規模宏遠,不守一家言,則時賢之所夙推而共譽也。”又說:“昔明季諸子,無不兼精哲史兩方面者。吾因蔭麟先生之歿,而深有慨乎其規模或遂莫有繼之這也。”(熊十力:《哲學與史學——悼張蔭麟先生》,見《張蔭麟先生文集》上冊第3頁,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84年初版)以熊之性格特點,如此評騭一位先逝的比自己小整整二十歲的當代學人,可謂絕無僅有。
另外在專史和斷代史領域,湯用彤、柳詒徵、蕭公權、岑仲勉、朱謙之、雷海宗、陳夢家、侯外廬、孟森、蕭一山、向達、楊聯升、羅爾綱等,都有足可傳世的代表性著作。而陳夢家的學術成就和遭遇,更令人感到震撼。他是浙江上虞人,1911年生,十六歲考取中央大學法律系,二十歲就是聞名遐邇的新月派詩人了。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變”,他投筆從戎,參加著名的淞滬抗戰。后來師從容庚,成為研究古文字學、古史的專家,先后執教于燕京大學、西南聯大、清華大學等學府,50年代以后轉到科學院考古所。《殷虛卜辭綜述》、《尚書通論》、《六國紀年》、《西周銅器斷代》等重要著作,都寫于1957年以前。
他的詩人氣質和學者的風骨,使他未能逃過1957年“不平常的春天”那一劫。他被下放到甘肅。但他那雙神奇的眼睛和神奇的手,似乎接觸什么就可以研究什么,而且都能結出果實。他在甘肅接觸到了漢簡,他撰寫了《武威漢簡》和《漢簡綴述》兩部涉獵新的學科領域的專著。他的文筆是優美的,優美到可以和張蔭麟相頡頏。誰都知道通解甲骨文的發現和研究過程是一件多么繁難的事情,但如果閱讀他的70余萬言的《殷虛卜辭綜述》,不僅可以輕松地實現你的學術目標,而且得到史學與藝術的美的享受。
但陳夢家的悲劇人生并沒有到此結束,還有更慘烈的一幕等待著他。1966年,當迎面而來的掀天巨浪不僅殘害知識精英,而且殘害文化的時候,他自己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年只55歲,正值學術的盛年。當然還有翦伯贊,一位一向被稱作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通史之才,也在那股掀天巨浪面前選擇了最簡便的結局。只是,也許他并不孤單,因為陪伴他同行的還有他的夫人。這些史學天才,是太知道歷史還是太不知道歷史?
疑古、釋古、考古,足以代表中國現代史學的三個學術派別了。錢穆分近世史學為傳統派、革新派和科學派(錢穆:《國史大綱》修訂本上冊“引論”第3頁,香港商務印書館1989年版),似不夠準確。還有的區別為史觀派、史建派、考證派、方法派等等(許冠三:《新史學九十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按許著爬梳勾勒百年史學,提綱挈領,每有特見,乃研究近世史學史的先發之著。即對史學各派別的歸納,亦自可成說。惟“考證學派”、“方法學派”、“史觀學派”、“史建學派”的提法,竊以為稍有未安),也未見科學。疑古、釋古、考古三派,都有自己的史學觀念和史學方法,也都離不開史料和考證,其目標也是為了建設。唯一例外的是以傅斯年為代表的史料學派,雖也可以范圍在釋古一派之內,但在史學觀念上確有自己的特色。況且講中國現代史學如果不講到傅斯年,不僅不公正,而且是嚴重的缺失。因為20世紀的歷史學,他是一位有力量的帶領者和推動者。
天下英雄獨使君:傅斯年
傅斯年字孟真,山東聊城人,1896年出生,十七歲考入北京大學預科,后轉為國文門。他是“五四”新思潮的學生領袖,他當時辦的刊物就叫《新潮》。陳獨秀、胡適之都很賞識他的才干,李大釗的思想對他也很有影響。1919年5月4日那天的愛國大游行,他擔任總指揮,扛著大旗走在隊伍的最前面。但火燒趙家樓的意外行為發生后,他退而回到學校。當年年底考取官費留學,赴英國倫敦大學研究院學習。1923年轉赴德國柏林大學文學院,比較語言學和歷史學成為他傾心鉆研的新的學科領域。趙元任、陳寅恪、俞大維、羅家倫、毛子水、金岳霖、徐志摩等青年才俊,是他在德國期間經常往還的朋友。1926年回國,應中山大學之聘,擔任文學院長兼文史兩系之系主任。1928年就任國家最高學術機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陳寅恪、趙元任、李濟,分別是史語所第一、二、三組的組長。他的“拔尖”政策使他有辦法聚集全國最優秀的學人。
他的最有影響力的文章是就任史語所所長后撰寫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他的經常被引用的名言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他說:“凡一種學問能擴張他研究的材料便進步,不能的便退步。”他說:“我們反對疏通,我們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則事實自然顯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貨,十分材料出十分貨,沒有材料便不出貨。”(均見《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國現代學術經典·傅斯年卷》第340至350頁,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他說:“史學便是史料學。”(傅斯年:《史學方法導論》,《中國現代學術經典·傅斯年卷》第243頁)他說了這么多容易斷章取義、容易被誤解的話,但真正的學術大家、史學重鎮,都知道他的苦心孤詣,很少發生誤解。不僅不誤解,反而承認他的權威地位,感激他對現代史學的建設所做的貢獻。
其實他是受德國朗克史學的影響,有感于西方漢學家的獨特建樹,目睹中國歷史語言學的衰歇,提出的振興救弊的主張。他說:
西洋人作學問不是去讀書,是動手動腳到處尋找新材料,隨時擴大舊范圍,所以這學問才有四方的發展,向上的增高。中國文字學之進步,正因為《說文》之研究消滅了漢簡,阮、吳諸人金文之研究識破了《說文》。近年孫詒讓、王國維等之殷文研究更能繼續金文之研究。材料愈擴充,學問愈進步,利用了檔案,然后可以訂史。利用了別國的記載,然后可以考四裔的史事。在中國史學的盛時,材料用得還是廣的,地方上求材料,刻文上抄材料,檔庫中出材料,傳說中辨材料。到了現在,不特不能去擴張材料,去學曹操設“發冢校尉”,求出一部古史于地下遺物,就是“自然”送給我們的出土的物事,以及敦煌石藏、內閣檔案,還由他毀壞了好多,剩下的流傳海外,京師圖書館所存摩尼經典等等良籍,還復任其擱置,一面則談整理國故者人多如鯽,這樣焉能進步?(見《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國現代學術經典·傅斯年卷》第344頁,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可知他是痛乎言之、有感而發。他還說:“在中國的語言學和歷史學當年之有光榮的歷史,正因為能開拓有用材料。后來之衰歇,正因為題目固定了,材料不大擴充了,工具不能添新的了。不過在中國境內語言學和歷史學的材料是最多的,歐洲人求之尚難得,我們卻坐看他毀壞亡失。我們著實不滿這個狀態,著實不服氣就是物質的原料以外,即便學問的原料,也被歐洲人搬了去乃至偷了去。我們很想借幾個不陳的工具,處治些新獲見的材料,所以才有這歷史語言研究所的設置。”(同上346頁)何以要把史料的作用強調到如此的地步,他講得再清楚不過,不需要我們再添加什么了。
傅斯年一生的壯舉,辦《新潮》、火燒趙家樓、創建史語所,固也。但他還有炮轟宋子文、攻倒孔祥熙兩項壯舉。
1938年抗戰開始后,傅斯年對國民黨高層的腐敗非常憤慨,他直接上書給蔣,歷數當時任行政院長職務的孔祥熙的諸種貪贓劣跡。蔣不理睬,他便再次上書,態度更堅決。國民參政會也成了他抨擊孔的舞臺,使得社會同憤,輿論嘩然。蔣不得已設宴請傅,問傅對他是否信任,回答信任。蔣說:“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應該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說:“委員長我是信任的,至于說因為信任你也就應該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腦袋我也不能這樣說。”(屈萬里:《傅孟真先生軼事瑣記》,轉引自李泉著《傅斯年學術思想評傳》第259頁,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年版)這成了傅斯年“史學便是史料學”之外的又一名言。孔祥熙后來終于被罷去了一切職務。傅與蔣在維護特定的政治利益上自無不同,所以1945年“一二一”昆明慘案發生后,傅直接受蔣之命處理學潮而未負所托。蔣對傅的能力膽識是欣賞的。但傅本質上是一名書生。抗戰勝利后蔣邀請他出任國府委員,他堅辭不就。北大校長一職,他也不愿擔任,為等胡適返國,只同意暫代。對胡適面臨國府委員兼考試院長的要職猶豫不決,他大動肝火,寫信給胡適說:“借重先生,全為大糞上插一朵花。”勸胡一定不要動搖。并說蔣“只了解壓力,不懂任何其他”(《傅斯年致胡適》,《胡適來往書信選》下冊第190頁,中華書局1980年版)。
另一方面,毛澤東對傅也很欣賞,1945年7月傅等文化界參政員到延安考察,毛澤東如對故人,整整和傅暢談一個晚上。臨別毛應傅之所請寫一條幅相贈,附書:“遵囑寫了數字,不像樣子,聊作紀念。今日間陳涉吳廣之說,未免過謙,故述唐人語以廣之。”條幅寫的是杜牧的一首詠史詩:“竹帛煙銷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坑灰未盡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兩人談話時,毛稱贊傅在“五四”時期的功績,傅說我們不過是陳涉、吳廣,你們才是劉邦、項羽。劉、項顯指國共兩黨的領導人。毛所書詩句“古典”、“今典”均極對景,回答了傅的謙遜,也稱贊了傅的以學問自立。
傅斯年1950年12月20日因突發腦溢血死于演講臺上,終年54歲,當時他擔任臺灣大學校長的職務。他以耿直狷介著稱,他以脾氣暴躁著稱,他以疾惡如仇著稱,他以雄才獨斷著稱。史語所的人私下里稱他為“傅老虎”,但都服他尊敬他。他對學問充滿了眷愛,對有真才實學的學者充滿了溫情。他與陳寅恪的特殊關系就是一顯例。對曾經幫助過影響過自己的人,他不忘舊。1932年陳獨秀被捕,他為之辯誣,說陳是“中國革命史上光焰萬丈的大彗星”。1927年李大釗就義,報紙上發表消息有謂李在北平“就刑”。傅斯年反駁說,不是“就刑”,是“被害”。難怪陳寅恪對他那樣服膺感佩,寫了《寄傅斯年》詩兩首,第一首為:“不傷春去不論文,北海南溟對夕曛。正始遺音真絕響,元和新腳未成軍。”第二首為:“今生事業余田舍,天下英雄獨使君。解識玉緘札意,梅花亭畔吊朝云。”(參見《陳寅恪集·詩集》第18頁,三聯書店2001年版)又1950年12月傅斯年逝世,陳寅恪當即亦有詩為之追念,只不過寫得很曲折,通過說傅青主(傅山)之詩句從而悼念之。陳詩題為《〈霜紅龕集·望海詩〉云:“一燈續日月,不寐照煩惱,不生不死間,如何為懷抱”,感題其后》,詩為:“不生不死最堪傷,猶說扶馀海外王。同入興亡煩惱夢,霜紅一枕已滄桑。”(見三聯版《陳寅恪集·詩集》第74頁)
我們了解了傅斯年,可以了解所謂學者的性格為何物,可以深層地了解陳寅恪的史學,可以了解那個特殊的史語所,可以了解中國現代史學所謂“史料學派”的懷抱與旨歸。
《文匯報》
 |
| 胡適(1891——1962) |
 |
| 陳寅恪(1890——1969) |
 |
| 錢穆(1895——1990) |
 |
| 傅斯年(1896——1950) |
|





mailto:guoxue@guoxue.com
![]() 010-68900123
010-68900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