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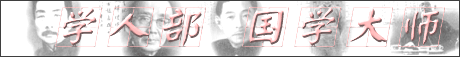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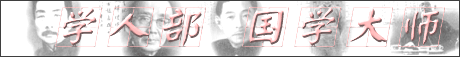 |
|
|
|
||
|
|
大師生平|著作年表|著述索引|作品選讀|大師研究|研究著述|書品推介|研究學(xué)人|相關(guān)鏈接
|
|
|
|
|
|
|
||
| 薛 冰 |
||
近年以來,尋找“思想史上的失蹤者”,成為中國知識(shí)分子中的一個(gè)熱門話題。其實(shí),二十世紀(jì)特別是后半葉人文領(lǐng)域中的“失蹤”現(xiàn)象,決不僅限于思想史,在文學(xué)史上同樣相當(dāng)嚴(yán)重。 2002年春,我在寫《金陵書話》的時(shí)候,由幾位前輩學(xué)人的遭際,想到一個(gè)問題,就是近百年來,尤其是近五十年來,對于中國近現(xiàn)代文化的種種偏見,使得那一時(shí)期中的大量優(yōu)秀文學(xué)作品,處于湮沒狀態(tài)。沈從文、張愛玲等的“出土”,是一個(gè)顯例;另一個(gè)不太明顯但可能更為重要的事實(shí),就是晚清到民國年間傳統(tǒng)文學(xué)樣式的創(chuàng)作成果,包括筆記小說、舊體詩詞、散曲、戲曲等,至今仍被文學(xué)史家與諸多理論家視而不見,更談不上整理與研究了。在他們眼中,似乎“新文化”的大旗迎風(fēng)一招展,一切的“舊”文學(xué)“舊”文化便該壽終正寢,即不甘歸于寂滅,也已屬遺老遺少的頑固不化,再無價(jià)值可言。 當(dāng)時(shí)就很想寫一點(diǎn)關(guān)于吳梅先生的文字。吳梅先生總給我一種切近而又遙遠(yuǎn)的感覺。說切近,是因?yàn)樽x現(xiàn)代南京的文獻(xiàn)資料和學(xué)人著作,常常會(huì)遇到先生的名字;說遙遠(yuǎn),則是因?yàn)橄壬膶W(xué)問給我以高不可攀之感。可是先生的著作,當(dāng)時(shí)還只見到零星幾種,且都是民國年間的舊版本;又聽說河北教育出版社即將出版的《吳梅全集》有四卷八冊三百余萬字,其中且有《瞿安日記》二巨冊,更是從未寓目,自知于先生生平著述,了解得太少,遂未敢貿(mào)然動(dòng)筆。 《吳梅全集》在2002年秋問世,吳梅先生的著作第一次得以全面系統(tǒng)地結(jié)為一集。雖然在與先生和昆曲都無關(guān)系的河北而不是在江蘇出版,也是一件讓人感慨的事情,但能出得像現(xiàn)在這樣完善精美,總是件幸事。承出版社的朋友贈(zèng)我一部。拜讀之下,愈覺洋洋大觀,如我之輩,真是只能望洋興嘆的了。尤其是其中的曲律研究,在昆劇極度衰微的當(dāng)世,恐將成為絕學(xué)。 吳梅先生自述其學(xué)術(shù)淵源,“游藝四方,詩得散原老人,詞得強(qiáng)村遺民,曲得粟廬先生”。散原老人陳三立,是晚清維新派的重要人物,也是清末民初中國詩壇的領(lǐng)袖,《光宣詩壇點(diǎn)將錄》中以他為“詩壇都頭領(lǐng)”,譽(yù)為“天魁星及時(shí)雨宋江”;《近百年詩壇點(diǎn)將錄》以他為“掌管機(jī)密軍師”,譽(yù)為“天機(jī)星智多星吳用”;不過,當(dāng)代中國人知道他,恐怕多是由于他的兒子陳寅恪了。強(qiáng)村遺民朱祖謀,為晚清四大詞人之一,被近代詞壇奉為宗匠,集大成而繼往開來,平生致力于詞籍校勘,“精詣獨(dú)絕”,人稱“律博士”;他所校編的《強(qiáng)村叢書》為我國詞集四大叢刻之冠,然而,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十幾年前影印一千二百部,降價(jià)處理至今尚未售完。粟廬先生俞宗海,是昆曲清唱的正宗傳人;昆曲在明代嘉靖、萬歷年間,經(jīng)魏良輔改進(jìn)而繁盛,并且形成“水磨腔”清唱一脈,至乾隆年間,編撰《納書楹曲譜》的蘇州人葉堂被奉為魏氏清唱正宗,葉派在道光、咸豐年間的傳人是婁縣人韓華卿,俞宗海是韓華卿的弟子;俞宗海的兒子,就是當(dāng)代著名昆劇、京劇表演藝術(shù)家俞振飛。這父子倆的名字,大約也只有戲劇史家和京昆票友才記得了。 吳梅先生的詩,在生前寫定為《霜崖詩錄》四卷,以編年體存詩三百八十一首,不但數(shù)量較詞、曲尤為多,而且更能看出先生的一生經(jīng)歷、過從交往,以及思想、藝術(shù)的發(fā)展脈絡(luò)。詩作始于1898年,終于1938年,對于四十年間的重大社會(huì)歷史事件,從戊戌變法、辛亥革命、洪憲復(fù)辟、軍閥混戰(zhàn)到日寇侵華、抗戰(zhàn)軍興,都有如實(shí)的反映,表現(xiàn)出詩人強(qiáng)烈的愛國精神;詠史懷人、評書讀畫之作,也無不寄寓真情實(shí)學(xué);其七古風(fēng)骨遒勁,歌行開闔流轉(zhuǎn),絕句輕倩流麗,律詩工于對仗,各有特色。詩人的自我評價(jià)是:“不開風(fēng)氣,不依門戶。獨(dú)往獨(dú)來,匪今匪古。”“不開風(fēng)氣”有自知之貴,因?yàn)橄壬逍训卣J(rèn)識(shí)到,“詩文詞曲,頗難兼擅”,他在曲學(xué)上用力至深,詩作上再想開一時(shí)風(fēng)氣是不現(xiàn)實(shí)的;但由于堅(jiān)持了“不依門戶”,所以能達(dá)到“匪今匪古”的境界。 《霜崖詞錄》也系先生生前寫定,存詞一百三十七首。先生于詩、詞、曲三體均有創(chuàng)作,詞風(fēng)豪放易近于詩,婉約則易近于曲,故而在詞作上頗難獨(dú)樹一格;但曲學(xué)上的造詣,又深化了先生對于詞律的理解,故集中登臨懷古、言志抒情之作,情致清新,辭采振拔,意象鮮明,含蓄雅訓(xùn),能嚴(yán)守詞律,因難見巧,遠(yuǎn)追南宋。論者或以為先生詞作的成就能高于詩作。 《霜崖曲錄》二卷,為先生高足盧前在1929年編次,后又有增補(bǔ),現(xiàn)卷一收小令六十八首,卷二收套數(shù)二十篇一百零三首。因?yàn)橄壬J(rèn)識(shí)到“欲明曲理,須先唱曲”,曾從名師學(xué)唱,能夠邊唱邊寫,所以才情與格律有機(jī)統(tǒng)一,達(dá)到格律精嚴(yán)而才情橫溢的高境界。在清末以來散曲日見寥落的局面下,先生的散曲異峰突起,并影響后學(xué),釀成風(fēng)氣,致時(shí)人有散曲“中興”之望。 當(dāng)然吳梅先生最重要的學(xué)術(shù)成就,還在戲曲創(chuàng)作與研究。浦江清先生說:“近世對于戲曲一門學(xué)問,最有研究者推王靜安與吳梅先生兩人。靜安先生在歷史考證方面,開戲曲史研究之先路;但在戲曲本身之研究,還當(dāng)推瞿安先生獨(dú)步。”龍榆生先生說他“專究南北曲,制譜、填詞、按拍一身兼擅,晚近無第二人也”。編校《吳梅全集》的王衛(wèi)民先生說,在中國戲曲史上的大家,或以制曲見長,或以曲論見長,或以曲史見長,或以演唱見長,就是在昆劇的全盛時(shí)期,“集二三特長于一身的大家已屈指可數(shù),集四五特長于一身的大家更為罕見”,然而生活于昆劇衰落時(shí)期的吳梅先生,卻能“集制曲、論曲、曲史、藏曲、校曲、譜曲、唱曲于一身”,且在戲曲教育上也卓有建樹,堪謂奇跡。 創(chuàng)作方面,先生在十六歲時(shí),就有傳奇《血花飛》之作,以紀(jì)念戊戌六君子;三十年間,共創(chuàng)作十四個(gè)劇本,現(xiàn)存十二,以先生五十壽誕時(shí)自選的《霜崖三劇》為代表,曲律詞采俱工,案頭場上,兩擅其美,人物鮮明而情節(jié)曲折,達(dá)到了那一時(shí)代的最高境界。傳統(tǒng)戲曲本身就是一種綜合藝術(shù),若非具有文學(xué)、音樂、舞蹈、美術(shù)等多方面的較高修養(yǎng),是不可能取得較高成就的。 曲律研究方面,先生有《顧曲麈談》、《曲學(xué)通論》、《南北詞簡譜》等專著,在前人研究成果和自己藝術(shù)實(shí)踐的基礎(chǔ)上,全面系統(tǒng)地論述了制、譜、唱、演的藝術(shù)規(guī)律。曲史研究方面,先生的《中國戲曲概論》是放眼全局的第一部中國戲曲通史;《元?jiǎng)⊙芯俊泛汀肚D渴枳C》對劇作家與作品的考證,也有承前啟后之功;《霜崖曲話》、《奢摩他室曲話》和《奢摩他室曲旨》等采取傳統(tǒng)的曲話形式,廣泛評述散曲、劇曲的形式與內(nèi)容,既為作者的進(jìn)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礎(chǔ),也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可貴的參考材料。 先生自十幾歲就注意搜求戲曲典籍,能購買的購買,能借抄的借抄,積三十年之艱辛,收藏曲籍六百余種,其中不乏精本、善本、孤本,成為全國首屈一指的藏曲大家。他并且利用自己的珍藏,精心校勘,編選《奢摩他室曲叢》,交商務(wù)印書館出版,以使這份遺產(chǎn)廣為流傳。這項(xiàng)工作,應(yīng)該說是受到朱祖謀刊行《強(qiáng)村叢書》的影響。后因上海“一·二八”戰(zhàn)事,使出版中斷,傳世僅得其半,仍大受好評,以為其選擇之精,校訂之善,當(dāng)在《元曲選》與《六十種曲》之上。此后鄭振鐸先生倡導(dǎo)刊行《古本戲曲叢刊》,就是受到吳梅先生的啟發(fā);而劉世珩選輯《暖紅室匯刻傳奇》,盧前選輯《飲虹叢刻》,更是直接得到吳梅先生的指導(dǎo)。 先生還為許多傳奇雜劇打下了聲情并茂、宜唱美聽的曲譜,使一些案頭名劇得以登上舞臺(tái),重?zé)ㄇ啻骸_@也因?yàn)橄壬谐墓Φ住N毫驾o曾總結(jié)唱曲經(jīng)驗(yàn)說:“曲有三絕:字清為一絕,腔純?yōu)槎^,板正為三絕。”聽過吳梅先生唱曲的人,都以為他是得到這份真?zhèn)鞯摹? 吳梅先生又是第一個(gè)在高等學(xué)府專授戲曲課的教師,他把吹笛、訂譜、唱曲這些被當(dāng)時(shí)學(xué)問家視為“小道末技”的內(nèi)容帶上講堂,言傳身教,開創(chuàng)了研究曲學(xué)之風(fēng)氣,二十余年間在南北兩京培養(yǎng)了一批有成就的戲曲史家、戲曲理論家。他還熱心扶持昆劇傳習(xí)所,每回蘇州,都要前去與老藝人切磋,給學(xué)員以指導(dǎo),被視為他們的知音。在昆曲的保存與提高方面,吳梅先生的功勞不可磨滅。 此外,吳梅先生在詞學(xué)研究上亦有很高造詣。朱祖謀先生曾四校《夢窗詞》,而吳梅先生重讀《夢窗詞》,還能有新的發(fā)現(xiàn)。他的專著《詞學(xué)通論》,寓史于論,史論結(jié)合,從格律到作法,多所創(chuàng)見。 吳梅先生的日記,自是了解先生生平經(jīng)歷、思想脈絡(luò)與學(xué)術(shù)源流的最好材料。惜《全集》中所收《瞿安日記》,僅見1931至1937年間之部分。其時(shí)先生主要在南京任教,除詳記日寇侵華事變外,不乏讀書心得、論學(xué)文字及購書藏書活動(dòng);尤其是學(xué)人聚散往來,令讀者如行山陰道上,目不暇接。倘有人以此為基礎(chǔ)做先生的師友錄與交游考,一定可以發(fā)現(xiàn)更多文化史上的“失蹤”者。此外所記亦多涉南京時(shí)事風(fēng)物,兼及方志掌故,直至市井生活與物價(jià)種種,對于了解三十年代的南京,也是極可貴的材料。 要全面論述吳梅先生的學(xué)術(shù)成就,至少可以寫成一部大書。讓我感觸至深的是,如吳梅先生這樣學(xué)術(shù)史上的大師級人物,在相當(dāng)長的歷史時(shí)期中,居然淡出了人們的記憶,以至一些研究戲曲的年輕人都不知道他的名字;他的學(xué)術(shù)成就尤其是創(chuàng)作成就,都沒有得到應(yīng)有的重視。要說文學(xué)史上的“失蹤”現(xiàn)象,吳梅先生身后的默默無聞,是可以作為典型的。 這其中的原因,說復(fù)雜真復(fù)雜,說簡單也簡單。簡而言之,大約有兩點(diǎn)。 一是二十世紀(jì)初,應(yīng)運(yùn)而生的新文學(xué),迅速崛起,以其通俗易懂,成為主流。這本應(yīng)是好事,使中國文學(xué)的園地大為豐富;遺憾的是,由于某些人有意無意的努力,將思想以至政治領(lǐng)域的新舊之爭,推延到文學(xué)領(lǐng)域之中,而且只論形式,不論內(nèi)容,更不論藝術(shù),一入舊式,即在掃蕩之列。對古典文學(xué)的研究,也只到清代中葉為止,“同光體”已不入法眼,遑論其余。 實(shí)則在大動(dòng)蕩、大變革、大悲大喜的二十世紀(jì)上半葉,中國的詩文詞曲,無論新體還是舊體,都不乏佳作,都曾達(dá)到一個(gè)不容忽視的高潮。作為南社的早期成員、一貫關(guān)心國事的吳梅先生,其作品更是具有強(qiáng)烈的愛國主義精神和革新思想。而二十世紀(jì)上半葉的文人學(xué)者,即使不能寫作舊體詩詞,欣賞舊體詩詞的人應(yīng)當(dāng)不會(huì)比欣賞新詩的人少。所以當(dāng)時(shí)學(xué)人對于吳梅先生的成就才會(huì)有那樣高的評價(jià)。 其二,舊體詩詞曲的衰退,是二十世紀(jì)五十年代以后的事情,1957年的反右和1958年的新民歌運(yùn)動(dòng),一則踐踏了詩人,一則踐踏了詩,共同的是踐踏了欣賞詩的眼睛。此后二十年中國可說無詩可讀,當(dāng)然,也包括新詩。在這一時(shí)間段里成長以至出生的人,不知道吳梅,不足為奇。 然而,二十世紀(jì)八十年代以來,也就是沈從文、張愛玲、周作人等先生相繼被發(fā)掘而紅極一時(shí)之際,吳梅先生的曲學(xué)成就卻依然無人問津,則是源于另一個(gè)令人悲哀的事實(shí),就是中國的昆劇已經(jīng)一蹶不振地衰落,“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吳梅先生獨(dú)步一時(shí)的曲學(xué)理論,成了屠龍之技。 昆劇藝術(shù)的后繼無人,固然有多方面的因素,但是民族虛無主義的一度橫行,全民族的傳統(tǒng)文化修養(yǎng)的急劇下降,應(yīng)當(dāng)也是一個(gè)重要的因素。 吳梅先生在《百嘉室遺囑》中,曾專門談到后輩的教育問題:“近日小學(xué)課程,殊不能滿人意。吾意身為中國人,經(jīng)書不可不讀。每日課余,宜別請一師,專授經(jīng)書。大約《論語》、《孟子》、《詩經(jīng)》、《禮記》、《左傳》,必須熟誦。既入中學(xué)后,則各史精華,亦宜摘讀;或主誦《群書治要》者,容嫌卷帙多,且刪節(jié)處間有乖異,不必讀也。十六歲后,應(yīng)略講經(jīng)史源流。”這自是治國學(xué)者的經(jīng)驗(yàn)之談,但在近半個(gè)世紀(jì)中,如果有誰重彈此調(diào),除了被扣上一頂頑固不化的帽子,決不會(huì)有別的結(jié)果。 吳梅先生培養(yǎng)出來的學(xué)生,對于老師的學(xué)業(yè)各有繼承,出現(xiàn)過一大批一流學(xué)者。在二十世紀(jì)后半葉尚能繼續(xù)從事學(xué)術(shù)研究或教學(xué)工作的,就有王玉章、任訥、唐圭璋、王煥鑣、錢紹箕、王起、汪經(jīng)昌、趙萬里、常任俠、游壽、潘承弼、陸維釗、胡士瑩等;其中約一半沒有再從事曲學(xué)研究,但都在各自的領(lǐng)域里取得了重大成就。從事曲學(xué)研究的幾位,為世所重的,則只是他們的古典文學(xué)研究或教學(xué)工作,他們的創(chuàng)作同樣默默無聞。 吳梅先生曾說到:“余及門人中,唐生圭璋之詞,盧生冀野之曲,王生駕吾之文,皆可傳世行后。得此,亦足自豪矣。”盧前是吳門子弟中,較全面地繼承了先生衣缽,一生與散曲、戲曲結(jié)不解之緣,在曲律和曲史研究、制曲、藏曲、校曲等方面均有成就的一位。然而在二十世紀(jì)五十年代初,他卻因被學(xué)校解聘失業(yè),生活無著,售盡藏書,終于病死。 吳門弟子中能制曲的還有一位孫為霆先生,南京六合人,后來在西安教書,霍松林先生曾從他受教。他在文化革命前印過一部《壺春樂府》,恐怕就更沒有什么人知道了。此書三卷,卷上、卷中為散曲,卷下收《太平爨》三雜劇,曾得盧前的盛贊。這或許竟是當(dāng)代人昆曲創(chuàng)作的尾聲了。 值得一提的是,吳梅先生對于新詩,就并不排斥。當(dāng)徐志摩去世時(shí),他曾代穆藕初作挽聯(lián):“行路本來難,況上青天,孤注全身輕一擲;作詩在通俗,雅近白傅,別裁偽體倘千秋。”評價(jià)是相當(dāng)高的,他對此聯(lián)也很滿意,“自覺頗工”,因此記入日記。 其實(shí),人文文化的領(lǐng)域是一個(gè)累積的領(lǐng)域,一種作品對于另一種作品,只有超越的可能,沒有取代的可能。各人頭上一方天,并存共榮才是理想的境界。倘若一定要將舊體文學(xué)的創(chuàng)作成果抹殺,才能顯示出新文學(xué)的成績,那這成績也就實(shí)在可想而知了。 1984年,吳梅先生的百年誕辰,在北京舉行了紀(jì)念活動(dòng),在蘇州舉行了學(xué)術(shù)討論會(huì)。我手邊恰有任訥先生給錢紹箕先生的一封信,說到當(dāng)年的一些有關(guān)情況,摘抄如下: “瞿安老師誕生百年,南京無人號(hào)召紀(jì)念,吾輩之憾!弟與胡忌(昆劇院領(lǐng)導(dǎo))擬屆期赴蘇,加入地方紀(jì)念活動(dòng),在蘇留三日。圭璋病腿腫,不能行動(dòng)。弟亦患腦貧血癥,擬力疾前往。吾兄于此,抑有意同行乎。紀(jì)念日在陰歷七月廿二日(陽歷八月十八日),乞示。” 這一年,幾位先生都是八十開外的人了。后來只有任先生曾赴會(huì)。倘在南京舉行,至少唐、錢二先生也是可以參加的。任訥先生是吳梅先生弟子中成名最早、成就也最大的一位。汪暉先生曾寫到他對任先生的一些印象,“二北先生早年做過胡漢民的秘書,一九四九年后在四川曾經(jīng)以賣花生米度日,大概也曾在中學(xué)教過書。他來揚(yáng)州時(shí)(引者注:在1980年),大家知道他是唐圭璋先生的師兄,吳梅先生的弟子,是揚(yáng)州師院唯一的博士導(dǎo)師。任先生一生坎坷,性格卻依舊倔強(qiáng),說起話來聲音高亢。”省里在揚(yáng)州師院開古籍整理會(huì)議,不知為什么竟沒有請任先生到會(huì),結(jié)果“他不請自來,當(dāng)著袞袞諸公,用拐杖直指中文系主任的臉,痛斥為‘飯桶'”,及至被人勸出,“他摔開攙扶者,邊走邊罵,手中的拐杖倒立著,直指天空,一步三晃”。 與任先生信中所說的“南京無人號(hào)召紀(jì)念,吾輩之憾”一樣,他所爭的決非個(gè)人名利,而是學(xué)術(shù)的尊嚴(yán)。 1986年,吳梅先生遺骨遷葬故鄉(xiāng)吳縣小王山,并且舉行了揭幕儀式,油印了紀(jì)念冊。主持其事的是蘇州市文聯(lián)。1994年舉行紀(jì)念吳梅先生誕辰一百一十周年的學(xué)術(shù)研討會(huì),地點(diǎn)在蘇州的吳縣。2001年5月18日,昆曲被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人類口述和非物質(zhì)遺產(chǎn)”,此事被當(dāng)作一種榮譽(yù)而加以宣傳,其實(shí)是不合適的。它一方面說明,過去我們對于昆曲的保護(hù)不力,另一方面也為今后如何保護(hù)好這一遺產(chǎn),向我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當(dāng)然,昆曲因此得到了某些特殊的保護(hù)政策,生存條件得到較大的改善,總是一件大好事。而真正要振興昆曲,對于吳梅先生這樣空前絕后的曲學(xué)大師,就不能不給予更多的重視。 2002年,《吳梅全集》出版,書后附有王衛(wèi)民先生所編《吳梅年譜》。同時(shí)出版的還有王衛(wèi)民先生重行修訂的《吳梅評傳》。同年,南京大學(xué)出版社出版了吳梅先生的再傳弟子吳新雷先生主編的《中國昆劇大詞典》。這幾件應(yīng)運(yùn)而生的工作,無疑將使世人對于吳梅先生的曲學(xué)成就能有更全面的了解,也為后人學(xué)習(xí)、研究、運(yùn)用這些成就以振興昆曲,提供了極大的方便,或可以算是對于這位曲學(xué)大師的“失而復(fù)得”吧。 前幾年編撰《江蘇省志·文學(xué)志》時(shí),聽人說蘇州尚有吳梅先生的紀(jì)念館,曾專程到蘇州去了解,才知道其實(shí)只是先生的故居尚在,淪為民居,百嘉室中已無書香可言,設(shè)館紀(jì)念更是沒有的事。2004年是先生誕辰一百二十周年,如今昆曲已經(jīng)成為寶貴的世界文化遺產(chǎn),但愿先生的故居有朝一日真能辟為紀(jì)念館。 我衷心地希望中國文化界對于吳梅先生的這一次“失而復(fù)得”,不會(huì)再變成“得而復(fù)失”。
| ||
|
||
 |
國學(xué)網(wǎng)站,版權(quán)專有;引用轉(zhuǎn)載,注明出處;肆意盜用,即為侵權(quán)。
mailto:guoxue@guoxue.com
![]() 010-68900123
010-68900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