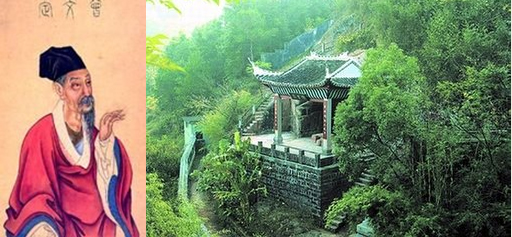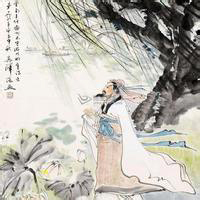宋人絕句鑒賞之十三
詠柳 曾鞏
亂條猶未變初黃,倚得東風勢便狂。
解把飛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
曾鞏(1019—1083),字子固,南豐(今江西省南豐縣)人,后居臨川(今江西撫州市西),世稱“南豐先生”。出生于世家,自稱“家世為儒”(曾鞏《上歐陽學士第一書》),尚書戶部郎中曾致堯之孫,太常博士曾易占之子。為“南豐七曾”(曾鞏、曾肇、曾布、曾紆、曾纮、曾協、曾敦)之一。南豐曾家自曾鞏之祖父致堯于太平興國八年(983)舉進士起,77年間曾家出了進士19位。進士中,致堯輩7人,其子易占輩6人,其孫鞏輩6人。此外,鞏之妹婿王安國、王補之、王彥深等一批人亦皆進士。曾鞏進士同年蘇軾、蘇轍贈詩稱:“儒術遠追齊稷下,文詞近比漢京西”,并非虛言。
曾鞏天資聰慧,記憶力非常強,幼時讀詩書,脫口能吟誦,與兄長曾曄一道,勤學苦讀,自幼就表現出良好的天賦。史稱鞏“十二歲能文,語已驚人”。其弟曾肇在《亡兄行狀》中稱其“生而警敏,不類童子”,而且記憶力超群,“讀書數萬言,脫口輒誦”。18歲時,赴京趕考,與隨父在京的王安石相識,并結成摯友。20歲入太學,上書歐陽修并獻《時務策》。歐陽修見其文筆獨特,非常賞識。歐陽修說:“過吾門者百千人,獨于得生為喜。”(《上歐陽學士第二書》)自此名聞天下,但因其擅長策論,輕于應舉時文,故屢試不第。慶歷七年(1047),其父去世,其身為次子(其上尚有一兄長),只好輟學回歸故里,盡心侍奉繼母。直至嘉祐二年(1057),歐陽修主持會試,堅持以古文、策論為主,詩賦為輔命題,曾鞏才與其弟曾牟、曾布及堂弟曾阜一同登進士第一。嘉祐四年(1059),任太平州(今安徽當涂縣)司法參軍,以明習律令,量刑適當而聞名。五年,由歐陽修舉薦到京師當館閣校勘、集賢校理,理校出《戰國策》、《說苑》、《新序》、《梁書》、《陳書》、《唐令》、《李太白集》、《鮑溶詩集》和《列女傳》等大量古籍,對歷代圖書作了很多整理工作,并撰寫了大量序文。熙寧二年(1069),任《宋英宗實錄》檢討,不久被外放越州(今浙江紹興)通判。熙寧五年后,歷任齊州、襄州、洪州、福州、明州、亳州等知州。為政廉潔奉公,勤于政事,關心民生疾苦。他根據王安石的新法宗旨,結合實際情況加以實施。致力于平反冤獄、維護治安、打擊豪強、救災防疫、疏河架橋、設置驛館、修繕城池、興辦學校、削減公文、整頓吏治、廢除苛捐雜稅,深受群眾擁戴。神宗元豐三年(1080),改任滄州(今河北)知州,途經京城開封時,宋神宗召見。宋神宗對其“節約為理財之要”的建議大為贊賞,留任為三班院勾判。元豐四年,朝廷認為“曾鞏史學見稱士類,宜典五朝史事”,任為史官修撰,管勾編修院,判太常寺兼禮儀事。元豐五年,拜中書舍人。同年九月,遭母喪,去官。次年,病逝于江寧府(今南京)。后葬于南豐源頭崇覺寺右。南宋理宗時追謚為“文定”,
曾鞏收集古今篆刻500卷,編為《金石錄》。所著文集《元豐類稿》50卷現存于世,有《四部叢刊》影元本。曾編校過《梁書》、《陳書》、《南齊書》、《列女傳》,整理過《戰國策》、《說苑》,另有《續稿》40卷、《外集》10卷,宋后亡佚。
曾鞏是北宋政治家、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在學術思想和文學事業上貢獻卓越。他是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積極參與者,宋代新古文運動的重要骨干。作為歐陽修的積極追隨者和支持者,幾乎全部接受了歐陽修在古文創作上的主張,他在理論上也是主張先道而后文的。但比韓愈、歐陽修更著重于道。在古文理論方面主張先道后文,文道結合,主張“文以明道”。其文風則源于六經又集司馬遷、韓愈兩家之長,古雅本正,溫厚典雅,章法嚴謹,長于說理,為時人及后輩所師范。《宋史·曾鞏傳》評論其文“立言于歐陽修、王安石間,紆徐而不煩,簡奧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謂難矣。”。王安石說:“曾子文章眾無有,水之江漢星之斗”。蘇軾認為:“曾子獨超軼,孤芳陋群妍”。蘇轍則用“儒術遠追齊稷下,文詞近比漢京西”來概括曾鞏的學術成就。朱熹也推崇他“予讀曾氏書,未嘗不掩卷廢書而嘆,何世之知公淺也。”其議論性散文剖析微言,闡明疑義;記敘性散文舒緩平和,翔實而有情致,對后世創作影響極大,明清兩代著名作家都將其作品奉為典范。曾鞏為文,自然淳樸,而不甚講究文采。在八大家中,他是情致較少的一個。曾鞏的學術和文章在他生前就享有很高的聲譽,降盛譽不衰。朱熹“愛其詞嚴而理正,居嘗誦習”在北宋各古文家中獨服膺曾鞏。呂祖謙編選《古文關鍵》時,只取曾鞏,不取王安石,可見當時風尚明代唐宋派散文家王慎中,唐順之、茅坤、歸有光,清代的桐城派方苞、劉大槐、姚鼐和錢魯斯等人都把他的文章奉為圭臬。《明史。王慎中傳》載:“慎中為文,初主秦漢,謂東京之下無可取,已司歐、曾作文之法,乃盡焚舊作,一意師仿,尤得力于曾鞏;順之初不服,久亦變而從之。”足見曾鞏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
曾鞏一生整理古籍、編校史書,也很有成就。《戰國策》、《說苑》、《列女傳》、《李太白集》和《陳書》等都曾經過他的校勘。《戰國策》和《說苑》兩書,多虧他訪求采錄,才免于散失。他每校一書,必撰序文,借以“辨章學術,鏡考源流”。曾鞏好藏書,珍藏古籍達兩萬多冊;收集篆刻五百卷,名為《金石錄》。
曾鞏還十分重視興教勸學,培養人才,培養了一批名儒,陳師道、王無咎、曾肇和曾布受業于他。《宋元學案》云:“陳無己(師道)好學苦志,以文謁曾子固,子固為點去百十字,文約而義意加備,無己大服”。在撫州居所側建有“興魯書院”,并親自定學規、執教席,推動撫州學風。今日南豐“子固公園”,有曾鞏幼時讀書處──讀書巖、曾文定公祠、仰風亭、思賢堂,縣博物館亦建在其內。南昌市有一條子固路,也是后人為紀念這位先賢而命名的。曾鞏墓南豐縣萊溪鄉楊梅坑村源頭里村對面的周家堡一山坡上,依山傍水,旁邊一條小溪,四季清水不斷“文革”時期,曾鞏墓被夷為平地,墓中之物亦遭散佚。
江西南豐曾鞏讀書臺
曾鞏詩名不高,甚至一直被人當做是個不會作詩的文學家.其實他也能詩。就“八大家”而論,他的詩不如韓、柳、歐、王與蘇軾,卻勝于蘇洵、蘇轍。但為文所掩,不受重視。曾鞏現存詩400余首,大都寫得比較質樸,雄渾超逸,含義深刻,略似其文。元代劉塤認為曾鞏“平生深于經術,得其理趣;而流連光景,吟風弄月,非其好也。往往宋人詩體多尚賦,而比與興寡,先生之詩亦然”(《隱居通議》卷七),其實并非如此。他并非只善賦體,也有一些詩長于比興,形象鮮明,頗得唐人神韻。他的各體詩中以七絕的成就最高,精深,工密,頗有風致。如《西樓》、《城南》、《詠柳》等,稱得上宋代近體詩中寫景抒情的佳作。下面就其中的《詠柳》加以賞析:
《詠柳》是首詠物詩。詠物詩當然是人的思想,情感和對生活的某種認識的抒發,只不過這種抒發是借物而作,因而也就比較含蓄而已。當然,也有一些詠物詩,其中社會生活的內容比較稀薄,甚至不過是為詠物而詠物。這樣的詩,盡管也有一些具有相當的可讀性,但可讀性的意義也只能局限在藝術技巧的純熟上。可以供人把玩和技巧上的借鑒,社會意義和審美意義終究不大。
曾鞏這首詩,其“內意”顯然是有感于柳的旺盛的生命力并由此聯想到現實生活中那些倚官仗勢、得志便猖狂的人,他們雖然得勢于一時,欺蒙于一時,終究逃脫不了時間的懲罰。這既是詩人對當時朝廷中讒邪小人的指斥,也是他對歷史經驗的思索與總結。詩中包含的哲學意味,即使在今天,也沒有失去它的發人深思、耐人尋味的作用。
借物喻理以達到驚世醒俗目的的詩,弄不好是會流于口號而味同嚼蠟的。宋詩中也確實有不少這樣的詩,因而敗壞了宋詩的名聲。其主要原因,也就是因其不解“外意欲盡其象”及“內外意含蓄”。這首《詠柳》,因“內意”的需要,而外盡柳的形象,連用“亂”、“倚”,“狂”三字,便把柳的旺盛的生命力和獨占春色的“狂”態,表現得淋漓盡致。詩人描繪的是一幅充滿蓬勃生機的圖畫,因此它使人很難一下子看出詩的“內意”到底是什么,這也就是其內外意含蓄的結果了。
然而,與賀知章的《詠柳》相比較,其“內意”的顯露還是非常明白的,因為“猶未……,勢便……”“解把……不知”兩組句式和和“亂”、“倚”、“狂”這類詞中所包含的固定的情感色彩,使人們容易推知詩人的寄托,而賀知章的《詠柳》的內意則似乎更為隱蔽:“碧玉妝成一樹高,萬條垂下綠絲絳。不知細葉誰裁出,二月春風似剪刀”。這種切近真實的“純客觀”的描寫,其“內容”之所在,人們也只能從詩中流露出的涓涓感情的細流中去體味和把握了。
詠物詩的表現形式,在不同的時代和不同的詩人那里,都是不盡相同的,有時甚至差別很大。一般說來,唐人詠物,總是非常注意被詠物體的“入畫性”,所以全詩的構
圖設色都很講究,但正因為如此,難免有些詩就會傷于小巧,晚唐孫光憲的《楊柳枝詞》四首其二,可為一例:
有池有榭即濛潦,浸潤翻成長養功。
恰似有人長點檢,著行排立向春風。
而宋人詠物,則往往很注意于詩中表現詩人對社會人生的體驗、感受,強調詠物詩的“入理性”,因此被詠物體在詩中的象征意義也就比較明顯。除曾鞏的《詠柳》外,我們再看一看韓琦的一首《小檜》:
小檜新移近曲欄,養成隆棟亦非難。
當軒不是憐蒼翠,只要人知耐歲寒。
這是一首典型的托物言志詩,雖名為“小檜”,但只字沒有描繪小檜的外形特征,只著意于檜的耐寒的品格。此詩亦隱含樹木容易樹人難之意。前二句說,檜柏雖然難長高大,但真要把它培養成棟梁之材卻也不難,后二句則交待自己植檜的原因:不是喜歡檜柏的蒼翠形色,而是為了讓檜柏成為自己培養“耐寒”品格的模范。但這種“以神寫形”的手法,仍然不失為詠物詩,是詠物詩之“一格”。這種形式在宋代以后的題畫詩中,一直保持并發展著。本書后面講到鄭思肖的題畫詩《畫菊》時,還要涉及這個問題,因此這里就不多講了。
我們再把話拉回去,談談曾鞏的《詠柳》詩。因為在我們引用的賀知章的《詠柳》中,不僅看到其與曾鞏詩風格的不同,也看到了二者對柳的評價的不同。這種不同是并不奇怪的,因為詩人之于物,本來就是各有眼光,其詠物詩,也是各從自己的生活體驗和感受出發的。而具體到柳,卻又是興味雋永,千百年來引千百萬詩人吟詠的題材。
柳作為藝術形象出現在詩中,由來已久。《詩經·小雅·采薇》就有:“昔我往矣,楊柳依依”,這大概是把柳作為與人不忍別離的多情物的最早的例子了。到了唐代,柳的這種形象已經固定,所以劉禹錫總結說:“城外春風吹酒旗,行人揮袂日西時。長安陌上無窮樹,唯有垂楊管別離!”柳既然如此多情,所以柳的形象當然也就成了人們歌詠禮贊的對象,這也就是賀知章不惜以工筆細描,替柳傳真留影的原因。鄭谷曾這樣來描寫柳的多情和持重;
半煙半雨溪橋畔,映杏映桃山路中。
會得離人無限意,千絲萬絮惹春風。
——《柳》
但是,既然柳如此多情,而且總是“會得離人無限意”,這不說明它多的正是“離情”么!它年年送人又年年綠枝婆娑,只見它送人卻不見它“迎人”,這不正說明它又實在是“無情”么!于是,柳作為“無情”的物體,又在詩中出現了。裴說《柳》說:“高拂樓臺低拂塵,溺橋攀折一何頻!思量卻是無情樹,不解迎人只送人!”杜甫在《漫興》中也說:“顛狂柳絮隨風舞,輕薄桃花逐水流”。這里,柳已被揭去了它的含情脈脈的面紗,一變而成了輕薄顛狂的宵小之徒。甚至連有些歌妓舞女也從這一形象出發,拿它自比:“莫攀我,攀我太心偏。我是曲江臨池柳,這人折來那人攀,恩愛一時問”(《敦煌曲子詞集·望江南》)。
可見,曾鞏從“狂”字著眼去刻劃柳的形象,是有其來歷的。這也是我們認為這首詩的“內容”是有感于柳的“狂”并由此聯想到現實生活中那些有恃無恐,得勢一時終必遭覆滅的小人的原因。看來,要把握一首比較好的詠物詩,還是需要下些工夫探討的。
亂條猶未變初黃,倚得東風勢便狂。
附
《宋史》卷三一九“曾鞏傳”
鞏性孝友,父亡,奉繼母益至,撫四弟、九妹于委廢單弱之中,宦學婚嫁,一出其力。為文章,上下馳騁,一時工作文詞者,鮮能過也。少與王安石游,安石聲譽未振,鞏導之于歐陽修,及安石得志,遂與之異。神宗嘗問:“安石何如人?”對曰:“安石文學行義,不減揚雄,以吝故不及。”帝曰:“安石輕富貴,何吝也?”曰:“臣所謂吝者,謂其勇于有為,吝于改過耳。”帝然之。
《養一齋詩話》卷四 清·潘德輿
昔人恨曾子固不能詩,然其五七言古,甚排宕有氣。近體佳句,如“流水寒更澹,虛窗深自明”,“宿幌白云影,入窗流水聲”,“一徑入松下,兩峰橫馬前”,“壺觴對京口,笑語落揚州”,“時見崖下雨,多從衣上云”,頗得陶、謝家法。七言如“濼水飛綃來野岸,鵲山浮黛入晴天”,“一尊風月身無事,千里耕桑歲有秋”,“微破宿云猶度雁,欲深煙柳已藏鴉”,“一川風露荷花曉,六月蓬瀛燕坐涼”,“娟娟野菊經秋澹,漠漠江潮帶雨渾”,“入陂野水冬來淺,對樹諸峰雪后寒”。又七言絕句,如“亂條猶未變初黃,倚得東風勢便狂。解把飛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紅紗籠燭照斜橋,復觀飛翚入斗杓。人在畫船猶未睡,滿隄涼月一溪潮”。“云帆十幅順風行,臥聽隨船白浪聲。好在西湖波上月,酒醒還對紙窗明”。皆清深婉約,得詩人之風旨,謂其不能詩者妄矣。
《明詩紀事》戊簽·卷九 清·陳田輯
《四庫總目》:正、嘉(按:指明代英宗正德和世宗嘉靖年間)之際,北地、信陽聲華藉甚,教天下無讀唐以后書。然七子之學得於詩者較深,得於文者頗淺,故其詩能自成家,而古文則鉤章棘句,剽襲秦、漢之面貌,遂成偽體。史稱慎中(按:明代唐宋派代表作家王慎中)為文,初亦高談秦、漢,謂東京以下無可取。巳而悟歇、曾作文之法,乃盡焚舊作,一意師仿,尤得力於曾鞏。演迤詳贍,卓然成家。與唐順之(按明代唐宋派代表作家)齊名,天下稱之曰王、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