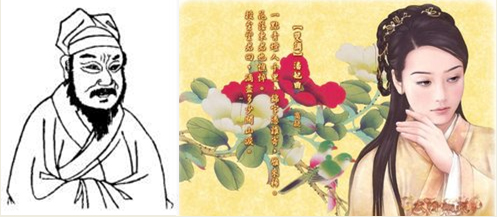元人小令鑒賞之四
【雙調·潘妃曲】 商挺
一點青燈人千里,錦字憑誰寄?雁來稀,花落東君也憔悴。投至望君回,滴盡多少關山淚。
商挺(1209——1288),字孟卿,一作夢卿,晚號左山老人。曹州濟陰(今山東曹縣)人。年二十四,東平嚴忠濟辟為經歷,出判曹州。蒙古憲宗三年(1253)入侍忽必烈于潛邸,遣為京兆宣撫司郎中,撫定關中。又升空撫司副使,受命兼治懷孟。蒙古憲宗八年(1258),復得忽必烈召見,與商軍政要務。元世祖至元元年(1264)力助忽必烈取得汗位。任陜西、四川等路宣撫副使,與宣撫使廉希憲等共同挫敗蒙古將領哈刺不花、渾都海等人的叛亂。改僉陜西、四川行省事,入京拜參知政事。于元初軍政制度多所創建。六年同簽樞密院事,八年升副使。九年(1272)十月,赴京兆皇子安西王王府相。十五年(1278)以王府內訌,株連罷職、籍家。無罪獲赦后,于至元二十年復樞密副使,以疾免。隱居不出,死于京城。仁宗延祐初年,追封推誠協謀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魯國公,謚“文定”。
商挺出生于一個文學氣氛極濃的家。父親商衟是一代文宗元好問的詩友,叔父商衜是個雜劇作家,寫過有名的《雙漸小卿諸宮調》以及【越調·天凈沙】、【南呂·一枝花】、【正宮·月照庭】等散曲。他的岳父趙滋(字濟甫,號蘧然子)是著名書法家。元好問拘囚于山東聊城時,兩人過往甚密,年輕的商挺亦從之游,得到元好問的文學熏陶和指教。趙滋去世后,由商挺撰寫“行狀”,元好問據此撰寫墓碑(據《元好問集》卷24《蘧然子墓志銘》)。商挺為人多才多藝,能詩賦,善隸書、山水墨竹。
有詩千余篇,惜多散佚。《元詩選》癸集存其詩四首。《全元散曲》從《陽春白雪》輯其小令十九首,多寫戀情及四季風景。著有《藏春集》6卷
商挺 一點青燈人千里,錦字憑誰寄
這首小令題目叫【雙調·潘妃曲】。其中“雙調”是元曲宮調名。“潘妃曲”是其曲牌名。潘妃是南朝齊東昏侯蕭寶卷的寵妃,小字玉兒,有姿色,性淫侈。蕭寶卷為其建神仙、永壽、玉壽三座宮殿,窮奢極欲,宮殿地鋪金蓮紋,潘玉兒行踏于殿,稱作“步步生金蓮”。這里用做曲牌名字,與潘妃本事并無關系。從題旨來看,這首小令并無多少過人之處,他所詠嘆的乃是中國古代詩人們千百次重復過的離別相思,也是3800多首元人小令反復詠歌的題旨。它之所以讓人刮目相看,在于它選材角度的獨特和情緒結構的精妙。
首先是選材角度的獨特。既然是相思,就是男女之間或夫妻雙方的事。尤其是男性作者,往往習慣于從天涯孤旅、思親懷鄉這一角度來展開。如同為元代散曲作家馬致遠的這首【雙調·壽陽曲·瀟湘夜雨】:
漁燈暗,客夢回,一聲聲滴人心碎。孤舟五更家萬里,是離人幾行清淚
孤舟燈暗,夢醒時分,抒發一位離家萬里的天涯游子對親人無盡的思念。楊朝英的【商調·梧葉兒·客中聞雨】,景云啟的【雙調·得勝令·孤零】等皆是描寫“關山淚”、“相思夢”,以一個男性的心理,游子的身份來表達相思,反映別情。就連馬致遠那首被稱為“秋思之祖”的【越調·天凈沙·秋思】在選材角度上也不例外。但這首小令卻別出蹊徑:以一個家居妻子的身份,從女性心理角度表達相思,雖然是同樣的時間——“一點青燈”;同樣的空間——“人千里”;同樣的情感表達方式——“滴盡多少關山淚”,但由于從女性的角度來表達,顯得格外細膩,格外柔情。作者不說客中游子如何思念妻子,反從對面落筆,敘說妻子如何思念客中的游子。這也顯得手法更為婉曲,更能突出相思的“相”字。這種表達方式,中國古典詩論中叫做“代擬法”,即代對方設想,所謂“心已神馳到彼,詩從對面飛來”(方回《瀛奎律髓》。它能起到一石二鳥的作用,使情致更加婉轉。當然,這種手法并不起自商挺,他也只是在繼承和借鑒。詩作如唐人王維的《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李商隱的《無題》:“曉鏡但愁云鬢改,夜吟應覺月光寒”。詞作如歐陽修的《踏莎行》:“寸寸柔腸,盈盈粉淚,樓高莫近危闌倚。平蕪近處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溫庭筠的《望江南》:“過盡千帆皆不是,斜暉脈脈水悠悠,腸斷白萍洲”。喜馬拉雅山高,是以青藏高原作為底座的‘長江水長,是以喀喇昆侖作其源頭的。商挺這首小令之所以能在選材上別出蹊徑,也是以前人優秀詩詞作為底座的。
其次,是情緒結構的精妙。一首散曲作品,曲作家為了表大某種情感的需要,都會處心積慮去尋找一種最合適的表達方式,從而呈現出不同的表達技巧。如:有的通過寫景,以景寓情,景中現情,如張可久的【雙調·落梅風·春晚】“東鳳景,西子湖,濕冥冥柳煙花霧。黃鶯亂啼蝴蝶舞,幾秋千打將春去”。通篇描景,再現西湖的春日美景,作者晚年的閑適心態和對大自然的熱愛,對生活的審美感受,亦從這幅畫面上暗暗流露出來。另一種則與此相反,通過人物言行動作,直接,表達自己的情志,如關漢卿的【雙調·沉醉東風·別情】:“咫尺的天南地北,霎時間月缺花飛。手執著餞行杯,眼閣著別離淚。剛道得聲‘保重將息’,痛煞煞教人舍不得。‘好去者,望前程萬里’”。相戀之情,傷別之意,通過手執餞杯、眼含別淚、口道珍重這些人物的言行動作直接道出,沒有任何場景的描繪和餞別過程的敘述。商挺的這首小令的情感表達和前兩者皆有所不同:既不是通過場景的客觀描繪,也不是通過人物的言行動作的直接道出,而是透過人物的心理、意識的流動和情感跳躍的方式來加以表現:這位在家中孤守的妻子深夜難眠,由眼前的青燈想到千里之外的丈夫。“一點青燈”是思念的觸發點,“人千里”則是產生情緒波動的本因。由夜不成眠想到千里之外的丈夫,再想到如何表達對千里之外丈夫的思念,于是便想到寄信。“錦字”之典出自前秦的才女蘇惠。蘇蕙的丈夫竇滔出鎮襄陽,蘇惠在長安獨守空閨。為表達對遠方丈夫的思念,她將所寫詩詞編排整理暗藏在29行、29列的841個字的詩句,織在八寸錦緞上名為《璇璣圖》。派人送交在長安的竇滔。因為此圖“縱橫反復,皆成章句”,且文辭纏綿凄婉,因此后人稱寄夫的詩函為“錦書”。如宋代女詞人李清照的《一剪梅》:“云中誰寄錦書來,雁字回時,月滿西樓”。商挺曲中的這位女性因思念丈夫而產生寄信的欲望,但卻此望難成,因為“雁來稀”,因為“錦字憑誰寄”?古時有鴻雁傳書的傳說,遠飛的大雁已被當作傳信的使者。“雁來稀”在此是借代,意味關山阻隔,音容兩茫,縱游千種相思也無法向遠方親人表達,只好對著“一點青燈”長吁短嘆、徹夜難眠了。至此,女主人的情思幾經延展、幾經波折,繞了個圈,又回到“一點青燈人千里”這個思緒的出發點。
上面三句是念遠, “花落東君也憔悴。投至望君回,滴盡多少關山淚”是悲己,則從時間的角度展露情思:“花落東君也憔悴”表面上是寫景,點明相思的季節是在春暮,實則以花喻人,抒發歲月流逝、青春難再之悲。唐人傳奇中有篇《柳氏傳》,其中的女主人公柳氏寫了首傷別詩給丈夫韓翊,也是托柳起興,以物喻人:“楊柳枝,芳菲節,可嘆年年贈離別。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君來豈堪折”。女人的青春本來就短暫,跟何況是在傷別之中呢?“一旦春殘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為什么不能朝夕相守,而要將歲月輕拋呢?這大概就是這位女性此時的心理。但在表現手法上,她不說自己憔悴,而說“東君也憔悴”,連春神都為之動情,為之憔悴,何況是人,又何況是離別中人兒呢!接下來的“投至望君回,滴盡多少關山淚”兩句又把時間向前延展,從眼前的憔悴遙想到未來的情形。“投至”是元人口語,“等到”、“挨到”之意。這位女性由眼前的相思、傷別到預卜歸期、計算歸程。心想要挨到丈夫歸來那一天,還要流多少相思淚啊!小令中不說相思淚而說“關山淚”,大概就像《詩經》《君子于役》和《卷耳》那樣,恐怕還包含對重重關山外的丈夫種種擔憂和懸掛吧!
總之,這首小令從時空兩個側面來展露思緒:一會兒眼前孤燈、落花,一會兒千里之外;一會傷嘆自己閨中獨守、青春將逝,一會又擔憂千里之外重重關山的丈夫;一會切指細數歸期,一會又欲遙寄錦字。思緒不斷延展,不斷跳躍又不斷回環。實際上都是青燈之下的枯坐懸想,既無語言動作,亦無環境描寫。這種完全靠思緒來連綴全篇的手法,有點類似今天的意識流。
附錄
《新元史》卷一百五十八·列傳第五十五 柯劭忞
商挺,字孟卿,曹州濟陰人,其先,本殷氏,避宋諱改焉。父衡,金進士,秦藍總帥府經歷官,河潼失守,為北軍所得,不屈死。挺年二十四,東平嚴實聘為諸子師。實卒, 其子忠濟辟為經歷
《元好問集》卷二十三、卷二十四 元好問
予居東州久,將還太原,行有日,蘧然子(按:即趙滋,字濟甫,號蘧然子)聞之,誦予詩文,恨相見之晚,而相從之不得久也,為之泣數行下。丁酉冬,復來東州,而蘧然子下世以數月矣。其婿商挺孟卿為予言,予已北歸,蘧然子為之飲食不美者數日,家人輩問言“元子得歸,在渠為可喜事,而公為之捐眠食何也”蘧然子曰“是豈兒輩所能知也哉”他日孟卿示予蘧然子故書,凡予所談,往往記之紙墨間,予詩文則間亦記之也,因竊為慨嘆。丙辰冬十月,予閑居西山之鹿泉,員生自奉天東來,持京兆宣撫使商挺孟卿所撰行狀,以墓碑為請,且道君臨終念念不相置,留語殷重,以撰述為顧。
文章分頁: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