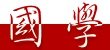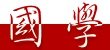[整理贅記]
圍繞著《談藝錄》和《管錐編》這兩部學(xué)術(shù)巨著,周振甫先生與錢鍾書先生作為編輯與作者之間的種種佳話,已廣為人知。這里只說《管錐編》。1972年3月,錢鍾書先生從干校回京,借住在文學(xué)研究所辦公室,楊絳先生說:"我和鍾書在這里住了三年,他寫完《管錐編》。"(《談〈堂·吉訶德〉的翻譯》)《管錐編》初稿寫定不久,大約在1975年,周振甫先生成為《管錐編》的第一個(gè)讀者。二十多年之後,當(dāng)人拿著錢先生《管錐編》序中"命筆之時(shí),數(shù)請益於周君振甫"這句話,來請周先生回憶當(dāng)時(shí)的情況時(shí),周先生說:錢先生那樣講,我實(shí)在慚愧。那還在"四人幫"控制時(shí)期,大概是1975年,錢先生住在那時(shí)文學(xué)研究所樓下的一間房間里。一天,他忽然要我去他家里吃晚飯,我不知道有什麼事情,下班後就去了。我到的時(shí)候,他已在院子里等我了。吃過飯,錢先生拿出一疊厚厚的稿子,說要借給我看,這稿子就是《管錐編》。錢先生的著作是非常珍貴的,我以前是不敢向他借的,怕丟失了就不好辦了。這次,他要借給我看,很出我意外。他只是說要我給他的稿子提點(diǎn)意見。提意見,我是沒有資格的。不談外文,就是中文,錢先生讀過的書,很多我沒有見過。我因?yàn)槟馨葑x到錢先生的著作而喜出望外,所以,就不管能不能提意見,先把手稿捧回去了。(錢寧《曲高自有知音--訪周振甫先生》,轉(zhuǎn)引自沉冰主編《不一樣的記憶--與錢鍾書在一起》,當(dāng)代世界出版社,1999年)
關(guān)於這次請周先生讀《管錐編》,錢先生以"小扣輒發(fā)大鳴,實(shí)歸不負(fù)虛往"(《管錐編》序)給予高度評價(jià)。周先生卻謙虛地說:我是讀到一些弄不清的地方,就找出原書來看,有了疑問,就把一些意見記下來。我把稿子還給錢先生時(shí),他看到我提的疑問中有的還有一些道理,便一點(diǎn)也不肯放過,引進(jìn)自己的大著中。錢先生的《管錐編》很講究文采,所謂"高文一何綺,小儒安足為"。他把我的一點(diǎn)意見都是用自己富有文采的筆加以改寫了。《管錐編》出版時(shí),我曾提請他把序中那幾句話改掉,他不肯,就只好這樣了。(同上)
錢先生《管錐編》序所署寫作時(shí)間為1972年8月,但"數(shù)請益於周君振甫"云云主要是就1975年的這次讀稿而言的。根據(jù)中華書局編輯部《管錐編》書稿檔案,現(xiàn)在我們知道,在《管錐編》書稿交付中華書局之後,即1977年底至1978年初,周先生還有一次認(rèn)真全面的審讀,并留下了詳細(xì)的記錄。
1977年10月24日,周先生向中華書局提交了《建議接受出版錢鍾書先生的〈管錐編〉》的選題報(bào)告。同年12月1日,完成《管錐編》第一部分書稿的審讀,并撰寫了《〈管錐編〉(第一部分)審讀報(bào)告》(以上兩篇報(bào)告,已整理發(fā)表於《書品》1999年第1期)。保存在檔案中的《審讀報(bào)告》,後面還附有38頁長達(dá)數(shù)萬言的具體意見,其中除了部分有關(guān)編輯技術(shù)處理的內(nèi)容外,絕大多數(shù)是具體問題的學(xué)術(shù)性探討。更為可貴的是,對於周先生提出的每一條意見,錢先生都有認(rèn)真的批注,短者數(shù)字,長則百言。并在書中作了相應(yīng)的刪改和修訂。閱讀這些文字,好像是在傾聽兩位智者的對談,娓娓之中,周先生的周詳入微,錢先生的淵博風(fēng)趣,如在眼前。
周先生的審讀意見,是按照《管錐編》原稿的順序,逐條記錄而成,每條前標(biāo)有原稿的頁碼。現(xiàn)在的整理稿,除保留了原稿的頁碼外,我們查核了每條意見在中華版《管錐編》中的相應(yīng)位置,并標(biāo)注書名、細(xì)目及所在冊頁,以便檢讀。對書中已經(jīng)刪去,或所指未詳?shù)母鳁l,則適當(dāng)予以說明和提示。錢先生的批注,原寫於審讀意見的頁眉、頁腳和行側(cè),現(xiàn)統(tǒng)置於相應(yīng)段落之下;少量行間批注仍置於相應(yīng)語句之下。其前均冠以"錢批",以相區(qū)別。間有文字訛誤、徵引簡省等處,稍作規(guī)范,其馀均盡可能保留原貌。
寫完這個(gè)贅記,我不禁想起1997年8月周先生作為"東方之子",回答中央電視臺主持人的一番話,主持人問:"因?yàn)楣ぷ鞯脑颍罱K沒有成為一個(gè)職業(yè)的學(xué)者,您覺得遺憾嗎?"周先生用濃重的鄉(xiāng)音,淡淡地回答:"中華書局給我編審,就可以了。"對這個(gè)回答,人們甚至?xí)詾榇鸱撬鶈枺?dāng)我們讀完這份審讀意見,也許就不難體會(huì)這句話的含義和份量了。
2000年5月30日第一部分整理畢,後學(xué)徐俊記。
序:"命筆之時(shí),數(shù)請益於周君振甫,小叩輒發(fā)大鳴,實(shí)歸不負(fù)虛往。"(中華版第一冊卷首)
頁Ⅰ序 "請益"、"大鳴"、"實(shí)歸"是否有些夸飾,可否酌改?
【錢批】如蒲牢之鯨鏗,禪人所謂"震耳作三日聾"者。不可改也。
目次(中華版第一冊卷首)
頁Ⅱ目次 擬編細(xì)目,請改定。十種書當(dāng)按四部排列,故《史記》列於《老子》前,《列子》為魏晉間作,要不要列《易林》後,或另有用意;《太平廣記》列《全上古文》前,是否以小說當(dāng)列於散文前?
【錢批】略參"四部",然四部以"術(shù)數(shù)家"置"道家"前,鄙意嫌其輕重倒置,故以《列子》先於《易林》;"小說家"屬子部,故在總集前耳。
《周易正義》一《論易之三名》(中華版第一冊第2頁)
頁2 《論語》《子罕》不作《論語·子罕》,當(dāng)有意如此標(biāo)法,擬即照排。
【錢批】已遵一一改正。"《詩》《小雅》《桑卮》"改為《詩·小雅·桑卮》,是否?
同前(中華版第一冊第4~5頁)
頁5(1) 以句中"是"兼然、此二義,"彼"兼他、非二義,所引例有的似不如此。"以是(然,不作此)其所非,而非其所是(然,不作此)。""彼(他,不作非)亦一是(然)非,此亦一是(然)非。"與"非"相對之"是"作然不作此,與"此"相對之"彼"作他不作非。兼有二義的,"物無非彼(他、非),物無非是(此、然)。""彼(他、非)出于是(此、然),是亦因彼。""彼"、"是"相對,兩字各兼二義。
【錢批】是也。然非兼引前數(shù)句,則襯托不明,拙文重點(diǎn)正如尊評所言,似不致誤會(huì)。
同前(中華版第一冊第6頁)
頁7倒9 《繫辭》下云"……",":"下用",",一般":"下用句號,下用","上不用":"。此處當(dāng)有意如此點(diǎn)法,擬即照排。
【錢批】此乃西文標(biāo)點(diǎn)習(xí)慣,似較合理,因此處語氣一貫為一單位觀念。乞再酌定。
《周易正義》五《觀》(中華版第一冊第20頁)
19(1) 借天變以誡帝王,可補(bǔ)帝王借天變以罷斥大臣,上下交相賊。
【錢批】遵補(bǔ)請審鑒。
《周易正義》一八《繫辭(二)》(中華版第一冊第42頁)
楊雄,從木作楊,是有意如此寫,當(dāng)照排。
【錢批】遵改,從通用。段玉裁《經(jīng)韻樓集》卷五《書漢書楊雄傳後》:"其謂雄姓從手者偽說也",故拙稿作"楊",但此等處不必立異,尊教甚當(dāng)。
《周易正義》一九《繫辭(三)》(中華版第一冊第44頁)
44-46(1) 幾:孔疏:"幾者離無入有,是有初之微。"入有是已入於有,特是有之微者。有是已成形,有之微者是未成形而微露端倪,易被忽視而還是可見的。注:"幾者去無入有,(【錢批】此處斷句,下另句。)理而無形,不可以名尋,不可以形睹者也。唯神也……故能朗然玄照,鑒於未形也。合抱之木,起於微末,吉兇之彰,始於微兆。"這里說幾是無形不可見,既是無形而不是未形,那末還是屬于無,沒有去無入有。既說"去無入有",又說"無形"不可見,是否矛盾。既然無形不可見,又"合抱之木起於微末",木的微末是有而非無,是可見而非不可見。《易》:"幾者動(dòng)之微,吉之先見者也。"還是可見的。無形不可見之說是否不確。(【錢批】此處似未的,韓注"無形"指"理"言(形而上者),"幾"者"去無[形]"云云也。尊糾其"神識未形",則確矣。)
疏:"幾,微也,是已動(dòng)之微,動(dòng)謂心動(dòng)事動(dòng)。初動(dòng)之時(shí),其理未著,唯纖維而已。若其已著之後,則心事顯露,不得為幾;若未動(dòng)之前,又寂然頓無,兼亦不得稱幾也。"照此說來看引的詩,"‘江動(dòng)將崩未崩石',石之將崩已著,特尚未崩耳,不得為幾也。"將崩未崩,似即"初動(dòng)之時(shí),其理未著,唯纖維而",詩人從未著的纖維中看到將動(dòng),是否就是幾。"盤馬彎弓惜不發(fā)",雖發(fā)之理未著,唯發(fā)之纖維而已,是否就是幾。又將動(dòng)未動(dòng)與引而不發(fā),與"雪含欲下不下意,梅作將開不開色",實(shí)際相同,一作非幾,一作幾,不好理解,倘均作幾,就好懂了。(【錢批】此乃程度問題;如熹微、昧爽、曉日、中天,難劃而未嘗不可分,心理學(xué)謂之"感覺門檻"(或高或低)。)
【錢批】此評《注》、《疏》之矛盾,精密極矣!非謂之"大鳴"不可。已增入并借大名增重,不敢掠美也。乞鑒定之。且增申說一段,或可稍圓。
《毛詩正義》五《關(guān)雎(四)》(中華版第一冊62~64頁)
63 比興 孔疏:"興者托事于物,則興者起也,取譬引類,起發(fā)己心,詩文諸舉草木鳥獸以見意者,皆興辭也。"這樣說,興就不必居于詩的開頭,在詩中也可有興。《離騷》中諸舉草木鳥獸以見意者也可說是興了。這樣的興,就不同于居于詩的開頭的興,如朱熹說的與下文全無巴鼻了。陳沆的《詩比興箋》,大概就從孔疏的說法來的。尊著中沒有談到這個(gè)意義的興,請考慮要不要補(bǔ)說一下。還有尊補(bǔ)的竇玄妻怨歌,據(jù)沈德潛注:"天子使出其妻,妻以公主。妻悲怨,寄書及歌與玄。"那末"煢煢白兔,東走西顧",是否可比被出的狼狽相呢?又引"孔雀東南飛",記得樂府詩:"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回顧,十里一徘徊。妻卒被病,行不能相隨。我欲銜汝去,口噤不能開。……"則孔雀東南飛正指夫婦生離之痛。所補(bǔ)兩例,請?jiān)倏紤]。
【錢批】拙論乃言於"興"之鄙見。孔疏於鄙意無可張目,故不及之。"詩中有興",孔未舉例;《離騷》篇中之鳥獸草木,恐"賦"、"比"可釋。竇玄妻歌,沈說正緣其不識"興"義;《焦仲卿妻》中數(shù)句,亦緣後人不識"興"義為搭橋引渡,故歷來通行本皆刪而不及,《玉臺新詠》即無此等句。
同前(中華版第一冊第63~64頁)
64 引項(xiàng)安世說"興",以《楊柳枝》、《竹枝詞》每句皆足以"柳枝"、"竹枝",當(dāng)指每句末加上"柳枝"或"竹枝",那似屬于聲辭合寫,句末兩字表聲而無義,與"興"之在句首者不同。兒歌之"一二一"好像也是聲而非辭,特是聲之位于句首者。詩中之"興"是辭而非聲。興既是辭,必有內(nèi)容。如"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李注:言長存也。人生天地間,忽如遠(yuǎn)行客。李注:言異松石也。""青青河畔草,春草年年綠,王孫歸不歸?見春草而思游子。綿綿思遠(yuǎn)道。"如朱子說,以柏石與草皆為興,則興與下文并非"全無巴鼻"。柏石并非比人生短促,故非比,但以反襯人生短促,故為興。草并非比思遠(yuǎn),故非比,但以引起思遠(yuǎn),故為興。此柏石草三句皆有內(nèi)容,不同於僅為表聲之字。劉勰《比興》:"比顯而興隱","興者,起也。……起情者依微以擬議","興則環(huán)譬以托諷","興之托諭,婉而成章","關(guān)雎有別,故后妃方德"。劉勰認(rèn)為興和比只有隱顯之異,只是一種隱的比,這正可說明朱子舉的例子。興和下文關(guān)係,不即不離,不即所以非比,不離所[以]非全無巴鼻。全無巴鼻之說與所舉例似不合。
【錢批】拙說未晰,因尊指摘而補(bǔ)申之。見稿上,請酌正。
《毛詩正義》二二《桑中》(中華版第一冊第88頁)
86(2) "艷遇"、善誘婦女之"宗匠"、"鴛鴦社",引號中的詞是否可改用貶義詞?
【錢批】遵改。
《毛詩正義》三九《蟋蟀》(中華版第一冊第119~120頁)
118-119 對于宗旨?xì)w于及時(shí)行樂之作,或略示貶義,或指出此種詩產(chǎn)生之背景如何?
【錢批】"背景"甚難臆斷,亂世平世、貧人("窮開心")富人,均有此心。拙稿此節(jié)結(jié)語"或?yàn)槭幾印?quot;一節(jié)已言之矣。姑加"貶詞"何如。請酌定。
此條就《陳風(fēng)·宛丘》而言,原文已刪去
125(1) 《宛丘》:"子之湯(蕩)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持)其鷺羽。"寫子之游蕩,有荒淫之情,無威儀可觀望。所謂游蕩,即擊鼓而舞,無冬無夏。這里似乎沒有"單相思"之意,儻以上解釋不謬,是否可說明此詩應(yīng)從鄭箋,但"有情"、"無望"可以抽出來表達(dá)另一意?
【錢批】甚善,即刪去此則。
《毛詩正義》四七《七月》(中華版第一冊第130頁)
131(1) "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余冠英先生注:"是說怕被公子強(qiáng)迫帶回家去。"本書引《箋》"始有與公子同歸之志,欲嫁焉"。女與公子地位懸殊,"欲嫁"之說與今日讀者之理解抵觸,以"傷悲"為"思男",亦同樣抵觸。此處是否可先批《傳》、《箋》之誤,然後轉(zhuǎn)入《正義》言時(shí)令感人之說亦有可取,與下文相貫。
【錢批】此意兄前次閱稿時(shí)已言之,弟非飾非拒諫也,以余公之解乃"張茂先我所不解"也。"怕被迫……"殆如《三笑》中之王老虎搶親耶?詩中無有也。"殆"可通"憚"耶?古之小學(xué)經(jīng)傳未見也。"地位懸殊"則不"欲嫁"耶?封建時(shí)代女賤而得入高門,婢妾而為后妃者,史不絕書,戲曲小說不絕寫,至今世鄉(xiāng)間女郎欲嫁都市高干者尚比比也。鄭、孔之注未必當(dāng),但謂之不切實(shí)際不可也。余解欲抬貴勞動(dòng)?jì)D女,用心甚美,然不啻欲抬高王安石、李贄而稱之為"法家"矣。下文又曰"為公子裳"、"為公子裘",則此女雖"怕"而終"被迫"乎?其見曹植《美女篇》,便知采桑女郎正亦名貴也。
《左傳正義》三《隱公元年》(中華版第一冊第172頁)
169 戴氏謂得"志"通"文",是對的,但說《詩》之志愈不可知,"斷以‘《詩》無邪'之一言,則可以通乎其志"。《傳》、《箋》曲解之說,無非是要斷以"詩無邪"造成的,斷以"詩無邪"之一言,怎麼能夠通貫所有《三百篇》之志。如何才能理解詩人作詩之志,此中大有事在,而且是很重要的,是否可以加以闡說。
【錢批】是否"詩無邪"三字能通《三百篇》之志,吾不知也。戴氏言之,吾即以其矛攻其盾耳。落得便宜,一笑。
《左傳正義》一六《僖公二十四年》(中華版第一冊第191頁)
188中 富辰若曰:"婦女之性,感恩不到底……",下接"蓋恩德易忘……",似可作"然恩德易忘……男女同之,不當(dāng)以苛責(zé)婦女"等語如何?
【錢批】吾師乎!吾師乎!此吾之所以"尊周"而"臺甫"也!
《左傳正義》一八《僖公二十七年》(中華版第一冊第192~193頁)
189(1)倒5行 "按蒍賈以此(治軍嚴(yán))為子玉必?cái)≈?quot;,按蒍賈曰:"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nèi)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
蒍賈說子玉敗是二點(diǎn):一是子文恐子玉不能靖而傳政,把政傳給恐不能靖的人會(huì)招致失敗;二是剛而無禮,似不由于子玉治軍之嚴(yán)。下文190,2行,主張"殺卒之半",則必激變,其說恐非,或者刪去"按蒍賈句",則子文與子玉之治軍是有寬嚴(yán)之異,與下文可銜接,對于"殺卒之半"或刪或加批。如何?
【錢批】甚是,原稿之疏闊也。然蒍賈語緊接此事,則"剛而無禮"當(dāng)亦指其鞭撻之威歟。改奉請酌定。
《左傳正義》二七《宣公十二年(二)》(中華版第一冊第203頁)
200倒3 "圍師必闕,窮寇勿迫"。按本則或?qū)Ee"困獸猶斗"諸論而不引"圍師必闕……";或引"圍師必闕……",再補(bǔ)引殲滅戰(zhàn)及追窮寇之論,顯得兩面都到。
【錢批】論"圍師必闕"見《全上古文》論《孫子》,此處提一下已可。
《左傳正義》三二《襄公四年》(中華版第一冊第211~212頁)
210中 "有窮后羿--……昔有夏之方衰也",語中斷而復(fù)續(xù);211中
"‘與兒逃於楊--'句未終……倒地而滅"語中斷而不續(xù)。兩者稍異要不要點(diǎn)一下?
【錢批】是也,遵補(bǔ)一句。
《左傳正義》三七《襄公二十一年(三)》(中華版第一冊第214頁)
213 以貌美比"深山大澤",似擬不于倫。貌美"生龍蛇以禍女",不過女禍之另一說法,是否要批一下。
【錢批】加數(shù)句請酌。
《左傳正義》五二《昭公十二年》(中華版第一冊第231~232頁)
229中 上言忠信之事則大吉為大吉,不然則大吉為大兇,是以善惠分;此言同一夢也,貴人為吉,賤人為妖,是以貴賤分。把這二者稱為"亦歸一揆"。按以善惡分者,是善的,賤人得大吉亦吉;是惡的,貴人得大吉亦兇,與以貴賤分吉兇的似非一揆。即《易》不勢利而占夢勢利。《火珠林》不分善惡貴賤,是吉即言吉,是兇即言兇,與《易》占夢又不同。是巫筮之道分而為三。王氏以君子為善不為惡故有取於《易》,無取於《火珠林》。易只就行善事的來分吉兇,是片面的,它不管做惡事的;《火珠林》兼管善惡,是全面的。似乎兩者只有片面與全面之不同,而異乎一本與二元之別。做二事的雖大吉亦兇,以兇為大吉是否鼓勵(lì)作惡的人去作惡呢?
【錢批】論王船山一節(jié),遵刪去。《潛夫論》"貴人"、"賤人"外,并舉"君子"、"小人",似與《左傳》意合。
《左傳正義》六二《定公四年》(中華版第一冊第243頁)
238(3) 鄭注:"曰:'某愿朝夕見於將命者'",即始見瞽之辭必同於始見君子之辭而略為"聞名"二字,"敵者"前略"始見","瞽"前略"始見"、後略"者"。按"亟見曰朝夕"下鄭注:"於君子則曰某愿朝夕聞名於將命者,於敵者則曰某愿朝夕見於將命者。"那末不約該作:"聞始見敵者,辭曰:某固愿見於將命者;聞罕見君子者,曰:某固愿聞名於將命者;聞亟見君子者,曰:某固愿朝夕聞名於將命者;聞亟見敵者曰:某固愿朝夕見於將命者;……"
【錢批】甚縝密,即照鈔加一注,并冠以大名:"周君振甫嘗足其辭曰:……"
《左傳正義》六三《定公十四年》(中華版第一冊第244頁)
240,5 其一為"信而不當(dāng)理",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九字似可刪,刪后上下文依舊銜接。因古今不同,古以直躬為不義,而今則以為義也。
【錢批】遵刪。
《史記會(huì)注考證》三《周本紀(jì)》(中華版第一冊253頁)
250,3 "城上烏,尾畢逋",狀拍翼聲。余先生注:"畢,盡也。逋,欠也。居高臨下的烏鴉都缺尾巴,比喻有權(quán)勢的沒有好收場。"兩說不同,未知孰是?
【錢批】余說與說漢鐃歌"妃呼狶"為"女喚豬"無異(請看漁洋《論詩絕句》"元白張王皆古意,不曾辛苦學(xué)妃狶"自注)。明人有不識"蒼黃"即"倉皇"者,釋為臉嚇青了、嚇黃了,亦其類。然"妃呼狶"、"蒼黃"尚望文即可生義,不必如"畢逋"之拐彎抹角也。余先生比類說詩(如以"殆"為"憚"之類),吾等辱在友好,當(dāng)如徐陵所謂"為魏公藏拙"耳。
《史記會(huì)注考證》四《秦始皇本紀(jì)》(中華版第一冊254頁)
288倒7 "按歸說是也",歸說云何,文中未引,必須翻檢《外戚世家》始知。是否可酌引于文中?
【錢批】甚是,已遵補(bǔ)矣。
《史記會(huì)注考證》五《項(xiàng)羽本紀(jì)》(中華版第一冊274頁)
266 《衛(wèi)青傳》校尉李朔一節(jié)。今錄原文於下:乃詔御史曰:"護(hù)軍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將軍擊匈奴,以千五百戶封敖為合騎侯。都尉韓說從大將軍出窳渾……以千三百戶封說為龍頟
侯。騎將軍公孫賀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賀為南{穴/卯}侯。輕車將軍李蔡再從大將軍獲王,以千六百戶封蔡為樂安侯。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朔為涉軹侯,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為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為從平侯。將軍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中郎將綰皆]有功,賜爵關(guān)內(nèi)侯,[沮、息、如意]食邑各三百戶。"以上加"--"是《漢書》刪去的,加[
]是《漢書》補(bǔ)的。《漢書》把前面封侯的戶數(shù)都刪了,但關(guān)內(nèi)侯的戶數(shù)不能刪,刪了怕讀者認(rèn)為沒有食邑了。這樣,食邑少的不刪,多的反而刪了,是不是輕重失當(dāng)。對公孫敖等都用全稱,對公孫賀卻不稱姓,中郎將綰也不稱姓,稱謂前後不一。《史記》沒有這兩個(gè)缺點(diǎn)。封爵、食邑是很重要的,所以《史記》都注明。綰沒有食邑,與以上各人有別,故從刪。食邑三百戶的合併敘述,食邑千三百戶的分別敘述,正是看重食邑之證。食邑的多少正表明功勞的大小,如李蔡功大封千六百戶,最多。所以《史記》的重復(fù)處還是勝過《漢書》。也許原來的詔書為了看重封邑,對李朔等三人就是這樣分別敘述的。
【錢批】甚精細(xì),已采入增一節(jié):周君振甫曰"洪虞"云云,請審之。剪裁尊旨為文,潔未傷意否?
《史記會(huì)注考證》一五《外戚世家》(中華版第一冊300頁)
293(1) "褚少孫記薄姬事云",《漢書》加"昨暮龍據(jù)妾胸"。按薄姬事見《史記·外戚世家》,考證同,此作褚少孫記不知何據(jù)。又《史記》原文已有"龍據(jù)妾胸"句,作《漢書》增亦不知何據(jù)。
【錢批】是極,弟之謬誤也,領(lǐng)教多矣!已改并移前。
《史記會(huì)注考證》二八《孟嘗君列傳》(中華版第一冊318頁)
311(1) 引李商隱書"市道何肯如此"云云,不識李書所言"市道"云何。讀下文知本于《宋清傳》,但《宋清傳》之所謂"市道"云何,已不復(fù)記憶。因檢《宋清傳》,始知宋"清之取利遠(yuǎn),遠(yuǎn)故大",與"炎而附寒而棄"者異,故柳先生稱"清居市不為市之道"。尊稿是否可多說幾句,以省讀者翻書之勞。又清之所謂"市道"實(shí)非市道,讀之深有啟發(fā)。
【錢批】遵添引柳文一句,似可明矣。
《史記會(huì)注考證》二九《春申君列傳》(中華版第一冊319頁)
311(2) "無刺一虎之勞",指刺者為受傷之虎非健強(qiáng)之虎,是否以為"修辭未當(dāng)",請酌。蚌鷸爭而田父"坐而利之",與騎虎難下似兩回事,一為得利,一為不能釋權(quán),不知何以稱"正猶"?
【錢批】一虎已死,一虎傷而未死,雖稍刺即死,亦是微勞,不得謂"無刺之勞"也。"正猶"非謂"騎虎難下"猶"鷸蚌相爭",乃謂或曰兩龍,或曰兩虎,或曰鷸蚌,或曰犬兔,正猶或曰"騎虎"或曰"騎龍",立意同而不妨取象異也。茲添一句以清眉目。
《史記會(huì)注考證》四三《魏其武安列傳》(中華版第一冊349、350頁)
338(1)行3 "執(zhí)其兩端,可得乎中","歌德談藝即以此教人也"。上引袁凱說,一者法之正,二者心之慈,兩者皆是。執(zhí)其兩端而用其中,是不是既不殺也不放,把他關(guān)起來?崔慰林說,朱、王皆不是,又如何執(zhí)兩用中?實(shí)際上殺、放、關(guān),應(yīng)該只有一種做法是對的,如應(yīng)該放,則殺不對,關(guān)也不對,似不宜執(zhí)兩用中?如認(rèn)為兩家皆不是,則兩皆不用,也不宜執(zhí)兩用中?或者執(zhí)兩用中另有解釋。又歌德如何用于談藝,可否點(diǎn)明一下?
【錢批】公乃實(shí)心直口之人,未識政客巧宦之滑頭行徑,蘇味道所謂"不欲決斷明白"。如袁凱肯說"關(guān)起來",則"明白",而明太祖亦不致"怒其持兩端"矣。且也,如說"關(guān)起來",則示"殺不是"而"赦亦不是"也,是"兩端"皆廢而不"持"也。徐大軍機(jī)之類只"持兩端",無意於"用其中";實(shí)心直口人(如公等)與慎思明辨人(如歌德等)方進(jìn)而"用其中",如禪家所謂化"俗諦"為"真諦"耳。
此非謂崔與袁同,而謂"說難",以示"執(zhí)兩端"與"廢兩端"皆不合"帝心"也。歌德之語,說來甚長,此處只能"引而不發(fā)"矣。
《史記會(huì)注考證》四五《李將軍列傳》(中華版第一冊352頁)
340(2) 中石沒鏃與自高臺下躍入水火無傷,似有不同。倘是跳水員,從高入水可無傷,否則會(huì)淹死;或穿石棉衣罩入火,否則會(huì)燒傷或燒死。
【錢批】拙文曰:"敢作能為每出於無知不思";李廣不知為石,商丘開不知為誕。非言所為事之相類也。
《史記會(huì)注考證》五八《太史公自序》(中華版第一冊391頁)
376 道家集其大成,佛氏"亦掃亦包",此但轉(zhuǎn)述而無評論。道佛非真能兼包各家之長者,亦有其所短,要不要點(diǎn)一下?
【錢批】遵加一句。
此條無審讀意見,原文也已刪改,所指具體篇章未詳
【錢批】386
"雅言",弟未謂其為"雅馴之言"。"普通話"之解即本《論語正義》所謂"官話",非今人創(chuàng)見。然重違尊旨,刪去此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