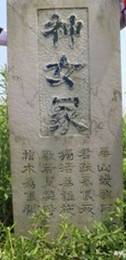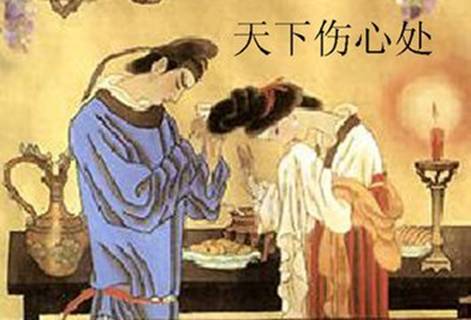漢魏南北朝樂府清賞之二十
南朝樂府·吳聲歌
華山畿
華山畿,君既為儂死,獨生為誰施?歡若見憐時,棺木為儂開!(之一)
啼著曙,淚落枕將浮,身沈被流去(之七)
相送勞勞渚,長江不應滿,是儂淚成許。(之十九)
此是“清商曲辭·吳聲歌”中《懊儂曲》的變聲,一共二十五首。其中第一首“華山畿,君既為儂死”為這組變聲曲的本事,起源于一個悲慘但又充滿浪漫色彩的愛情故事。據陳朝釋智匠《古今樂錄》介紹,據說在南朝宋少帝(423—424)年間,南徐(今江蘇丹徒縣)有個書生到云陽(今江蘇丹陽縣)去,路過華山(今江蘇句容市北十里)腳下,愛上了客店里一位姑娘。因“悅之無因”,無法接近。回家后“隨感心疾”害了相思。病中,他把此事告訴了母親。母親趕到華山腳下,找到客店這位姑娘。姑娘聽說后很感動,解下身上的圍裙,吩咐這位母親將它偷偷藏到兒子的臥席下,病就會痊愈。這位母親回來后照此辦理,果然,這位書生的病一天好似一天。某天,他無意中掀開席子看到圍裙,從母親口中得知原委后,便把圍裙吞到肚里。臨死前囑咐母親,靈車一定要從華山腳下經過。母親按其囑咐繞道華山。當靈車行到華山腳下客店前,挽車的牛不肯走了,打牠也不動。這時,姑娘從客店中走了出來,對書生之母說:“稍稍等我一會”。回到店中沐浴更衣、梳洗打扮后款款而出,對著靈車哭道:“華山畿,君既為儂死,獨生為誰施?歡若見憐時,棺木為儂開”。這時,棺木應聲而開,姑娘跳入棺中后隨即合攏。兩家人敲也敲不開,只好將兩人合葬在一起,人們稱之為“神女塚”。
這個富有浪漫色彩的愛情悲劇,顯然是受了漢樂府《孔雀東南飛》的影響。雖然沒有像《孔雀東南飛》那樣提及這場悲劇的制造者,也沒有告訴我們這對情人不能結合的原因究竟何在,但它的思想意義同樣很深廣:男方是深深愛著女方的,以至因相思而是去;從姑娘的哭訴來看,也是深深愛著男方的,以至以死相殉,如果沒有外界因素的阻擾,他們是能夠也完全應該結合到一起的。但事實是男方在客店里卻“悅之無因”,連接近都不可能,更談不上表明心跡,兩相結合了這也許就是他回家后“隨感心疾”,抱恨終生的原因吧。而姑娘盡管為書生的摯情深深打動,甚至以死相殉,但生前也是連見一面也不可能,只能托書生之母把自己的“蔽膝”捎去作為愛情信物。因此這首詩中雖沒有像《孔雀東南飛》中那樣,具體點出焦母、劉兄這類封建禮教和家長制的代表人物,但我們仍能感受到封建倫理和傳統勢力的巨大壓迫力。唯其沒有點出具體的人和事,我們更能感受到這張落網的廣漠和無形,黑暗的巨大和濃重。
今江蘇句容市北十里的華山村
華山村旁的“神女冢”
這首詩在藝術手法上也有可圈可點之處。前面已多次說過,南朝樂府寫相戀、相思,尤其是女方的相思,往往都比較含蓄,多用借代和暗示,且纏綿而低沉,如《子夜歌》(之十一):“高山種芙蓉,復徑黃檗塢。果得一時蓮,流離嬰辛苦”;《子夜歌》(之三十五):“我念歡的的,子行由豫情。霧露隱芙蓉,見憐不分明”。但這首吳聲歌卻截然不同,而是公開表白,毫不隱晦,而且感情摯烈,噴薄而出。一開頭就是呼天搶地,悲愴欲絕:“華山畿,君既為儂死,獨生為誰施?”“畿(jī)”,本義指京都附近,這里指華山附近,即山腳下;“儂”我,吳地方言;“為誰施”,為誰而活下去。施,施用。沒有含蓄的暗示,沒有曲折的言辭,甚至沒有未婚少女在談論兩情相悅常有的羞澀和吞吐,而是沖口而出、盡情傾吐自己內心的感受,直接道出自己殉情的決心:指華山為證,你既然為我而死,我也不會獨自活在世上!流金鑠石般的熾熱,感天動地般的悲愴,讓人感到其悲憤之氣壅塞胸間,此時此刻,長歌當哭,一吐為快。一旦突出,就可使天地失色、草木含悲。他使我們聯想起漢樂府《上邪》那種火山爆發式的愛情表白,也使我們聯想起《公無渡河》那種痛徹肺腑的呼喊!我在《漢魏南北朝樂府鑒賞·前言》中曾經指出:南朝樂府的婉曲柔媚、含蓄隱晦,既不同于時代相同的質樸剛健的北朝樂府,也不同于同為民歌的質樸清新、直白抒情的漢樂府。但這首《華山畿》是個特例。它抓住事情發生后兩人一生一死、相遇于華山畿這個瞬間,沒有去侃侃敍述事件發生的經過,也沒有細細表說自己的處境和心情,而是長歌當哭,直抒胸臆、痛切直白地道出殉情的決心和這個決心產生的原因:“君既為儂死,獨生為誰施?”。從這一角度看,它也是南朝樂府溝通北朝樂府和漢樂府的橋梁,在中國文學史上自有其獨特的價值!
其次,這則民歌中還帶有一個重要的荒誕情節,即姑娘殉情的奇特方式:“歡若見憐時,棺木為儂開”。根據釋智匠《古今樂錄》中記載,這個愿望居然實現了:當姑娘哭求“棺木為儂開”時,棺則應聲而開,姑娘跳入棺中后隨即合攏。兩家人敲也敲不開,只好將兩人合葬在一起。“合葬”的情節可能受漢樂府《孔雀東南飛》的影響,但哭求“棺木為儂開”,而且棺木居然為之開,合上后又居然再也打不開,好讓這對情人永遠“生不同床死同穴”。這個浪漫神奇的想象,像“天柱絕、地維裂”一樣令人瞠目結舌,像夸父逐日、荊軻去秦一樣悲慘壯烈,從而成為《華山畿》這首南朝樂府最動人之處,也對后人創作產生巨大的影響:明代湯顯祖《牡丹亭》中那位為了愛情出生入死、死而復生的杜麗娘,傳說中亦是以死殉情、“棺木為儂開”的祝英臺,從他們身上都可以看到這位華山畿姑娘的影子。
從文學發展觀念來看,《華山畿》中姑娘哭求“棺木為儂開”時,棺則應聲而開這個荒誕情節,以釋智匠《古今樂錄》中這個故事的相關記載,如姑娘要書生之母將自己“蔽膝”捎去放在臥席之下,就可以治好書生的相思之病等,這已不只是對漢樂府《孔雀東南飛》、《上邪》等相關情節的繼承,而是時代的創新,已帶有六朝志怪的色彩。而六朝的志怪小說中,有的又采用同樣的方式呈現類似的情節,如干寶《搜神記》中的《吳王小女》、《王道平》、《河間男女》,托名曹丕的《列異傳》中的《望夫石》,托名陶潛的《搜神后記》中的《白水素女》;劉義慶《幽明錄》中的《龐阿》、《賣胡粉女子》等,都是采用荒誕的方式來反映現實的苦難,對男女忠貞愛情的摧殘以及他們在摧殘下的忠貞!這說明六朝樂府與六朝志怪是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的,這是文學史上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
《華山畿》共二十五首,上面為第一首,是本事。其余的二十四首則是按其曲調傳唱的樂府民歌。其內容與《華山畿》的傳說并無關聯,但基調是相近或想通的:反映愛情的受阻在女子心中產生的哀傷。下面選的是第七首和第十九首。他們有個共同手法:以極度的夸張來抒發女子在愛情失意中的悲哀。
第七首“啼著曙,淚落枕將浮,身沈被流去”。這位女子的悲苦,是由愛情的受阻而引起的。詩人在剪裁上頗為高妙:他不去交代受阻的原因,也不去訴說心中的悲苦,而是以哭泣的時間之長“啼著曙”——一直哭到天亮,以此來夸張她愁思之深。詩人這樣處理出于以下兩個原因:一是她哭泣愁苦的原因在第五首中已作交代:“未敢便相許,夜聞儂家論,不持儂與汝”。因為父母對他們的結合持反對態度。在封建禮教的威壓下,這位脆弱的女性也就不敢答應對方的求愛。但不敢答應并不意味著他不想答應,更不能遏止她內心的相思:“隔津嘆,牽牛語織女,離淚溢河漢”(之十一)。封建勢力的干擾成了阻遏兩人結合的天河。這對情人只能像牛郎織女那樣隔河相望,淚流不止!二是這樣寫可以讓讀者透過她的情態來揣測她的內心,使詩歌更富有想象力,與其浪漫主義的基調也更為吻合。這位女主人公從傍晚一直哭到天亮,哭泣時間之長既可見愁苦之聲,也足見其找不到解決辦法之無奈。當然,這也會引起讀者對其哭泣之態的想象,哭泣原因之思考。在此基礎上,詩人又加以極度的夸張:“淚落枕將浮,身沈被流去”。傷心的淚匯成滔滔的河,讓枕頭浮起來了,整個身體也被洶涌的淚水卷走了。這種極度的夸張,讓我們在震驚之中又引起聯翩的浮想,更能引起我們對女主人公愛情遭遇的同情,更能引起我們對阻遏者的厭惡和憎恨!
長江不應滿,是儂淚成許
第十九首“相送勞勞渚,長江不應滿,是儂淚成許”與上一首采用同樣的手法來達到同樣的目的,只不過背景不同而已:它不是寫夜晚的相思而是寫白日的相別。勞勞渚,位于南京城東南勞勞山下的大江邊。山上有“勞勞亭”,又叫“臨滄觀”、“望遠樓”,始建于東吳,借用樂府民歌《孔雀東南飛》中“舉手長勞勞,二情同依依”而得名,是著名的送別之地。亭內有李白著名的題詩《勞勞亭》:“天下傷心處,勞勞送客亭。春風知別苦,不遣柳條青”“勞勞”的本意是非常憂傷,成語中就有“勞燕分飛”之說。詩人選擇在勞勞渚送別,本身就有兩重含義:一是古今同悲,“多情自古傷別”,勞勞亭自古就是“天下傷心處”,著名的送別之地;二是暗示內心的憂傷,為下面的夸張做好鋪墊,因為“勞勞”的本意是非常憂傷。至于下面兩句“長江不應滿,是儂淚成許”則是極度的夸張。那位概嘆“多情自古傷別”的宋代詞人柳永在其代表之作《雨霖鈴》的上闋,曾出色地描繪過一對情人在江邊分別的情景:“寒蟬凄切。對長亭晚,驟雨初歇。都門帳飲無緒,留戀處、蘭舟催發。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噎。念去去、千里煙波,暮靄沉沉楚天闊。”詞人通過清秋的暮景,凄切的蟬鳴,不忍離別的執手和不得不別的淚眼,細致地描述了這對情人再離別時分的種種情態,不知打動了古往今來多少讀者,這可以說是寫實手法的勝利!而這首《華山畿》則是浪漫藝術的豐碑。它不再細描別景,細抒別情,而是簡括成一句:“相送勞勞渚”,把重筆放在后面兩句極度的夸張之上。在女主人公看來,長江水為何如此猛漲呢?大概是由于我的淚水太多了吧!這是女主人公的主觀猜測,更是她的藝術夸張。她用這種方式來表達由于離別而產生的無限哀怨。這種浪漫的表達手法,就其所達到的藝術效果來說,并不比《雨霖鈴》的寫實手法遜色。
在語言結構上,它和上面兩首《華山畿》一樣都是雜言,句數不等,字數也不等,并不是南朝樂府“吳聲歌”普遍采用的五言四句,這在“吳聲歌”中算是比較特殊的。但就它自身的結構來看,對仗得又異常工整,如第七首的“淚落枕將浮,身沈被流去”兩句,就是極為工整的對仗。詩人用“淚落”、“身沉”來抒發人的情感,用“枕將浮”和“被流去”來表現物的漂流。而“淚落”是“枕將浮”和“被流去”之因,“枕將浮”和“被流去”又是“淚落”之果。因此無論在構思上,還是結構上都很精巧、我以為南朝樂府中這種整散結合的詩歌形式,長短不齊的外在形式和局部上工整對仗的精巧句式,直接影響了后來唐五代詞的結構和表現形式。
最后想說的是,這首“相送勞勞渚”也使我們再一次聯想到漢樂府《上邪》。在那首民歌中,女主人公用一連串不可能出現的自然現象:“山無陵,江水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來表示兩人的結合不可分離,抒發她那種火山爆發式的熾熱情感。而這首《華山畿》(之十九)則用生活中不可能發生的現象——淚水使得長江溢滿來形容兩人分離所造成的苦痛,抒發她那如江水滾滾而來的憂傷。這兩首詩猶如美玉的兩端,盡管兩者方向相背,角度相反,但對于構成一塊美玉——中國古典詩歌美,都是不可缺少的。
天下傷心處,勞勞送客亭
附:古今樂錄·華山畿陳·釋智匠
《華山畿》者,宋少帝時懊惱一曲,亦變曲也。少帝時,南徐一士子,從華山畿往云陽。見客舍有女子年十八九,悅之無因,遂感心疾。母問其故,具以啟母。母為至華山尋訪,見女具說聞感之因。脫蔽膝令母密置其席下臥之,當已。少日果差。忽舉席見蔽膝而抱持,遂吞食而死。氣欲絕,謂母曰:“葬時車載,從華山度。”母從其意。比至女門,牛不肯前,打拍不動。女曰:“且待須臾。”妝點沐浴,既而出。歌曰:“華山畿,君既為儂死,獨活為誰施?歡若見憐時,棺木為儂開。”棺應聲開,女透入棺,家人叩打,無如之何,乃合葬,呼曰神女冢。
搜神記·吳王小女晉·干寶
吳王夫差小女,名曰紫玉,年十八,才貌俱美。童子韓重,年十九,在道術,女悅之,私交信問,許之為妻。重學于齊、魯之間,臨去,屬其父母,使求婚。王怒,不與女。女結氣死,葬閶門之外。
三年,重歸,詰其父母。父母曰:“大王怒,女結氣死,已葬矣。”重哭泣哀慟,具牲幣往于墓前。玉魂從墓中出,見重,流涕謂曰:“昔爾行之后,令二親從王相求,度必克從大愿,不圖別后遭命,奈何。”玉乃左顧,宛頸而歌曰:“南山有烏,北山張羅。烏既高飛,羅將奈何?意欲從君,讒言恐多。悲結生疾,沒命黃壚。命之不造,冤如之何?羽族之長,名為鳳凰。一日失雄,三年感傷。雖有眾鳥,不為匹雙。故見鄙姿,逢君輝光。身遠心近,何嘗暫忘!”歌畢,唏噓流涕,不能自勝,邀重還冢。重曰:“死生異路,懼有尤愆,不敢從命”。玉曰:“死生異路,吾亦知之。然今一別,永無后期,子將畏我為鬼而禍子乎?欲誠所奉,寧不相信?”重感其言,送之還冢。玉與之飲宴,留之三日三夜,盡夫婦之禮。臨出,取徑寸明珠以送重,曰:“既毀其名,又絕其愿,復何言哉!愿郎自愛。若至吾家,致敬大王”。
重既出,遂詣王,自說其事。王大怒曰:“吾女既死,而重造訛言,以玷穢亡靈。此不過發冢取物,托以鬼神。”趣收重。重走脫,至玉墓所,訴之。玉曰:“無憂,今歸白王。”王妝梳,忽見玉,驚愕悲喜,問曰:“爾緣何生?”玉跪而言曰:“昔諸生韓重來求玉,大王不許。玉名毀義絕,自致身亡。重從遠還,聞玉已死,故赍牲幣,詣冢吊唁。感其篤終,輒與相見,因以珠遺之。不為發冢,愿勿推治。”夫人聞之,出而抱之,玉如煙然。
讀曲歌
打殺長鳴雞,彈去烏臼鳥。
愿得連暝不復曙,一年只一曉。
“讀”或作“獨”,指唱歌時沒有音樂伴奏的清唱,當時叫做“徒歌”。清人納蘭性德《淥水亭雜識》卷二云:“唯人聲而無八音謂之徒歌”。語出南朝宋代顏延之《直東宮答鄭尚書》詩:“跂予旅東館,徒歌屬南墉。”據《晉書·樂志下》:當時樂府中的《子夜歌》、《鳳將雛歌》等“凡此諸曲,始皆徒歌,既而被之管弦。”
關于《讀曲歌》的起源,則有兩種說法,一種出自《宋書·樂志》:“《讀曲歌》者,民間為彭城王義康所作也,其歌云:‘死罪劉領軍,誤殺劉第四”。此說是說民間為被宋文帝劉義隆殺害的彭城王劉義康鳴冤叫屈而作。劉義康(409-451),小字車子,南北朝時期劉宋王朝的宗室,封彭城王。宋武帝劉裕第四子,故《讀曲歌》中稱其為“劉第四”。其兄宋文帝劉義隆即位后,加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元嘉六年(429),征為侍中、都督揚、南徐、兗三州諸軍事、司徒、錄尚書事,領平北將軍、南徐州刺史,入朝與王弘共同執政。內外眾務,斷之己手。為人淺陋不好讀書,驕縱,率心而行,不復存君臣形跡。史稱其“時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次者供御。”從元嘉十六年起,劉義康與文帝嫌隙加深。元嘉二十二年十一月,徐湛之告發太子詹事范曄、孔熙先等密謀擁立義康。于是范曄等以謀反罪被處死刑,劉義康及子女被廢為庶人,徙安成郡。元嘉二十八年北魏拓跋燾的大軍南下,文帝擔心有人奉義康為亂,下令將他誅殺,遣中書舍人嚴龍赍藥賜死。時年四十三,以侯禮葬。這就是《讀曲歌》中所說的“誤殺劉第四”,對于宋文帝來說,當然也不算誤殺。至于詩中所說的“死罪劉領軍”的劉領軍,即領軍將軍劉湛。劉湛字弘仁,南陽涅陽(今河南省鎮平縣南侯集鎮趙河東岸以北一帶)人。撫軍將軍江夏王劉義恭鎮守江陵時,朝廷任命劉湛為使持節、南蠻校尉、任撫軍長史一職,管理所轄州府的事務。當時王弘、王華在朝中主管政事。劉湛認為自己的才能并不在他們之下,認為這次調離朝廷,是王弘等人的有意排斥,心里很不痛快。元嘉八年,召劉湛任太子詹事,加給事中、本州大中正職銜,與殷景仁一道被任用。當時彭城王劉義康獨攬朝政,劉湛過去曾是他的幕僚,于是憑借這一關系傾心巴結劉義康,想借此排斥殷景仁,獨掌政務,因此在劉義康與文帝的矛盾中他站在劉義康一邊,對皇上也就不再有為臣子的禮節。劉湛剛剛回朝時,皇上委以重任,早晚接見,恩賞禮遇十分優厚。到了后期,他煽動劉義康,欺凌朝廷,皇上心中早已與他決裂,但表面上的禮遇仍然不改。元嘉十七年(440),劉湛生母去世。當時皇上與劉義康的矛盾已經很明顯,大禍將起,劉湛也知道已經沒有保全的余地了。等到母喪離職,他對親近的人說:“今年是必定要完結了。已經到窮途末路了,再也沒有指望了,不久大禍就要來臨了。”這年十月,劉湛在獄中被處死,時年四十九歲。民間輿論認為劉湛有野心,無人臣禮,傾心巴結劉義康,這樣的人該殺。但劉義康因謀反罪被廢為庶人,后又被殺,這是冤枉的,所以說“死罪劉領軍,誤殺劉第四”。
另一種說法出自陳·釋智匠的《古今樂錄》:“《讀曲歌》者,元嘉十七年,元后崩,百官不敢作歌聲。或因酒宴,止竊聲讀曲細吟而已。以此為名”。智匠所說的該曲產生年代也是元嘉十七年,但不是殺劉湛一事而是袁后去世。袁后為宋文帝劉義隆的皇后,名齊媯,左光祿大夫袁湛之之女。按封建禮節,國母去世,是要禁止婚嫁喜慶和宴飲活動的。因此官吏們只得飲酒時不敢奏樂,只得小聲地清唱,于是便產生了這種沒有音樂伴奏的“徒歌”。但即使是清唱,恐怕也不會是歡樂的歌聲。所以上述兩種說法都含有對死者的哀悼之意,因此曲調特別哀婉凄厲,一些民間歌者藉此來表現凄苦的戀情。郭茂倩《樂府詩集》共收《讀曲歌》八十九首,在“吳聲歌”各曲中數量最多,可見當時受歡迎的程度。
“打殺長鳴雞”是《讀曲歌》第五十五首。它的選題和表達方式在《讀曲歌》中甚至在南朝樂府中都是獨具一格的。如前所述,南朝樂府中表達戀情的詩章,多是女性抒發不能結合的凄苦、離別的憂傷,如前面幾篇提到的:“始欲識郎時,兩心望如一。理絲入殘機,何悟不成匹。”(《子夜歌》之七);“得郎日嗣音,令人不可睹。熊膽磨作墨,書來字字苦。”(《子夜歌》之十六)等皆是如此。但這首《讀曲歌》表現的卻是一個沉浸在歡會之中的一個幸福的女性,這個處于幸福之中的女性的愿望和心理感受也是很獨特的:詩人用幾乎失真的夸張手法,來表達她對幸福的進一步祈求,這就是:“打殺長鳴雞,彈去烏臼鳥。愿得連暝不復曙,一年都一曉”。“長鳴雞”是指長啼的公雞。公雞有個特性,天亮時就會從長啼。過去沒有時鐘,人們就用牠來報曉起床。俗話“雞鳴早晴天,催人快下田”。“烏桕鳥”,烏桕樹上的小鳥。烏桕樹,一種生長于我國黃河以南地區的高大落葉喬木。霜降過后,還未等楓葉變紅,它已經開始染色了,故而宋代林和清有詩曰:“巾子峰頭烏桕樹,微霜未落已先紅。”而且樹葉變紅的過程也有特色:是由綠色漸漸變成紅色、紫色、黃色,橙色,再加上它的果殼呈烏色,果實又呈白色,小鳥特別喜歡啄食。所以整棵樹顯得色彩斑斕,紅彤彤,金燦燦,在陽光下如跳動的火焰,神奇飄逸。
烏桕樹·小鳥
南朝又有詩曰:“紅葉秋山烏桕樹,回風折卻小蠻腰。”魯迅在描寫紹興一帶風物的作品如《故鄉》、《社戲》等也經常提到這種落葉喬木。
烏桕樹和長鳴雞都是江南民間常見之景,也是許多這首《讀曲歌》以此景色開篇,也帶有江南風物的典型特征。很多詩人也都選取晨雞和鳥啼作為早起或晴日特有之景,如“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溫庭筠《商山早行》);““鳥雀呼晴,侵曉窺檐語”(周邦彥《蘇幕遮》)。但是,詩中的這位女主人公似乎并不喜歡這只才長鳴雞和樹上的烏桕鳥,而要把它們“打殺”、“彈去”,因為他們的啼叫意味著黑夜的結束、清晨的到來,而這位沉浸在歡會中的女子覺得黑夜太短暫了、白日的到來太早了。夜的長短,本來是個恒量,但由于人們心態的不同,夜的長短也就成了變數,它會變得出奇的短和漫漫的長,其規律則是“歡娛嫌夜短,憂愁恨時長”。對于一個離婦或陷入相思中的女子來說,夜往往漫長的沒有盡頭:“憂人不能眠,耿耿夜何長”,這是漢樂府中離婦心中的夜;“心有雙思網,中有千千結。夜過也,東方未白凝殘月”,這是五代詞人輾轉難眠少女心中的夜。但對于《讀曲歌》中這位沉浸在幸福之中的女子來說,此夜卻太短暫了。他們的結合,是否經過坎坷,有過同阻遏勢力的抗爭,我們不得而知;是否有過誤解、有個反復,有過漫長的等待,我們也無從知曉。但我們從女主人公對此夜的結合如此珍惜,看來這幸福時刻的到來是極為不易的,以至要“打殺長鳴雞,彈去烏桕鳥”,因為雞的長鳴,鳥的晨啼,宣告著夜的結束、晨的到來,也就意味著這場歡會的結束。盡管夜的結束,時光的流逝是不可阻攔的,但這位一心要留住情人、留住黑夜的女子卻不管不顧,她希望黑夜連著黑夜,永遠沒有白天。要有的話,也是一年只有一個早晨——“愿得連暝不復曙,一年只一曉”。由于她不愿去正視時光流逝的不可避免,卻怪罪于報告這一客觀規律的晨雞和啼鳥,寧愿相信這是黑夜的結束是雞鳴、鳥啼的結果,所以她要殺雞趕鳥,以為這樣就可以與情人長久廝守、永不分離了。應當說,這種心理是很奇特的,因為女主人實際上也不會相信只要趕走鳥、殺死雞,黑夜就會永遠繼續下去,太陽就不會升起。這只不過反映了理智和情感的矛盾,既是對女主人公真摯純情的夸張,也真實地反映了一位沉溺于情網之中的女性所特有的迷戀。可見詩人對此時此刻、此人此情的處理手法是相當出奇也相當高妙的。因為讀過此詩,在獲得情感愉悅和滿足后,我們也會產生這樣一個疑問:這位女主人公對此夜晚如此沉溺迷戀,難道白天就不能夠相守了嗎?這恐怕不像有的人所理解的那樣意在表現色情,恐怕還有更深層的原因。我想,可能有以下兩個因素:第一,這可能是個偷偷的約會,兩人不能公開見面,只能借著黑夜的掩護相會,所以她希望“連暝不復曙”,永遠是黑夜,永遠和情人在一起;第二,南朝民歌中,城市下層婦女的戀愛對象往往是市民、藝人、商人或貴族,由于他們的職業特點或層級懸殊,其結合基礎是很不牢靠的,這造成了女性的不穩定感,即使在相會之際、情濃之時,也會產生顧慮,前面篇章中談到的《團扇歌》、《子夜歌》中都有這種時代情緒的反映。所以《讀曲歌》中這位女性在與情人歡會時,希望時間停留在這個節點上,將短暫化為永恒。因此,她不希望天亮,所以才要打殺報曉的長鳴雞,彈去啼晨的烏桕鳥。以上兩點,都反映了南朝婦女心理上的重負,也體現出南朝情歌獨有的特質!這也大概是這首《讀曲歌》的弦外之音吧!
唐代詩人金昌緒有首情節與此相類的絕句,其中寫道:“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這位女性也希望夜能繼續,夢能繼續,也同樣要打走啼晨的鳥兒。但詩人卻給這首絕句題了個意味深長的題目——“春怨”。也就是說,主人公希望“連暝不復曙”的原因卻是“怨”,這首模擬《讀曲歌》的唐人之作也可以作為這首歌的一個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