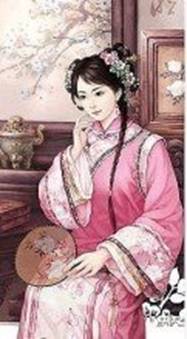漢魏南北朝樂(lè)府清賞之十八
南朝樂(lè)府·吳聲歌
歡聞變歌(之二)
歡來(lái)不徐徐,陽(yáng)窗都銳戶。
耶婆尚未眠,肝心如推櫓。
《歡聞變歌》是《歡聞歌》的變聲。據(jù)南朝陳代釋智匠《古今樂(lè)錄》云:此調(diào)制于晉穆帝升平初年(357),每曲結(jié)束時(shí)則高呼“歡聞不?”,以此作為尾聲,后來(lái)就用此作為取名曰《歡聞歌》。到了升平中期(359年左右)一些童子改此詞而歌,開(kāi)頭是“阿子聞”,尾聲則高呼“阿子聞汝不?”。沒(méi)多久,晉穆帝死,褚太后哭歌“阿子聞汝不?”,聲調(diào)凄苦,因以名之,《歡聞變歌》因此得名。不過(guò)到了南朝樂(lè)府中,《歡聞變歌》已不是喪歌而變成了情歌,僅取其哀苦之調(diào)來(lái)表達(dá)相思的怨嘆和相別的哀苦。宋人郭茂倩的《樂(lè)府詩(shī)集》收《歡聞變歌》六首,這是第二首。
南朝樂(lè)府常以巧妙地比喻以及諧音、雙關(guān)等修辭手法,作為它表情達(dá)意的主要手段:詩(shī)中常用芙蓉來(lái)比喻青春美好,用霜下草來(lái)比喻青春的消逝(《子夜歌》);用落入井中的飛鳥(niǎo)和織不成布的殘絲來(lái)比喻愛(ài)情受挫(《讀曲歌》)。至于以“絲”諧“思”、以“蓮”諧“憐”、以“藕”諧“偶”,以“棋”諧“期”,在《子夜歌》、《大子夜歌》、《讀曲歌》中則比比皆是,但這首《歡聞變歌》倒是獨(dú)樹(shù)一幟,它撇開(kāi)南朝樂(lè)府中同類作品常用的比喻、雙關(guān)等手法,直接表達(dá)自己的情感:天都快亮了,赴約的情郎還遲遲未來(lái),這讓她既焦急又擔(dān)心。媽媽也真是的,都啥時(shí)候了居然還沒(méi)有入睡,真讓人不安和心煩!
這種直接抒情的方法,表面上看似乎很平直,實(shí)際上是經(jīng)過(guò)精心處理的。在五言絕句這個(gè)五言四句這個(gè)狹小的天地里,要想敘事、抒情,最好的方法就是通過(guò)一個(gè)特定的鏡頭,集中抒發(fā)某個(gè)瞬時(shí)特定的情感。《子夜歌》之三十三“夜長(zhǎng)不得眠”;之九“今夕歡已別”等皆是如此。這首歌也不例外。所不同的是:這個(gè)特寫(xiě)鏡頭的背景似乎比其它同類型的詩(shī)歌更富有戲劇性,作為典型時(shí)刻的特定情感也遷延等更加漫長(zhǎng)。他以不是一般的特寫(xiě)鏡頭,簡(jiǎn)直是一個(gè)母女之間的暗中互相較量的獨(dú)幕劇!開(kāi)頭兩句“歡來(lái)不徐徐,陽(yáng)窗都銳戶”看似一句女主人公的獨(dú)白,訴說(shuō)她等候情郎的到來(lái),幾乎等了整整一夜。把情人稱作“歡”,固然是南朝樂(lè)府的通用手法,但也透露出自己的情感。“徐徐”是行走的從容之態(tài),她懸想著情郎徐徐而來(lái),但每次都落了空。“陽(yáng)窗都銳戶”是個(gè)緊縮句,指天都亮了,陽(yáng)光已穿透窗戶,也就是說(shuō)等候情郎赴約等了整整一夜。整整一夜的盼望和等待,這位女主人公是在一種什么樣的心情下度過(guò)可想而知。明代有首山歌描繪一位女性在約會(huì)中久等的心情是:“約郎約在月上時(shí),等郎等到月偏西。莫非是儂處山低月上早,還是郎處山高月上遲”(《山歌·劈破玉》)。這位山歌中的女性也幾乎是等了一夜。即使如此,她也沒(méi)有朝壞處想,而是離奇地猜測(cè):“莫非是郎處山高月上遲”,千方百計(jì)為情郎開(kāi)脫(當(dāng)然也是為了欺騙和安慰自己)。但在這首《歡聞變歌》中,無(wú)論原因和處理手法都不同于這首明代山歌,也不同于南朝樂(lè)府中同類題材。
首先,它的主題不是譴責(zé)男方負(fù)心和背盟。盡管這種譴責(zé)或擔(dān)心在南朝樂(lè)府中多有表現(xiàn),如“常慮有貳意,歡今果不齊。枯魚(yú)就濁水,長(zhǎng)與清流乖”(《子夜歌》之十八),“我與歡相憐,約誓底言者?常嘆負(fù)情人,郎今果成詐。”(《懊儂曲》),這是譴責(zé)男方的負(fù)心和背盟;“攬枕北窗臥,郎來(lái)就儂嬉。小喜多唐突,相憐能幾時(shí)”(《子夜歌》之十三),“今夕已歡別,合會(huì)在何時(shí)?明燈照空局,悠然未有期”(《子夜歌》之七)這是男方的毀約和背盟擔(dān)心。但這首《歡聞變歌》的主題并非是譴責(zé)或擔(dān)心男方的失約或變心,而是這位姑娘的母親沒(méi)有入睡,情郎不敢前來(lái)赴約。因此她不必像明代山歌那樣為了欺騙和安慰自己而千方百計(jì)為情郎開(kāi)脫,更不會(huì)像其它南朝樂(lè)府類似題材那樣去譴責(zé)和埋怨情郎。而是把全部埋怨發(fā)泄在她母親身上:“耶婆尚未眠,肝心如推櫓”!“耶婆”即“阿婆”,“婆”在此專指母親。北朝樂(lè)府《折楊柳歌》歌云:“阿婆不嫁女,哪得孫兒抱”亦是如此。這兩句是此詩(shī)的點(diǎn)睛之筆,內(nèi)涵十分豐富:它既點(diǎn)破情郎未能赴約的原因,不是情郎毀約而是母親未睡,他無(wú)法前來(lái)赴約,顯示出這首詩(shī)不同于其他南朝樂(lè)府的獨(dú)特主題;同時(shí)也暗示這位女主人與情郎的相約是封建道德規(guī)范所不允許的,只能背著封建家長(zhǎng)進(jìn)行。既然老母未睡,情郎當(dāng)然不能前來(lái)赴約,女主人公也不敢讓他前來(lái)赴約。
其次,這短短兩句,卻寫(xiě)出人物極其復(fù)雜的心理活動(dòng),簡(jiǎn)直是一出獨(dú)幕劇:老母到天快亮?xí)r仍然未眠,情郎到天快亮?xí)r仍然不能前來(lái),這位姑娘自然也是一夜如熱鍋螞蟻,徘徊不停、焦灼難耐。詩(shī)人用了個(gè)比喻:“肝心如推櫓”。“櫓”是劃船工具,安放在船尾,通過(guò)左右搖擺“推櫓”,使船前行。這位姑娘此時(shí)心如推櫓搖擺不停,這個(gè)比喻不但準(zhǔn)確表現(xiàn)出女主人公此時(shí)的焦灼、忐忑、祈求、希冀等種種復(fù)雜的情感和思緒;也可看出這是位船民的女兒或出身與下層市民,不會(huì)是貴族千金,否則,不會(huì)采用“推櫓”這個(gè)比喻的。這兩句更為出彩的是它富有戲劇性,暗暗點(diǎn)破母女間進(jìn)行的一場(chǎng)無(wú)聲的較量。“耶婆尚未眠”應(yīng)當(dāng)說(shuō)是有兩種可能的:一種是老年人瞌睡少,難以入眠,所以到天快亮?xí)r“尚未眠”;另一種可能是老母似乎有所覺(jué)察,有意提防,久久未睡。從這首詩(shī)所作的暗示來(lái)看,后一種可能性更大。這兩句把母女間各懷心思又互不道破的微妙之狀寫(xiě)的相當(dāng)生動(dòng),意味深長(zhǎng)。所以我們說(shuō),這首歌表面上簡(jiǎn)單直白,實(shí)際上經(jīng)過(guò)精心處理,含蘊(yùn)是很豐厚的。
最后想提及的是,男女之間約會(huì)受到父母的阻隔,表現(xiàn)其間的悲愴或擔(dān)憂,中國(guó)歷代民歌中都有出色的詩(shī)章,如《詩(shī)經(jīng)》中的《柏舟》,一位姑娘愛(ài)上了一位髧彼兩髦的漂亮小伙子,但母親不同意,她只好悲愴地高呼:“之死矢靡惹。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漢樂(lè)府《有所思》中女主人回憶當(dāng)年與情人約會(huì)時(shí),提心吊膽的情形:“雞鳴狗吠,兄嫂當(dāng)知之”。這都說(shuō)明,家長(zhǎng)的不體諒所造成的阻隔,以及支撐這個(gè)家長(zhǎng)制的封建制度,一直是封建時(shí)代青年男女相戀相愛(ài)一個(gè)不可逾越的障礙,也一直是中國(guó)古代民歌中詠歌不衰的一個(gè)永恒主題。這是這首《歡聞變歌》在前人多方開(kāi)拓、難乎為繼的情況下,又獨(dú)辟蹊徑,以這種表面直白、實(shí)則含蘊(yùn)豐厚的內(nèi)容,以及用這母女間各懷心思又互不道破的獨(dú)幕劇形式加以表現(xiàn),確實(shí)是獨(dú)具一格,具有開(kāi)創(chuàng)性意義!
耶婆尚未眠,肝心如推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