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數(shù)我的平生知交良師益友很多,獲益匪淺,然細(xì)想起來,惟有鄭天挺先生是我的畏友,而且是能知道我、最能幫助我和愛護(hù)我的同志。我這個(gè)人的為人是大大咧咧的,說起話來,不加思索,信口而出;做起事來,粗枝大葉;寫起文章來,隨所欲言,錯(cuò)誤難免,凡是知道我的人,都知道我有這些毛病,我也深引以為恨事。我還記得五十年代初期,鄭先生和我同在天津南開大學(xué)任教,我的教學(xué)效果并不理想,有時(shí)使同學(xué)們提出了意見。這時(shí)正值教改高潮,須要認(rèn)真?zhèn)湔n,要把每節(jié)課的主題、內(nèi)容,讓同學(xué)聽得明了,方可取得成效。每寫完一章講稿,須要試講一次,由教務(wù)處、歷史系負(fù)責(zé)同志,到我家里親自來聽。我本是性情爽快隨隨便便的一個(gè)人,說錯(cuò)了話,連自己還不知道,這時(shí)候,我真是如坐針氈,顧慮重重,不知怎樣講才好。鄭先生總是叫我不要著急發(fā)慌,叫我坐下來吸一口紙煙,慢慢地談。他坐在一旁,慢慢地聽著,講完之后,別位同志提出意見,鄭先生總是不著一語;人散之后,他才把我錯(cuò)誤的地方告訴給我。后來想起來,我的體會(huì)是,凡是做一件事情,非經(jīng)一段訓(xùn)練不可,而且必需虛心受教,才能有所長(zhǎng)進(jìn)。后來我到各地方去講學(xué),每遇大場(chǎng)合的集會(huì),發(fā)言不致于發(fā)生過大的錯(cuò)誤,還有人說我到老年來,思想清楚,說起話來還不至胡言亂語,這都是受了鄭先生的督促所致。還有,我雖然多年從事教學(xué)和科學(xué)研究,有時(shí)也辦理過采購(gòu)書籍的事務(wù),鄭先生就經(jīng)常告誡我要公私分明。聽說鄭先生在西南聯(lián)大任總務(wù)長(zhǎng)時(shí),當(dāng)時(shí)是時(shí)局變動(dòng)時(shí)期,米珠薪桂,物價(jià)一日萬變。先生是奉公守法,廉潔自守,克己利人,一絲不茍。同時(shí)我還有一位老前輩徐森玉先生,他以平易近人的態(tài)度,對(duì)我談不要占書商的便宜,致形成被動(dòng),拔不出腳來,以至于后患無窮。他們的這些話,使我聽了受到很大教育。回想起來,這都不能忘鄭先生和一些老前輩的語重心長(zhǎng),幫助我的好處。
鄭先生是著名明清史的史學(xué)家,學(xué)問淵博,思想極有系統(tǒng),他除了研究明清史以外,學(xué)問涉及的方面很廣,凡閱書泛濫所及,都寫有分類的卡片,講起書來,旁征博引,是極其有條理的。在明清史學(xué)當(dāng)中,尤其熟于滿洲的興起,及清初未入關(guān)前的社會(huì)性質(zhì),有其獨(dú)到的見解和發(fā)明。就我個(gè)人所感覺到的是:先生不僅是并世著名的學(xué)者,而且是兼教育家。以先生的器量恢宏,和藹可親,能夠領(lǐng)導(dǎo)群倫,只要來學(xué),無不循循善誘,如坐春風(fēng)化雨之中,凡是聽他課的人,無不各有所獲,受到益處而去,培養(yǎng)了一批后進(jìn)有用的人才,為社會(huì)主義社會(huì),建設(shè)四化,創(chuàng)造了有利的條件。他真可以說是一位卓越的學(xué)者而兼教育行政家。鄭先生是以學(xué)術(shù)事業(yè)的專家來做領(lǐng)導(dǎo)行政職務(wù),所以處理教學(xué)和科學(xué)研究工作,推行起來,就極見成效了。鄭先生在學(xué)術(shù)上有深厚的造詣,向以謙虛謹(jǐn)慎的態(tài)度,不肯輕于下筆著書,而是以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從事于教學(xué)和研究的工作。做起事來,極為認(rèn)真,這是人所共知,“有口皆碑”的。我是聽過他講課的,我看見他授課之前搜輯了大批資料,寫成了成萬張卡片,到講課的時(shí)候,將這些卡片,從事編排,持之有故學(xué)有實(shí)據(jù),寫成了教學(xué)的提綱和講稿,講起來?xiàng)l理非常清楚,從容不迫,委婉動(dòng)人,我就是得到實(shí)惠的一個(gè)人。同時(shí)他為了教學(xué)工作,曾勤勤懇懇地為大專院校編寫教材,凡是高教部所制定有關(guān)歷史課程參考資料,和校點(diǎn)《廿四史》中的《明史》的工作,都是由先生精心主持的。他在南開大學(xué)時(shí)設(shè)立了明清史研究室,領(lǐng)導(dǎo)有志于研究明清史的同志們,做科研工作,編寫論文,發(fā)表于世,卓有成效。他還指導(dǎo)同志們校點(diǎn)有用的書籍,如蔣良騏《東華錄》等書,其沾惠后學(xué),受益非淺。他著書立說,以教誨來者,從事于網(wǎng)羅舊聞,整理出有系統(tǒng)的史料,提供了為作科學(xué)的研究的專門的科研事業(yè),以傳示后人。今先生往矣,問業(yè)無人,真是感慨系之!
我認(rèn)為明清史是在近古史中最主要的課題,凡研究近代事務(wù)的起源,都與明清史書極有關(guān)系,這項(xiàng)事業(yè),極為國(guó)人和國(guó)際學(xué)術(shù)界所重視,是一門熱門的科學(xué)。可是由于為時(shí)較近,又由于清代的禁網(wǎng)森嚴(yán),鉗制了人民的思想,明清時(shí)代的著述,湮沒而不彰的,實(shí)不在少數(shù)。這和研究考古學(xué)一樣,正在要從事于大量的發(fā)掘,今后一定會(huì)發(fā)現(xiàn)不少罕見而有用的精湛的著述,和文物中的珍品。我雖老矣,仍愿追隨其后,稍盡棉薄,愿與諸位同志共相勉之。一九八二年三月十二日識(shí)于北京團(tuán)結(jié)湖畔之瓜蒂盦。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我從曹貴林同志處得知先生病逝,益覺悲痛,懷念之心情不能已,因隨筆成詩(shī)一首,以為悼念,詩(shī)曰:
猶記華北淪陷日,乘槎浮海結(jié)同心;
韭菜園中獲聚首,八里臺(tái)畔倍情親。
日月不居驚歲月,雞鳴風(fēng)雨大星沉;
方期追隨函丈后,噩耗傳來恐未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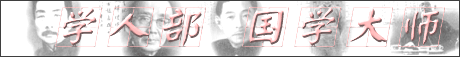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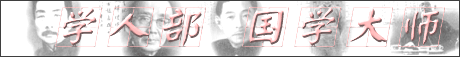

mailto:guoxue@guoxue.com
![]() 010-68900123
010-68900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