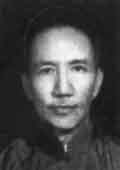
陳寅恪
生卒:1890~1969
年代:民國
籍貫:江西修水
簡評:歷史學家
二、學術成就
陳寅恪先生畢生從事學術研究和著述事業,他的研究范圍非常廣泛,包括歷史學、宗教學、語言學、人類學、校勘學、文字學等學科。其中尤以魏晉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古史、唐代和清代文學以及佛教典籍的研究著稱于世。他的學術著作被譽為“劃時代的意義”。被尊為一代史學宗師,在國內外學術界享有很高威望。
蔣天樞先生概括陳寅恪先生治學特色約有四端:
一、?以淑世為懷。篤信白居易“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與元九書》)之旨;
二、?探索自由之義諦。見《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及《論再生緣》;
三、?珍惜傳統歷史文化。此意則文詩中隨地見之,而“迂叟當年感慨深,貞元醉漢托微吟”、“東皇若教柔枝起,老大猶能秉燭游”之句,尤為澹蕩移情;
四、?“續命河汾”之向往。此雖僅于贈葉遐庵詩、《贈蔣秉南序》中偶一發之,實往來心目中之要事。
史學領域
治史觀點:“文化超越于政治、經濟、民族等等之上。”在悼念王國維的有關詩文中,陳先生的這一觀點有集中反映。如《挽王靜安先生》詩有云:“文化神州喪一身。”挽詞序云:“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兩年以后所撰《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進一步闡述了文化超越政治,真理必須獨立自由的道理:“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于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感望?先生之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論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所以,陳先生在挽詞中雖有“一死從容殉大倫”、“回思寒夜話明昌,相對南冠氣數行”,以及“他年清史求忠跡,一吊前朝萬壽山”之類的句子,表面上是在哀悼作為清室遺老的王靜安,實際上,王靜安之死有其更深刻的原因,不是一姓之興亡所造成的。陳先生的這種文化至上的觀點始終未變。
余英時先生在《陳寅恪史學三變》中把陳先生的史學成就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923-1932),佛典譯本及其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和唐以來中亞及西北外族與漢民族之交涉。俞大維在《懷念陳寅恪先生》中記述:“寅恪先生又常說他研究中西一般關系,尤其是文化的交流佛學的傳播、以及中亞史地,他深受西洋學者的影響……,其他邊疆及西域文字,寅恪先生在中國學人中是首屈一指的。除梵文外,他曾學過蒙文、藏文、波斯文及土耳其文……茲以元史為例略作說明。”
第二階段(1932-1949),魏晉及隋唐的研究。從三十年代初期,陳氏史學逐漸轉向第二階段,開辟魏晉至隋唐的研究領域。1935年他撰《西域人華化考序》,說:“寅恪不敢觀三代兩漢之書,而喜談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這是他第二階段史學研究的重心。民族與文化的分野尤適于解釋唐帝國統一和分裂的歷史。故他在1936年讀韓愈《送董邵南序》眉識及1941年《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特別標明此義。
第三階段(1949以后):心史。
陳寅恪在《馮友蘭哲學史審查報告中》說“寅恪平生為不古不今之學,思想囿于咸豐同治之世。議論近乎曾湘鄉、張南皮之間,”。關于“不今不古之學”,汪榮祖在《史家陳寅恪傳》中解釋為中國歷史的中古一段,即魏晉到隋唐這一時期。所以,學術界一般公認,陳寅恪史學方面的最大成就還是中古史研究,陳氏史學并非如大多數學者所論的繼承乾嘉考據,而是直接繼承宋賢史學并有所發展。陳寅恪史學思想可分為求真實供鑒誡、民族與文化、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貶斥勢力尊崇氣節及重視社會經濟的重大作用等。
語言與文學、宗教領域
詩史互證問題、漢語特點問題、宗教與文學關系問題、佛教進入中國及與小說、彈詞等題材演變發展問題、中國古典小說之結構問題等。陳先生開辟了運用文學作品闡述歷史問題,又用歷史知識解釋文學的嶄新途徑。陳先生淵博的梵文以及滿蒙藏文知識使他的學問具備另一特色。他不僅利用漢文以外的語言文字從對音和釋義來考察漢文典籍、史書與詩文,還探索中國與印度在宗教思想和以及文章體裁上的關系和影響。樹立了如何深入研究文化交流和比較文學的光輝典范。比如《蒙古源流箋證》由張爾田先生修訂時,大都根據了陳先生用梵藏文字勘校所得的成果。
著作的出版
陳寅恪先生早年多發表學術論文,單本的學術著作其生前出版的有三種,即1943年重慶商務初版《唐代政治史論述稿》及1944重慶商務初版《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兩種皆為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之專刊,1945重慶再版,抗戰勝利后,1946年商務印書館又在上海重印,是為上海初版。
1946年商務初版《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另《唐代政治史論述稿》除書名外都封面都與此同。第三種為《元白詩箋證稿》,1950年11月嶺南大學文化研究室初版線裝本。
1955年,經陳寅恪先生校正錯誤,增補脫漏的《元白詩箋證稿》由北京文學古籍出版社平裝出版,初版3000冊,1958年,作者再次修訂之后交由中華書局出版,初版800冊,1962年二印1000冊。《元白詩箋證稿》之1959年中華書局版,并不是北京中華書局而是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即上海古籍出版社之前身,自1958年開始,中華上編就已經開始約請身在嶺南的陳寅恪先生將其有關古典文學的論著編集以便出版成書,1958年陳先生致信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有云:
負責同志:?
昨接尊處1958年9月2日函“函詢論文集交稿日期由”。拙著擬名為“金明館叢稿初編”,若無特別事故,大約可在1959年2月以后8月以前交稿。專復,此致敬禮。
陳寅恪1958年9月6日
1961年陳先生致信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云:
負責同志:???????
來函敬悉。寅恪現正草錢柳因緣詩釋證,尚未完稿,擬一氣呵成,再整理《金明館叢稿初編》。年來舊病時發,工作進行遲緩,想必能鑒諒也。此復,并致敬禮。
陳寅恪1961年9月2日
這里的“錢柳因緣詩釋證”,正是后來的《柳如是別傳》,此書于1954年開始撰稿,1964年完成,也正是出于中華上編的約請,不過時局已不同,陳寅恪先生1962致信云:
上海編輯所負責同志:
來函并約稿合同四份均收悉。披閱應共同遵守各條:(甲)約稿第一條中之第二目,于拙著中所引書一一注出頁數及出版者和出版年月等,皆不能辦到。又拙著中故意雜用名、字、別號。人名如錢謙益、受之、牧齋、東澗、聚沙居士等。地名有時用虞山,有時用常熟等,前后不同,以免重復,且可增加文字之美觀。故不能同意。(乙)拙稿不愿意接受出版者之修改或補充意見。故第二條完全不能同意。(丙)拙稿尚未完畢,交稿日期自不能預定,字數更無從計算。故此兩項亦不能填寫。
因此將約稿合同四份寄還,請查收。總之,尊處校對精審,本愿交付刊行。但有諸種滯礙,未敢率爾簽定。儻能將上列諸項取消,則可再加考慮也。專復,此致,敬禮。
陳寅恪 一九六二 五 十四?
《柳如是別傳》由此擱淺,不過陳寅恪先生還是將《金明館叢稿初編》稿件寄給中華上編,收文章二十篇。《金明館叢稿初編》自序云:
此舊稿不拘作成年月先后,亦不論其內容性質,但隨手便利,略加補正,寫成清本,即付梓人,以免再度散失,殊不足言著述也。一九六三年歲次癸卯陳寅恪識于廣州金明館。
中華上編接稿后,即由梅林、金性堯二編輯先后審讀,之后由二人分出審讀報告,就稿件中涉及少數民族稱呼和鄰國關系等問題提出處理意見。中華上編領導反復審讀后,決定報請上海市出版局批準出版,時為1966年2月。嗣后“大革命”開始,一切遂告停止(詳見高克勤回憶專文)。
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成立,不久即始著手籌劃出版陳寅恪文集,時李俊民為上古社長,魏同賢同志專門負責編務,特別約請陳氏弟子復旦大學蔣天樞先生整理,陳寅恪先生生前即把自己的諸多稿件交付蔣天樞先生委托其整理,1977年,蔣先生將《元白詩箋證稿》的第三次修訂本交給出版社刊印。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三次修訂版《元白詩箋證稿》。1982年2月,包括《寒柳堂集》、《金明館叢稿初編》、《金明館叢稿二編》、《柳如是別傳》、《元白詩箋證稿》、《唐代政治史論述稿》、《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及蔣天樞先生為其師所撰《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一冊,全套七種九冊陸續出齊。
蔣天樞先生對其師極為尊敬,復旦為海上學林重鎮,多知名教授,一次復旦會議,中文系主任朱東潤先生大致有言:“陳寅恪先生學問了不起,不過為晚年為柳如是這樣的人作傳太不值得。”同為復旦教授的蔣天樞先生當即拂袖而去以捍護師道,整理陳寅恪先生遺稿更是嘔心瀝血,1988年,蔣天樞去世,與蔣同為清華研究院畢業生的姜亮夫先生有唁電云:“義寧陳寅恪先生全集是您收集、編纂、考訂,是我們同學中最大的成就者。”蔣天樞先生整理陳寅恪先生遺稿時可謂盡心盡責,另外,某些地方也并不是完全不作改動,由此轉入本篇之重點。
???????????????????????????
此信(一九六二年五月十四日與上海編輯所信)其他幾條暫且不論,單說第三條,蔣云:
《元白詩箋證稿》里的“周一良”處五字,當時曾同您講,是否改成四個字,后來想,改動,總不太妥。是否只把“一良”兩字易為“某某”,或者易為兩個□□,這樣,五個字的地位仍可照舊。
周一良先生也是一代大家,也是陳寅恪先生的學生,要領會上文之意思,還得有所交待。陳寅恪先生所撰之《魏書司馬睿傳江東民族條釋證及推論》有前言云:
盧溝橋事變前,寅恪寓北平清華園,周一良君自南京雞鳴寺往復通函,討論南朝疆域內氏族問題。其后周君著一論文,題曰“南朝境內之各種人及政府對待之政策”,載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七本第四分者是也。此文寅恪初未見,數年之后流轉至香港,始獲讀之,深為傾服。寅恪往歲讀南北朝史,關于民族問題,偶有所見,輒識于書冊之眉端,前后積至如(若)干條,而道經越南,途中遺失,然舊所記者多為周文所已言,且周文之精審更勝于曩日之鄙見,故舊稿之失殊不足惜。惟憶有數事,大抵無關宏旨,或屬可疑性質,殆為周君所不取,因而未載入其大著。旅中無聊,隨筆錄之,以用此篇,實用竊道家人棄我取之義,非敢謂是以補周文之闕遺也。憶當與周君往復商討之時,猶能從容閑暇,析疑論學。此日回思,可謂太平盛世。今則巨浸稽天,莫知所屆。周君又遠適北美,書郵阻隔,商榷無從。搦管和墨,不禁涕泗之泫然也。一千九百四十二年九月九日陳寅恪記于桂林良豐雁山別墅。
《魏書司馬睿》一文收入《金明館叢稿初編》,不過上面的這段話并沒有正文一同收入,周一良先生晚年回憶:
蔣天樞先生編陳先生全集,所收江東民族條釋證文中,刪去了此節,這當然不可能是蔣先生自作主張,定是本陳先生意旨。我看到全集后,不假思索,立即理解陳先生的用意。陳先生為文遣詞用字都極考究,晚年詩文寄慨之深,尤為嚴謹。對于舊作的增刪改訂,必有所為。刪去此節,正是目我為‘曲學阿世’(《贈蔣秉南序》中語),未免遺憾,因而不愿存此痕跡。
令周一良先生自責不已的是其“梁效”經歷,“梁效”為四人幫御用寫作班,1978年后遭人唾棄,不過陳寅恪先生已于1969年含冤離世,《魏書司馬睿》一文前言的刪除當蔣天樞先生所為,上海古籍版陳寅恪文集之《元白詩箋證稿》第158頁有“周某某先生謂齊東昏侯善作擔幢之戲”(本朱在融匯與貫通之說北朝篇中,有人即有提醒周先生所言此條,),即是改動的痕跡,而第256頁則仍有“周一良先生”,或蔣天樞先生遺漏。(此亦詳見高克勤之《陳寅恪文集》出版述略)
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出版了陳寅恪文集七種九冊之后,還雙色套印了《唐代政治史論述稿》手稿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初版精裝2000冊,近年有據此影印重印本。陳寅恪先生手跡另外尚有1989年《陳寅恪讀書札記——舊唐書新唐書之部》及1992年之《陳寅恪史學論文選集》。《陳寅恪讀書札記——舊唐書新唐書之部》初版3000冊,《陳寅恪史學論文選集》初版4000冊。至此陳寅恪先生的著作大致完備,以后三聯十三種十四冊《陳寅恪集》都是在上海古籍版基礎上再整理出版的(三聯于五十年代單冊出版過《唐代政治史論述稿》與《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此兩種與三聯《陳寅恪集》書影常見,故此不再詳列)。上海古籍版《陳寅恪文集》分精裝平裝兩種,精裝一般都為1700冊,平裝印數多為4000冊,各種都有二印,早年常見,今非昔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