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秦漢刑制的演變
第一節(jié) 先秦刑制蠡測(cè)
就文獻(xiàn)記載而言,早在夏代就已用"五刑"以懲治罪犯。所謂"五刑",即大辟、臏(刖)、宮、劓、墨(黥)五種刑罰。除"大辟"為死刑而外,其余四種均為肉刑。但是關(guān)于夏代的資料流傳下來(lái)的很少,且為春秋、戰(zhàn)國(guó)時(shí)人的記述,不盡可信。殷墟甲骨卜辭的發(fā)現(xiàn),證明至遲在殷商時(shí)期,"五刑"的刑名已大體具備
。西周繼承了這一刑制,并加以完善,形成"九刑"。據(jù)《漢書(shū)·刑法志》"周有亂政,而作《九刑》"注引韋昭曰:"九刑"即"謂正刑五,及流、贖、鞭、撲也"。但流、贖、鞭、撲僅作為五刑的補(bǔ)充。《尚書(shū)·舜典》曰:"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撲作教刑,金作贖刑",就是說(shuō)的這種情況。《舜典》屬偽古文,可以不論,但五刑作為西周時(shí)期的"正刑",應(yīng)該是沒(méi)有疑問(wèn)的。西周夷、厲時(shí)期的《匜》銘文記錄了這樣一個(gè)案例
:小貴族牧牛與其上司爭(zhēng)訟五名奴隸而敗訴,伯揚(yáng)父的判決詞曰:"我義(宜)(鞭)女(汝)千,女(汝)。今我(赦)女(汝),義(宜)(鞭)女(汝)千,黜女(汝)。今大(赦)女(汝),(鞭)女(汝)五百,罰女(汝)三百寽(鋝)。"""同"幭",通"幪",《方言》:"幪,巾也。"""見(jiàn)《廣韻》:"墨刑"。"黜",貶減,罷官免職之意。為黥面并蒙黑巾,"黜"則為黥面并罷官,較""為輕。
在這里,鞭刑始終作為墨刑的附加刑而使用。因最終的"三百寽"是"黜"的贖金,算是對(duì)牧牛的寬大處理,故"鞭五百"仍然不為主刑。《曶鼎》為西周孝王時(shí)器,記載貴族匡季因指使家奴搶劫而受審。匡季向負(fù)責(zé)審訊的東宮請(qǐng)求:"余無(wú)攸具寇,正□□不□□(鞭)余。"據(jù)郭沫若考證:"大率謂所寇無(wú)多,不必苛責(zé)也。"
盛張考釋認(rèn)為"不□□余"為"不笞鞭余"
。此時(shí)審訊正在進(jìn)行之中,匡季卻發(fā)出如此請(qǐng)求,說(shuō)明鞭笞也用于審訊過(guò)程中。總之,鞭撲之刑在西周刑制中只處于輔助地位。
五刑作為正刑即主要的刑罰手段,一直到春秋時(shí)期也沒(méi)有改變。《國(guó)語(yǔ)·魯語(yǔ)》:"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鉆笮;薄刑用鞭撲。"韋昭注:"甲兵,謂臣有大逆,則被甲聚兵而誅之,若今陳軍也";"斧鉞,軍戮";"割劓用刀,斷截用鋸,亦有大辟";"鉆,臏刑也;笮,黥刑也";"鞭,官刑也;撲,教刑也"。鞭、撲仍為"薄刑"。
春秋時(shí)期鞭撲之刑仍然作為五刑的補(bǔ)充而存在,而且肉刑與鞭撲之刑對(duì)受刑者的身份地位的影響也有著本質(zhì)的區(qū)別。
《左傳·襄公十四年》載:衛(wèi)獻(xiàn)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師曹受鞭刑之后,身份并未下降,職位也沒(méi)有改變。肉刑則不然,如《左傳·成公十七年》,齊國(guó)貴族鮑牽以"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的罪名被處以刖刑,然后"齊人來(lái)召鮑國(guó)而立之"。杜預(yù)注:"國(guó),牽之弟文子。"說(shuō)明鮑牽被處刖刑之后就不能繼續(xù)參與政務(wù)和擔(dān)任宗族之長(zhǎng)了。
《左傳·莊公十九年》:"初,鬻拳強(qiáng)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為大閽,謂之大伯,使其后掌之。"《周禮·天官·閽人》:"閽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后來(lái),楚子為巴人所敗,還,"鬻拳弗納"。及楚子死,鬻拳自殺,"葬于绖皇"社預(yù)注:"冢前闕。生守門,故死不失職。"
可知大閽之職與《周禮》之"閽人"相合。據(jù)《周禮·天官·敘官》:閽人無(wú)爵,孫詒讓《正義》:"此閽人無(wú)爵,則亦庶人在官者也。"據(jù)此,閽人本來(lái)由無(wú)爵之庶人擔(dān)任,鬻拳自刖無(wú)法參與貴族事務(wù),只好充當(dāng)閽人之頭目"大閽"。鞭撲之所以為"薄刑",五刑之所以為"正刑",于此可見(jiàn)一斑。
貴族在受肉刑以后,雖身份有所下降,卻不致于因此而成為奴隸或刑徒。春秋時(shí)期沒(méi)有發(fā)現(xiàn)貴族因受肉刑而降為奴隸的例子。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對(duì)貴族打擊最為嚴(yán)厲的商鞅,也不曾將貴族刑為徒隸。商鞅劓公子虔,黥公孫賈,二人只是"杜門不出",不參與政務(wù),并沒(méi)有變?yōu)?quot;城旦"或"隸臣"。
《商君書(shū)·算地》僅主張"刑人無(wú)國(guó)位,戮人無(wú)官任",春秋時(shí)期對(duì)貴族的刑罰不會(huì)比此更重。
以上所說(shuō),都是刑加于貴族的事例,那么,庶人與貴族有何異同呢?就鞭、撲等"薄刑"而言,庶人與貴族并無(wú)不同,即都不會(huì)改變身份和地位。如《左傳·莊公八年》,齊侯田于貝丘,"隊(duì)(墜)于車,傷足喪屨。反,誅(杜預(yù)注:責(zé)也)屨于徒人費(fèi)。弗得,鞭之,見(jiàn)血"。徒人費(fèi)應(yīng)為"庶人在官者",他因不能為齊侯找回失去的屨而受鞭刑,但并未因此而降低身份或改變職位。至于庶人被施以"正刑",就與貴族大不相同了。《周禮·秋官·司刑》所說(shuō)"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guān),宮者使守內(nèi),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積",恐怕主要是針對(duì)庶人而言的。庶人一旦被施以肉刑,將終身在官府從事看守等卑賤職業(yè),失去自由身份,實(shí)際上已等同奴隸。
有的學(xué)者認(rèn)為,春秋以前,黥刑以上的罪犯都屬于收奴(即沒(méi)官為奴)的對(duì)象
,這一結(jié)論未免顯得武斷。首先,他忽略了貴族與庶人的等級(jí)差別,而這一差別是確實(shí)存在的,已如上述。第二,就庶人而言,將黥刑劃為是否剝奪罪人自由身份的界線也不符合史實(shí)。《周禮·秋官·大司寇》曰:
以圜土聚教罷民,凡害人者,置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其能改者,反于中國(guó),不齒三年。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
鄭玄注:"明刑,書(shū)其罪惡于大方版,著其背。"《周禮·秋官·司圜》曰:
凡圜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cái)。
可見(jiàn)"圜土"中之"罷民"并不被施以肉刑,"其能改者"還能返回鄉(xiāng)里("中國(guó)"即"國(guó)中")。值得注意的是,"其不能改者",這些人將永遠(yuǎn)在"圜土"中服役,如若逃亡,則被處死。這些"不虧體"而又"不能改"的"罷民"也將終身失去人身自由。如此,把是否施以黥刑做為是否喪失自由身份的界線就不能成立了。
"圜土"中的罪人,除了不能改過(guò)而終身服刑者外,"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
。也就是說(shuō),進(jìn)入"圜土"的罪人能夠"改過(guò)自新"者,要根據(jù)罪行輕重服刑一至三年。除此而外,《周禮》中又有"嘉石"制度:
以嘉石平罷民,凡萬(wàn)民之有罪過(guò)而未麗于法,而害于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期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
凡"坐諸嘉石"者,要服三個(gè)月到一年的勞役。秦律中上自城旦舂、鬼薪白粲下至貲徭、貲戍的徒刑制度,以及"齊法"中的"公人"制度,與《周禮》中的"圜土"、"嘉石"制度頗為近似,說(shuō)明秦、齊法律中的徒刑制度絕非憑空出現(xiàn)的,而是有著很長(zhǎng)的歷史發(fā)展過(guò)程。
"圜土"與"嘉石"的關(guān)系,據(jù)《周禮·地官·司救》:
司救掌萬(wàn)民之邪惡過(guò)失而誅讓之,以禮防禁而救之。凡民之有邪惡者,三讓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恥諸嘉石,役諸司空。其有過(guò)失者,三讓而罰,三罰而歸于圜土。
這一表述無(wú)疑加入了作者許多理想的成分,西周春秋時(shí)期的刑罰制度不可能如此整齊周密,也不可能如此溫情脈脈。然而在秦律乃至于《法經(jīng)》之前,早已存在著五刑與徒刑制度,則是可以肯定的。
第二節(jié) 秦律中之肉刑與徒刑的關(guān)系
與春秋以前相比,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的刑罰體系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而肉刑與徒刑關(guān)系的變化就是其重要內(nèi)容之一。下面就探討一下秦律中的肉刑與徒刑的關(guān)系。
首先,春秋以前作為"正刑"的五刑,在秦律中已與徒刑并列;其中的肉刑(包括髡、耐
),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甚至與徒刑相互滲透,復(fù)合使用。
從《周禮》所反映的情況看,"圜土"只關(guān)押、役使犯有輕罪的"罷民",且不加"虧體"之刑;而被施以肉刑的庶民則主要從事看守一類的卑賤職業(yè)。秦律則不然,黥、劓甚至斬左趾(即刖)的刑人也得從事"城旦"之類的繁重勞役。如《法律答問(wèn)》中有這樣一條:"五人盜,臧(贓)一錢以上,斬左止,有(又)黥以為城旦;不盈五人,盜過(guò)六百六十錢,黥劓以為城旦;不盈六百六十到二百廿錢,黥為城旦。"
同時(shí),隸臣妾在通常情況下所承擔(dān)的勞役要輕于城旦舂,而且他們還有資格監(jiān)視城旦舂服勞役:"城旦司寇不足以將,令隸臣妾將。"
盡管如此,隸臣妾也難免體膚之刑,如《法律答問(wèn)》中有隸臣之妻企圖改變其子作為"隸臣子"的身份而被"黥顏頯為隸妾"
。從秦簡(jiǎn)律文看,肉刑(包括髡、耐)已滲透到從城旦舂到司寇、候的各個(gè)徒刑等級(jí)中。這種情況說(shuō)明,以五刑為主的刑罰體系已被打破,肉刑與徒刑已難分主次。
其次,秦律中決定刑徒服刑期限的是徒刑而非肉刑。
關(guān)于秦律刑徒的刑期間題,學(xué)術(shù)界爭(zhēng)論較多,大體上說(shuō),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diǎn):
1.劉海年認(rèn)為中國(guó)的有期徒刑發(fā)端于西周,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則大量使用。從法律規(guī)定看,秦的刑徒是有期的,有期徒刑不是自漢文帝改革才開(kāi)始
。黃中業(yè)在其所著《秦國(guó)法制建設(shè)》一書(shū)中也持這種觀點(diǎn)。
2.錢大群認(rèn)為,秦朝的肉刑犯人都有終身罪隸身份;秦朝的各級(jí)徒刑,就一定等級(jí)的苦役來(lái)說(shuō)是有一定期限的,但就罪隸身份來(lái)說(shuō),隸臣妾以上都具有無(wú)限的罪奴身份
。
3.高恒認(rèn)為秦律中的城旦舂、鬼薪白粲、隸臣妾、司寇、候都是終身服役的刑徒,而貲徭、貲戍、貲居邊以及居貲、居贖、居債者為有服刑期限的刑徒
。栗勁在其所著《秦律通論》一書(shū)中也持類似觀點(diǎn)。
本文同意第三種觀點(diǎn)。貲的本意為罰金,見(jiàn)《說(shuō)文解字·貝部》:"貲,小罰以財(cái)自贖也。從貝,此聲。漢律,民不徭,貲錢二十三。"不過(guò)"貲"在這里并不限于"罰金"。秦律中關(guān)于貲徭、貲居邊、貲戍的期限都有明文規(guī)定,系有期徒刑無(wú)疑;贖為納財(cái)免罪,債為欠官府債務(wù)的罪犯如拿不出現(xiàn)錢,可以以刑徒的身份為官府服役作為抵償,因而都有服刑期限,故相當(dāng)于有期徒刑。對(duì)此,高恒已有論證,其說(shuō)可從。需要指出的是,栗勁將貲徭、貲戍、貲居邊歸為"貲作"類,而與貲物、貲金并列,對(duì)居貲、居贖、居作又未多加注意,則有不妥
。因?yàn)橥叫痰闹饕攸c(diǎn)就是犯法者要在官府有關(guān)部門的監(jiān)督之下服一定期限的苦役,而罰服苦役與罰金是不同的。
持第一種觀點(diǎn)的人注意到秦律刑徒與西周春秋的淵源關(guān)系,并能聯(lián)系到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的相關(guān)材料,其基本思路是正確的,但他們把秦律中的"貲作"與"居"放在一邊,偏要把秦律中的城旦舂等當(dāng)做有期徒刑,而與漢制相比附,則很難自圓其說(shuō)。
錢大群認(rèn)為,秦朝的肉刑犯人都有終身罪隸的身份,這一說(shuō)法也值得商榷。錢大群以秦簡(jiǎn)《法律答問(wèn)》中有人臣甲與人妾乙盜賣主人的牛逃亡而被"城旦黥之"的事例
,又有"人奴擅殺子,城旦黥之,畀主"和"人奴妾治(笞)子,子以死,黥顏頯,畀主"等條目
,來(lái)支持自己的論點(diǎn),而實(shí)際上這些材料并不足以為證,因?yàn)檫@些被施黥刑的人本身就是奴婢。就文獻(xiàn)記載而言,商鞅變法之初,公子虔、公孫賈分別被施以劓、黥之刑,并未變成終身罪隸
。如果說(shuō)這兩人都有貴族身份,不足以說(shuō)明問(wèn)題的話,我們?cè)倏辞睾?jiǎn)中的例子。
秦律中存在著贖刑制度,但是對(duì)于具有終身罪隸性質(zhì)的徒刑,其贖免的條件是非常苛刻的。《秦律十八種·倉(cāng)律》規(guī)定:
隸臣欲以人丁粼者二人贖,許之。其老當(dāng)免老、小高五尺以下及隸妾欲以丁粼者一人贖,許之。贖者皆以男子,以其贖為隸臣。"
整理小組注:"粼,疑讀為齡。丁齡即丁年 。《軍爵律》規(guī)定:
欲歸爵二級(jí)以免親父母為隸臣妾者一人,及隸臣斬首為公士,謁歸公士而免故妻隸妾一人者,許之,免以為庶人。
贖隸臣妾必須用丁壯年男子,或用軍功爵,這對(duì)一般人而言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因此秦律中的贖刑所針對(duì)的主要是肉刑(包括髡、耐)。
《法律答問(wèn)》:"甲謀遣乙盜,一日,乙且往盜,未到,得,皆贖黥。"
這是一個(gè)因盜竊未遂而判"贖黥"的例子;"決籥(鑰),贖黥"也是因?yàn)橛斜I竊嫌疑而判"贖黥"的例子
;"盜徙封,贖耐" 和"內(nèi)(納)奸,贖耐" 則是"贖耐"的例子。以上各例都沒(méi)附加徒刑名稱,說(shuō)明犯人只要繳納足夠的財(cái)物贖了肉刑,就不必承擔(dān)徒刑的勞役,更不可能成為終身罪隸。
《法律答間》中有這樣一個(gè)例子:大夫甲負(fù)責(zé)監(jiān)督鬼薪,如果鬼薪逃亡,大夫?qū)⒈涣P在官府服役,直到逃亡者被抓獲。如果在此期間大夫甲也逃跑,一個(gè)月后被抓獲,將被罰一盾;如果大夫再次逃亡,一年以后才被抓獲將被處以耐刑,盡管如此,只要逃亡的鬼薪被拿獲,大夫即恢復(fù)自由,不會(huì)因耐罪而成為罪奴
。雖然從嚴(yán)格意義上說(shuō),耐并不是肉刑,但至少就秦律條文形式而言,耐罪不附加徒刑名即不服徒刑勞役,肉刑未附加徒刑名也同樣不會(huì)成為刑徒和奴隸。
《法律答問(wèn)》中有這樣的規(guī)定:"父母擅殺、刑、髡子及奴隸,不為'公室告'"
;"擅殺、刑、髡其后子,讞之"
。父母擅自刑、髡其子,而這些被刑、髡之子并沒(méi)有變成奴隸,反證當(dāng)時(shí)秦律中存在這種單獨(dú)施用肉刑的制度。在這種情況下,受懲罰者不用服苦役,更不會(huì)變成奴隸。
春秋及其以前,貴族被施以肉刑之后,身份降低,但不致于淪為奴隸。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等級(jí)制度變動(dòng)的結(jié)果,不但使一些有爵者,也使部分庶人在被處以肉刑之后,只是人格受辱,但一般不至于淪為奴隸或刑徒。《史記·黥布列傳》"秦時(shí)為布衣,少年,有客相之曰:'當(dāng)刑而王。'"如果秦時(shí)一旦受刑,將終身為奴,"當(dāng)刑而王"豈非無(wú)稽之談?英布怎肯輕易相信?布衣而有王者之夢(mèng),正是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社會(huì)等級(jí)流動(dòng)性增強(qiáng)的反映;刑人有此非分之想,是與肉刑可以不附加徒刑因而不改變其庶人身份密切相關(guān)的。
學(xué)術(shù)界討論最充分的無(wú)過(guò)于秦律中的隸臣妾。隸臣妾不論是否附加肉刑,都是終身刑徒,不會(huì)因不附加肉刑而有固定服刑期限,這一點(diǎn),錢大群也沒(méi)有否寶。同樣,比隸臣妾重的城旦舂、鬼薪白粲和比隸臣妾輕的司寇、候都是終身刑徒,只是服刑種類不同、勞役輕重有別而已。
第三、秦律中的肉刑在與徒刑復(fù)合使用時(shí),一般只起劃分刑等的作用。
秦律中的肉刑是從前代繼承而來(lái),本身已有刑等。就秦律而言,肉刑與徒刑復(fù)合使用的主要例證如下:完城旦以黥城旦誣人,當(dāng)黥為城旦
;當(dāng)黥城旦而以完城旦誣人,當(dāng)黥(劓)為城旦 ;"五人盜,臧(贓)一錢以上,斬左止,有(又)黥以為城旦;不盈五人,盜過(guò)六百六十錢,黥(劓)以為城旦。"
秦律對(duì)"群盜"懲治重于普通的盜竊行為,所以最后一例中五人盜竊一錢以上的贓物("群盜"),所受懲罰要重于盜竊六百六十錢以上贓物的非"群盜"犯罪。耐罪輕于刑罪,就不必舉例了。因此,秦律中與徒刑復(fù)合使用的肉刑(包括耐罪)的輕重順序是:耐,黥,劓,刖(斬左止)。髡與宮刑未見(jiàn)與徒刑復(fù)合使用的情況,估計(jì)髡當(dāng)介于耐與黥之間;至于宮刑,春秋戰(zhàn)國(guó)以來(lái)的文獻(xiàn)中,都將其置于刖與大辟之間,即僅次于死刑,也可能只適用于某種特定的犯罪,由于沒(méi)有具體材料,姑且存疑。
秦律中的徒刑本身也有輕重之別。《法律答問(wèn)》:當(dāng)耐司寇而以耐隸臣誣人,要將誣告者耐為隸臣;當(dāng)耐為候的罪犯又誣告他人,將被耐為司寇
,說(shuō)明隸臣重于司寇,而司寇又重于候。《秦律雜抄》:"有為故秦人出,削籍,上造以上為鬼薪,公士以下刑為城旦。"
秦律中不同爵位的人享有不同的特權(quán),上造爵位高于公士,因此在犯了同樣的罪時(shí),上造所受懲罰要輕。由此可知,鬼薪輕于城旦。從這些例證中,我們看到,秦律中徒刑刑等的排列順序與漢律大體相同,由輕而重依次是:候,司寇,隸臣妾,鬼薪白粲,城旦舂。所不同者,漢律中未見(jiàn)"候"這一刑名。
既然肉刑與徒刑各有等級(jí),二者復(fù)合使用,看似可以使刑罰體系更加嚴(yán)密,刑等劃分更為精確。然而由于二者的不同性質(zhì),實(shí)際情況并非如此。
日本學(xué)者堀毅,在其《秦漢刑名考》一文中,曾就秦律中徒刑與肉刑的關(guān)系列一圖表,本文對(duì)其疏略之處加以修正,重新繪制如下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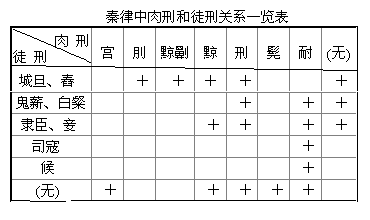
從表中我們可以看到,耐罪只與鬼薪白粲以下徒刑合并使用,而刑罪則只與隸臣妾以上的徒刑復(fù)合使用。睡虎地秦簡(jiǎn)雖非秦律之全部,但表中所顯示的肉刑與徒刑的關(guān)系當(dāng)不致與實(shí)際情況相差太遠(yuǎn)。司寇與候在秦律的終身徒刑中刑等最輕,而黥刑以上的肉刑只適用于比較嚴(yán)重的犯罪行為,二者難以合并使用。候與司寇如果再觸犯法律,一般只判更重的徒刑,而不是附加黥刑以上的肉刑,如耐候判為耐司寇,耐司寇加重則為耐隸臣
。盜竊罪在秦律中是受到嚴(yán)懲的,盜竊贓物達(dá)到一百一十錢,就要耐為隸臣
。兩人圖謀盜竊未遂也要"贖黥"
。而身為司寇的刑徒在盜窈一百一十錢的贓物后投案自首,卻只耐為隸臣或貲二甲
。即使隸臣妾再犯罪,也不輕易施以黥刑以上的肉刑,如:"當(dāng)耐為隸臣,以司寇誣人,可(何)論?當(dāng)耐為隸臣,有(又)毄(系)城旦六歲"
。根據(jù)這些例證推斷,秦律中黥刑以上的肉刑很可能不做為候和司寇的附加刑。
城旦舂是徒刑中的最高等級(jí),而耐罪只是剃去犯人的須鬢,用作城旦舂的附加刑似乎不足以體現(xiàn)出輕重的等級(jí)來(lái)。完城旦再犯罪,動(dòng)輒課以殘酷的肉刑(黥刑以上),如:"完城旦以黥城旦誣人,可(何)論?當(dāng)黥。"
"當(dāng)黥城旦而以完城旦誣人,可(何)論?當(dāng)黥(劓)。"
據(jù)此,耐、髡等較輕的懲罰手段很可能也不作為坡旦舂的附加刑。總之秦律在肉刑與徒刑的關(guān)系上,試圖體現(xiàn)出一種輕重相應(yīng)的原則。
問(wèn)題在于,肉刑旨在通過(guò)對(duì)人的肢體的殘害程度來(lái)懲罰不同罪行的犯人,而徒刑則主要通過(guò)勞役的輕重來(lái)達(dá)到同一目的。二者由于目的相同,復(fù)合使用固然有一定基礎(chǔ);但二者性質(zhì)有別,互相之間缺乏可比性,因此復(fù)合使用時(shí)也會(huì)出現(xiàn)一些問(wèn)題。姑且不談耐罪和髡罪,如果黥刑以上的肉刑只作為徒刑最高等級(jí)城旦舂的附加刊,使肉刑在徒刑與死刑之間起一種過(guò)渡作用,矛盾也許不會(huì)很大。但實(shí)際的情況是,徒刑中的隸臣妾已開(kāi)始附加黥刑。由此而導(dǎo)致的問(wèn)題之一是,犯人一旦被施以黥刑以上的肉刑,就將永遠(yuǎn)帶著這個(gè)恥辱的標(biāo)記。假如黥隸臣妾又犯罪當(dāng)判為(完)鬼薪白粲或完城旦舂時(shí),事實(shí)上已經(jīng)不可能了,只能在"黥"的基礎(chǔ)上加刑。張家山漢簡(jiǎn)《奏讞書(shū)》之四記錄了這樣一個(gè)案例:解曾因罪被處以黥劓之刑,恢復(fù)庶人身份后成為隱官工
,后來(lái)娶逃亡女子符為妻而觸犯了法律:"取(娶)亡人為妻,黥為城旦。"因?yàn)榻庠诖饲耙咽荀糌嬷蹋豢赡茉俅伪惶庽粜蹋Y(jié)果被"斬左止為城旦"
。漢初基本沿用秦律,這一案例明顯暴露了秦律刑制中的弊端。《史記·扁鵲倉(cāng)公列傳》載:
文帝四年中,人上書(shū)言(淳于意),以刑罪當(dāng)傳西之長(zhǎng)安……(少女緹縈)乃隨父西,上書(shū)曰:"妾父為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dāng)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復(fù)生,而刑者不可復(fù)續(xù),雖欲改過(guò)自新,其道莫由,終不可得。妾愿入身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用權(quán)得改行自新也。"書(shū)聞,上悲其意,此歲中亦除肉刑法。
說(shuō)明犯法之人一旦被施肉刑,即使以后改過(guò)自新也無(wú)濟(jì)于事了--肉刑實(shí)際上是純粹的懲辦主義手段,其消極作用是顯而易見(jiàn)的。
問(wèn)題之二是:由于性質(zhì)不同,肉刑與徒刑之間缺乏精確的可比性。舉一個(gè)簡(jiǎn)單的例子,一個(gè)只處以黥刑、終身帶者恥辱的標(biāo)志而未改變庶人身份的人,與一個(gè)被判為完城旦、體膚雖未受損害卻要終身服苦役的人,二者所受懲罰,孰輕孰重?再如,一個(gè)黥隸臣與一個(gè)完城旦,前者終身帶著恥辱的印記而服較輕的勞役,后者體膚保持完好而終生服沉重的勞役,如何比較二者所受懲罰的輕重?實(shí)際情況當(dāng)更復(fù)雜。兩種缺乏精確可比性的刑罰體系復(fù)合使用,無(wú)疑會(huì)給科罪量刑帶來(lái)一定困難,這不僅對(duì)信賞必罰的法家理論是一個(gè)挑戰(zhàn),而且與法律自身發(fā)展規(guī)律不相容。
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徒刑制的發(fā)達(dá)與傳統(tǒng)五刑制的衰落,為肉刑與徒刑的復(fù)合使用創(chuàng)造了條件。肉刑與徒刑的復(fù)合使用在某種程度上使刑罰體系更為嚴(yán)密的同時(shí),也產(chǎn)生了上述矛盾。短祚的秦王朝無(wú)暇顧及于此,這些問(wèn)題的解決,就只好留給漢代了。
第三節(jié)
漢代刑制的變化
漢代刑制方面最重要的變化莫過(guò)于文帝時(shí)期的廢除肉刑及規(guī)定刑期。學(xué)術(shù)界對(duì)此研究頗為深入,
因此本文擬探討另外一些問(wèn)題。
一、肉刑廢除以后的徒刑等級(jí)
秦律肉刑與徒刑復(fù)合使用,再加上其他各種刑罰手段,刑名復(fù)雜,因而就刑制本身而言具有不便操作、刑等不易區(qū)分等等不利因素;至于其社會(huì)效果方面,則弊端更多。孝文帝廢除肉刑,使刑徒"有年而免",這不僅使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擺脫了傳統(tǒng)刑制的野蠻性,而且使刑等更簡(jiǎn)明、更便于操作。不過(guò)由于文獻(xiàn)對(duì)此記載不是很清楚,因此有必要對(duì)文帝廢除肉刑以后的刑等問(wèn)題作一簡(jiǎn)要分析。
為方便起見(jiàn),先將有關(guān)材料引述如下。《漢書(shū)·刑法志》:文帝十三年,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敬根據(jù)文帝的指示,做出如下規(guī)定:
諸當(dāng)完者,完為城旦舂;當(dāng)黥者,髡鉗為城旦舂;當(dāng)劓者,笞三百;當(dāng)斬左止者,笞五百;當(dāng)斬右止,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賕枉法、守縣官財(cái)物而即盜之,已論命復(fù)有笞罪者,皆棄市。罪人獄已決,完為城旦舂,滿三歲為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歲,為隸臣妾;隸臣妾一歲,免為庶人。隸臣妾滿二歲,為司寇;司寇一歲,及作如司寇二歲,皆免為庶人。其亡逃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前令之刑城旦舂歲而非禁錮者,如完為城旦舂歲數(shù)以免。
根據(jù)上述規(guī)定,原來(lái)可以與隸臣妾以上徒刑復(fù)合使用的肉刑,上移到完城旦舂之上,同時(shí)把肉刑的斬右止歸入死刑。其他肉刑如斬左止和劓分別用數(shù)目不等的笞刑代替,黥刑用髡鉗代替,然后服完城旦舂的勞役。而完城旦舂以下諸徒刑,都規(guī)定了服刑期限,由無(wú)期變?yōu)?quot;有年而免"。因此服城旦舂刑者至少包括以下四個(gè)等級(jí):1.笞五百(代斬左止)為城旦舂;2.笞三百(代劓)為城旦舂;3.髡鉗(代黥)為城旦舂;4.完為城旦舂(無(wú)附加刑)。這四個(gè)等級(jí)除了附加刑不同而外,服刑期限與完城旦舂相同。
這里涉及到對(duì)于"諸當(dāng)完者,完為城旦舂"一句的理解。師古注引臣瓚曰:"文帝除肉刑,皆有以易之,故以完易髡,以笞代劓,以釱左右止代刖。今既曰完矣,不復(fù)云以完代完也,此當(dāng)言髡者完也。"以釱左右止代刖大概是后來(lái)刑制又有所變化,在此姑且不論。臣瓚的意思是,既然刖、劓等肉刑"皆有以易之",就不應(yīng)該有"以完代完"的說(shuō)法,因此他懷疑此句當(dāng)為"諸當(dāng)髡者,完為城旦舂"。其實(shí)"完"就是保持身體毛發(fā)完好,并不是刑罰手段,只能與城旦舂等徒刑名稱合在一起表示不附加任何身體刑,只服苦役
,而且臣瓚也沒(méi)有否認(rèn)"完"的這一含義。這一解釋最明顯的證據(jù)見(jiàn)《秦律十八種·軍爵律》:
工隸臣斬首及人為斬首以免者,皆令為工。其不完者,以為隱官工。
意思是說(shuō),工隸臣斬獲敵首或有人斬獲敵首來(lái)贖免他,則讓他做普通的工匠。如果此工隸臣已受過(guò)肉刑,形體有殘損,就用他作隱官工(即在不易被人看見(jiàn)的處所作工匠)。"完"與"不完"是相對(duì)比而言的,既然"不完"系指形體受損,則"完"當(dāng)然是指形體完好。既然髡與耐是剃去犯人的須發(fā),有損于人的外表,當(dāng)然不應(yīng)算做"完"而只能視為"不完"--除非等到須發(fā)再恢復(fù)原狀,否則是不能算"完"的。
文帝的詔令是"其除肉刑,有以易之"
,而肉刑在秦律中稱"刑罪",作為法律術(shù)語(yǔ),"刑罪"是有嚴(yán)格界定的,它只包括黥刑以上的肉刑,髡、耐不在其中
。而且在文帝修改以后的刑制中,仍有"髡鉗";《后漢書(shū)·陳寵列傳》又有"耐罪千六百九十八"之語(yǔ);東漢簡(jiǎn)牘中所錄漢代律令,有"吏部中有蝗蟲(chóng)水火比盜賊,不以求移,能為司寇□",
"能為司寇"即"耐為司寇"。因此文帝所除的肉刑是不包括髡和耐的。"完城旦舂"在秦律中是徒刑的最高刑等(在不附加肉刑的情況下),"諸當(dāng)完者,完為城旦舂"意即按照舊刑制應(yīng)當(dāng)服"完城旦舂"刑的,在新的刑制中仍然保留這個(gè)刑名而不附加其他刑罰。這并不是"以完代完"或"以完代髡"的問(wèn)題,因?yàn)橥瓿堑┡c肉刑無(wú)關(guān),不需要"有以易之";又因?yàn)橥瓿堑┫低叫堂饲靶杞K身服刑,而現(xiàn)在則規(guī)定了具體刑期,"有年而免",比以前大大減輕了。因此。文帝改革以后,"完城旦舂"這個(gè)刑名雖然沒(méi)變,而其含義與以前大不相同了。臣瓚只注意到了文帝詔令中的對(duì)肉刑"有以易之",而忽視了對(duì)徒刑"有年而免",又錯(cuò)誤地把髡、耐劃入肉刑之中,因而導(dǎo)致了他理解上的失誤。栗勁對(duì)完、髡、耐的考證極其精審,其結(jié)論令人信服,但在對(duì)"諸當(dāng)完者,完為城旦舂"一語(yǔ)的理解上,也為臣瓚所惑,這是需要指出的。總之,《漢書(shū)·刑法志》對(duì)此語(yǔ)的記述并沒(méi)有錯(cuò)誤,如果改為"諸當(dāng)髡者,完為城旦舂",則反失原意。
根據(jù)張蒼等人所議定的刑制,完城旦舂以下幾個(gè)等級(jí)的刑名依次是鬼薪白粲、隸臣妾和司寇。其中完城旦舂的刑期是:城旦舂三歲,鬼薪白粲一歲,隸臣妾一歲,共五歲;隸臣妾的刑期是:隸臣妾二歲,司寇一歲,共三歲;司寇二歲(如淳曰:"罪降為司寇,故一歲;正司寇,故二歲也。")。令人不解的是,鬼薪白粲的刑期不知為何沒(méi)有明確規(guī)定?師古曰:"男子為隸臣,女子為隸妾。鬼薪白粲滿三歲為隸臣,隸臣一歲免為庶人。隸妾亦然也。"《漢書(shū)·刑法志》中并無(wú)此語(yǔ),不知顏氏別有所據(jù)?抑或根據(jù)上下文推測(cè)而得?王先謙《補(bǔ)注》認(rèn)為顏氏"三歲"當(dāng)"一歲"之誤,也沒(méi)提出根據(jù)。而且如果從王氏《補(bǔ)注》,鬼薪白粲滿一歲為隸臣妾,隸臣妾一歲免為庶人,總共只有兩年,相當(dāng)于司寇的刑期,似乎與情理不合。根據(jù)上下文推測(cè),高于鬼薪白粲的城旦舂是五歲刑,低于鬼薪白粲的隸臣妾、司寇分別是三歲、二歲刑,則鬼薪白粲當(dāng)為四歲刑,顏師古之說(shuō)不宜輕易否定。
上文已經(jīng)提出,文帝改革刑制之后,仍有耐罪。耐罪在新的刑制當(dāng)中處于哪一等級(jí)?這里只能做一推測(cè)。《漢書(shū)·文帝紀(jì)》元年"刑者及有耐罪以上,不用此令"注引蘇林曰:"一歲為罰作,二歲刑以上為耐。"《后漢書(shū)·光武帝紀(jì)》建武七年"耐罪亡命,吏以文除之"注引《前書(shū)音義》與此同。漢代二歲刑為司寇,前面所引漢簡(jiǎn)有"能(耐)為司寇"之語(yǔ),說(shuō)明二歲刑的司寇可以與耐復(fù)合使用。但張蒼等奉文帝之命議定刑制時(shí)曾說(shuō)"其亡逃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說(shuō)明二歲刑以上的刑徒并不一定都施耐刑。不過(guò)由此可以知道,耐罪刑等要高于司寇。《漢書(shū)·惠帝紀(jì)》即位之初詔令"上造以上及內(nèi)外公孫耳孫有罪當(dāng)刑及當(dāng)為城旦舂者,皆耐為鬼薪白粲",作為對(duì)皇族、外戚及有爵者的優(yōu)待,說(shuō)明耐為鬼薪白粲的刑等較城旦舂為低。這雖然是文帝以前的材料,但因?yàn)椴簧婕叭庑蹋虼斯烙?jì)有關(guān)刑等與新的刑制差別不會(huì)很大。上一節(jié)已談到,秦律之髡、耐只與鬼薪白粲以下各徒刑復(fù)合使用。在新的刑制中我們注意到,髡與鉗結(jié)合后才與城旦舂復(fù)合使用,因而耐刑可能仍然不能在城旦舂之上構(gòu)成一個(gè)刑等。沈家本《漢律摭遺》卷九稱"《王子侯諸表》坐罪耐為司寇、耐為隸臣、耐為鬼薪、耐為城旦者屢見(jiàn)"
,然而遍查《漢書(shū)》諸表及《二十五史補(bǔ)編》之《后漢書(shū))諸表,"耐為城旦"不曾一見(jiàn),恐沈氏筆誤,不足為據(jù)。由此觀之,文帝改革后的耐罪大致有三個(gè)等級(jí),即耐為鬼薪白粲、耐為隸臣妾、耐為司寇,介于城旦舂和司寇之間。更具體的情況則有待于進(jìn)一步研究。
在司寇之下,還有復(fù)作與罰作,《漢舊儀》:
男為戍罰作,女為復(fù)作,皆一歲到三月。
關(guān)于復(fù)作,《漢書(shū)·王子侯表》平侯劉遂"坐知人盜官母馬,為臧,會(huì)赦,復(fù)作";又居延漢簡(jiǎn):臨之隧長(zhǎng)薛廠德"見(jiàn)為復(fù)作"
。據(jù)此,則復(fù)作并不限于女犯。《漢書(shū)·宣帝紀(jì)》"使女徒復(fù)作淮陽(yáng)趙征卿、渭城胡組更乳養(yǎng)"注引孟康曰:"復(fù)音服,謂弛刑徒也,有赦令詔書(shū)去其鉗釱赭衣。更犯事,不從徒加,與民為例,故當(dāng)復(fù)為官作,滿其本罪年月日,律名為復(fù)作也。"則復(fù)作的關(guān)鍵是不戴刑具,不穿囚服,在官府中服役。"作于官府"是對(duì)囚徒的優(yōu)待,秦簡(jiǎn)《法律答間》:"將上不仁邑里者而縱之,可(何)論?當(dāng)毄作如其所縱,以須其得;有爵,作官府。"
這一原則可能為漢代繼承。平侯遂爵為侯,薛廣德可能亦系有爵者,故為"復(fù)作"。漢律優(yōu)待女犯,所以有輕微罪過(guò),也"復(fù)為官作".《漢舊儀》并不全錯(cuò),只是過(guò)于籠統(tǒng)。
關(guān)于罰作,《漢書(shū)·文帝紀(jì)》二年詔"民適作縣官及貸種食未入、入未備者,皆赦之",沈家本認(rèn)為"此即罰作之法"
。居延漢簡(jiǎn)EPT59:59載:"第十候長(zhǎng)傅育,坐發(fā)省卒部五人會(huì)月十三,失期,毋狀,今適載三泉茭二十石致城北燧給驛馬,會(huì)月二十五日畢。""適"通"謫"。候長(zhǎng)傅育發(fā)省卒失期,被罰運(yùn)載二十石茭從三泉燧到城北燧。從發(fā)省卒"會(huì)月十三失期"到運(yùn)茭"會(huì)二十五日畢"來(lái)看,中間只有十天左右,另一支簡(jiǎn)61.3+194.12記載候長(zhǎng)田宗發(fā)省卒"不以時(shí)","適為驛馬載三茭五石致止害",運(yùn)載量更小,估計(jì)期限也不會(huì)長(zhǎng)。結(jié)合《漢舊儀》來(lái)看,罰作的最高期限是一年,而最低期限可能只有十天或更短的時(shí)間,而且罰作也不限于戍邊。《法律答問(wèn)》有"貲徭三旬",《秦律雜抄》有"貲日四月居邊"、"貲戍一歲"、"貲戍二歲"等等,大概相當(dāng)于漢代的"罰作"。
文帝對(duì)刑制的改革,并沒(méi)有達(dá)到預(yù)期的效果,"外有輕刑之名,內(nèi)實(shí)殺人"
。景帝時(shí)又先后兩次下詔減少加笞的數(shù)目,并定"箠令","自是笞者得全"
。
《漢舊儀》所述"秦制",非但不是秦的刑制
,甚至也不同于文帝改革的刑制。前引臣瓚曰"以釱左右止代刖",并不是張蒼等人所議定的制度。據(jù)《三國(guó)志·魏書(shū)·鐘繇傳》:"若今蔽獄之時(shí),訊問(wèn)三槐、九棘、群吏、萬(wàn)民,使如孝景之令,其當(dāng)棄市,欲斬右趾者許之。"說(shuō)明漢景帝時(shí)尚無(wú)釱左右趾以代刖的制度。估計(jì)在景帝之后刑制又有調(diào)整,是否發(fā)生于武帝大規(guī)模編修律令之時(shí),由于資料不足,難以詳考。
二、"無(wú)任"與"五任"
一九六四年,考古工作者對(duì)洛陽(yáng)城南郊的東漢刑徒墓地進(jìn)行發(fā)掘,發(fā)現(xiàn)刑徒墓五百二十二座,出土墓磚八百多塊。完整的磚銘一般刻有刑徒的部署、無(wú)任或五任、獄名或郡縣名、刑名、姓名、死亡日期,并注明尸體埋在此處。例如:"右部無(wú)任少府若盧髡鉗尹孝永初元年五月四日物故死(尸)在此下"(
T2M77:1) 。其中關(guān)于"無(wú)任"與"五任"的解釋,很多學(xué)者認(rèn)為"五任"是指有一定技術(shù)的刑徒,而"無(wú)任"是指沒(méi)有專門技能,只能從事粗重勞動(dòng)的刑徒
。本文認(rèn)為"無(wú)任"、"五任"與刑徒是否有技術(shù)專長(zhǎng)無(wú)關(guān),而是一個(gè)法律術(shù)語(yǔ)。
認(rèn)為"五任"、"無(wú)任"系指刑徒有無(wú)技術(shù)的觀點(diǎn),主要是根據(jù)胡三省對(duì)《資治通鑒》的一條注釋。《通鑒》卷一五九,梁武帝大同十一年:"徒居作者具五任,其無(wú)任者著升械。"胡注:"任,謂其人巧力所任也。五任,謂任攻木者則役之攻木,任攻金者則役之攻金,任摶埴者則役之摶埴。魏武帝定甲子科,犯釱左右趾者,易以升械;是時(shí)乏鐵,故易以木焉。"
《周禮·冬官·考工記總敘》"以飭五材"鄭玄注:"玄謂此五材,金、木、皮、玉、土。"胡注"五任"或取于此。可是用技術(shù)專長(zhǎng)("巧力所任")解釋"任",不免牽強(qiáng)。退一步即使這一解釋能夠成立--即"無(wú)任"者從事粗重勞動(dòng),"五任"者從事技術(shù)工作--也不能說(shuō)明為什么只給"無(wú)任"者戴刑具。
《說(shuō)文解字·人部》:"任,保也。"秦漢選官有保舉制度。"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
,這是由舉薦而產(chǎn)生的法律連帶關(guān)系,即為防止選拔官吏時(shí)營(yíng)私舞弊,要求舉薦者要對(duì)被舉薦者的行為負(fù)責(zé)。"任"是擔(dān)保的意思。
"任者保也"這一用法在秦漢典籍中比較普遍,尤其是在與法律相關(guān)的事例中。居延漢簡(jiǎn)的買賣契約中也經(jīng)常看到"任者"一詞,如:"終古燧卒東郡臨邑高平里召勝字游翁,貰賣九稯曲布三匹,匹三百卅三,凡直千,觻得富里張公子所,舍在里中二門東入,任者同里許廣君";"驚虜隧卒東郡臨邑呂里王廣,卷上字次君,貰賣八稯布一匹直二百九十,觻得安定里隨方子惠所,舍在上中門第二里三門東入,任者閻少季、薛少卿"
。當(dāng)買賣雙方出現(xiàn)爭(zhēng)端時(shí),"任者"要起到"公證"的作用,"擔(dān)保"契約的效力,維護(hù)當(dāng)事人雙方的利益。
《周禮·地官·大司徒》:"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鄭玄注:"保猶任也。"孫詒讓《正義》:"五家家數(shù)既少,居又相比,有罪過(guò)不容不知,故使相保任。"自商鞅變法之后,什伍組織的作用更受重視,"伍人"之間既有互相監(jiān)督的法律責(zé)任,也有相互扶助的義務(wù)。《法律答問(wèn)》:"賊入甲室,賊傷甲,甲號(hào)寇,其四鄰、典、老皆出不存,不聞號(hào)寇,問(wèn)當(dāng)論不當(dāng)?審不存,不當(dāng)論;典、老雖不存,當(dāng)論。"
說(shuō)明伍人之間互相救助,也是法律所要求的義務(wù)。
沿著這條思路,我們可以對(duì)秦漢時(shí)期"保、任"在法律上的含義有更多的了解。我們認(rèn)為,"無(wú)任"與"五任"所表示的是對(duì)罪犯的擔(dān)保制度:"五任"是指犯人的家屬或同伍之人出具擔(dān)保,保證犯人在服刑期間不逃亡,或再犯罪,從而使犯人在勞動(dòng)時(shí)免戴刑具;"無(wú)任"則指無(wú)人為犯人提供擔(dān)保,為防止犯人逃跑,而必須給他戴上刑具。這樣解釋,"其無(wú)任者著升械",而"五任"者則不然的原因就不言自明了。
沈家本在《刑法分考》"保任"條中引用《隋書(shū)·刑法志》的《梁律》"徒居作者具五任,其無(wú)任者著斗械"以及《北齊律》"三曰刑罪,并鎖輸左校而不髡,無(wú)保者鉗之"等材料之后,加按語(yǔ)說(shuō):"無(wú)任者,著械防其逃也,北齊之鉗亦是此意。保即任也。"
甚為精當(dāng)。
關(guān)于文帝改革刑制以后收孥、從坐等制度的具體情況,將在下一章"秦漢法律的倫常化"中加以討論。
|


![]()
![]() web@guoxue.com
web@guoxu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