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重慶時(shí),馬衡來渝了,聽說故宮博物院運(yùn)出來的文物,分別疏散在云南的昆明、四川的重慶、樂山、峨眉等處。當(dāng)然就是最初赴英展覽的一批,以及張?jiān)儡妿兔\(yùn)出的一部分,此外遺留在北平的全部、以及南京庫房沒有搶出的都聽之任之了。我是比較知道的。而他們的個(gè)中人告訴我說,除去文獻(xiàn)館小部分外,都出來了。
馬衡一到重慶,不知如何打聽得我的住址,來至圣宮造訪,他固然好意,我卻因故宮是
非謝絕了他。后來,他又到山王廟軍司令部來,我也未見。他請(qǐng)我的大兒祖光吃飯,請(qǐng)他疏通;三顧了弊寓,我不便堅(jiān)拒,于是彼此相見。他又請(qǐng)我吃飯,二人不免感慨一番,我倆應(yīng)屬故宮創(chuàng)建時(shí)的最早同仁,同是做的具體院務(wù),且因北大系得誤解,發(fā)生過不少的矛盾。
他著重向我說到,他與徐森玉經(jīng)過這么多年的親眼所見,說明我是一個(gè)有情有義的朋友,尤其我對(duì)易培基的蒙冤,拔刀相助,不計(jì)后果,弄得后半生留離在外,不能返回北京,十分的不安。我也直言不諱地再次批評(píng)了他,在易院長受冤枉之后他的態(tài)度曖昧,始終不明朗。連易院長去世他都沒有出現(xiàn),而在故宮早期創(chuàng)辦的時(shí)候,易院長是十分的重用他的。李玄伯也是他很要好的朋友。對(duì)此,他依然是回避不言,似乎是有難言之隱。
我知道他畢竟是既得利益者,能有現(xiàn)在的態(tài)度已屬不易了,他希望與我重續(xù)友誼。并說最近要選一部分文物參加美國的博覽會(huì),對(duì)于古物陳列所的文物,我是老人,比較熟悉,從建院展覽就參與其事。要請(qǐng)我擔(dān)任審查委員,我礙于當(dāng)時(shí)情況沒有答應(yīng)。
我說:“我是待罪之身,不便受聘。也免得生出許多麻煩。你如果一定要我審查,你可以拿古物陳列所的目錄給我,我替你圈出可以送出去的,不一樣嗎?”
他贊同這樣做,邀我到他辦公處去一次,他拿出目錄大致由我看一下,也就算答拜。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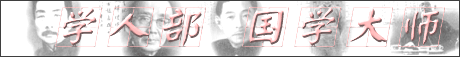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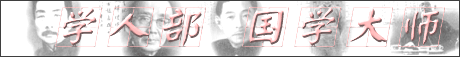

mailto:guoxue@guoxue.com
![]() 010-68900123
010-68900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