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背后,摞著高高的書,當然。他的沙發前,是一個可以推拉的正好卡在沙發扶手上的小條案,案上鋪著一張張書寫整齊的稿紙,當然。《光明日報》曾有文章說京城學界書最多的有二人,那第二人我熟悉,第一人大家都熟悉——季先生。
記得季先生家里的墻,好像是用四庫全書曲折砌成。走進季先生的家,方知什么
叫坐擁書城。沒想到的是,久住醫院的季先生,把病房也住成了書城。
當然,醫院是不能隨便堆砌書的。季先生也只是在他那單人沙發的后邊碼著書。不過,有季先生端坐沙發,這一方小小的空間,便如一座書城,一個文化重鎮。
季先生的助手李先生,特意在這座書城的左右各放上一把椅子,讓夢溪和我坐在季先生的近旁。季先生聽力減退,左耳是聽不見了。李先生在一米多的“遠處”,盡可以說季先生的逸事,反正先生聽不見。她說起季先生這一輩子都是守時,總是凌晨四點半起床,夜晚九點半睡眠。幾十年前季先生常打乒乓,正打呢,一想起有什么事到了時間,放下球拍就走,把她氣的
“不讓我聽見?”季先生的眼睛隱隱地有一種調皮。
李先生知道季先生聽不見,接著說:他打乒乓大都是小碎球,打得又笨
“我什么都笨。”季先生笑笑地、輕輕地說:“我屬豬。”
他怎么都聽見了?
我們大笑。我說李先生,你講季先生乒乓打得不好,可是季先生這話就好像反應極快的一記抽球
如果將來發明一種乒乓,不是用球拍打球,而是用思維對打,那么,季先生是很難有對手的。幾年前鐘敬文先生問夢溪:“你是北大畢業的吧?”夢溪不是北大畢業,但他的知交好友,多在北大。夢溪還未及回話,季先生的乒乓球已經發將出去:他不是北大畢業,但比北大還北大。
季先生的思維,像乒乓球運動員,又像潛水員。潛得很深很深,再深再深。當年胡適說,研究佛學,就要像季羨林那樣。從胡適說話到21世紀的今天,多少年了?然而季先生還潛在佛學的深海里。我們看他那天,沒坐多久他就說起“佛”字的來源問題。他說佛教從印度傳來,一般都認為“佛”是“佛陀”的省略,“佛”字應該是梵文;但不是,是吐火羅文。為什么?夢溪說季先生1947年寫過《浮屠與佛》,探討的就是這個問題。1989年又寫過一篇。也許兩篇文章還不能讓季先生盡情盡意,所以他坐在醫院的書城里,越想越深。季先生這么說的時候,那種“屬豬”的調侃全沒了,只有一種智者、思想者的大痛苦。
我看到他右側的電視機上,放著一只絨毛的博士熊,氣象極大。熊博士頭帶博士帽,一手抱著一卷博士證書,毛衣上繡著5個大字:季羨林教授。
季羨林教授就是坐在病室里,就是坐在電視上,也是氣象萬千 也讓人懾服于震撼于智者的力量。
他左側床邊的燈罩,用透明塑膠條貼著一張紙,上邊寫著藥物服法的一條條。這些事情不是他思考的范圍,所以只能逐一記在最不會找不到的燈罩上。
這只燈罩,向我提醒畢竟季先生在病中。我和夢溪拿出一樣樣好玩的東西給季先生。我一直相信人皆有童心,不管他是9歲還是90歲。大智者尤其是大兒童。這次發現季先生胖了些許,臉色也紅潤了,變成一個可愛的孩兒臉。我好像第一次讀到那四個字:鶴發童顏。
我拿出一只玩具兔,按動開關。那兔子飛快地撥動它手中的電吉他,為季先生獻上一曲。兔子邊走邊唱,偶而停一剎那,又想著變換一種方式來取悅它的觀眾———來回晃動腦袋,轉動眼睛,伸展耳朵。季先生從他那小條案上,使勁探過頭來,高興地觀看這位流行歌手的表演。那專注好奇的神情,一看就是9歲。兔子停頓的剎那,季先生說:它在琢磨琢磨。
是的,兔子要琢磨琢磨不斷地出新花樣。孩童最喜歡新奇,智者最不能承受的不是缺鈣缺鋅缺營養缺維他命,而是缺新。所以兒童和智者,常常是一步之遙。
曾經有位季先生的崇拜者,苦苦地想跟我們去看望季先生。我們如何地說不可以的,那朋友還是不依不饒。夢溪被逼無奈,只好打電話問李先生怎么辦。李先生說,季先生說了,一個祖芬就夠熱鬧了。
有一個工藝品,是一個小女孩騎在一只大紙鶴上,她的手里又舉著一只小紙鶴。女孩的童花頭跟我相似,我送這個騎鶴女孩給季先生,也是想送上我的祝福。
李先生大笑:這女孩的頭和祖芬完全一樣
季先生立刻用雙手作一個短發披到雙頰的模樣:祖芬的發型是這樣的。
連我自己都覺得我和那女孩的發型很像,而季先生一下就能看出不同。我又一次看到一位年方95的乒乓球運動員的敏銳。
我知道季先生背后常管我叫“長不大”。其實,只有長不大才能懂長不大。
季先生的同輩學者,許多都故去了。唯季先生童真依舊,依然孜孜于學問。他說:如果他們都在,我季羨林算什么?
李先生笑:你四十幾歲的時候就當學部委員,那時你是最年輕的。
前幾天,中秋前夕,亞洲華文作家文藝基金會一行18人,特地從海外來京,為季先生送上一塊終身成就獎的獎牌,上寫:“季羨林大師,著作等身,文通中外,豐富了中華文學的內涵,拓展了白話文的境界,誠為文化瑰寶,本會為表崇高敬意,謹贈紀念牌一座。”我么,更看重一幅絲織的季先生的照片。本來是一位朋友在杭州為季先生訂做的,沒想到浙江的普通工人們一聽是季羨林先生,激動得都要求織上一把。結果這幅絲織像是200名工人你一把我一把地用心織就,而且有200名工人的簽名。華文作家送終身成就獎給季先生,那是順理成章。浙江的工人們崇拜季先生,那真是一份驚喜,一份來自民間的終身成就獎。
再看那端坐電視機上的熊博士,大氣象里透著一種孩子氣。知季先生者,熊博士也。
我們回到家里,才發現本來帶去3本書,不知怎么糊里糊涂地又帶回了一本。電話鈴響,是李先生的:夢溪,也真奇怪了。你們一來,你們的話先生都能聽見。你們一走,他又聽不見了。還有,季先生說,你們明明帶來3本書,還有一本怎么找不到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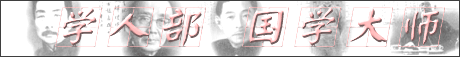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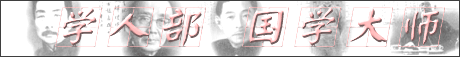

mailto:guoxue@guoxue.com
![]() 010-68900123
010-68900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