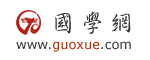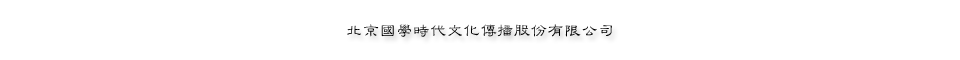康熙帝玄燁(1654—1722)是否會下圍棋,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正史中并無玄燁弈棋的記載,但是在野史、軼聞中卻有一些這方面的材料。例如:小橫香室主人《清朝野史大觀》中有一段記載:
清初鰲拜輔政,因正白旗圈地事,直隸總督朱公(昌祚)、巡撫王公(登聯(lián))、戶部尚書蘇公(納海)與之齟齬,乃悉加誅夷,圣祖不預(yù)知也。嘗托病不朝,要親往問疾,圣祖幸其第,入其寢,御前侍衛(wèi)和公(托)見其色變,急趨至榻前,揭席刀見,圣祖笑曰:“刀不離身,滿洲故俗,不足異也。”即返駕。以弈棋召索相國(額圖)入謀。數(shù)日后,鰲拜入見,召羽林士卒立擒之。
又據(jù)周家森《留余簃弈話》載:
黃霞,字龍士,又字月天,清儀征入。善弈,能自出新意,窮極變化,康熙時稱為“弈圣”。嘗十萬壽節(jié)日,在御前圍棋,下完后于棋盤上排一“壽”字,而四角上亦均各排蝙蝙一只,以示福壽之意。殊為難能可貴矣!
以上所引兩段材料,皆透露出玄燁喜愛圍棋的些須情況,但是否事實,由于缺乏旁證材料,還難以斷言。即以康熙除鰲拜一事看,據(jù)《清史稿·圣祖本紀》載:
康熙八年,上久悉螯拜專橫亂政,特慮其多力難制,乃選侍衛(wèi)拜唐阿年少有力者,為撲擊之戲。是日螯拜入見,即令侍衛(wèi)等掊而系之。
其中并無玄燁以弈棋召索額圖入謀的記載,或許《清朝野史大觀》另有所據(jù),只是我們今天難以查考而已。
關(guān)于吳三桂如何謀殺永歷帝一事,某些史料語焉不詳。清人筆記中的劉獻廷《廣陽雜記》提供了一些細節(jié):
……永歷之自緬歸也,吳三桂迎入,坐輩中,百姓縱觀之,無不泣下沾襟。……予曰:“聞帝崩之日,天有風云之變,果然否?”曰:“吳三桂既得密旨,請帝于北門庫飲弈,遂弒之。百姓初不之知也。”
由此可知,吳三桂是奉清帝密旨后,請永歷帝飲酒弈棋,加以謀害。據(jù)劉獻廷講,此事乃江寧吉坦然親眼所見。坦然曾隨其父扈從永歷帝去云南,甲午開科中式,授大理府云龍州知州,后改授姚安府姚州知州。清兵至,投誠,授蒙自縣知縣,后出縣流寓粵東。對云南的事知之最詳,故他的敘述大致是可信的。
吉坦然的敘述表明,永歷帝顯然喜歡飲酒弈棋,吳三桂大約知道他的這種嗜好,所以用為誘餌,將他騙來殺害。
張潮(1650—?),清文學(xué)家,字山來,號心齋,安徽歙縣人。以歲貢任翰林院孔目。他所著的《幽夢影》中有一些關(guān)于圍棋的妙論,讀之令人心曠神怡:
雖不善書,而筆硯不可不精;雖不業(yè)醫(yī),而驗方不可不存;雖不工弈,而楸枰不可不備。
昔人云:“若無花月美人,不愿生此世界。”予答一語云:“若無翰墨棋酒,不必定作人身”。
春雨宜讀書,夏雨宜弈棋,秋雨宜檢藏,冬雨宜飲酒。
春聽鳥聲,夏聽蟬聲,秋聽蟲聲,冬聽雪聲。白晝聽棋聲,月下聽簫聲,山中聽松聲,水際聽欵乃聲,方不虛生此耳。若惡少斥辱,悍妻詬誶,真不若耳聾也。“空山無人,水流花開”,二句極琴心之妙境;“勝固欣然,敗亦可喜”,二句極手談之妙境。
張潮的這些妙論,充滿生活的情趣,也表現(xiàn)出封建文人的高雅情懷。如若將其中的圍棋言論擇出連接一起,就會構(gòu)成一幅生動的圖景:“雖不工弈,而楸枰不可不備”,“若無翰墨棋酒,不必定作人身”。“夏雨宜弈棋”,“白晝聽棋聲”,“勝固欣然,敗亦可喜”。這難道不是作者圍棋生活的真實寫照嗎?
張潮認為“翰墨棋酒”勝過“花月美人”,在封建文人圈子中,不見得會引起廣泛擁護,但在那些胸懷磊落,志趣高雅的文人中,自會得到充分地響應(yīng)。自唐、宋以來似乎已成定論。
與張潮基本同時的尤侗(1618—1704),康熙時召試博學(xué)鴻詞,授翰林院檢討。他寫過一篇《棋賦》,其中有這樣的字句:“試觀一十九行,勝讀二十一史”。與張潮遙相呼應(yīng),表現(xiàn)對圍棋的極端推崇。尤侗的觀點自然有些偏頗,但也確實道出康熙年間部分知識分子的心聲。圍棋唯一的壞處就是太迷人,煙酒可以戒,唯有圍棋無法戒。一個人一旦學(xué)會下圍棋,就等于找到一個不能分離的“情人”,她將伴隨你快樂地度過終生,而你卻無從抗拒。
乾隆時期,社會上的文士名流推崇圍棋,有助于圍棋浪潮的不斷高漲。其中應(yīng)該特別提到著名詩人袁枚,倡導(dǎo)圍棋不遺余力。
袁枚(1716—1797),字子才,號簡齋、隨園老人。錢塘(今浙江杭州)人。乾隆進士,任翰林院庶吉士,后出知溧水、江浦、沐陽、江寧等縣。年四十即告歸,筑“隨園”于江寧之小倉山,專以著述詩文為事。有《小倉山房詩文集》七十余卷及其它著述三十余種。
袁枚一生嗜好圍棋。其所著《山中行樂詞》云:“何物共閑戲?圍棋亦偶然。買碑爭舊搨,染筆試新箋。食品何曾纂,茶經(jīng)陸羽編。搜奇兼志怪,俱是小游仙。”詩中所列舉的幾項;圍棋、金石、書畫、飲食、搜奇,構(gòu)成了袁枚文化生活的主要內(nèi)容。但詩中說:“何物共閑戲,圍棋亦偶然。”是不是袁枚只是偶爾下下圍棋呢?恐怕這樣寫只是想表明圍棋在他生活中所占的位置。而據(jù)有些資料記載,情況也不盡如此。例如晚清學(xué)者俞樾曾看過袁枚玄孫袁潤所保存的《袁隨園紀游冊》,其中所記袁枚79歲、80歲兩次出游蘇、杭、浙東、金陵期間,幾乎天天下棋,并詳細記錄輸贏情況。俞樾因此題詩云。“日日舟窗幾局棋,輸贏幾子必書之。”可知袁枚對下棋的態(tài)度是嚴肅認真的,而且愈老興趣越濃。
在袁枚的詩集中,詠圍棋的專篇和散句頗為不少。如《觀弈》:“清簟疏簾弈一盤,窗前便是小長安。不關(guān)我事眉常皺,閱盡人心眼更寬。黑白分明全局在,輸贏終竟自知難。憑君著遍飛棋好,老譜還須仔細看。”再如《詠觀棋》:“悟得機關(guān)早,都緣冷眼明。代人危急處,更比局中驚。張步臨奔海,陳宮見事遲。分明一著在,未肯告君知。肯舍原非弱,多爭易受傷。中間有余地。何必戀邊旁。”模擬觀棋人的心情,頗為傳神。從“肯舍原非弱,多爭易受傷。中間有余地,何必戀邊旁”一句看,袁枚對棋理還是很有研究的,估計他的棋也下得不錯。
袁枚曾為棋圣范西屏、國手徐星標標撰寫墓志銘,對他們的精湛技藝和杰出人品推崇備致。袁枚曾親見西屏對弈,可能與西屏有較深的交往。他說:“余不嗜弈而嗜西屏,初不解所以,后接精髹器者盧玩之,精竹器者李竹友皆醰粹如西屏,然后嘆藝果成皆可以見道。今日之終身在道中,令人見之怫然不樂。尊官文儒,反不如執(zhí)伎以事上者,抑又何也?……”一藝之成皆可以見道,誰都會這樣說,并不算出奇的言論。而袁枚將“尊官文儒”與西屏等人對比,認為他們“終身在道中”,“反不如執(zhí)伎以事上者”,則是一種發(fā)自內(nèi)心的感嘆,透露出袁枚對現(xiàn)實中那些“尊官文儒”的諷剌與不滿。
圍棋雖然長期名列中國四大藝術(shù)之一,但在歷代士人心目中,難與詩文、書畫比肩,因此專事下棋的人也被看作技藝之徒。這種情況在清代已有很大改變,也就是說,圍棋作為中華的國技,日益受到士人的尊崇;國手的聲望也與日俱隆,到處受到上層社會和知識分子階層的熱烈歡迎。我們可以用雍、乾時期的著名詩人沈德潛、趙翼與范西屏作一比較,沈、趙的詩名只局限于一個小范圍之內(nèi),難比范西屏的棋名舉國震響,有口皆碑。而范西屏在全國各地受到的歡迎和款待、士夫名流皆以結(jié)識為榮,更是沈、趙所難企及的。袁枚是雍、乾時期最負盛名的詩人,他對國手的稱譽,在社會上會帶來很大影響。且看他為范西屏所寫的墓志銘:
雖顏、曾世莫稱,惟子之名,橫絕四海而無人爭。將千齡萬齡,將以棋名,松風丁丁。
直是認為西屏的名望,竟比顏回、曾參這些二等圣人還要高。評價似有過甚之處,但也未必不是現(xiàn)實情況的一種反映。
紀昀(1724—1805),字曉嵐,乾隆、嘉慶年間著名學(xué)者,曾任《四庫全書》館總纂官,刪定總目提要。其所著《閱微草堂筆記》中,多次敘及圍棋,對于了解乾隆、嘉慶時期朝野圍棋的興旺情況很有幫助。
紀昀本人也會下棋,但他比較欣賞蘇東坡、王安石對圍棋的態(tài)度,即不以勝負為懷,著重于追求其中的意趣。《閱微革堂筆記》中有“弈棋雜感”一則,抄錄如下:
南人則多嗜弈,亦頗有廢時失事者,從兄坦居言:丁卯鄉(xiāng)試,見場申有二士,畫號板為局,拾碎炭為黑子,剔碎石灰塊為白子,對著不止,竟俱曳白而出。夫消閑遣日,原不妨偶一為之,曰此為得失喜怒,則可以不必。東坡詩曰:“勝固欣然,敗亦可喜。”荊公詩曰:“戰(zhàn)罷兩奩收白黑,一抨何處有虧成?”二公皆有勝心者,跡其生平,未能自踐此言,然其言則可深思矣。帝卯冬,有以八仙對弈圖求題者,畫為韓湘、何仙姑對局,五仙旁觀,而鐵拐李枕一壺盧睡。余為題曰:“十八年來閱宦途,此心久似水中鳧。如何才踏春明路,又看仙人對弈圖?”“局中局外兩沉吟,猶是人間勝負心。那似頑仙癡不省,春風蝴蝶睡鄉(xiāng)深!”今老矣,自跡生平,亦未能踐斯言,蓋言則易耳。
紀昀所記場中二士,為弈棋爭勝,連功名都不要了,足見圍棋迷人之深。這種作法自然是不足取的。紀昀由此而發(fā)的感慨也很有意思,他認為蘇東坡、王安石對棋局的勝負看得很超脫,但在生活中卻很難超然物外,即“皆有勝心者”。紀昀并且承認自己也達不到與世無爭的地步。看來局中的勝負和人間的“勝負”是有差別的,然而人活在世上,沒有一點勝負心,形同死灰槁木,那活著還有什么意義呢?
圍棋的魅力之一,就在于它有強烈的勝負,符合了人的欲念和世間的競爭法則。如若沒有勝負,它也很難在長達幾千年的時間里,贏得億萬愛好者的心。
《閱微草堂筆記》中,還有一段乾隆時期高手程念倫與乩仙下棋的事,讀來頗有趣:
程念倫,名思孝,乾隆癸酉甲戌間,來游京師,弈稱國手,如皋冒祥珠曰:“是與我皆第二手,時無第一手,遽自雄耳。”一日,門人吳惠叔等扶乩問仙善弈乎?判曰:“能。”問:“肯與凡人對局否?”判曰:“可。”時念倫寓余家,因使其弈。初下數(shù)子,念倫茫然不解,以為仙機莫測也,深恐敗名,凝思冥索,至背汗手顫,始敢應(yīng)一子,意猶惴惴。稍久,似覺無他異,乃放手攻擊,乩仙竟全局覆沒,滿室嘩然。乩忽大書曰:“吾本幽魂,暫來游戲,托名張三豐耳。因粗解弈,故爾率答,不虞此君之見困!吾今逝矣。”惠叔慨然曰:“長安道上,鬼亦誑人。”余戲曰:“一敗即吐實,猶是常安道上鈍鬼也。”
所謂“仙”,無非是扶乩的巫師裝神弄鬼,他雖自誇善弈,但遇到高手,自然會全軍盡墨。程念倫、冒祥珠大約是士大夫中的高手,在乾隆時期弈壇強手如云的情況下,能達到二手的程度,已是相當不錯了。只是關(guān)于他們弈棋的情況,除上述一則趣聞之外,史料中卻未留下絲毫記載。
圍棋一般是兩個人下的,人多了也可。比如“聯(lián)棋”,有時竟多達幾十位,分為兩班人馬,一人走一步,輪流走下去,取其熱鬧而已。
那么,一個人是否也能下圍棋?答案是肯定的。不僅高手,既使一般愛好者,在研究和學(xué)習(xí)棋藝的過程中,也常常自己和自己下棋。這實際上是一個思維的過程,即在頭腦中設(shè)一個假想的對手,先構(gòu)思他怎么走,然后再構(gòu)思自己如何應(yīng)對。一盤棋就這樣下出來了。清代散文家魏禧(1624——1680)所著《魏叔子集》中,有一篇《獨弈先生傳》,記述了一位專門自己和自己下棋的人——黃在龍。
據(jù)魏禧描述:黃在龍性不治生產(chǎn),絕世務(wù)而好弈。常閉戶居,戶外人聞子聲丁丁然,窺之,則兩手各操白、黑子,分行相攻殺。或默然上視而思,或欣然笑也。人稱曰:“獨弈先生”。
“獨弈先生”兄弟三人,伯好鼓琴、仲好藝花竹,而先生獨好弈。或求對,亦不辭也。先生開枰布子,伯、仲常侍局,先生微問可否?伯、仲各以意對,先生說:“若長于守,若長于攻,然皆偏將材也,使握中權(quán),決機兩陣,難哉”!年七十有七卒,其獨弈未嘗稍衰云。
魏禧發(fā)表感想說:“古嗜弈者眾矣,未有獨弈者?曰:有之。弈,攻圍沖劫,變化通于兵法。諸葛武侯臥隆中時,未聞有十夫之聚,指揮旌幟,教坐作也。出而戰(zhàn)必勝,以仲達之智,畏之如虎。吾意其獨居抱膝時,日夜之所思,手所經(jīng)營,未嘗不在兩陣間也,非獨弈而何哉?先生之意,其不可測識哉!”
魏禧說諸葛亮隱居隆中時,獨自研習(xí)兵法,有類于“獨弈”,是不錯的。但因此認為黃在龍的獨弈,其意不可測識,則未免貽笑大方。前面說過,對于圍棋愛好者來說,獨弈乃是一種普遍的現(xiàn)象。黃在龍既使比一般人更嗜好獨弈,恐怕也難說他象諸葛孔明一樣,有志圖王吧。
寫到這里,筆者不禁想起有關(guān)圍棋巨星吳清源的一段趣事。吳清源也可說是一位“獨弈”的專家,他獨自一人苦心研究出的新手、新定式不勝枚舉。因此,日本著名九段棋手武官正樹曾說:“我們作為職業(yè)棋手感到很光彩,有一半是托了吳先生的福。”自然,吳清源所創(chuàng)造出的新手和新定式,在未發(fā)表之前屬于個人“專利”,是秘而不宣的。而一旦在實戰(zhàn)中走出來,常常使對方措手不及。五十年代初期,第一次“吳清源——高川格”三番棋中,吳清源在“大雪崩”定式中走出向里曲的新變化,使高川格大驚失色。在觀戰(zhàn)室中的年輕棋手紛紛議論說:“吳先生把定式搞錯了!”殊不知這正是吳清源苦心孤詣的變著。這局棋最終以吳清源的徹底勝利而宣告結(jié)束。
曾國藩(1811—1872)是中國近代史上具有深遠影響的人物。在鎮(zhèn)壓太平天國起義的過程中,成為維持搖搖欲墜清王朝的中流坻柱。他學(xué)識淵博、詩文傳世,文治武功足以名彪青史。一般的學(xué)生大約只知道曾國藩是屠殺天國義士的劊子手,稍有學(xué)識的人還知道有一部《曾文正公文集》。然而恐怕沒有幾個人知道,曾國藩一生嗜棋如命,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大“圍棋迷”。
曾國藩在道光二十年考中進士,旋任翰林庶吉士,時年28歲。在他傳世的日記中,詳細記載了他自己日常的圍棋活動。僅就這些日記中的記載大致統(tǒng)計,從道光二十一年起的十三年中,他共對弈一千三百余盤棋,觀棋還不在其中。自然,實際對局的數(shù)目還不僅于此。
據(jù)記載,曾國藩“終身患癬,每晨起必圍棋,公目注楸枰,而兩手自搔其膚不息,頃之案上肌屑每為之滿。”從記載中看,有時他一天下兩盤棋、有時一天下三盤,最多一天下四盤。作為朝廷大員,曾國藩公務(wù)繁冗,但他常忙里偷閑,弈棋遣興。有一次他在處理兩百件公文后,仍要下兩局棋方能入睡。有一天曾不斷接待來訪者五回,忽然發(fā)了棋癮,非下兩盤棋后才人內(nèi)室休息。還有一次為來訪者書寫對聯(lián)十七幅,不顧疲勞繼續(xù)弈棋。有時半日內(nèi)分別與兩人對陣,有時一日內(nèi)連與兩人對壘角逐。這些都是曾國藩在日記中親手所記,可見圍棋已成為他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娛樂活動。不僅如此,往往下完棋后余興未盡,半夜時分進了內(nèi)室,他還要擺開棋盤,或打譜或復(fù)盤,仔細玩味一番。當身邊無人可為對手或遇風雨無法外出,曾國藩只好自己一人對弈,實在無以遣懷,就把夫人拉出來下一局,也有自得之樂。
曾國藩的棋友,在他日記中就可找出五十余位。從身份看范圍極廣,諸如親朋好友、幕僚職屬、看病的大夫、過往的官員以及不第的士子,還有他的兄弟曾國荃和弟媳等等。除此而外,當時國手周小松、黃南坡等也與曾國藩有過棋藝交往。曾國藩于棋友常引為同調(diào),情意眷眷。棋友別去,他親送行,棋友辭世,他則痛哭,并吟詩作賦以寄懷念之情。這里應(yīng)特別提到曾國藩與僚屬下棋,大凡他棋癮發(fā)作,即不顧封建等級尊卑的界限,常找下屬手談。從他的日記中可以看到,小小的桐城縣令薛炳煒是他常年的棋友。有一個不曾記下姓名的普通舉人,因棋藝頗佳,也受到曾國藩的青睞。咸豐九年十二月,已是子夜二更時分,曾國藩旁觀魯秋航、李榕二入夜戰(zhàn),四時許才入睡。之后幾天不下棋,技癢難耐,就悄悄到下屬如毛鴻賓、胡蓮舫家中求戰(zhàn)。以總督的身份,為了下棋,不惜屈尊下就,這不正說明圍棋的巨大魅力嗎?
不僅在家中弈棋,既使公務(wù)在身,曾國藩也往往見棋就忍不住要比試一番。道光年間他人宮當值,至勤政殿引見前也要下兩盤棋過癮。一般官員見皇帝前往往誠惶誠恐,不敢稍有松懈,而他卻要先下兩盤棋,棋癮之大是自不待說了。后來在鎮(zhèn)壓太平天國起義時,曾國藩率軍征戰(zhàn),更是以圍棋隨身自娛,而且愈是不順心愈要下棋。這時圍棋已成為他排遣憂患,不可須臾分離的精神寄托。咸豐九年,在三河戰(zhàn)役中,他的胞弟曾國葆和愛將李續(xù)賓被太平軍擊斃,不久湖南寶慶被圍,曾國藩“心急如焚”,遂拉棋友吳子序弈棋兩局。其間他瘧疾發(fā)作,手疼兼生坐板瘡,可以說是坐立不安,只好下棋以“解心煩”,看完病便與大夫郭霈霖手談兩局。咸豐十年七月,曾國藩正與程桓生下棋,忽接圣旨,朝廷補授其為兩江總督。一時府邸車水馬龍,冠蓋如云,程桓生欲罷戰(zhàn),而他堅持棋局收盤后才接見道喜的客人。咸豐十一年,英王陳玉成一舉圍殲湘軍三百余人,曾國藩“心煩意亂”,遂下三盤棋定神。同治二年二月在丁家洲船上,一日之內(nèi)連戰(zhàn)六局,每局約兩刻許。七月金陵解圍戰(zhàn)失敗,他“寸心如割”,又下兩盤棋。不久其妾陳氏病重吐血而死,“哭聲凄涼”,他“心緒殊劣”,又與歐陽兆熊連弈四局以解哀愁。同治三年,太平天國天京失陷,曾國藩由安慶趕至金陵,親審忠王李秀成。一時找不到對手,便與其弟曾國荃隨便下兩局應(yīng)景,據(jù)他在日記中說,只有這樣才算未虛度時日。
同治四年四月,朝廷調(diào)他鎮(zhèn)壓捻軍,他自南京北上,一路上因剿捻失敗“焦灼之至”,途經(jīng)山東泰山,上山前在泰安考棚中與人對弈兩局,下山后又下兩局。返寧途中在淮安適逢漕運總督吳棠,兩人是多年棋友,遂弈戰(zhàn)不休,十七天內(nèi)竟酣戰(zhàn)六十八局棋。
以上所述是曾國藩在戎馬生涯中與圍棋結(jié)下的不解之緣。他不僅以圍棋排憂解難,也曾有意識地將圍棋用于軍事。據(jù)載,一次部下向他報告大將多隆阿收隊之法,他便命人“以棋子擺列陣式”進行實戰(zhàn)研究。
曾國藩一方面嗜棋,一方面又屢屢發(fā)誓戎棋。大約愛之深反又恨之切,矛盾的心情頗為有趣。他認為下圍棋“最耗心血”,多下則“頭昏眼花”,有時“眼蒙太甚”,“明知曠工疲神而屢蹈之”。一度發(fā)誓“戎棋”,他在日記中曾寫道:“為棋所困,費光陰至一時之久,妨正務(wù),以后戒之。”甚至說再下棋便“永絕書香”,決心不謂不大。為了戎棋就只看他人下棋,結(jié)果如何呢?仍“躍躍欲試,不僅如見獵之喜,口說自新,心中實全不真切”。愈戒棋癮愈大,終于也未能戒掉。
清代圍棋的繁榮,不可避免地會反映到小說之中,著名小說如《聊齋志異》、《紅樓夢》、《儒林外史》、《鏡花緣》中都有關(guān)于圍棋活動的描寫。由于這幾部小說均產(chǎn)生于康熙、乾隆時期,也就間接地反映了康、乾盛世社會圍棋活動的某些情況。
《聊齋志異》的作者蒲松齡(1640—1715),字留仙、號柳泉,山東淄川人。蒲松齡是否喜愛下棋,還未見到這方面的材料。但在《聊齋志異》中談到圍棋的有十五篇之多,較為著名的有《嬌娜》,《連瑣》、《陸判》、《云蘿公主》等。還有一篇《棋鬼》,對現(xiàn)實生活中嗜棋如命的人作了形象、深刻的描繪。小說寫一個“湖襄人”,癖嗜弈,產(chǎn)蕩盡。“父憂之,閉置齋中,輒逾垣出,竊引空處,與弈者狎。父聞詬詈,終不可制止。父赍恨死,閻王以書生不德,促其年壽,罰入餓鬼獄”。后來“東岳鳳樓成,下牒諸府,征文人作碑記,王出之獄中,使應(yīng)召自贖”。誰知這位書生又半道與人下棋,遷延誤期,結(jié)果“仍付獄吏,永無生期矣”。
小說雖然寫的是鬼,實際上卻是刻畫現(xiàn)實中活生生的人。請看如下描寫:
揚州督同將軍梁公,解組鄉(xiāng)居,日攜棋酒,游林丘間。會九日登高,與客弈,忽有一人來,逡巡局側(cè),耽玩不去。視之,面目寒儉,懸鶉結(jié)焉,然意志雅溫,有文士風。公禮之,乃坐,亦殊搛。公指棋謂曰:“先生當必善此,何不與客對壘?”其人遜謝移時,始即局。局終而負,神情懊熱,若不自己。又著又負,益憤慚,酌之以酒,亦不飲,惟曳客弈。自晨至于日昃,不逞溲溺。方以一子爭路,兩互喋聒……
寥寥幾筆,一個嗜棋而棋力又不高的形象躍然紙上。愛丁棋的人都知道,象蒲松齡所描寫的這種類型的人,俗稱“屎棋”經(jīng)常可以見到,不能不說蒲松齡對生活的觀察十分仔細,勾勒人物也非常傳神。蒲松齡寫這個故事的用意比較明顯,旨在諷喻嗜癖誤事。但世上因嗜癖誤事的例子盡多,為什么作者偏偏選中嗜棋呢?我們可以設(shè)想,是現(xiàn)實生活中的真人真事觸動了作者,使他產(chǎn)生了“勸戒”的欲望。作者最后形容嗜棋的人說:“見弈遂忘其死,及其死也,見弈又忘其生。”也就是“見弈而忘生死”,世上有這樣的人嗎?曰有,圍棋之迷人可謂深矣。
《紅樓夢》前八十回寫圍棋的地方不多,除第六十二回寫“探春便和寶琴下棋,寶釵,岫煙觀局”這樣幾個字以外,還提到過丫環(huán)們用圍棋“趕子”(一種簡單的盤戲)。但是在后四十回中,有關(guān)圍棋的描寫卻多了起來。例如第八十七回寫惜春和妙玉下棋,還提到古譜中的著名套子:“倒脫靴”、“茂葉包蟹”、“黃鶯搏兔”等。再如第九十二回較詳細地描寫賈政與清客詹光下棋的情景。上述的情況顯然表明,曹雪芹與高鶚對圍棋的認識和喜愛,有一定的差異。大約高鶚比曹雪芹嗜好下棋,所以在他的筆下,圍棋自然而然成為描寫的對象。近年海外有些學(xué)者考證,《紅樓夢》前八十回與后四十回系出于一人手筆。但依筆者淺見,即使從書中前后對圍棋的描寫不同來看,出于一人之說也是不能成立的。
清代小說中,于圍棋史最具參考價值的,要算《儒林外史》。書中有三處關(guān)于圍棋的描寫,對當時社會上的圍棋活動作了真切而深刻的敘述。
第八回“王觀察窮途逢世好,婁公子故里遇貧交”寫王太守與蘧公子一番對話:
……當下酒過數(shù)巡,蘧公子見他問的都是些鄙陋不過的話,因又說起:“家君在這里無他好處,只落得個訟簡刑清。所以這些幕賓先生,在衙門里都也吟嘯自若。還記得前任臬司向家君說道:“聞得貴府衙門里有三樣聲息。”王太守道:“是那三樣?”蘧公子道:“是吟詩聲、下棋聲、唱曲聲。”主太守大笑道:“這三樣聲息卻也有趣的緊。”蘧公子道:“將來老先生一番振作,只怕要換三樣聲息。”王太寧問:“是那三樣?”蘧公子道:“是戥子聲、算盤聲、板子聲。”
以“吟詩聲、下棋聲、唱曲聲”,反襯“戥子聲、算盤聲、板子聲”,表現(xiàn)當時“清官”與”貪官”雅俗之不同,體現(xiàn)了作者對官場情況的反思以及深沉的精神寄托。
第五十三回“國公府雪夜留賓,來賓樓燈花驚夢”,描寫南京妓院里的圍棋活動。吳敬梓一生大部分時間是在南京度過的。因此他筆下的人物和故事往往取材于秦淮河畔發(fā)生的事情。秦淮河歷來為六朝金粉之地,“一帶妝樓臨水蓋,家家分影照嬋娟”。比較高級的妓女,為了侍奉公子王孫、達官貴人,都需要學(xué)習(xí)琴、棋、書、畫,以抬高身價。“來賓樓燈花驚夢”即寫妓女聘娘向國手鄒泰來學(xué)棋時發(fā)生的故事。
國公府的親戚陳木南去“來賓樓”梳櫳聘娘,恰值聘娘與南京國手鄒泰來學(xué)棋。陳木南乘興取出一錠銀子權(quán)作彩頭,入局與鄒泰來對弈,從七子至十三子,只是下不過。因說:“先生的棋實是高,還要讓幾個才好。”鄒泰來說:“盤上再沒有個擺法了,卻是怎么好?”聘娘說:“我們另有個擺法,鄒師父,頭一著不許你動,隨便拈著丟在那里就算,這叫個憑天降福。”鄒泰來笑道:“這成個什么款,那有這個道理。”陳木南逼著他下,只得叫聘娘拿一個白子來混丟在盤上,接著下了去。這一盤鄒泰來被殺死四五塊,陳木南正暗歡喜,又被他生出一個劫來,打個不清。陳木南又要輸了,聘娘手里抱了烏云復(fù)雪的貓,往上一撲,那棋就亂了……
這一段故事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形象逼真地再現(xiàn)了當時圍棋國手的一些生活情況。作者在這一回的開始說:“又有那一宗老邦閑,專到這些人家來替他燒香、擦爐、安排花盆、揩抹桌椅、教琴棋書畫。”鄒泰來即是這樣一個“老邦閑”,他雖身為國手,但為生計所迫,只好出入妓院,靠教妓女下棋,贏些嫖客的彩金混日子。從史料記載看,清代康、乾時期的國手,其最好前途即是出入達官富豪的家門,充當清客。其末流即是像鄒泰來那樣,在妓院充邦閑。因此,吳敬梓筆下的鄒泰來,是對現(xiàn)實生活中棋客命運的真實寫照,具有相當?shù)牡湫鸵饬x。
然而在民間,也有一些身懷絕技的人,不甘仰承豪貴的鼻息,依仗一點小手藝自食其力過活。《儒林外史》第五十五回“添四客述往思來,彈一曲高山流水”記述一個名叫王太的人,自小最喜下圍棋。他祖代是三牌樓賣菜的,他每日到虎踞關(guān)一帶賣火紙筒為生。一日妙意庵做會,王太走將進去,見三四個大老官簇擁著兩個人在那里下棋。一個穿寶藍的說:“我們這位馬先生前日在揚州鹽臺那里下的是一百一十兩的彩,他前后共贏了二千多銀子。”一個穿玉色的少年說:“我們馬先生是天下的大國手,只有這卞先生受兩子還可以敵得來。只是我們要學(xué)到卞先生的地步,也就著實費力了。”王太挨著身子上前去偷看,小廝們看見他穿的襤褸,推推搡搡,不許他上前。底下坐的主人說:“你這樣一個人,也曉得看棋?”王太說:“我也略曉得一些。”撐著看了一會,嘻嘻的笑。那姓馬的說:“你這個人會笑,難道下得過我們?”王太說:“也勉強將就。”主人說:“你是何等之人,好同馬先生下棋!”姓卞的說:“他既大膽,就叫他出個丑何妨。才曉得我們老爺們下棋,不是他插得嘴的!”王太也不推辭,拿起子來,就請姓馬的動著。旁邊的人都覺得好笑。那姓馬的同他下了幾著,覺得他出手不同。下了半盤,站起身來說:“我這棋輸了半子了!”那些人都不曉得,姓卞的說:“論這個局面,卻是馬先生略負了一些。”眾人大驚,就要拉著王太吃酒。王太笑道:“天下那里還有個快活似殺屎棋的事,我殺過屎棋,心里快活極了,那里還吃的下酒!”說畢,哈哈大笑頭也不回,就去了。
從這一段故事里,我們可了解一些當時南方圍棋活動開展的情況。像妙意庵國手棋會、馬先生在揚州鹽臺處下棋贏兩千多兩銀子等情節(jié),都真實地再現(xiàn)了當時圍棋回手的某些生活。吳敬梓筆下的馬先生,是一位靠下棋吃飯的“職業(yè)”棋手,王太雖然棋藝很高,卻靠賣火紙筒為生。在這里,吳敬梓實際上對王太這樣自食其力的市井小民,給予很高的評價,認為他們完全可以名列儒林而毫無遜色。但對國手馬先生,筆調(diào)中則頗含諷剌的意味。
吳敬梓生于1701年(康熙四十年),于1754年(乾隆十九年),與棋圣范西屏、施襄夏屬于同一時代的人。他本人喜愛下棋,因此他筆下所描寫的圍棋故事,即使在細節(jié)上也絕無隔膜之處。他長期居住圍棋興盛的南京,晚年也曾到過當時的圍棋中心揚州。大約他接觸過一些圍棋高手,并以他們的生活為原型,塑造了鄒泰來、王太、馬先生三個不同的人物形象。其中尤以王太這個人物,寄托了作者的贊美與期望。筆者認為,王太這個人物,不僅僅是作者虛構(gòu)的理想形象,而是現(xiàn)實生活中真實人物的反映。象類似的民間棋手,在其它史料中也有所記載。例如前面己提到的,《揚州畫舫錄》中弈勝范西屏的“擔草者”等等。我們?nèi)粢浴度辶滞馐贰分械耐跆c《揚州畫舫錄》中的“擔草者”對照分析,就不難發(fā)現(xiàn)這樣一個事實;康、乾之際,在民間確實出現(xiàn)了一些業(yè)余圍棋高手,他們不以棋名世,而是自食其力,但是他們的棋藝卻可以和當時的國手相媲美。
清代的著名小說中,還有一部《鏡花緣》,描寫圍棋活動既多而又詳細,這是因為它的作者李汝珍(約1763—1803)極為嗜好圍棋。李汝珍曾編選《受子譜》二百余局,對棋藝有相當研究。在《鏡花緣》中,下圍棋是百花諸仙女和才女們?nèi)粘I钪械闹饕仓弧V皇沁@些下棋的場面寫得不算精彩,其間還充斥一些圍棋知識的議論,破壞了藝術(shù)的形象性。對于圍棋史來說,也較少參考價值。
晚清還有一部小說《新聊齋》,僅存殘本卷一,不甚著名。作者“治世之逸民”,具體姓氏不詳。書中有一篇《談棋》,有可注意之處。小說敘述太平天國起義期間,鳧山鄉(xiāng)人周鵒,以圍棋邀知于曾(國藩)、彭(玉麟)諸軍帥,居軍慕之上舍。周鵒善于談棋,以口代手,不假枰局。嘗說:“吾生平閱人多矣,凡弈者,……唯口談至八十余著而不紊者,僅襲侯曾紀澤。”小說又通過一僧人之口介紹彭玉麟:“我聞李軍請濟師,彭公且至,大夫也,醉心于此道……”
曾國藩、彭玉麟、曾紀澤都是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有關(guān)他們在軍中弈棋的情況,也見于其它史料記載。例如《清代軼聞》曾記述晚清大國手周小松與曾國藩弈棋往來:
曾國藩最好弈,而不工。嘗召小松弈,意厚贐之。小松授曾九子,裂其棋為九片,皆僅乃得活。曾大怒,遂一文不之贐。曾患癬,終身不愈。每與人弈將負,則半身伏案上,癬益癢,爬騷膚屑盈案,人莫不厭苦之。嘗與某武員弈,至相詬詈,幾至揮拳。明日乃嘉其有膽氣,保薦之。
從這一段記述,筆者頗疑《新聊齋·談棋》,是根據(jù)周小松的某些經(jīng)歷,所敷衍的一篇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