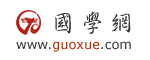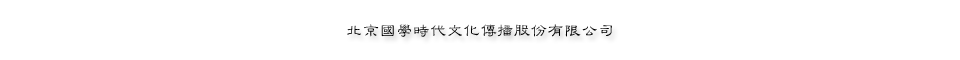明太祖朱元璋雖然出身卑微,沒念過什么書,然而在他叱咤風云的軍事、政治生涯中,卻養成了愛下棋的習慣。“煙雨湖山六朝夢,英雄兒女一枰棋”。據說朱元璋常與徐達“在南京莫愁湖邊下棋。一次朱元璋連吃徐達兩子,自以為勝局已定,徐達卻說:“請陛下仔細觀局。”朱元璋一看,原來徐達的棋子隱約連成“萬歲”二字,不禁心花怒放。于是將湖邊的一棟樓賜給徐達,后人稱此樓為“勝棋樓”。
如今“勝棋樓”仍點綴在莫愁湖畔的綠蔭之中,勾引游人醉賞。樓里樓外有不少對聯,其中有一副云:
占全湖綠水芙蕖,勝國君臣棋一局;
看終古雕梁玳瑁,盧家庭院燕雙飛。
記述了明初開國君臣下棋遣興的一番勝事。
朱元璋善下模仿棋,據清魏瑛《耕蘭雜錄》載:
明太祖智勇天縱,于藝事無所不通,惟于弈棋不耐思索。相傳其與人對弈,無論棋品高低,必勝一子。蓋每局必先著,輒先于枰之中間,孤著一子。此后,黑東南,則白西北;黑右后,則白左前,無不遙遙相對,著著不差。至局終,則輒饒一子也。帝王自有真,非幾手所能擬議矣。
這里所說即“模仿棋”,先行者于“天元”置一子,然后對手走在那里,即于相對的地方著棋,招招模仿。模仿棋從戰略上講,有一定的實用價值,可以在布局階段盡量保持局面的均衡。但如魏瑛所說,模仿棋必勝一子,則是不正確的。因為后走的一方,也有破模仿棋的方法。況且專事模仿,也就將圍棋變成了枯燥無味的游戲,失去了其中藝術的魅力。如果《耕蘭雜錄》中的傳說屬實,則朱元璋雖然愛下棋,而棋藝水平卻不高。
在下棋的問題上,朱元璋也有嚴酷的一面,據明周漫士《金陵瑣事》載:
明太祖造逍遙樓,見人博弈者、養禽鳥者、游手游食者,拘于樓上,使之逍遙,盡皆餓死。
懲罰的方法,非常理可以忖度。又據顧啟元《客座贅語》載:
洪武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奉圣旨:在京但有軍官、軍人學唱的割了舌頭,下棋、打雙陸的斷手。
明初,在多年戰亂以后,需要恢復經濟、發展生產。因而朱元璋痛恨游手游食的人是可以理解的,但把下棋這樣正當的娛樂活動也加以禁止,甚至施行苛刻的懲罰,不免是極為過火的作法。明末董含對此評論說:“明初立法之酷,何以至此,幾乎桀紂矣!”
看來朱元璋雖然自己喜歡下棋,也不反對皇室、官吏、士人下棋,但卻反對百姓和軍人下棋。這就是封建統治者不能出以公心的一種表現。在他們眼里,平民百姓只是一些能干活的機器,不必有娛樂活動。你要娛樂,他就說你不務正業、游手好閑。甚至明令禁止、予以嚴懲。但是,朱元璋這種“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作法,并未取得什么顯著的效果。明朝的圍棋照樣蓬勃發展,不僅在官僚、士人中間,既使在城市市民階層中,也得到廣泛的普及。
劉基(1311—1375),字伯溫,青田(今屬浙江)人。明初政治家、文學家。他曾扶佐朱元璋推翻元政權,被朱元璋比作諸葛亮。
劉伯溫喜愛弈棋,也常與朱元璋下棋。據清張英《淵鑒類函·巧藝部·圍棋》載:
明王文祿《龍興慈記》曰:圣祖賜劉誠意一金瓜,曰:“擊門。惟有急,則擊之。”一夕夜將半,擊宮門,乃洞開重門迎之。問:“何也?”曰:“睡不安,思圣上弈棋耳。”命棋對弈。俄傾,報太倉災,命駕往救,劉止之曰:“且弈,請先遣一內使充乘與往。”遂如言。回則內使已斃車中,圣祖驚曰:“何以知朕厄?”曰:“觀乾象有變,特來奏聞耳。”
伯溫曾任御史中丞兼太史令,封誠意伯,故此處稱之為“劉誠意”。洪武四年,伯溫辭官歸隱,據清張庭玉《明史·劉基傳》載:
劉基……賜歸老于鄉。……基佐定天下,料事如神。性剛嫉惡,與物多忤。至是還隱山中,惟飲酒弈棋,口不言功。
劉基辭官之舉,是為避免“狡免死,走狗烹”的下場。“還隱山中,惟飲酒弈棋”,也有全身避禍的意思。但也說明棋和酒是他生平之好,不能須臾分離。
劉璟,字仲璟,劉基次子。論說英侃,喜談兵,是一位很有個性的人。
劉璟曾與燕王朱棣下棋,并因此得罪了朱棣。據《明史·劉基傳》載:
璟……弱冠通諸經。……嘗與成祖弈,成祖曰:“卿不少讓耶?”璟正色曰:“可讓處則讓,不可讓者不敢讓也。”成祖默然。……成祖即位,召璟,稱疾不至,逮入京,猶稱殿下,且云:“殿下百世后,逃不得一‘篡’字。”下獄,自經死。
劉璟的性格頗類他的父親劉基。劉基“性剛嫉惡,與物多忤”,劉璟也剛直不阿,對于燕王朱棣這樣的驕橫人物也敢于頂撞。本來在棋藝面前應該人人平等,不能摻雜私心雜念。但是在封建社會,藝不敵貴,高手故意讓棋,阿諛奉承權貴的現象屢見不鮮。因此,象劉璟那樣,“不可讓者不敢讓也”的精神是難能可貴的。
朱元璋的一家人似乎很有下棋的傳統。朱元璋和朱棣喜愛圍棋,朱元璋的另一個兒子朱權甚好象棋,并親自編過象棋譜。朱棣的兒子朱高熾在作太子時,不僅自己下象棋,也愛看內侍們下象棋。他還曾與狀元曾子棨賦象棋詩唱和,以助弈興。由于朱氏父子、爺孫的喜好,明宮中棋藝活動非常盛行,對朝野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成祖朱棣是一位粗人,性格兇殘,但對詩詞、圍棋卻興趣甚濃。當時有一位御醫盛寅,與同僚下棋,被朱棣撞見,盛寅惶恐無地,深懼帝怪罪,不料結果卻出人意料。《明史·盛寅傳》載:
盛寅,字啟東,吳江人。成祖召入便殿,令診脈,寅奏上脈有風濕病,帝大然之。進藥,果效,遂授御醫。他日,與同官對弈御藥房,帝猝至,兩人斂枰伏地謝死罪。帝命終之,且坐以觀之。寅勝,帝喜,命賦詩,立就。帝益喜,賜象牙棋枰并詞一闋。
盛寅受到成祖的寵愛,固然因為他治好成祖的風濕病,但也與成祖喜愛下棋有關。愛棋的人見棋自會有一種親切的感覺,所以成祖不僅不責怪盛寅在御藥房下棋,反而要看他下棋,并賜以象牙棋盤。
唐理,字孟淳,明永樂三年鄉舉,官陜西河渠提舉。唐理一生好弈,據清《無錫縣志》載:
唐理……嘗于陽羨山中遇蜀雅州道士買茶者,與對局三日夜,理遂為吳中第一。家有竹素園,楸枰滿四座。諸妾臧獲無不能之,其婿得其傳,久之與理爭勝負焉。
唐理雖稱吳中第一,但也只是區域好手,尚不能稱通國之善弈者。
然而,唐理家中的圍棋活動,在明初卻很有些代表性。使我們可以了解圍棋傳播普及過程中的某些情況。唐理好弈,家中楸枰滿四座。他個人的喜好影響了一家人,以致諸妾、奴婢(臧獲)、女婿等都會下棋,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圍棋家庭。這種由個人影響眾人,也即由點到面的方式,在圍棋傳播中頗有典型意義。
唐理雖然在吳中很有名氣,但他的影響力不可能太大,大約只局限于家庭的范圍之內,和周圍的其它一些人。在社會上不會產生廣泛的影響。
但對于一國之主的皇帝來說,影響力就非同小可。圍棋史的研究表明,中國圍棋的幾次大發展,都和當時最高統治者的喜好和支持倡導分不開。例如南北朝時期的宋文帝、梁武帝,唐朝的唐玄宗,宋朝的宋太宗等等。皇帝的影響,不管自覺與不自覺,都是一個逐層擴展的過程。皇帝的喜好首先會影響宮庭里的人,如后妃、內侍、宮女,形成一個下棋的圈子。然后會影響朝廷中的大臣、官吏,也形成一個下棋的圈子。接下去又會影響社會上的知識分子,形成一個更大的下棋的圈子。最后還有一個由平民百姓組成的下棋的圈子。這實際上也是一個由點到面的過程,象聲波和水波的傳播一樣逐層向外擴展。
如果從廣義的角度去探討中國歷代圍棋人口的組成,也可以按上面的方式劃分四個圈子。這四個圈子互相包含、互相影響、互相制約。一般說,越往里的圈子影響力越大,而知識分子的圈子最具穩定性,其它三個圈子會隨時間、條件的不同,增大或者縮小。所謂知識分子的圈子,只是一個籠統的概念。這個圈子里的圍棋人口包括文人、士紳、隱逸、僧侶、棋手等等。自然,它也可以包括朝廷里的人物,因為朝廷的大臣、官吏大多是文人、士紳中的人物。他們在做官前后,也都可以歸到知識分子的圈子里來。這個圈子還可以包括平民百姓中的一些人物,如城市中善弈的手藝人,三教九流中的某些特殊的下棋人物,如妓女、城市邦閑等。
知識分子圈子里的人,歷來是中國圍棋運動的主流。一、這個圈子里的人文化素養較高,對于圍棋這樣的高智能藝術最易接受、也最易喜愛。因此圍棋活動在這個圈子里最活躍。二、這個圈子里的圍棋人口具有相對穩定性。例如元朝,由于種種原因,宮庭、朝廷、平民百姓中的圍棋人口銳減,唯有這個圈子里的圍棋人口相對不變。三、由于這個圈子里圍棋開展最活躍,并且包括各類棋手(主要指高手、國手),因此也就代表了中國圍棋藝術發展的水平。
最后,我們再簡單探討一下,平民百姓中圍棋人口的變動情況。在封建社會中,平民百姓處于受壓迫受剝削的地位,文化知識水平較低,對于圍棋的接受能力,比知識分子要低得多。因此,圍棋在平民百姓中的開展,始終是一個普及的問題,而不是提高的問題。這個圈子里的圍棋人口最易受社會各種因素的影響,增減變化較大。例如在圍棋十分繁榮的明中期,按理平民百姓中的圍棋人口應該大大增多,但卻相應有所“減少”,原因也帶喜有劇性,即當時象棋由于變化較少,受到廣大平民百姓的喜愛,十分流行,結果就拉走了一部分圍棋人口。
明宣宗朱瞻基也愛下棋,他曾叫大臣黃福下棋,卻被黃福當場拒絕,君臣之間的對話十分有趣。據《從信錄》載:
宣德中,召用舊人蹇義等,皆承順,惟黃福持正不阿。命圍棋,曰:“臣不會看棋。”問:“何以不會?”曰:“臣幼時父師嚴,只教讀書,不教無益之事。”
黃福在性格上確布嚴肅剛直的特點,既使在對待下棋的問題上,也有充分地表現。只是他認為下棋是無益之事,則有失偏頗。但黃福的態度也有一定的代表意義,即有一部分讀書人仍認為下棋只是荒廢時間,并無太大意義。在圍棋發展的過程中,反對圍棋的呼聲一直沒有停止過。但我們可以看到這樣一種現象,漢、三國時期,這種呼聲比較強烈,而從兩晉、南北朝、唐、宋以來,這種呼聲逐漸減弱。比及明朝,只是個別人表示反對。有關明朝的史料中,象黃福這樣的例子極為少見。這種情況令人信服地說明,岡棋在發展的過程中,越來越深入人心。
明武宗朱厚照正德年間,朝廷中弈風大熾。明武宗本人十分喜歡下棋,有關他與寵臣江彬下棋的故事,《明史·江彬傳》中有一段簡單記載:
江彬,宣府人。……與賊戰淮上,被三矢,其一著面,鏃出于耳,拔之更戰。武宗聞而壯之……擢都指揮僉事。出入豹房,同臥起。嘗與帝弈不遜,千戶周騏叱之,彬陷騏死……
江彬的受寵,是因為做戰驍勇。但君臣“出入豹房,同臥起”,關系變得很不正常。江彬也是個佞人,專事慫恿諂媚,引誘武宗四出巡游,擄掠婦女珍寶。從江彬與武宗下棋不遜,也可以看出昏君與寵臣特殊關系的一個側面。所謂不遜,無非是江彬恃寵撒嬌,在下棋時,言語行動有逾君臣之分。千戶周騏叱之,結果“彬陷騏死”。因為一盤棋而惹下命案,自古以來還是第一次。
明朝中期圍棋活動無比興盛,是和官僚士大夫階層中的代表人物愛好圍棋分不開的。這些人或是臺閣重臣,或是文壇領袖,他們的喜好行止,對全國社會各階層,尤其在知識分子中,自有不容忽視的影響。
正德年間,臺閣重臣李東陽、楊一清、喬宇等三人深嗜圍棋,技藝不凡,時有“士大夫之冠軍”的稱譽。
李東陽(1447—1516),字賓之,號西涯,湖南茶陵人。天順年間進士,明孝宗時官至至文淵閣大學士。工詩文,是“茶陵派”之首領,明中期復古運動的先驅。
楊一清(1454—1530),字應寧,鎮江丹徒人。成化年間進士,正德時任吏部尚書,嘉靖初加華蓋殿大學士,為朝廷之首輔。
喬宇,字希大,樂平人。成化間進士,武宗時任南京兵部尚書,后加少保,嘉靖初吏部尚書。
李東陽等三人官居宰揆之地,棋藝也屬于業余高手,經他們身體力行的倡導,朝臣中弈風大熾,并經常比賽較量技藝,所以這三人才有冠軍之稱。李東陽等三人都和當時的國手范洪有過棋藝交往。“每延致對局,備極歡洽”。楊一清還與永嘉派著名棋手鮑一中交好,稱鮑一中為“小友”。這是因棋藝而引為同調,遂結為忘年之交。
宰臣與棋手交好,說明棋手的社會地位已大大提高。明朝的國手與唐、宋相比,身份有所不同。唐、宋時的國手大都在翰林院任棋待詔,大小是朝廷命官。明朝的國手幾乎全是布衣,趙九成因棋授官只是一個例外。因此他們的社會地位本不太高。李東陽等宰臣肯屈身下交,無疑樹立了一種良好的榜樣。從明中期乃至明末,名公巨紳無不以與著名棋手相交為榮,平常士紳人家也常延致著名棋手到家教棋,一時形成風氣。可以說,在當時士大夫眼里,著名國手與著名的詩人和小說家一樣。同屬于社會名流的范圍之內。
王穉登(1535—1612)字伯谷,武進(今屬江蘇)人。明文學家,嘉靖末游京師,入太學,晚年召修國史,未行而卒。王穉登生當圍棋活動熾熱的時候,因而在他的某些文章中記述了時人下棋的情景,如《荊溪疏》載:
王穉登入荊溪之日,坐舟中看萬子寅與吳幼元弈。子寅寬然長者也,喜怒不見顏色。惟弈,顧獨使氣,每楚風不競,輒提局擲子,迸散如走盤。幼元愈捧腹謔之,其氣愈盛,甚者自蒱頰。俄復手談,津津忘之矣。
王穉登的這一段記述,活生生刻畫出一個嗜棋人的形象,十分傳神。萬子寅平時喜怒不見顏色,唯獨下棋時“楚風不競,提局擲子”,甚至自批面頰。圍棋能移人性情一至于此。圍棋本是具有勝負之爭的競技,失卻勝負也就失卻了生命力。但是不同時期的人,對勝負的認識是不相同的,因此下棋時的表現也有很大不同。例如蘇東坡的“勝固欣然,敗亦可喜”,與萬子寅的“楚風不競,提局擲子”,恰成鮮明的對比。明人比宋人更重視勝負,并不是僅根據一兩個事例所得出的結論,而是一種普遍現象。這是因為,明時不僅下棋的人多,而且比賽頻繁,社會上各階層的人士經常進行正式或非正式的比賽,棋下得好的人,如高手、國手,社會地位也比較高。因此,明人對圍棋勝負的追求,要高于對藝術境界的追求。
明中期的文士名流,如“吳中四才子”的唐寅、文徵明、沈周等酷愛圍棋。這三位才子不樂仕進,不傍門戶,而以詩畫名世。在士大夫眼中,是清高類型的代表人物。
唐寅三人常在一起切磋棋藝,樂而忘返。沈周曾繪《觀弈圖》:古松之下,左文徵明、右唐寅,紋枰鏖戰,沈周自己居中作壁上觀。大門口白鹿徜徉,二童子捧茶而來。烘托出一種清幽典雅、不落世俗的氣氛,大抵是三人弈棋情景的真實寫照。
唐寅有詩云:“日長全賴棋消遣,計取輸贏賭買魚。”文徵明有詞云:”……難忘碧鳳坊中,酒散風生棋局,詩成月在梧桐。”可見棋癮是大的,態度也是認真的。據記載,沈周下棋從無架子,棋癮上來,便步入街坊,與“粗俚下人”對弈,興盡而歸。對于這些才子來說,酒,棋、詩構成了他們生活的主要內容。也正因為志趣相投,才結成了好友。
著名戲劇家湯顯祖也是一位圍棋愛好者,他有一段記述很值得注意:“潞河迎拜龍峰張老師,舟中琴客、棋師。”說明當時某些達官貴人,家中蓄有琴客、棋師,外出時也帶在身邊。湯顯祖的好友藏懋循、汪廷納、程伯書等人也都對圍棋入迷。棋友們遇在一起,往往“一局且優游”。其中藏懋循也是一位劇作家,《列朝詩集小傳》說他“每出必以棋局、蹴毬系于車后”。藏懋循謫歸湖北,湯顯祖曾設宴為之送行,贈詩曰:“深燈夜雨宜殘局,淺草春風恣蹴毬”。
象唐寅、沈周、湯顯祖、藏懋循等人,或無意功名,或官場失意,皆是對現實有所不滿的成名人物。他們熱衷于圍棋自有其思想根源,這就和作詩以傲世、飲酒以蔑俗一樣,下棋可以充實生活、寄托精神,聯絡朋友之間的感情,就一定意義上說,也是對統治者禁錮思想的一種抵制。唐寅有詩云:“眼前富貴一枰棋,身后功名半張紙。”這與他說:“我也不登天子船,我也不上長安眠。”在思想上是一脈相承的。既然把下棋看得比功名富貴還要重要,那就不只是愛好的問題了。
明中期圍棋的繁榮,吸引了大量的文人,將圍棋寫入他們的作品。明代的詩、畫、小說中表現圍棋或棋人棋事特別多,是歷代所不及的。
明代的圍棋詩,最具史料價值的,要屬吳承恩的兩首敘事詩:《圍棋歌贈鮑景遠》、《后圍棋歌贈小李》。
吳承恩(約1500—1582),字汝忠,號射陽山人,淮安府山陽人。嘉靖二十三年被錄為歲貢生,曾為長興縣丞,后徙寓南京,賣文為生。其所著神魔小說《西游記》,是深受中外人民歡迎的不朽之作。
《圍棋歌贈鮑景遠》云:
海內即今推善弈,溫州鮑君居第一。我于二十五年前,已見縱橫妙無匹。當時弱冠游淮安,后來蹤跡多江南。品流不讓范元博,收獎先蒙楊邃庵。能棋處處爭雄長,一旦遇君皆悵惘。甲第公侯飾馬迎,玉堂學士題詩訪。去年我客大江東,雞鳴寺中欣相逢。四方豪雋會觀局,丈室之間圍再重。架肩駢頭密無縫,四座寂然凝若夢。忽時下子巧成功,一笑齊聲海嘲哄。……
詩中所記鮑景遠,即永嘉派首領鮑一中。有關鮑一中的史料無多,這首詩卻提供了一些細節,極有價值。詩人與鮑一中的友情,可以追溯到鮑一中弱冠游淮安的時候。二十五年后相遇時,鮑一中已名被海內。詩中記述了當時社會對圍棋的推崇,“甲第公侯飾馬迎,玉堂學士題詩訪”,國手的身份是何等榮耀!“四方豪雋會觀局,丈室之間圍再重”,國手棋戰,引來各方知名人士,場面非同凡響。直到晚年,吳承恩仍回憶雞鳴寺的這一場棋賽:“夏簟照瑯玕,涼飔忽又至。一枕夢江南,棋聲在秋寺。”
吳承恩的另一首詩《后圍棋歌贈小李》,其中小李是何人,棋界頗多紛歧。有人認為小李是指永嘉派的另一位國手李沖。但筆者認為,更有可能是指京師派的國手李釜。原因是,詩中有云:“今年邂逅得小李,未知與鮑誰雌雄?”可知小李并未與鮑一中較量爭雄。李沖雖比鮑一中晚出,但兩人年齡相去不是太遠,又同為一派棋手,彼此之間不可能沒有較量。而李釜則是三派棋手中的后輩,據王世貞《弈旨》記載,李釜英氣無倫,四出挑戰之際,李沖已垂垂老矣。故可知李釜與李沖、鮑一中的年歲相去較遠。他未與鮑一中下過棋的可能性較大。
詩中對小李的技藝備加贊賞:“嗟君此手信絕倫,滿室觀者驚猶神。男兒不藝則已矣,藝則須高天下人。”小李傾慕吳承恩的文才,“苦苦索詩攀鮑例”,所以吳承恩才又寫這首《后圍棋歌》贈給他。名士與國手交往,可謂相得益彰。如果再聯系王世貞、馮元仲等人與棋手結交,并為之立傳,可知明中期時,士大夫階層已經打破歷史上對棋手的偏見,并以引為同調為榮。
吳承恩曾為劉幾曾《諸史將略》寫序云:“夫兵家之法,猶弈旨醫經,而史氏所載,則棋之勢、藥之方也。藥不必執方,而妙于處方者必效;棋不必拘勢,而妙于用勢者必贏……”吳承恩認為兵法、棋道、醫術有相通之處,可概括為“隨機應變”四個字。藥不必執方、棋不必拘勢,自然,兵也不必泥法。運用之妙,全在靈活變通。即以圍棋而論,吳氏所謂“棋不必拘勢,而妙于用勢者必贏”,確是千古不移之談。
吳承恩在他的傳世名著《西游記》中,多處描寫圍棋活動。如“老龍王拙計犯夭條,魏丞相遺書托冥吏”,虛構唐太宗與魏征下棋,魏征夢斬涇河龍的故事。其中引錄一段《爛柯經》,內容與《棋經十三篇·合戰篇第四》基本相同。并賦詩云:“棋盤為地子為天,色按陰陽造化全。下到玄微通變處。笑夸當日爛柯仙。”在吳承恩生花妙筆之下,圍棋活動遍及仙界人間。既使是樵夫李定也“閑觀縹緲白云飛,獨坐茅庵掩竹扉。無事訓兒開卷讀,有時對客把棋圍”。李定的形象帶有作者主觀的色彩,可以看作是吳承思自己嗜好圍棋的某種反映。
明代的著名小說中,除《西游記》外,《三國演義》、《金瓶梅》、《初刻拍案驚奇》等書中均有關于圍棋的描寫。《三國演義》描繪曹操、孫策、建安七子弈棋,均甚簡略,但也有史實依據,只有關云長下棋刮骨療毒,系作者虛構。但《三國演義》成書于元末明初,故其中關于圍棋的描寫,很少能見到明朝圍棋活動的影子。從圍棋史的角度考慮,《金瓶梅》、《初刻拍案驚奇》較有參考價值。
《初刻拍案驚奇》中“小道士一著饒天下,女棋童兩局注終身,”即是一篇描寫兩個圍棋高手,因下棋終成眷屬的傳奇故事。故事來源于《續夷堅志》中的一段極為簡略的記載,而由凌濛初大事鋪衍。考其內容,作者揉合大量歷史上有關圍棋的記載、傳說、故事,又結合明代社會上圍棋活動的一些情況,虛構而成小說。例如,圍棋史上“王質爛柯”、“王積薪遇孤姥”等傳說,“顧師言鎮神頭勝日本王子”、“劉仲甫錢塘奉饒天下棋先”等故事,作者皆改頭換面寫進小說。小說雖假托為宋代,但其中許多情節,尤其是細節的描寫,并不見于宋代的史料記載,而與明代的一些記載相吻合。故也可幫助我們了解明代社會圍棋活動的某些情況。
小說以主人公國能下棋求親為線索,從農村寫到都市。小說寫國能在農村,“因為棋名既出,又兼年小希罕,便有官員、士夫、王孫公子與他往來。又有那不伏氣、甘折本的小二哥與他賭賽,十兩五兩輸與他的。國能漸漸手頭饒裕,禮度熟嫻,性格高傲,變盡了村童氣質,弄做個斯文模樣”。小說寫國能在京師,“但是對局,無有不輸與小道人的,棋名大震。往來多是朝中貴人,東家也來接,西家也來迎,或是行教,或是賭勝,好不熱鬧過日”。
這些描寫基本是現實主義的。表現國能如何由一個村童,因棋下得好,而為上流社會所接納。如若聯系明代中末期一些圍棋國手的生平來看,國能的經歷多少和他們有相似之處。特別是國能在京師名利雙收。“或是行教、或是賭勝”,也可以概括明代一些圍棋高手的日常生活情況。明代的高手已不如唐,宋,想憑棋藝做官是不容易的,生活來源主要靠教棋和賭彩。有時也接受達官貴人的饋贈,關于這一點,小說在后半部分也有所表現。
小說幾次描寫國能與女棋手妙觀對弈的情景,模擬真實,沒有破綻。想來凌濛初于圍棋也有相當造詣。但其中寫妙觀受朝廷冊封為“女棋童”,設個棋肆,教授門徒,“多有王侯府中送將男女來學棋”,則不見于宋、明史料記載,或許只是小說家的虛構。
有關我國民間圍棋的發展情況,正史中的記載幾近闕如,大多見于稗官野乘、小說筆記之中。例如明代著名小說《金瓶梅》中,有多處關于圍棋活動的描述。是對現實生活的真實反映,抑或只是小說家的虛構?無疑是一個有待探討的問題。
作為一部現實主義的杰作,《金瓶梅》主要描寫的是明代城市市民階層中的人物和他們的生活。諸如亦官亦商的惡霸土豪西門慶,他們的侍妾潘金蓮、孟玉樓,市井無賴應伯爵、謝希大,娼妓李桂姐等。以至于太監、門官、僧侶、尼姑、道士、媒婆,形形色色在城市里寄生和活動的這一類人物,都生動活潑地走進作品里來了。《金瓶梅》將市民各階層的人物的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寫得如此詳瞻遼闊,這是任何一部歷史教科書所無法比擬的。
因此,從一定意義上講,《金瓶梅》中有關圍棋的描述,應是對現實生活的真實概括,可補史料記載之不足。對于我們了解明代中期市民階層的圍棋活動,有相當的認識價值。
明代中期我國圍棋無比繁興的局面,在前面已多所敘述。圍棋興旺發展的情況,不可避免地會反映到文學作品如小說之中。《金瓶梅》的可貴之處在于,它并不是描寫社會上層,如臺閣重臣,士林雋彥、國手名流的圍棋活動、而是描繪社會下層的一部分——城市市民階層的圍棋活動。
據筆者粗略統計,《金瓶梅》一書中描寫下棋(圍棋、象棋)的地方有十四處,以較大篇幅描寫圍棋活動的有四處。下面就書中的有關描寫,做一些簡單分析。
一、《金瓶梅》介紹出場人物時,往往有“能否下棋”這一項。如第二回介紹西門慶“使得些好拳棒,又會賭博,雙陸象棋、抹牌道字無不通曉”。如若對照《水滸傳》描寫西門慶的文字,就會發現,所謂“雙陸象棋,無不通曉”,乃是《金瓶梅》的作者加上去的。其它如第三回王婆向西門慶介紹潘金蓮:“雖然微末出身,卻倒百伶百俐,會一手好彈唱,針指女工,百家奇曲,雙陸象棋,無般不知。”第七回媒婆薛嫂兒介紹販布楊家的寡婦孟玉樓:“風流俊俏,百伶百俐。當家立紀、針指女工、雙陸棋子,不消說……又會彈一手好月琴。”第十八回寫西門慶的女婿陳經濟:“詩詞歌賦、雙陸象棋、拆牌道字,無所不通,無所不曉。”
需要指出,這里雖然只講“雙陸象棋”,但從第十一回描寫西門慶與潘金蓮、孟玉樓下棋,“三人下了一盤,潘金蓮輸了,西門慶才數子兒,被婦人把棋子撲撒亂了”。可知這三人也都會下圍棋。
《金瓶梅》在介紹人物時,往往加上“能否下棋”這一項,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我們知道,在唐、宋的史籍中,能否下圍棋是判斷士人才能高低的一種標準。但沒有材料表明,當時在市民階層中也曾應用這種標準。可是到明代中期,情況已經發生變化。這種變化表明,圍棋和象棋在市民階層中廣泛流行,成為他們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文娛活動,只有在這樣的情況下,“能否下棋”才會成為市民階層判斷人物的一種標準。
二、《金瓶梅》描寫市民階層的圍棋活動是比較深入的,既描寫了家庭和婦女的圍棋活動,也描寫了社會上妓女和市井邦閑的圍棋活動。
家庭是社會構成的基本單位。《金瓶梅》主要表現西門慶一家的生活,這個家庭人口眾多,構成復雜。而社會上形形色色的人物也經常出入這個家庭,使這個家庭成為社會生活的一個縮影。據《金瓶梅》的描寫,這個家庭上上下下都喜愛圍棋、象棋,例如:第十一回寫西門慶和他的侍妾孟玉樓、潘金蓮下圍棋取樂,贈一兩銀子的東道。第十八回寫潘金蓮與陳經濟下棋,“便使丫環,叫進房中,與他茶水吃,常時兩個下棋作一處”。第十九回寫西門慶的夫人吳樂娘約同眾侍妾去新花園賞玩,在臥云亭里與孟玉樓、李嬌兒下棋。第二十三回寫午間孟玉樓、潘金蓮都在李瓶兒房里下棋,賭五錢銀子的東道,買豬頭燒著吃。
不僅主人一層的人物下棋,就連仆婦、丫環也常以下棋取樂。第二十三回寫家人來旺的媳婦惠蓮常去潘金蓮處,“和金蓮、瓶兒兩個下棋抹牌,行成伙兒”。第七十八回寫“丫環迎春打發吃了飯,走到隔壁和春梅(金蓮的丫環)下棋去了”。
從書中的這些描寫可以看出,下棋(圍棋、象棋)已經成為西門慶一家人普遍喜愛的消遣,也是他們生活中很普通、但又不可缺少的文娛活動。這個家庭里的成員出身和社會地位十分復雜:西門慶屬于市民階層中的暴發戶,他的繼室吳月娘是官宦千金,而在他的侍妾中,潘金蓮來自小本經營(賣炊餅)、孟玉樓來自商賈家庭(販布)、李嬌兒,李瓶兒則屬于妓女從良。此外,陳經濟是書香子弟,下人惠蓮、迎春、春梅大致來自市民或鄉村中的貧寒家庭。這一干人的出身、地位、教養、趣味都有很大差異,但又都喜愛下棋,說明當時圍棋和象棋在市民階層中廣泛流行。
對于社會上的圍棋活動,《金瓶梅》主要描寫市民階層中兩類地位比較卑賤的人——妓女和市井邦閑的下棋情況。如第四十九回,西門慶招待兩淮巡鹽蔡御史,叫來兩個妓女董嬌兒、韓金釧兒陪酒,“令書童取棋桌來,擺下棋子,蔡御史與董嬌兒兩個著棋,西門慶陪侍,韓金釧把金樽在旁邊遞酒”。蔡御史先贏董嬌兒一盤,飲了酒兩人又下,董嬌兒贏了。再如第五十四回,寫市井邦閑應伯爵、謝希大、白來創、常時節弈棋賭彩的情景,模擬真實、細致入微。大凡妓女要接待文化情趣較高的人物,如官僚、讀書人等,市井邦閑也要出入有錢有勢的上等人家,因此這兩類人都需掌握一定的棋藝技能,以抬高自己的身價,作為謀生的手段。這兩類人盡管社會地位“卑賤”,所干營生也非光彩,但圍棋在他們之中卻很流行。《金瓶梅》在這些地方的刻畫都是真實可信的。
三、《金瓶梅》一書中,描寫圍棋活動最長的文字,要屬第五十三回“應伯爵郊園會諸友”。這一回從細節上全面刻畫市井邦閑白來創、常時節下圍棋的情景、情態逼真,維妙維肖。例如寫白來創悔棋耍賴:
……那白來創果然要拆幾著子,一手撇去常時節著的子,說道:“差了,差了,不要這著。”常時節道:“哥子來,不好了!”伯爵奔出來道:“怎的鬧起來?”常時節道:“他下了棋,差了三、四著,后又重待拆起來,不算帳。哥做個明府,那里有這等率性的事。”白來創面色都紅了,太陽里都是青筋綻起了,滿面涎唾的嚷道:“我也還不曾下,他又撲的一著了。我正待看個分明,他又把手來影來影去,混帳得人眼花撩亂了。那一著放才著下,手也不曾放,又道我悔了。你斷一斷,怎的說我不是?”……
下棋而悔棋,并非市井邦閑的“專利”,在圍棋愛好者中也常見到悔棋的現象。但象白來創那樣悔棋耍賴,強辭奪理,一點不講棋品道德,很符合池市井無賴的身份。
從書中的描寫看,白來創與常時節下棋是有二、三錢銀子的彩頭。聯系前面所述,西門慶與潘金蓮等下棋賭一兩銀子,潘金蓮與孟玉樓等下棋賭五錢銀子,可知當時市民之間下棋也往往是有彩的。大約從宋朝開始,乃至明、清之際,圍棋賭彩已成為職業棋手謀生的重要手段,賭注有時也大得驚人,這在宋、明、清的史料中屢見不鮮。《金瓶梅》所描寫的市民下棋賭彩,由于是在家庭或朋友之間進行,賭注不大,所謂聊以應景而已。然而圍棋賭彩在明中期已成為社會風氣,則是毫無疑問的。
王世貞(1526—1590),字元美,號“鳳洲”、“弇州山人”。太倉(今屬江蘇)人。明代著名文學家。嘉靖二十六年進士,官至南京兵部右侍郎、邢部尚書。與李攀龍、謝榛等人倡導文學復古運動,史稱“后七子”。
王世貞活動的年代,正棋壇無比興旺,永嘉、新安、京師三派鼎立,群雄紛爭之際。王世貞既好圍棋,曾親睹國手顏倫對弈,又與新安派程汝亮、京師派李釜(時養)交好。世貞經常與李釜討論有關圍棋的問題,縱談古今的高手及當時三派棋手的特點。《弈問·序》云:
余既與李時養論弈,歸而臆數其人與品,手書貽之。乃其事有奇而未可據者,因再疏一通為《弈問》,俟后博考傳記,毋妨再續也。
這里說的是他寫《弈旨》、《弈問》的經過。《弈旨》有云:“吾請得為時養略言之……”,又云:“余因作《弈旨》,手書一通貽時養。”可見《弈旨》是為李釜而作。大約世貞與李釜論弈,受到啟發或受李釜之托,歸而寫《弈旨》后因余興未盡,又將“其事有奇而未可據者”,再寫為《弈問》。
《弈旨》從“堯造圍棋,丹朱善之”寫起,敘述歷代圍棋興衰及代表人物,雖簡而約卻包羅完備,以一千余言,即概括兩千余年的圍棋史,確是手筆不凡。其于明代敘述較詳,尤其是正德、嘉靖年間,棋壇流派,特點以及各派棋手之變遷,皆有中肯的論述。世貞似乎對當時的國手十分折服,他將《弈旨》貽時養,“謂與顏而程四子者,不知于古何如,以當明第一品無愧也!”言外之意是說,今天與顏倫、程汝亮受四子的人,大約可以和古代高手相比肩,未免溢美之過甚。
《弈問》的內容,主要是對圍棋史上的一些疑難問題予以解答,其中不乏獨到的見解。例如:顧師言三十三著勝日本國王子,世貞持懷疑態度。對僧一行所說“四語乘除,人人國手,”以及陸子靜一悟河圖數而勝國手等事,世貞認為是不可能的。圍棋藝術有其獨特性,其它學問雖可觸類旁通,有所啟發,但要達到國手的水平也是十分困難的。如若將各類事物的共性混為一談,忽略各自的特性,認為精于數學就能成為國手,顯然是錯誤的。對于南北朝時范寧兒勝王抗、宋時祝不疑勝劉仲甫,世貞認為不是勝在棋力上,而是勝在“有心”和“乘暇”等機會上,大抵是公允之論。又如王粲、陸瓊“覆局”,歷來被吹得神乎其神,世貞認為:這并不表明他們的棋高,只是善于記憶罷了。《弈問》最后云:
問:孟堅之有旨也,應璩之有勢也。馬融、曹攄、王粲、劉恢、蔡洪、梁宣之有賦也,李尤之有銘也,高品哉?曰:唯永嘉林生(林應龍)有集焉,而品第五也。此工于文者也,非與于品者也,問:吾子何如?曰:猶之乎數子而已矣。
在這里,世貞承認自己的棋藝水平不高,但認為寫圍棋著述不必非棋品高不可,即所謂“此工于文者也,非與于品者也”。世貞自許可與馬融、王粲、應璩等人同列,意在表明自己著述圍棋的志愿。以他文壇領袖的地位,又于圍棋深有研究,要寫棋史方面的著作,自是“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了。
王思任(1574—1646),號謔庵、遂東。山陰(今浙江紹興)人。萬歷進士,曾任九江僉事、袁州推官。清兵破南京后,魯王監國,任禮部右侍郎,進尚書。順治三年紹興城破,絕食而死。
思任善畫,詩文俱佳。其所著《弈律》,乃是一篇有關圍棋方面的奇文,初看似是游戲筆墨,細讀起來卻也耐人尋味。
文章開宗明義即說:“律之作也,以繩強也;而予之作律,以繩弱也。……情通之不可,理解之不可,則不得不齊之以法!”意思是說:下圍棋本是雅事,如若棋品低下,不通情理,不得不繩之以法。從這一點看,王氏可謂嗜棋而好事者矣。
他所擬定的“弈棋”條文,都是下棋的人應遵守的規矩,或是應講求時道德。試舉數例如下:
1.凡局已分勝負,因而挾憤逃去不終者,杖一百。
2.凡旁觀原無確見,而恣口得失,代人驚喜者,笞五十。
3.凡旁觀將機密重情及緊關事務泄漏,而又代為打點者,枚一百。
4.凡對局時,兩相忿爭者,各杖七十。
5.凡下子須正大明白,若翻混、起倒、觀望者,俱以違法論,笞五十。
6.凡弈時腐吟優唱,手舞足蹈,狂惑觀聽者,俱笞五十。
7.凡以弈諂事貴長,巧為稱頌者,杖七十。或隱忍退敗,有所圖為者,杖一百。
作者所列舉的這些情況,都是某些棋手和棋藝愛好者常犯的毛病,即使在今天也屢見不鮮。有時習慣成自然,也就不以為非了。然而“棋雖小道,品德最尊”,提倡棋品道德,講求文明禮貌,還是十分必要的。一位棋德不佳,不拘小節的棋手,他在探索棋藝的道路上,恐怕很難有長足的進展。
《弈律》的出現,極大適應了明中期至明末社會上圍棋活動異常活躍的情況。由于下棋的人越來越多,其中不免魚龍混雜,各種不良的風氣也隨之而生。其末流,不僅不講究棋品道德,簡直把圍棋當作商品或手段,諂事貴長,巧為稱頌,賭博騙錢,不一而足。王思任目睹弈棋時,不良風氣所帶來的種種弊端,有感于棋道之不振,作《弈律》而提倡良好的弈棋風尚,用心可謂良苦。千載而下,仍可為棋手及棋藝愛好者所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