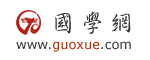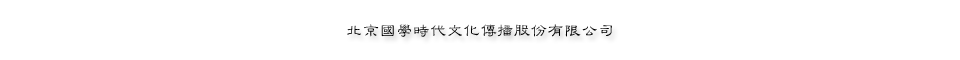第五節 民國時期的圍棋著作、書譜
民國時期,圍棋著作、書譜比清末有較大發展,日本名手的著作、對局逐漸上升為重點介紹內容。日本圍棋理論、日本棋手等級制度、中日圍棋交流狀況、日本棋界動態等,開始成為中國棋手與棋藝愛好者共同關注的問題。
從民國初期直至三十年代初,編譯的日本棋譜主要有《日本第一國手棋譜》(上海有正書局出版,主要介紹道策等日本古代國手對局),《新桃花泉》(上海有正書局出版,介紹日本圍棋定式),《東瀛圍棋精華》(陶審安編譯,介紹日本自19世紀以來的名局,由張澹如委托日本東京高橋印刷所刊印),《布局詳解》、《圍棋布局研究》(日本布局著作,二書均由吳祥麟編譯,上海共和書局出版),《丈和弈譜》(即日本棋譜《國技觀光》,上海文瑞樓重印),《圍棋布局要則》(胡檢如編譯,過旭初編校,江西建設廳圖書館發行)等。以上書譜,反映了當時所了解到的日本先進圍棋技術,深受讀者歡迎。其中,《東瀛圍棋精華》一書選材較精,評解細致,又附有對局者簡介,被公認為編譯棋譜中的成功之作。
介紹中日圍棋交流的棋譜有《問秋吟社弈評初編》(汪云峰評輯,1917年北京宣元閣印刷,選載日本高部道平與中國北方棋手的對局)和《中日圍棋對局》(1919年上海有正書局出版,選載日本高部道平、長濱彥八等與我國南方棋手的對局,另附有少量顧水如留日時期對局)。這些棋譜將民國初期中、日圍棋水平的巨大差距如實展示在讀者面前,具有文獻價值。可是,從二十年代直至抗戰勝利間的大量中、日棋手對局,都從未系統整理,僅在報刊偶有披露,以致散失情況嚴重。
重刊中國古譜,在民國棋譜中也占有一定比重。其中,以上海文瑞樓印數最多,前后近30種,其中十之七八均是古代棋譜,在普及、宣傳圍棋方面起了作用。
圍棋筆記、棋話是民國圍棋著作中別具特色的一部分,較有影響的有黃銘功撰《棋國陽秋》(1917年羅湘黃氏刊本),陶審安以“東籬軒居士”筆名發表的弈話(刊于二十年代《新聞報》),胡先庚撰《繹志齋弈話》(刊于《小說月報》),沈子丞編著《圍棋叢談》(附于沈著《圍棋與棋話》中),徐潤周撰《近樓弈話》(刊于《圍棋通訊》)。這類著作或記述耳聞目睹的棋人棋事,或介紹日本棋界動態,或選編地方文獻、史書、說部中有關圍棋資料,使讀者對圍棋常識有較深入的了解,也為后人系統研究棋史提供了材料。
另有上海徐去疾編著的《圍棋入門》(1929年上海文明書局出版。)此書除闡述一般圍棋著法外,還包括當時國內名手、中日圍棋等級制度、傳統圍棋術語、古代圍棋藝文的有關著錄,堪稱是一本比較全面的圍棋知識教材。按著者自序,此書脫稿于著者旅歐期間,曾被譯為意、英、法文字在歐洲發行,直至著者歸國后始在國內付印。據傳,這是我國第一冊譯為西方文字的圍棋著作。
民國期間,部分地方棋會、棋手曾編印定期圍棋刊物,這對圍棋普及、提高無疑有重要意義,但因多種社會原因,鮮有能維持一年以上的。例如:1922年“成都圍棋俱樂部”發行我國最早的定期圍棋刊物《弈學月刊》(由鄧元鏸等編)。在此刊發行后不到半年間,“成都圍棋俱樂部”就曾三遷會址:1922年1月設于“總府街福建會館內”,同年4月遷至“凍青樹上全堂南間壁”,旋又遷至“丁公祠三友軒”。僅此一端,就可斷定在創辦刊物時困難重重。因此,僅發行1年12期。
1937年1月,上海“中國圍棋社”編印《中國圍棋月刊》(由劉于長、沈伯樂編輯)創刊,曾在南京、北京、杭州、漢口、成都、重慶、沈陽、太原、福州、廈門等全國20個大、中城市出售,一時頗具聲勢。可是前后僅見7期,就此戛然而止,顯然受到了抗戰全面爆發的影響。
1948年4月,上海棋手胡沛泉、余世浚發行《圍棋通訊》,每月1號,至1949年5月上海解放時停刊,計12號,每號不足10頁。這是民國時期最后發行的圍棋定期刊物。
此外,抗戰前夕北京的“北平圍棋會”,建國前夕的“中國圍棋會重慶分會”均曾發行圍棋特刊,但期數更少,影響亦小。
以上圍棋刊物雖然發行時期短暫,無法反映民國圍棋發展的全貌,但因民國年間報刊盛行,而圍棋信息又是讀者喜聞樂見的內容之一,所以客觀上保存了部分圍棋資料,也多少彌補了棋譜、刊物的不足。這些報刊有民國初期至二十年代后期的《時報》、《時事新報》、《生報》、《新聞報》、《北京晨報》、《小說月報》、《雅言》、《藝觀》;三十年代前后的《大公報》、《商報》、《前線日報》、《無錫日報》、《新春秋》;三四十年代的《庸報》、《鐵道雜志》等,都曾采用各種形式宣傳圍棋。其中,如三十年代上海張恒甫等選送報刊登載的《豳風·圍棋欄》就具有采摭面廣(除介紹中日名手對局外,還選載少量德國棋手的對局),選譜、評譜質量較高,又經常登載上海及各地圍棋活動信息等特點,具有文獻價值,對當時棋界也廣有影響。
民國時期發行的書譜(包括報刊圍棋欄)遠遠不能滿足讀者的需求。一般棋譜印刷比較粗糙,又限于水平,在編輯方法上也存在次序凌亂、內容貧乏等很多問題,說明當時棋藝出版事業仍處于落后的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