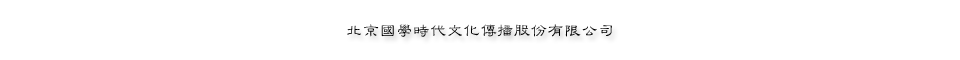第六節(jié) 著名國(guó)手
(1)一代大師吳清源
吳清源,1914年生,福建閩侯人。祖上世代作官,但是到他父親一輩家道中落。他的父親吳炎曾留學(xué)日本,因?yàn)橄埠脟澹?jīng)常出入本因坊村瀨秀甫創(chuàng)立的“方圓社”。
吳清源8歲時(shí),父親開(kāi)始教他下棋,并讓他學(xué)習(xí)從日本帶回的棋譜。10歲時(shí)父親帶他到“海豐軒”等茶館棋室下棋,結(jié)識(shí)了當(dāng)時(shí)的一些名手。11歲時(shí)一些老國(guó)手如汪耘豐已不是他的對(duì)手,因此被譽(yù)為神童。當(dāng)時(shí)在北京有個(gè)“日本人俱樂(lè)部”,聞聽(tīng)吳清源的聲名,邀請(qǐng)他去下棋,對(duì)手是個(gè)有職業(yè)初段棋力的人,結(jié)果吳清源獲勝。
在觀戰(zhàn)者當(dāng)中有一位日本商人,名叫山崎有民,與日本著名棋手瀨越憲作熟識(shí),他寫(xiě)信給瀨越,說(shuō)北京有個(gè)圍棋天才少年。后來(lái)他作為吳清源的代言人,與瀨越之間書(shū)信往來(lái)多達(dá)五十余封,商討吳清源赴日本留學(xué)事宜。
1926年夏天,巖本薰六段、小杉丁四段訪(fǎng)問(wèn)北京。吳清源與他們下了幾局棋,與巖本受三子兩局全勝、受二子一局輸兩目,與小杉丁受二子一局勝。結(jié)果吳清源的實(shí)力被大大證實(shí)。消息傳到日本后,瀨越等人決心促請(qǐng)吳清源赴日。瀨越積極奔走,向犬養(yǎng)術(shù)堂、大倉(cāng)喜七郎等財(cái)、政界人士游說(shuō)。最后由日本國(guó)內(nèi)發(fā)出指令,委托駐北京公使芳澤全權(quán)交涉辦理。芳澤去找吳清源的義父、剛從“北京政府國(guó)務(wù)次官”寶座上退職的楊子安商量。告訴他日本方面的決定:由日本棋院副總裁大倉(cāng)喜七郎作保,以?xún)赡隇橄蓿吭掳l(fā)給吳清源200元生活費(fèi),并徹底考察其才能之深淺。但楊子安以“清源尚是幼童,身體亦非健壯”為由,希望等兩年再說(shuō)。
1927年,吳清源執(zhí)白勝劉棣懷,名副其實(shí)坐上國(guó)內(nèi)第一把交椅。那年夏天,井上孝平五段來(lái)北京,指名與吳清源對(duì)局,目的是想試探一下他的棋力。先讓二子一局,井上大敗,他自認(rèn)沒(méi)有力量讓二子,又改為讓先下三局。第一局弈于青云社,僅137手,井上已明顯劣勢(shì),被迫封局。第二局弈于李律閣宅,吳清源快勝。第三局弈于張伯駒宅,井上使出渾身解數(shù)方始獲勝。井上回國(guó)后,稱(chēng)贊“吳清源有勝過(guò)傳聞之才能”,引起日本棋界的高度重視。山崎有民還將吳清源的一些對(duì)局譜寄給瀨越先生,瀨越經(jīng)仔細(xì)研究之后,認(rèn)為吳清源的棋風(fēng)與棋圣秀策極為相似,是一個(gè)罕見(jiàn)的天才,應(yīng)盡早予以培養(yǎng),將來(lái)一定能取得杰出的成就。
這一年秋天,瀨越先生給吳清源發(fā)來(lái)正式邀請(qǐng)書(shū),內(nèi)容如下:
謹(jǐn)啟,前幾日,通過(guò)山崎氏收到了你的來(lái)涵,謝謝!我雖未有與你直接見(jiàn)面的機(jī)會(huì),但過(guò)去從巖本氏那里聽(tīng)說(shuō)你年紀(jì)雖幼,但棋力高強(qiáng)。這次,我又看了你與井上氏對(duì)弈的三局棋譜,更加敬服你的非凡器量。若是敝人的健康與時(shí)間允許的話(huà),我真想去拜訪(fǎng)貴地,與你親切切磋棋藝。然而事情可能不允許,我深感遺憾。
我急切盼望你身體強(qiáng)健,完成大禮后,到日本留學(xué),從而共同不斷地研究。愿你能在不久的將來(lái)榮升為名人。我的拙劣之作一二冊(cè)已寄到山崎氏那里,在你來(lái)日之前,若肯為我研究一下,我將感到十分榮幸。你和劉氏下的二局棋譜,加上我妄下雌黃式的評(píng)論,已在《棋道》六月號(hào)上登載,同時(shí)綜述貴國(guó)棋界現(xiàn)狀的文章也冒昧登載于上。因此,務(wù)必請(qǐng)你諒解。
擱筆之時(shí),謹(jǐn)拜托你向貴國(guó)的棋伯諸賢們轉(zhuǎn)達(dá)我的問(wèn)候,遙祝你身體健康!
對(duì)于不了解內(nèi)情的人,恐怕很難想象這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著名棋士寫(xiě)給12歲孩子的信。瀨越先生求賢若渴的遠(yuǎn)見(jiàn)卓識(shí)、虛懷若谷的非凡雅量,在這封信中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
1928年,瀨越先生又派遣高徒橋本宇太郎四段來(lái)到北京,正式考察吳清源的棋力。吳清源執(zhí)黑弈了兩局,以六目和四目獲勝。
這樣,在中日兩國(guó)有關(guān)人氏的盡力促成之下,吳清源赴日留學(xué)一事最后決定下來(lái)。日本方面的安排是由望月圭介先生作保,吳清源入瀨越先生門(mén)下修業(yè),并由大倉(cāng)喜七郎以?xún)赡隇橐黄谙蓿吭轮Ц?00元生活費(fèi)。
有關(guān)吳清源赴日之際,還有一段插曲。當(dāng)時(shí)在北京維持治安的靳云鵬將軍曾答應(yīng)送吳清源1000元路費(fèi),但在吳清源即將動(dòng)身時(shí),這位北洋將軍正在河南與國(guó)民軍打仗,不想突然犯了煙癮,滿(mǎn)地打滾,結(jié)果一敗涂地逃回北京。原答應(yīng)給吳清源的錢(qián)因此降為500元,雖說(shuō)少了一半,但對(duì)吳清源到日本后的生活也很有幫助。
1928年10月18日,14歲的吳清源在母親和兄長(zhǎng)吳浣陪同下,從天津塘沽上船,告別祖國(guó),向那傳說(shuō)是日出的地方進(jìn)發(fā)。當(dāng)時(shí)中日兩國(guó)棋界都對(duì)這個(gè)孩子寄予很大期望,而他也沒(méi)有辜負(fù)這種期望。
吳清源初到日本,首先遇到的問(wèn)題是日本棋院究竟授予他幾段稱(chēng)號(hào)?瀨越先生堅(jiān)持說(shuō)他完全有三段的實(shí)力,但大多數(shù)棋士認(rèn)為頂多授予初段。于是決定按三段資格進(jìn)行“試驗(yàn)對(duì)局”。
這次“試驗(yàn)對(duì)局”充滿(mǎn)濃烈的國(guó)際比賽氣氛,這是因?yàn)閰乔逶粗皇且粋€(gè)14歲的中國(guó)孩子,而日本的棋士14歲能入段的都極少,如果吳清源一來(lái)就定為三段,許多人感情上接受不了。吳清源第一局對(duì)篠原正美四段,執(zhí)黑中盤(pán)勝。第二局對(duì)秀哉名人(受二子),此戰(zhàn)關(guān)系重大,因?yàn)榘串?dāng)時(shí)的規(guī)定,九段讓三段三子,只讓二子已經(jīng)是破格對(duì)待,這盤(pán)棋也就成為年輕棋手們極為注目的一局,對(duì)局過(guò)程中,他們?cè)j(luò)繹不絕地前來(lái)觀戰(zhàn)。結(jié)果吳清源四目勝,秀哉名人評(píng)論說(shuō):“黑棋態(tài)勢(shì)極其莊重堅(jiān)實(shí),成功地將優(yōu)勢(shì)保持到了最后,布武堂堂,未給白棋以可乘之隙,此二子局可作為快心之杰作。”隨后,吳清源又對(duì)村島紀(jì)誼四段黑先五目勝,被正式定為三段。
從1929至1932年這三年時(shí)間中,是吳清源來(lái)日本后最熱心學(xué)棋的時(shí)期。尤其在黑棋對(duì)本因坊秀策、白棋對(duì)本因坊秀榮的對(duì)局譜如饑似渴地深入研究。那一時(shí)期,吳清源段位不高,執(zhí)黑棋為多,以秀策流為主體,戰(zhàn)績(jī)輝煌,獲得了“黑先無(wú)敵”的美譽(yù)。例如1932年的對(duì)局成績(jī)是44勝5敗1平,晉升為五段。
升入五段之后,吳清源執(zhí)白增多,由于當(dāng)時(shí)無(wú)貼子的規(guī)定,若仍然照昔日的小目定式,白棋無(wú)論如何會(huì)落后于人。吳清源開(kāi)始打出三三或星的布局,一手占據(jù)角地,盡快向邊展開(kāi)。這種思路在吳清源看來(lái)是理所當(dāng)然的,但以小目締角為傳統(tǒng)的日本棋界卻受到巨大震動(dòng)。
這一時(shí)期的木谷實(shí),布局總是投在低線(xiàn)位上,但戰(zhàn)績(jī)不佳,便不斷地改為高線(xiàn)位上投子,開(kāi)始“比角地更重視中央勢(shì)力”的摸索階段。這樣吳清源和木谷實(shí)這兩位年輕的俊杰,在各種棋戰(zhàn)中都有意識(shí)地打破常規(guī),在布局階段即占據(jù)高位,使對(duì)手大驚失色,當(dāng)時(shí)被稱(chēng)為“新布局”,在日本棋界掀起一場(chǎng)革命。吳清源和木谷實(shí)運(yùn)用“新布局”勝率很高,從而鼓動(dòng)起人們對(duì)它的熱情,棋手們紛紛模仿“新布局”,棋盤(pán)上到處都展開(kāi)壯麗的“空中大戰(zhàn)”。
從幕府初期本因坊算砂開(kāi)始,日本拋棄中國(guó)“座子”制度,開(kāi)創(chuàng)自由落子。但在300余年的發(fā)展過(guò)程中,又形成以“小目”為基礎(chǔ)的模式。“新布局”的誕生,使“小目”定式所束縛的布局又得到解放,棋手的思維方法獲得自由,棋盤(pán)上的世界變得更加寬廣。日本著名作家川端康成曾寫(xiě)《新布局的青春》一文,贊揚(yáng)說(shuō):
木谷實(shí)、吳清源創(chuàng)造新布局的時(shí)代,不僅是二人蓋世天才的青春時(shí)代,實(shí)際上也是現(xiàn)代圍棋的青春時(shí)代。新布局仿佛是一陣春風(fēng),她吹燃起青春獨(dú)具的創(chuàng)造與冒險(xiǎn)的熱情之火,給棋界帶來(lái)了絢麗燦爛的春天。雖然繼木谷、吳之后,又涌現(xiàn)出了優(yōu)秀的后來(lái)者,但是可以想象,像新布局時(shí)代的木谷、吳那樣旗幟鮮明地振興棋壇、劃時(shí)代的一代新人還未光臨。當(dāng)年木谷、吳創(chuàng)造的新布局,是今日弈苑鮮花盛開(kāi)的祥瑞。
1933年,正當(dāng)“新布局”的旋風(fēng)席卷日本棋壇之際,《讀賣(mài)新聞》社舉辦“日本圍棋選手權(quán)戰(zhàn)”,并規(guī)定棋戰(zhàn)的優(yōu)勝者可以執(zhí)黑與秀哉名人一決高低。由當(dāng)時(shí)實(shí)力最強(qiáng)的16名棋士參加單淘汰比賽,結(jié)果吳清源在最后關(guān)頭連勝木谷實(shí)、橋本宇太郎而獲優(yōu)勝。
日本各新聞報(bào)刊都以“不敗的名人對(duì)鬼才吳清源的決戰(zhàn)”那樣醒目的標(biāo)題大肆宣揚(yáng),引得全國(guó)無(wú)數(shù)圍棋愛(ài)好者傾心注目。
當(dāng)時(shí),吳清源正處于用“新布局”下棋的顛狂時(shí)期,思想無(wú)拘無(wú)束,開(kāi)局便按照三三、星、天元順序打了出來(lái)。不想這種下法引起了一場(chǎng)軒然大波,從而轟動(dòng)朝野。原來(lái)吳清源的這三手棋與本因坊家的布局教條格格不入,尤其是三三,在本因坊一門(mén)中被定為“禁手”,因此坊門(mén)弟子個(gè)個(gè)怒氣沖天。社會(huì)上的棋迷們也分為截然不同的兩派,一派連連喝彩,另一派則認(rèn)為豈有此理,“是對(duì)名人的不禮貌”,霎時(shí)間抗議信雪片般地飛到《讀賣(mài)新聞》社。
恰恰就在這個(gè)時(shí)候,日本策劃和挑起了“滿(mǎn)洲事件”,中日關(guān)系異常險(xiǎn)惡。因此這盤(pán)棋從始至終籠罩著“中日對(duì)抗”的強(qiáng)烈色彩,社會(huì)上的陰風(fēng)冷雨陣陣向吳清源襲來(lái)。正是在這樣嚴(yán)峻的情況下,年僅19歲的吳清源與日本第一高手展開(kāi)了世紀(jì)性的決戰(zhàn)。
這局棋從1933年10月16日開(kāi)始,經(jīng)過(guò)漫長(zhǎng)的冬天,直到次年1月19日方宣告結(jié)束。按當(dāng)時(shí)的規(guī)矩,名人有視情況暫停的權(quán)利,因此對(duì)他絕對(duì)有利。例如第8天,秀哉一開(kāi)始便將預(yù)先考慮成熟的一手棋打出,吳清源僅考慮兩分鐘便應(yīng)下一手,而后秀哉長(zhǎng)考3個(gè)半小時(shí)也未落子,即宣告暫停收兵回營(yíng)。每一次暫停后,秀哉召集弟子們徹底研討局面,事關(guān)日本和本因坊一門(mén)的榮譽(yù),坊門(mén)弟子全部積極行動(dòng),出謀獻(xiàn)策,必欲將吳清源打敗而后快!
秀哉身材非常瘦小,然而一旦坐在棋盤(pán)前,卻又顯得無(wú)比高大莊嚴(yán),自有一種震懾人心的氣勢(shì)。面對(duì)吳清源的新布局,秀哉依舊采用傳統(tǒng)的小目套數(shù),步調(diào)略給人以緩慢的感覺(jué)。但是他畢竟技藝精湛、老謀深算,因此棋到中盤(pán)時(shí),黑棋也只是略微優(yōu)勢(shì)。但是在關(guān)鍵時(shí)刻,秀哉打了出第160的“妙手”,吳清源終以二目敗而終局。
關(guān)于第160的“妙手”,傳說(shuō)是秀哉的弟子前田陳爾四段(當(dāng)時(shí))想出來(lái)的,但也一直未能得到證實(shí)。只是在對(duì)局的最后一天,吳清源抽空去廁所時(shí),看到對(duì)局休息室中,秀哉的弟子們黑壓壓一片,手中拿著許多棋譜,都是將收官至終局的各種下法徹底研究透的記錄。這也說(shuō)明秀哉與弟子們已經(jīng)事先做了充分的準(zhǔn)備,所以第160的“妙手”無(wú)疑是集體智慧的結(jié)晶。事隔15年,1948年時(shí)瀨越憲作在一次座談會(huì)上曾披露說(shuō):“這是一樁秘密,那時(shí)被吳清源打過(guò)一手之后,苦思冥想的秀哉回府后立即召集弟子們,為考慮下一手棋研究了各種打法。結(jié)果采用了還擊的那一手(即指第160手),是前田這個(gè)弟子想出來(lái)的……”盡管瀨越先生聲明:“此話(huà)非正式,不得發(fā)表!”但《讀賣(mài)新聞》仍舊登報(bào)泄露出去,結(jié)果惹得坊門(mén)弟子們勃然大怒,嚴(yán)厲向?yàn)|越追究責(zé)任,瀨越無(wú)奈只好辭去日本棋院理事長(zhǎng)的職務(wù)。
總之,這局棋影響之大,在近代日本圍棋史上是絕無(wú)僅有的。不僅顯示了吳清源的蓋世才華,也預(yù)告了“吳清源時(shí)代”即將來(lái)臨。
1936年,吳清源加入日本國(guó)籍。這是聽(tīng)從山崎有民等友好人士的勸告,他們認(rèn)為,在當(dāng)時(shí)中日戰(zhàn)爭(zhēng)已無(wú)可避免的情況下,吳清源若想繼續(xù)學(xué)棋修業(yè)的話(huà),不取得日本國(guó)籍,終歸難以在日本立足。1945年日本戰(zhàn)敗后,吳清源又恢復(fù)了中國(guó)國(guó)籍。這說(shuō)明吳清源在日本棋界始終處于“客籍棋士”的特殊地位。日本人從未忘記他是一個(gè)中國(guó)人,而中國(guó)人也從未忘記他是自己的親人,并為他所取得的每一個(gè)成就而歡欣鼓舞。
盡管有瀨越憲作、山崎有民等友好人士的關(guān)懷支持,吳清源在日本的處境仍十分艱難。“吳清源時(shí)代”的到來(lái)雖然給他帶來(lái)巨大聲譽(yù),但同時(shí)也使他成為整個(gè)日本棋界的“對(duì)立面”,“打倒吳清源”已成為所有日本專(zhuān)業(yè)棋手的座右銘。一些懷有民族情緒的日本人不時(shí)向吳清源發(fā)動(dòng)攻擊和咒罵,更有甚者,投寄恐嚇信、往家里扔石頭的事件也發(fā)生過(guò)。今天回顧當(dāng)時(shí)某些人的幼稚行為,僅值一笑。因?yàn)闉踉平K將過(guò)去,當(dāng)中日兩國(guó)人民再次沐浴在友好的陽(yáng)光之下,吳清源和他杰出的棋藝活動(dòng),也就成為中日兩國(guó)悠久的文化聯(lián)系的一種象征。
“吳清源時(shí)代”的到來(lái)是與秀哉名人的引退聯(lián)系在一起的。1938年秀哉決定引退之際,將世襲300余年之久的“本因坊”名位轉(zhuǎn)讓給日本棋院。有關(guān)秀哉這個(gè)決定的原因歷來(lái)眾說(shuō)紛紜,但主要是吳清源、木谷實(shí)等青年俊杰的崛起,本因坊一門(mén)并無(wú)相應(yīng)的人才足以對(duì)抗。秀哉深感已無(wú)法保持“本因坊”的無(wú)尚榮譽(yù),遂忍痛做出上述決定。
秀哉引退之后,日本棋壇八段位上空無(wú)一人,七段位除瀨越、鈴木、加藤三長(zhǎng)老外,年輕的棋士只有木谷實(shí)和吳清源。誰(shuí)是日本棋界最強(qiáng)者?《讀賣(mài)新聞》就此舉辦“吳清源、木谷實(shí)擂爭(zhēng)十局棋”。為了始終保持莊嚴(yán)肅穆的氣氛,決定主要選用座落在鐮倉(cāng)的建長(zhǎng)寺、圓覺(jué)寺等作為對(duì)局場(chǎng)所,這就是日本圍棋史上著名的“鐮倉(cāng)十盤(pán)棋”。
1939年9月28日,“鐮倉(cāng)十盤(pán)棋”第一局揭幕。木谷實(shí)執(zhí)黑,一改“新布局”的風(fēng)格,占低位堅(jiān)實(shí)取地。吳清源則瀟灑地捷足先登,構(gòu)成大模樣,黑棋就此陷入苦戰(zhàn)。誰(shuí)知吳清源在第120手時(shí),不慎走出失著,木谷實(shí)猛烈反擊造成大劫。此時(shí)雙方均嘔心瀝血殊死拼殺,忽然木谷實(shí)鼻孔流血側(cè)身昏倒,而吳清源由于棋勢(shì)不妙,血壓劇增,似乎鮮血欲從天靈蓋中噴出,只顧絞盡腦汁思考,竟沒(méi)有注意到周?chē)l(fā)生了什么事情。后來(lái)有讀者投書(shū)報(bào)社質(zhì)問(wèn)吳清源說(shuō):“當(dāng)木谷七段鼻血流出,異常痛苦之時(shí),你卻佯作不知,只顧繼續(xù)下棋,這簡(jiǎn)直太殘忍了。你為什么不馬上休息一下?你為什么不能說(shuō)幾句照拂的話(huà)?你簡(jiǎn)直是個(gè)不懂武士俠義、殘無(wú)人道的賭棍!”這樣的質(zhì)問(wèn)自然帶有較多的感情色彩,旁觀者無(wú)法理解在這樣重大的比賽中,對(duì)局者已經(jīng)進(jìn)入“無(wú)我”的境地,在他眼前出現(xiàn)的只是棋子、棋盤(pán)所構(gòu)成的變幻紛紜的局面,而無(wú)心顧及其他。
打劫的結(jié)果白棋凈損七目,敗局已無(wú)可挽回。不想在收官的緊要時(shí)刻,木谷實(shí)也走出失著,吳清源再次挑起劫爭(zhēng),終于實(shí)現(xiàn)逆轉(zhuǎn),獲兩目勝。這是一場(chǎng)勢(shì)均力敵、從始至終苦戰(zhàn)不休的勝負(fù)大較量。
“鐮倉(cāng)十盤(pán)棋”至1940年10月第六局下完后,吳清源五勝一敗,將木谷實(shí)的交手棋份降為“先相先”(即三局中兩局執(zhí)黑)。
“擂爭(zhēng)十盤(pán)棋”可以說(shuō)是一場(chǎng)懸崖上的決斗,特別是在爭(zhēng)奪棋界第一把交椅的擂爭(zhēng)勝負(fù)中,勝者名揚(yáng)四海、譽(yù)滿(mǎn)天下;敗者一蹶不振,棋士生命就此斷送。對(duì)于吳清源來(lái)說(shuō)情況更為嚴(yán)酷,因?yàn)樗强图迨浚坏┍蝗舜蛳吕奕ィ蛯⑸頂∶眩瑬|山再起的機(jī)會(huì)實(shí)際上微乎其微。
盡管如此,吳清源在10多年時(shí)間內(nèi),與日本當(dāng)時(shí)所有的最強(qiáng)棋士輪番決斗了10回,下了近百局“十盤(pán)棋”,將他們一一降服于腳下。可以說(shuō)他的無(wú)與倫比的光輝業(yè)績(jī),正是在“擂爭(zhēng)十盤(pán)棋”中建立起來(lái)的!
繼“鐮倉(cāng)十盤(pán)棋”之后,1941年,吳清源與雁金準(zhǔn)一八段再次進(jìn)行“十盤(pán)棋”角逐。雁金準(zhǔn)一是當(dāng)時(shí)在野的棋界長(zhǎng)老,德高望重,有“力戰(zhàn)之雄”的美稱(chēng)。這次決斗是應(yīng)雁金氏的要求舉行的,由于吳清源當(dāng)時(shí)只是七段,交手棋份應(yīng)為“先相先”,但雁金表示,想與吳清源以分先對(duì)弈一次。以長(zhǎng)老的身份,承諾與后輩的棋手分先對(duì)局,即已表明他的不平凡的雅量。但是到第5局結(jié)束,吳清源4勝1負(fù)遙遙領(lǐng)先。有關(guān)人士考慮到雁金先生的名聲與健康,決定將以后的對(duì)局全部終止。
接著《讀賣(mài)新聞》社又物色藤澤庫(kù)之助六段與吳清源對(duì)壘。藤澤的棋風(fēng)簡(jiǎn)樸堅(jiān)實(shí),若執(zhí)黑先投,從不給白棋以可乘之隙,因此被贊揚(yáng)為“黑先無(wú)敵”。但他與吳清源相差兩段(吳清源此時(shí)已升入八段),故按規(guī)定對(duì)局為藤澤“常先”(即始終執(zhí)黑)。賽前大多數(shù)人估計(jì),黑棋會(huì)以壓倒優(yōu)勢(shì)獲勝。結(jié)果吳清源4勝6負(fù),保持“讓先”的棋份不變。
中日戰(zhàn)爭(zhēng)的最后兩年,吳清源為生活和信仰所驅(qū)使,整日顛沛流離日本各地,完全脫離了棋藝生涯。在他的心目中,再次馳騁棋壇的日子已經(jīng)不會(huì)重返。戰(zhàn)敗后的日本一片凋蔽,然而有志之士也在廢墟上計(jì)劃復(fù)興大業(yè)。1947年7月,《讀賣(mài)新聞》社派人尋訪(fǎng)吳清源,敦請(qǐng)他出山回歸棋界,并希望他與橋本宇太郎八段進(jìn)行“擂爭(zhēng)十盤(pán)棋”對(duì)局。
8月26日,第一局拉開(kāi)戰(zhàn)幕。吳清源雖然執(zhí)黑先行,但棋藝畢竟已荒廢兩年之多,結(jié)果稀里糊涂敗下陣來(lái)。棋界人士大失所望:當(dāng)年的吳清源哪里去了?第2局吳清源執(zhí)白仍不見(jiàn)起色,盡管他在心里大聲疾呼:“絕不能輸!”但弈至中盤(pán),行將崩潰的白棋七零八落,已呈必?cái)o(wú)疑之勢(shì)。誰(shuí)知橋本宇太郎突然開(kāi)始失常,錯(cuò)著緩手迭出,吳清源終于枯木逢春、乾坤倒轉(zhuǎn),僥幸獲一目勝。瀨越憲作當(dāng)時(shí)十分生氣,說(shuō):“橋本簡(jiǎn)直是異常,這樣好的棋要是再輸?shù)簦R上給我趕出門(mén)去!”社會(huì)上流傳著這樣一種說(shuō)法:一到橋本先生該落子時(shí),不知從哪里傳來(lái)陣陣鼓聲,妨礙他繼續(xù)思考。也有人說(shuō):當(dāng)橋本先生思考時(shí),蜘蛛就從房頂上垂落下來(lái),倒掛在他的眼前……從第3局開(kāi)始,吳清源終于恢復(fù)了本來(lái)面目,順風(fēng)滿(mǎn)帆勢(shì)如破竹,至第八局結(jié)束,6勝2負(fù)將橋本打到“先相先”的地步。
1948年,《讀賣(mài)新聞》社又舉辦吳清源對(duì)巖本薰“擂爭(zhēng)十盤(pán)棋”決斗。巖本薰棋風(fēng)清淡強(qiáng)韌,有“撒豆棋”之稱(chēng),當(dāng)時(shí)他從橋本宇太郎手中奪得“本因坊”桂冠,正值春風(fēng)得意之時(shí)。但吳清源畢竟技高一籌,鏖戰(zhàn)至第6局時(shí)已5勝1負(fù),將巖本薰降了一格。
1949年,藤澤庫(kù)之助在棋士升段大賽中由八段晉升九段,成為“當(dāng)代第一人”(秀哉去世后,日本僅有的九段)。由于戰(zhàn)前吳清源曾在“十盤(pán)棋”擂臺(tái)上將他擊敗過(guò)。因此日本棋院不得不考慮,藤澤都升為九段,吳清源豈能擱置在八段位上而不顧呢?于是決定舉行“吳清源對(duì)六、七段選拔十盤(pán)棋”,即集中10名年輕的高段棋手(4名六段、6名七段),讓他們輪番向之挑戰(zhàn),作為吳清源的“九段升段試驗(yàn)比賽”。按照規(guī)定,吳清源除對(duì)高川格、前田陳爾兩位七段執(zhí)黑外,于其他8名六、七段高手均執(zhí)白棋,而且當(dāng)時(shí)沒(méi)有貼目的規(guī)定。結(jié)果吳清源8勝1負(fù)1平,被日本棋院贈(zèng)授九段,時(shí)年36歲。
這樣,《讀賣(mài)新聞》社以“爭(zhēng)奪真正的名人位之決斗”為題,立即著手籌劃“吳對(duì)藤澤擂爭(zhēng)十盤(pán)棋”的計(jì)劃。這對(duì)吳清源來(lái)說(shuō)無(wú)所謂,但藤澤卻遲遲不肯應(yīng)戰(zhàn)。《讀賣(mài)新聞》社無(wú)奈,只好又匆忙制定吳清源對(duì)橋本宇太郎的第二次十盤(pán)棋計(jì)劃。當(dāng)時(shí)橋本剛從巖本薰手里奪回了“本因坊”位,正積極創(chuàng)立關(guān)西棋院,是風(fēng)云一時(shí)的實(shí)力人物。由于第一次十盤(pán)棋吳清源多勝一籌,所以這一次的交手棋份仍規(guī)定為“先相先”,結(jié)果吳清源5勝3負(fù)2平。
然而自從吳清源和藤澤庫(kù)之助升入九段之日起,就命里注定要進(jìn)行一場(chǎng)你死我活的較量。經(jīng)過(guò)兩午時(shí)間的交涉,藤澤終于同意應(yīng)戰(zhàn)。這次十盤(pán)棋,曾被稱(chēng)為“昭和二十年代最大的爭(zhēng)棋”。結(jié)果吳清源7勝2負(fù)1平,將藤澤降為“先相先”。為此,社會(huì)上的一些知名人士呼吁說(shuō):“早該授予吳清源名人位了!”這雖然只是一部分人的意見(jiàn),并未得到廣泛響應(yīng),但實(shí)際上吳清源已成為日本棋界的“第一人”了。1952年,吳清源與藤澤庫(kù)之助再次進(jìn)行“擂爭(zhēng)十盤(pán)棋”,交手棋份為“先相先”。弈至第6局,吳清源5勝1負(fù),將藤澤擊退到定先的地位。據(jù)說(shuō)第6局時(shí),藤澤害怕被擊敗后有損日本棋院的名譽(yù),故而懷揣辭呈前來(lái)對(duì)局,如此重大的比賽對(duì)棋手產(chǎn)生的沉重壓力,于此可見(jiàn)一斑。
1953年,《讀賣(mài)新聞》社繼續(xù)主辦吳清源對(duì)坂田榮男的“擂爭(zhēng)十盤(pán)棋”。當(dāng)時(shí)的坂田八段是后進(jìn)棋士中的杰出代表,在各項(xiàng)棋戰(zhàn)中都取得超群的成績(jī),他那剃頭刀般犀利的棋風(fēng)、略帶苦澀味的堅(jiān)忍意志,都預(yù)示著他的全盛時(shí)期即將到來(lái)。廣大棋迷也都熱切期望,吳清源與坂田進(jìn)行一場(chǎng)正式的生死決斗。在這場(chǎng)舉世矚目的棋戰(zhàn)中,吳清源以6勝2負(fù)的成績(jī)將坂田降格到“定先”而高奏凱歌。
至此,吳清源已橫掃日本棋壇。但還有一個(gè)人當(dāng)時(shí)已四次獲得“本因坊”冠軍,他就是高川格。高川的棋風(fēng)被人稱(chēng)作“流水不爭(zhēng)先”,但嚴(yán)謹(jǐn)?shù)拇缶钟^和良好的均衡感覺(jué),使他前后共獲得9次“本因坊”的頭銜。戰(zhàn)后吳清源喪失日本國(guó)籍以及日本棋院正式會(huì)員資格,只被贈(zèng)予“名譽(yù)會(huì)員”稱(chēng)號(hào),因此他不能參加每年一度的“本因坊”戰(zhàn)的角逐。但人們常說(shuō):“吳清源若參加‘本因坊’戰(zhàn),肯定是穩(wěn)操勝券!”為此,主辦“本因坊”戰(zhàn)的《每日新聞》社決定:自1952年起,每年舉辦吳清源與“本因坊”無(wú)貼目的三盤(pán)棋對(duì)局。到1955年,吳清源與高川格在“三盤(pán)棋”中,共角逐12局,吳清源11勝1負(fù)。因此吳清源又成為高踞“本因坊”之上的超級(jí)棋士。在人們的印象中,高川格只要與吳清源交手是上來(lái)即輸,因此普遍認(rèn)為他不是吳清源的敵手。但是縱觀日本棋壇,已經(jīng)找不出能與吳清源分庭抗禮的人,因此《讀賣(mài)新聞》只得將高川格拉出來(lái),作為吳清源“擂爭(zhēng)十盤(pán)棋”的最后壓軸大戲。1955年7月,《讀賣(mài)新聞》社發(fā)出如下通告:
經(jīng)常為讀者介紹最高對(duì)局的敝社,決定再次舉辦吳清源九段與高川本因坊秀格擂爭(zhēng)十盤(pán)棋之決戰(zhàn)。
天才蓋世的吳清源自嶄露頭角以來(lái),人們連年不斷地驚呼:誰(shuí)能擊敗吳氏?然而被視為當(dāng)代最強(qiáng)者的雁金、木谷、橋本、巖本、藤澤、坂田等老將新秀皆敗于吳氏手下。嗣后,正值眾稱(chēng)吳氏難尋軒輊之?dāng)车臅r(shí)刻,一位孜孜不倦地埋頭鉆研技藝、終于打破前人紀(jì)錄、建立了“本因坊”四連霸偉業(yè)的人出現(xiàn)了,他就是高川氏。因此,敝社在此宣布:又一場(chǎng)世紀(jì)性的決戰(zhàn)將震驚天下!
……
這一次決戰(zhàn)的結(jié)果,吳清源在第8局結(jié)束,已經(jīng)6勝2負(fù),將高川本因坊降服。
吳清源自戰(zhàn)前的“鐮倉(cāng)十盤(pán)棋”開(kāi)始獨(dú)霸擂臺(tái),連續(xù)15年,將日本所有一流棋士與之對(duì)局的交手棋份,不是降為相差一段的“先相先”,就是降為相差二段的“定先”。這15年,是他建立輝煌業(yè)績(jī)的全盛時(shí)代,因此被稱(chēng)為“昭和之棋圣”!
1987年,日本《圍棋俱樂(lè)部》征求當(dāng)今超一流棋手,如加藤正夫、武宮正樹(shù)、小林光一、大竹英雄等人的意見(jiàn):誰(shuí)是圍棋史上最強(qiáng)者?雖然也有人舉出道策、秀策,但他們一致認(rèn)為吳清源最強(qiáng)!因?yàn)樵谒r(shí)期是所向無(wú)敵的。武宮正樹(shù)曾推崇吳清源是代表昭和時(shí)代的偉大巨人。他說(shuō):“吳先生富于獨(dú)創(chuàng)性,他創(chuàng)造的新手、新定式不勝枚舉。如果說(shuō)現(xiàn)在我們作為職業(yè)棋手感到很光榮,有一半是托了吳先生的福,那也并非言之過(guò)分。吳先生給予現(xiàn)代圍棋界的影響就是這么巨大!”
(2)民國(guó)時(shí)期的國(guó)手
民國(guó)初期可以算作國(guó)手的人,有張樂(lè)山、汪耘豐等人,后起的國(guó)手大致有顧水如、王子晏、劉棣懷、過(guò)惕生等人。
張樂(lè)山,安徽合肥人,曾任山東某縣縣令,工書(shū)善畫(huà),嗜棋如命。一日方與客弈,因爭(zhēng)一劫而難解難分,有朝廷欽差過(guò)境,竟未前去迎接,因而被劾罷官。樂(lè)山的棋藝在北方頗負(fù)盛譽(yù),其人也一向自視甚高,平生從未與周小松親教,視為憾事。
清末宣統(tǒng)年間,日本高部道平五段首次來(lái)中國(guó)時(shí),耆宿丁禮民因年衰而不能應(yīng)接,勉下二局,由張樂(lè)山接替,受先不敵又改為二子,前后共下過(guò)七十二局,結(jié)果高部竟勝五十九局。樂(lè)山是當(dāng)時(shí)國(guó)內(nèi)屈指可數(shù)的高手,不料遭此慘敗,不僅中國(guó)棋界深為震驚,就連日本棋界也大惑不解。在無(wú)可辯駁的事實(shí)面前,我國(guó)棋界如夢(mèng)初醒。小小棋枰上的輸贏,從一個(gè)側(cè)面反映了整個(gè)國(guó)家的落后狀態(tài)和政治機(jī)器的腐朽。長(zhǎng)期閉關(guān)自守、固步自封所帶來(lái)的惡果,不僅使國(guó)家遭到莫大損害,而且給圍棋這樣的智能藝術(shù)也造成無(wú)可挽回的惡劣影響。教訓(xùn)是慘痛的,近代的前輩棋手只好含淚吞下這顆苦果,開(kāi)始學(xué)習(xí)和模仿日本的圍棋理論和技術(shù),但是在當(dāng)時(shí)的情況下,要讓他們突破自身的束縛,迅速趕上國(guó)外先進(jìn)水平,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中國(guó)“勢(shì)子”制度的廢棄,并開(kāi)始采用日本新法,樂(lè)山是最早承先啟后者。1912年病歿于上海廣慈醫(yī)院。
汪耘豐,名富,北京人。民國(guó)初年的國(guó)手之一,乃北方名手劉云峰的高足。周小松晚年授二子者,以劉云峰為最強(qiáng),因此汪耘豐也可算做小松的再傳弟子。劉云峰籍貫江南,但常年住在北京,周旋于滿(mǎn)族親貴間,遂成為北方棋壇的領(lǐng)袖人物。而汪耘豐是北方人卻好游江南,晚年在上海時(shí),每日必去茶樓,到即拉人對(duì)局,性格爽朗,不計(jì)黑白高下,眼明手快,善等漏著取勝。對(duì)手思考時(shí),輒取書(shū)報(bào)翻閱,若不經(jīng)意。有一次,汪耕豐與上海名手吳祥麟對(duì)局,祥麟一塊棋被圍,經(jīng)冥思苦想走一著棋,滿(mǎn)以為可活,誰(shuí)知耘豐看都不看,舍此而走它處。原來(lái)這塊棋再走一著仍是死棋,俗稱(chēng)“后手死”是也。所奇者耘豐一眼便知,祥麟久算仍迷。旁觀者多喜歡快棋,因而大多對(duì)耘豐有好感。
民國(guó)初年,日本綽號(hào)“獨(dú)眼龍”的廣瀨平治郎七段來(lái)華,耘豐首先應(yīng)戰(zhàn),初盤(pán)采用傳統(tǒng)古法“金井欄”定式,廣瀨對(duì)此定式不甚熟悉,應(yīng)對(duì)有差,結(jié)果吃了大虧。回到寓所苦思善策,通宵未眠,這段逸事曾轟傳一時(shí)。
耘豐編有《閱秋吟館弈選》,采列同時(shí)高手對(duì)局,以窺新舊交替的時(shí)代風(fēng)格。逝世時(shí)年約八十歲。
顧水如(?—1970年),名思浩,嘉興楓涇人。楓涇地方不大,清末卻出了三位圍棋名手:程善初、陳仲專(zhuān)、方金題,這三人都從周小松受二子。水如幼年,與其兄月如一起,受這些名師的啟發(fā)指導(dǎo),于棋藝已打下扎實(shí)的基礎(chǔ)。二十歲左右去上海,出入茶樓棋座,與諸名手角藝,成績(jī)頗佳,一時(shí)轟動(dòng)棋壇。
1914年,顧水如到北京,與日本專(zhuān)業(yè)棋手高部道平累戰(zhàn)不下百局,因技藝不俗,年輕有為,為段祺瑞、汪有齡所賞識(shí)。1915年被選送日本留學(xué)深造,結(jié)識(shí)名手瀨越憲作、廣瀨平治郎、野澤竹朝等,系統(tǒng)研習(xí)日本圍棋,是我國(guó)棋界出國(guó)觀察學(xué)習(xí)的第一位棋手。
歸國(guó)后,水如先在上海主持《時(shí)報(bào)》圍棋欄,又在天津《商報(bào)》辟?lài)鍣冢榻B日本圍棋發(fā)展?fàn)顩r。后來(lái)去北京供職,為段祺瑞座上客。日本一些高手訪(fǎng)華,因多是舊時(shí)相識(shí),嘗與招待聯(lián)系,瀨越憲作并曾住在他家里。此時(shí)水如名至望歸,儼然成為棋壇領(lǐng)袖。1933年后因段祺瑞下野,水如又移居上海,曾與過(guò)惕生共同組織“上海弈社”。1937年“中國(guó)圍棋社”成立,任甲組指導(dǎo),1942年日本棋院授予四段稱(chēng)號(hào)。
水如的一生,對(duì)宣傳日本圍棋新法有很大貢獻(xiàn),他很重視培養(yǎng)人才,著名棋手吳清源、陳祖德少年時(shí),都曾受其悉心指導(dǎo),并予以鼓勵(lì)揄?yè)P(yáng)。
水如1971年病逝,年近80歲。
王子晏(1892—1951年),名咸熙,浙江嘉興人。年輕時(shí)出入上海茶樓棋座,初從吳祥麟授九子,逐漸升至對(duì)子,終乃超越。與茶樓諸棋手較量,屢戰(zhàn)屢勝,當(dāng)者披靡,成為上海棋壇冉冉升起的新星。張澹如遂安排他在自己的“證券交易所”當(dāng)會(huì)計(jì),掛名支薪,俾能專(zhuān)心研究棋藝。
子晏的棋風(fēng)穩(wěn)健細(xì)致,官子功夫尤深。從民國(guó)期間的幾次中日圍棋交往來(lái)看,我國(guó)棋手?jǐn)⊥苏呔佣啵í?dú)子晏能應(yīng)付,取得較好的成績(jī)。據(jù)他自訂棋譜云,從1920至1930年十年中,他與日本棋手共弈49局,其中勝34局,負(fù)12局,平1局。這一成就不僅受到日本方面稱(chēng)贊,對(duì)于提高我國(guó)棋手的自信心,也曾起了相當(dāng)作用。
30年代后,子晏因患肺病,對(duì)局減少。晚年在自己家中創(chuàng)辦“正風(fēng)棋社”,組織“正風(fēng)棋隊(duì)”,從學(xué)者尚有在滬的日本人。社內(nèi)制定學(xué)員考核制度,按比賽成績(jī)授予段位,是我國(guó)私家實(shí)施段位制的創(chuàng)始者。
子晏還撰著棋書(shū)多種,稿本未刊。只有遺稿《官子指南》,解放后在《圍棋》月刊發(fā)表。
劉棣懷(1897—1979),名昌華,安徽桐城人。早年從僧可慧學(xué)弈。可慧湖南人,名手丁禮民授以三子。棣懷不及見(jiàn)丁禮民,得可慧指授,不久便與之相抗衡。繼而北上參加段祺瑞家棋會(huì),他不打譜,不循常規(guī),以扭殺見(jiàn)長(zhǎng),有“劉大將”之稱(chēng),年未三十而蜚聲北地,成為段門(mén)中年輩稍后之翹楚。
30年代,劉棣懷在上海與日本三、四段棋手對(duì)弈中,成績(jī)頗佳。抗戰(zhàn)時(shí),劉棣懷西上,轉(zhuǎn)戰(zhàn)貴州、廣西、四川一帶,棋藝日進(jìn)。戰(zhàn)后來(lái)上海,在滬諸強(qiáng)已均難與敵。1942年,被日本棋院授予四段稱(chēng)號(hào)。
建國(guó)后,劉棣懷奪得兩屆全國(guó)冠軍,50年代,曾雄踞中國(guó)棋壇之首,與過(guò)惕生并稱(chēng)為“南劉北過(guò)”。這時(shí)他的技藝日臻成熟,將中國(guó)中盤(pán)扭殺的傳統(tǒng),與日本重視布局、講究棋理的優(yōu)點(diǎn)結(jié)合在一起,形成一種力戰(zhàn)型的剽悍獷野的棋藝風(fēng)格。并在1960年,日本圍棋代表團(tuán)首次訪(fǎng)華時(shí),擊敗了七段棋手瀨川良雄。
劉棣懷著述頗多,如《怎樣下圍棋》、《圍棋定式基本知識(shí)》、《圍棋布局初步》、《圍棋中盤(pán)戰(zhàn)術(shù)》、《圍棋官子常識(shí)》等等,對(duì)于普及推廣圍棋,起到相當(dāng)作用。

“南劉北過(guò)”為代表的一批老棋手在經(jīng)濟(jì)凋敝和社會(huì)動(dòng)蕩之中艱難奮斗,保住了中國(guó)圍棋的一線(xiàn)香火,為新中國(guó)圍棋提供了一個(gè)雖然水平不高,卻至關(guān)重要的起點(diǎn),他們是承上啟下的一代。
林勉(右)、顧水如(前左一)、魏海鴻(前左二)、王幼宸(后左一)、劉棣懷(后左二)、汪振雄(后左三)等人悉心指導(dǎo)少年陳祖德(左)。
過(guò)惕生(1970—1989),安徽歙縣人。自幼喜愛(ài)圍棋,年輕時(shí)在弈風(fēng)如熾的皖南地區(qū)已很知名。1929年在上海結(jié)識(shí)顧水如,了解到日本圍棋的發(fā)展?fàn)顩r,從此苦心研究日本圍棋的理論和實(shí)踐,并率先應(yīng)用吳清源、木谷實(shí)“新布局”的手法,這對(duì)他后來(lái)成為國(guó)內(nèi)棋壇的翹楚,起了決定性的作用。1932年加入顧水如創(chuàng)辦的“上海圍棋社”。后移居北京,創(chuàng)辦“四宜軒弈社”,成為北京弈壇的重鎮(zhèn)。在黑暗的舊時(shí)代,為振興我國(guó)的圍棋事業(yè),做出有益的貢獻(xiàn)。
解放后,過(guò)惕生在1957年、1962年,兩度獲取全國(guó)冠軍。他深明棋理,局勢(shì)的均衡感覺(jué)尤為出色,行棋氣魄雄偉、膽略過(guò)人,與劉棣懷同被譽(yù)為“一代大師”。
過(guò)惕生心胸開(kāi)闊、平易近人,提攜后學(xué)不遺余力,是著名九段棋手聶衛(wèi)平的啟蒙老師。曾先后編寫(xiě)《圍棋名譜精選》、《圍棋戰(zhàn)理》、《古今圍棋名譜鑒賞》等書(sh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