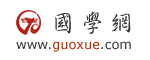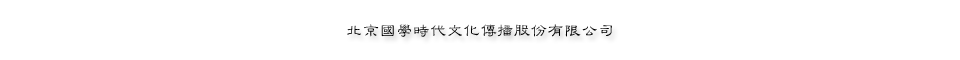第六節 廢除“座子”——中國圍棋的重要改革
高部道平的來訪,震動了中國棋壇,對敏感的知識分子階層,尤其具有非同一般的影響,也引起人們的憂慮、反思。改變中國圍棋的落后狀況,此時已刻不容緩。
另外,通過枰場競技,迫使中國棋手不得不懷疑傳統著法是否能一成不變地適用于現代。宣統年間,李子干在《詠棋十絕》中就曾寫下:“古法拘泥計本疏,兵情頃刻不相如。趙家十萬長平骨,誤在將軍讀父書!”這正是目睹中日棋手對壘后深有感觸的痛切之作。名手張樂山的棋友黃銘功更是大膽地提出:“棋法自范西屏而精,亦自范西屏而始壞。”認為后來棋家唯有“大抉其藩籬”,才能使中國圍棋飛躍到嶄新的高度。中國棋手在迭遭慘敗之后,能領悟長期奉為經典著作的“古法”也有不足法的地方,甚至敢于對“棋圣”之藝作出新的估價,這確實是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
中國古譜著法既然不行于時,那末,引進日本先進圍棋技術,學習日本棋理棋法,才是此時提高中國圍棋水平的唯一捷徑。“禮失若援求野例,未妨俎豆本因坊。”(見黃俊《弈人傳·劉叔通詩》)正反映了中國棋手迫切希望掌握日本棋藝技術的心理。但是,長期以來,中、日圍棋著法、規則不盡相同,其中首當其沖的無疑是關于“座子”問題。
“座子”,指中國古代圍棋在開始對局之前,規定要先在對角“星”的位置上固定放置黑白各兩個子,它又稱“勢子”、“角子”或“雅”。其中“雅”字起源甚古,音義與“岳(嶽)”同,表示中國古代曾經附會地將棋盤象征大地的傳統觀念。大地上的“岳”不可動搖,棋盤上的“座子”自然也固定不移。這一規定,流行中國前后至少不下2000年。而在日本,約16世紀永祿年間(1558—1569),“座子”已廢除不用。清人黃遵憲《日本國志》在記述日本棋事時稱:“惟行棋而不行雅”,就注意到日本與中國在圍棋對局時的主要不同。
中國圍棋在“座子”流行的漫長歲月里,無疑創造過許多足以傳世的佳局。可見,隨著圍棋藝術的不斷發展,“座子”的設置卻使圍棋的邊角變化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影響了圍棋戰略戰術的發展,更不利于中國棋手掌握日本圍棋技術。《棋國陽秋》稱:“日人對弈,不置角(座)子,即其破陳式之道。華人與之對局,古譜公式,廢然無所用之。”正說明此時廢除“座子”已勢在必行。
當然,要讓“座子”從此淘汰,還須經過一個擇優而存的比較過程。即先從與日本棋手交流過的中國名手之間試行,然后在棋界逐步擴大影響,最后通行于國內。
從現在棋譜資料分析,清末宣統年間(1909—1911),我國名手已開始廢除“座子”的探索性對局。如宣統年間李子干編印的棋譜《手談隨錄》中,共刊登清末棋手對局130余譜,其中就有陳子俊與丁禮(理)民廢除“座子”分先兩局。在全書中,這兩局所占比重雖小,但已說明此時“座子”的權威已被動搖。(丁、陳都是最早與高部道平交流的中國棋手,由他們率先進行嘗試,是合乎情理的。)遺憾的是,這兩局棋雖有可能是現存我國棋手最早廢除“座子”的實戰譜,付印時間也最早,但沒有注明對局的準確日期。
舍此之外,在吳祥麟、黃瀛仙合編的《周小松受子譜》中,刊有張樂山與吳祥麟在上海對弈10局,均由吳先走。在這10局中,采用每兩局中一局置有“座子”,一局廢止“座子”的對局形式。據記載:張樂山1910年10月在南京迎戰日本高部道平,然后前來上海與吳祥麟對局,1912年病歿。因此。這10局無疑弈于1910年底至1912年間。時間更準確的還有陳子俊、吳祥麟對子6局,亦載于《周小松受子譜》,其中4局廢除“座子”,2局列有“座子”。據吳祥麟記載,這6局弈于1911年,即清宣統三年。
由此可見,清末民初間大型城市的中國名手已在比較中、日兩種不同對局形式的優劣。約經五六年后,廢除“座子”的對局已占有絕對優勢,終于通行于棋界。這是中國圍棋史上一次重大的改革,它始于清末,完成于民國初期。
隨著傳統“座子”的淘汰,不久,關于“還棋頭”的規定也逐漸廢止,讓子棋應還子數也起了變化。但這類規則上的變動與“座子”的存在與否相比,就只能算是細節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