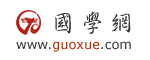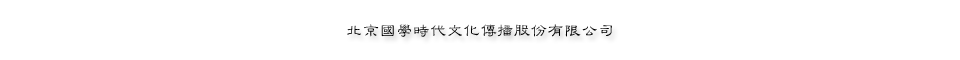第五節 高部道平訪華——中日近代圍棋交流開始
清代末年,當中國圍棋節節下降的時候,與中國一衣帶水的日本圍棋活動正在蓬勃興起。中、日圍棋的一衰一盛,形成了強烈、鮮明的對比。
圍棋自我國傳人日本后,長期以來深受日本人民喜愛。早在距今400年前,日本已完成了廢除圍棋“座子”的重大改革。待到16世紀,日本豐臣秀吉(1536—1598)、德川家康(1542—1616)相繼執政,對優秀棋家賜于世襲俸祿,使他們有條件心無旁騖地鉆研棋藝,開創流派,傳子授徒。從此,日本圍棋在多組織、多流派的優勝劣汰的激烈競爭中不斷提高發展。到了19世紀明治維新以后,秀甫、秀榮、秀哉先后執棋界牛耳。“方圓社”、“本因坊”兩大圍棋門閥英才輩出,日本圍棋水平已遠遠超過了中國。
事實上,中國古代有識之士對日本人民酷愛國棋的情況也并非全然無知。在清末以前,兩國圍棋愛好者已進行過多次接觸,從中國《杜陽雜編》、《舊唐書》到日本《三代實錄》、《懷風藻》等多種古典文獻中,都散出有關于雙方圍棋交往的軼事。明代李言恭、郝杰在《日本考》中,甚至還扼要介紹了部分日本圍棋術語,足可證明此時中國學者對日本圍棋已作過并非泛泛的觀察。及至晚清時期,少量日本、琉球棋譜已經輸入我國,當時棋譜編印家認為“中山(指琉球)、日本,皆我同文”(見《寄青霞館弈選?凡例》),加以收藏、翻印。但此時處于自足狀態的中國棋手對海外來譜早有先入之見,并不認為其中有可資借鑒的內容。由于歷史的(如清王朝的閉關自守政策、日本幕府時期的鎖國政策)、地理的、民族的(如習俗、語言等)各種原因,兩國棋手彼此之間始終缺乏應有的了解,棋手的交流也遲遲未能實現。。
光緒年間,學者黃遵憲在1887年寫成的《日本國志?禮俗志》中已提到:“(日本)圍棋最多高手,豪富子弟、風雅士夫,無不習之者……”接著,到了光緒后期,旅日華人中也出現了以棋會友的圍棋愛好者,民間的圍棋交往漸漸頻繁。可是,上述這些交流,或沒有留下實戰紀錄,或僅屬于業余愛好者之間的相互切磋,不能用以判定兩國圍棋水平的高下。而真正兩國棋手等級的較量,始于高部道平來訪。
高部道平(1882—1951)生于日本東京,17歲入日本“方圓社”深造,曾先后師事名手巖崎健造與日本本因坊秀榮,22歲獲四段稱號。27歲時,他參加日本圍棋組織“圍棋同志會”。接著,他開始了足以輝煌弈史的漫游,走向朝鮮、中國……
1909年間,高部道平來到保定,順路走訪了在中國擔任翻譯的中島比多吉。中島是一名業余棋手,他認識當時在保定任陸軍學堂總辦的段祺瑞,并經常與聚集在段祺瑞周圍的中國棋手交流,雙方互有勝負。經中島出面介紹,高部戰勝了包括段祺瑞在內的所有中國名手。將對手紛紛降至讓子,顯示出日本職業棋手的先進技術與扎實功力。從此,高部成為段府的上賓。據日本瀨越憲作《支那之棋界》引中島比多吉的口述,當高部向段祺瑞縷述日本棋界狀況,表明自己僅是一名“四段”棋手時,使在座中方棋手大為震驚。
同年,段祺瑞改任第六鎮統制,他將高部道平介紹給任商部右侍郎的棋友楊士琦(見日本渡邊英夫《中國古棋經之話》)。據汪云峰評輯的《問秋吟社弈評初編》,1909至1910年間,楊士琦出使江南,召集南方名手在南京與高部道平對局。結果王彥卿、陳子俊等知名棋手均被高部讓2子,雙方互有勝負。棋界人士認為,高部的棋力不弱于已故國手周小松。于是,高部的棋名在中國不脛而走。
1910年下半年,南京舉辦由清末官商合辦的博覽會“南洋勸業會”,招徠各大商埠的來往游人。江蘇、浙江、安徽、上海等地名手也相繼來到南京。此時,多數棋手對高部的棋藝僅屬耳聞,并未一試,難免將信將疑。于是,有社會名流愿出面為東道主,邀請高部至南京赴會。
南京會戰,自然引起四方名手與社會人士的一致關注。上海名手范楚卿等率先登場與高部下對子,結果大敗;繼而被高部讓2子,又敗。鎮江籍名手丁學博此時年事已高,被推為棋界耆宿,與高部受2子連弈2局,勝負各一(見《棋國陽秋》)。
10月,高部道平在南京楊士琦府邸“韜園”讓中國名手張樂山2子對局,高部又以三子半獲勝。這局棋譜紀錄至今猶存,成為中日圍棋交流史中值得回顧的一局(見《中國古棋經之話》)。接著,高部在“南洋勸業會”讓張樂山2子繼續對局,兩人前后共弈七八十局,張樂山僅勝13局(見高部道平《圍棋圣典?緒言》)。面對鐵一般事實,人們不得不承認雙方實力懸殊。一名日本四段棋手,已足以讓中國一流高手紛紛甘拜下風。那么,中日兩國圍棋的巨大差距也就可想而知了。
高部道平30歲時曾歸國半年,晉升五段。隨后又來中國,他的足跡遍及北京、上海、保定、青島、濟南、南京、東北等地,來往中國南北前后達17年之久,到處宣傳日本棋法。他與中國棋手對局數量極多。據1926年《新聞報?快活林》記載,高部讓潘朗東、吳祥麟、顧水如2~3子均不下百局。又從流傳棋譜中可見:他與汪云峰、伊耀卿、段俊良、范楚卿、姜鳴皋等亦曾大量對局;此外,受到他指導的還有王子晏、陶審安、何星叔、劉玉堂、林新猛、朱叔莊、周美權、唐善初、王幼宸等。高部道平交流廣泛,國民黨元老胡漢民、張靜江都曾邀他對局。至于段祺瑞與張靜江之弟張澹如是當時棋界重要支持者,他們與高部對局的數量更是多得難以統計。這些對局譜,部分散見于報刊圍棋欄,部分被棋譜《問秋吟社弈評初編》(1917年北京宣元閣版)、《中日圍棋對局》(1919年上海有正書局版)及《海上近年名手彙集》(未刊)收錄,估計失散或未經發表的尚有十之七八。
高部道平除了與中國棋手交流外,還曾與同時來訪日本棋家進行示范表演。如1919年lO月(陰歷),高部在上海東亞飯店與訪華日本棋手廣瀨平治郎表演;接著,他又與日本少年棋手巖本薰表演。據《海上近年名手彙集》批語:這兩局棋由中方社會名流集資,每局懸賞100銀元。由此推斷,當時對來訪日本棋手待遇豐厚,這是他們樂意繼高部以后接踵來訪的重要原因。
高部道平的來訪,揭開了近代中日圍棋交流的序幕。大量對局,以無可辯駁的事實將中日雙方棋力懸殊的實況大白于天下,使中國棋手懂得了長期閉關自守、固步自封帶來的嚴重危害,同時也激發了他們強烈的民族自尊心。從此,日本圍棋書刊不斷引進,學習日本棋法蔚為風氣,促成了中國圍棋(包括廢除“座子”及“還棋頭”在內)的一系列重大改革。這些頗有生氣的變化都是在高部來訪后迅速引起的,因此棋界有識之士對高部訪華給予很高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