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浩對話龔一:追尋古琴背后的君子之道
主持人:云浩 學者、古詩詞人,中央美術學院教授,《北京晨報·名家悅讀》特約主持人
嘉 賓:龔一 我國著名的職業古琴演奏家、上海音樂學院碩士生導師、中國民族管弦樂學會古琴專業委員會副會長、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古琴藝術)代表性傳承人。

【編者按】
琴棋詩書畫中的琴,指的是古琴,它與中國文人相伴了至少兩千多年,留下了豐厚的文化遺產。從某種意義上說,它就是我們民族文化的圖騰。
然而,該如何面對這份沉重的遺產?是原封不動地傳承下去,還是繼續豐富它?是將它神話,還是堅持以內容為本?是追尋空霧縹緲的境界,還是腳踏實地?
幸運的是,面對這些問題,得到了當代古琴大師龔一先生的點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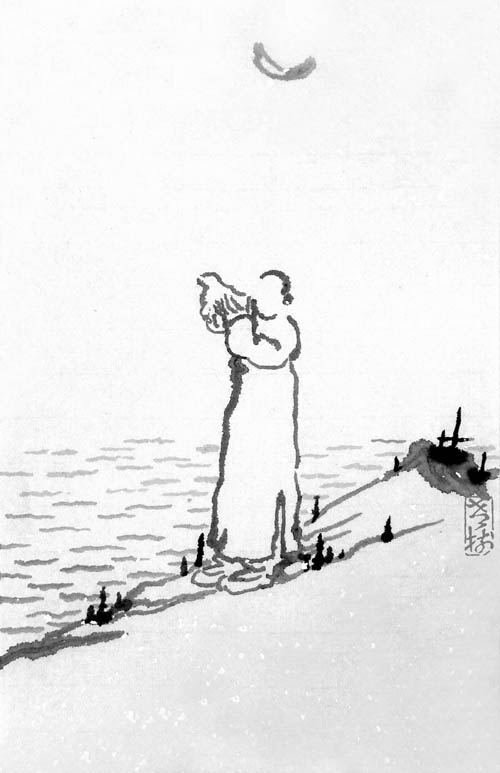
月下來到水邊,酒醉裝作逍遙。江河萬里東去,偷偷喝了一瓢。
音樂不僅僅是個人修為
云浩:一談到古琴,我有一個感覺,就是它試圖把人和音樂做一個融合。所以東方可能更多強調的是一個古琴師的個人道德修為、人生境界之類,而西方音樂則先解決一些技術問題,因為把西方音樂一套技法都學完了,一腦袋褶子都長出來了,可不可以這么看,西方音樂在某種意義上更強調技術性?
龔一:我覺得古今中外相通,尤其在藝術上,你這個觀點是不完整的,好像西方音樂只是重技術、技巧,這說明對西洋音樂缺乏了解。
云浩:您來談談音樂和修養的關系。
龔一:說只有古琴注重人倫修為的涵養,是自我的一種修煉,這也不完全。二胡、笛子、琵琶、鋼琴、小提琴,哪一個不是在表現人的思想感情呢?那么多的古琴曲,怎么就變成了光是個人習性的修為呢?音樂就是表現人的思想感情、社會的重大題材,東西方都如此。貝多芬把拿破侖寫進去了,《第五交響曲》呢,把人類的一種命運思考寫進去了,《第九交響曲》呢,把全人類期盼頌揚和平寫進去了,誰說貝多芬只是個人修為呢?古琴中的《廣陵散》,寫的是《刺客列傳》里的聶政刺韓,也義正詞嚴呢。
沒有技巧,不成韻味
龔一:很多曲子其實都是寫人的、寫社會的,我的觀點也許和部分琴家不同,我現在還堅持著我的思維,為什么呢?我的思維是基于事實。任何研究脫離了事實,單純主觀臆斷,那是不成熟的表現。
云浩:基于事實?也就是說要以古琴曲描述的實際存在作為基礎。
龔一:這不是太簡單的道理了嘛,簡單到讓我感覺到有點著急,這么簡單,怎么變成了少數呢?變成了人家認為離經叛道呢?所以說我著急的不是我自己,我著急的是事業。任何學科進行研究的時候,一定要從本體的角度去考慮,本質的研究、課題的研究必須要求以歷史的事實存在作為依據。
而修為這個問題,是藝術的共同功能,書法、鋼琴、太極拳這些,都是可以起到提煉自己修為功能的,古琴只是其中之一。也就是說,不要變成唯獨古琴才是增加了文化修養的。不論西方音樂、中國音樂,沒有技巧都是完不成韻味的,這就像你要造房子,地基打不牢,你的房子是造不好的,造起來是危房,是不能出售的房子。
空談意境沒意義
龔一:其實,中國、外國都是一樣的。有的人說,外國人光講技巧,我們中國是講韻味的,我不同意。小提琴曲《無窮動》如果拉得不熟練的話,他彈慢的曲子也不行的。所以我們古琴技巧不好的話,這韻味是達不到的。
云浩:舍去技巧,空談意境,肯定是……
龔一:對,不能空談意境,倪云林如果一支筆都攥不好,他哪里能夠畫出那些稀稀疏疏、清微淡遠的感覺呀?所以,我是把藝術的最高境界和最初步的技術性的訓練看成是兩者不可分的。技巧在先,藝術的最高境界在后。你是畫畫的,你該知道的,如果技巧都沒有,你畫什么畫呢?
藝術總抓著陽光一面
云浩:那么,從歷史上看,古琴是什么時候誕生的?
龔一:不論是文字記載,還是實物出土,都可以證明,至少在春秋時代就已經有古琴了,《詩經》里面有記載,曾侯乙墓里也出土了,后來馬王堆漢墓里也出土了,所以說中國古琴在三千年前就有了,但那時叫“琴”,后來叫“古琴”。
云浩:琴與古琴有什么區別?
龔一:一脈相承,結構、振動原理、發聲原理、形制基本相同,但是在尺寸上有點不一樣。我們現在能見到的最早的古琴是唐朝的,形制和今天一模一樣,以后1000多年來基本沒有變化。唐朝早期的作品有寫孔子的,也有寫文王的,到后來有寫屈原的,還有《刺客列傳》的,到了南宋,有寫文人憂國的《瀟湘水云》,到清朝還有寫岳飛《滿江紅》的。我的結論是,古琴和別的樂器一樣,是抓住了社會重大題材,表現人的思想感情的。再說得時髦一點,它抓住了“主旋律”這三個字。我說的主旋律是更大范圍的,古琴總是寫正面的,寫岳飛,可不會寫秦檜,寫屈原,可沒有寫楚懷王,藝術作品都是抓住了陽光的一面。
文化高度源自內容
云浩:或者換一個說法,是不是它是一種君子之道。
龔一:是君子之道,但不要把二胡、笛子、琵琶、鋼琴都排在外面,彼此都是一樣的,都是君子之道,這是藝術的共同規律。
云浩:但是古琴的地位可比它們高太多了。是不是可以這么理解,古琴的這種演奏方式,包括它的形制本身,都藏著一個中國人這種審美的一種極致的追求,別的琴也有審美,但不是頂尖。而古琴的這個形制呢,千古以來就是沿著中國人審美的那個最核心的東西在發展,它代表了音樂文化的至高境界。
龔一:在我看來這是表象的,最根本的是它的內容所決定的。別的樂器的歷史也很長,但是它沒有這個內容。
云浩:為什么呢?
龔一:首先,你有一千年以前的內容嗎?沒有,五百年以前呢?也沒有。第二,我動不動就是《史記·刺客列傳》,我動不動就是漢代文人與名人蔡文姬的故事,我們一表現就是20多分鐘,像《廣陵散》,如此深刻,如此勁道,這才讓古琴占有了這么高的文化地位。
越完整的藝術越難突破
云浩:像塤、笛子、簫,包括一部分拉弦樂器、彈撥樂器,也都很早,并不比古琴晚,為什么它們就沒有這么高的地位?
龔一:因為皇帝把這件樂器捧得至高無上。城里頭、皇宮里頭都喜歡把頭發梳得高高的,老百姓不就全部都要模仿嗎?這樣的一個內容,又是那么有深度、廣度,又有社會的大題材,加上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抬轎子,當然這門藝術就高了。雖然笛子很流傳,也有《梅花烙》等題材,可它沒有曲子。古琴有曲子存在,還有完整的記譜法。
云浩:完整的記譜法嗎?
龔一:對,這就是所有的民族樂器所不具備的條件。它時間那么長,有那么豐富的遺產,又有自己的理論體系。所以說呢,它就成了一個堡壘,完整的一個體系。就像京劇、昆劇一樣,但是到了這個階段,一門藝術再要突破,也就有了它的難處。因為你太堅壘,從外面打進來,從里面打出去,都不是很容易的。所以說在這樣的體系完整、理論、審美、社會地位、樂曲、歷史,都是比較具有代表性的一件樂器、一門藝術,要改革就有它的難處。因此在革新中出現阻力,出現不同的學術觀點,也很自然。
四千年前的審美符號
龔一:在四川,金沙遺址,四千多年以前的一個古墓,他的墓里挖出來一種器皿,這個器皿的形制和古琴完全一樣。這個器皿大概20多厘米長、5厘米寬,這么一件小器物,從四千多年前一直到現在,明清出土的文物中都有它的存在。
云浩:五厘米,這么小。
龔一:這個連臺灣故宮里面的長者都說不清它叫什么。這種東西我們也有叫做“琴撥子”的,這是一種家里頭的一種小用具。我是想跟你說,這個形狀就是我們華夏民族所喜歡的一種線條、一種結構。我的聯想:這個美學延續了四五千年,因此,到了古琴上,是這個形狀,這個美學的擴大、延伸。
云浩:相對于西方的“黃金分割率”,這就是我們的形制。
龔一:對。這個我一直沒有找到正確的名稱,在臺灣故宮博物院參觀時,我和他們的館長秦孝儀說:“你們這個標錯了,這不是琴撥子,我們不會用它來撥琴的。”他馬上帶我找一位老前輩,老前輩謙虛得讓我驚訝:“哎呀,我們也不懂啊,我們也就隨便地先標上個名字吧,您跟我們說一說。”搞得我有點難為情了。總之,這個東西我們還要細膩地去研究,不要糊里糊涂地去研究學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