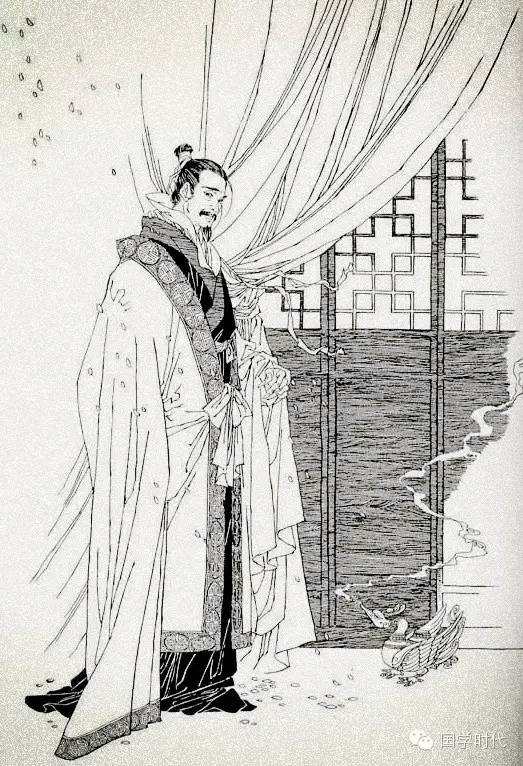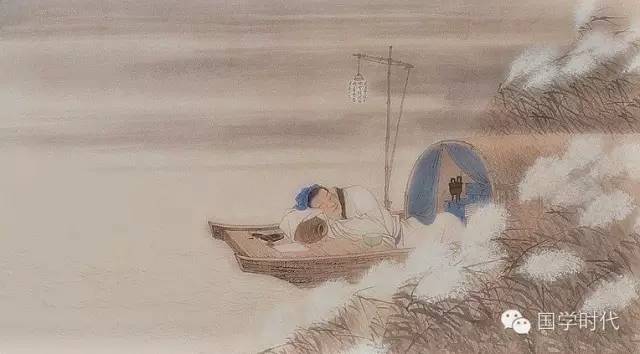詞中之帝
李煜,字重光,號鐘隱,少聰慧,美風儀,“廣顙隆準,風神灑落,居然自有塵外意”(宋·史溫《釣磯立談》)。25歲嗣位南唐國主,39歲國破為宋軍所俘,囚居汴京三年,被宋太宗賜藥毒死。
李煜雖不善治國,但精通六經,洞曉音律,工書善畫,尤善詩詞文章。其詞流傳下來的總共不過三十余首,但有不少堪稱千古絕唱,被后人尊為“詞中之帝”。
李煜的詞,以其亡國為界分為前后兩期。前期的詞多描寫奢侈的聲色和旖旎的風情。毫不掩飾自己對宮廷享樂生活的沉迷與陶醉,如《玉樓春》:
曉妝初了明肌雪,春殿嬪娥魚貫列。笙簫吹斷水云間,重按霓裳歌遍徹。
臨春誰更飄香屑,醉拍闌干情味切。歸時休放燭光紅,待踏馬蹄清夜月。
李煜詞的價值主要體現在后期,寫亡國之痛,血淚至情。由一國之君而淪為國家易姓、家人不保、人盡可辱的囚徒,其心理落差是可以想見的。入宋后,其詞作的風格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深衷淺貌,短語長情。如《烏夜啼》:
林花謝了春紅,太匆匆。無奈朝來寒雨晚來風。
胭脂淚,留人醉,幾時重。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
有凄清,有悲慨,有沉凝,也有郁結。從惜花寫起,“太匆匆”三字,極傳驚嘆之神,“無奈”句,又轉怨恨之情,說出林花速謝之故。朝是雨打,晚是風吹,花何以堪,人何以堪。說花即以說人,以花落之易,觸及人別離之易。花不得重上故枝,人亦不易重逢。愁與恨如此之濃,直如胭脂和淚,化解不開。最后以水之必然長東,喻人之必然長恨,沉痛已極。
身為亡國之君的李煜,在詞中很少作帝王家語,倒是以近乎普通人的身份,訴說自已的不幸和哀苦。這些詞,便具有了可與人們感情上相互溝通、喚起共鳴的因素。如《浪淘沙》:
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耐五更寒。夢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
獨自莫憑欄,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
從生活實感出發,抒寫心底的深哀巨痛。“流水落花春去也”,美好的東西總是不能長在;“別時容易見時難”,又擴展為一種普遍的人生體驗。
李煜的詞,藝術上最突出也是最著名的,還是那首《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詞中不加掩飾地流露出故國之思,并把亡國之痛與人世無常的悲慨融合在一起,把往事、故國、朱顏等長逝不返的悲哀,擴展得極深極廣,滔滔無盡。一任沛然莫御的愁情奔涌,自然匯成“一江春水向東流”那樣的景象氣勢,形成強大的感染力。物候與心境,自然與生命,天命與人事,是那樣互相融通與感應,又是那樣互相隔膜與巨斥。是愁如春水,還是春水如愁?人,就在這無限的追問中向審美世界沉入。
無論是前期還是后期,李煜的詞有其一貫的真。這位“生于深宮之中,長于婦人之手”,閱世甚淺的詞人,始終保持較為純真的性格。在詞中一任真實情感傾瀉,而較少理性的節制。
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贊曰:“詞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變伶工之詞而為士大夫之詞。”李煜在詞史上最重要的貢獻便是他改變了詞的傳統,在內容上由寫思婦怨女、離愁別緒傾向寫國破家亡的深哀與劇痛,在形式上逐漸減少乃至消釋了詞的宮廷貴族式的娛樂性。李煜詞不再“以男子作閨音”,而是徑由自我發端,直接書寫自我,增強了詞作者的主體意識。
【國學時代,時代國學】
GuoxueTimes
Sheer
Reading Pleasure
與您一起分享文化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