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存古學堂是趙啟霖仿張之洞在湖北創辦國家機構而設,對人選學生要求極高,大多要求為舉人,貢生及新式學堂中頂尖人才,而其旨在“保存國學,尊重蜀賢”。蒙文通進入學堂后,仍“兩耳不聞天下事,一心只讀經史書”,時刻鉆研于國學之中,且不拘于大師們平時所言,課余自行購置大量書籍,廣涉經、史、子、集,對四庫全書也開始涉及,早年廣博的知識使蒙文通在后來治經、史、佛中都能顯示出深厚的根基。
蒙文通治佛學,發源于中國20年代初期的今古文的大論戰。1918年蒙文通從四川存古學堂畢業后,返回家鄉鹽亭以辦私塾為生,繼續在破廟里從事經史研究,長達三年之久。五四運動以后,中國掀起一場新興的文化革命。以魯迅、陳獨秀等為代表的新文化干將與吳宓、章士釗等學衡派發生激烈論戰。在這場莫衷一是的爭論中蒙文通難以取舍,便辭去重慶府聯中和重慶省立二女子師范學校的職務,“游學于吳越之間,訪學于各大經史家門下,與章太炎論古今之流變,與歐陽竟無論佛典之影響”。在長期的游學過程中,蒙文通仍難以在二者之間取舍.卻悟及佛學在中國思想中的深層的潛意識影響,蒙文通便停留在歐陽竟無所辦的“支那內學院”內,潛心研究佛學,從1923年到1927年,長達四年之久。此期,蒙文通與湯用彤、能十力、呂澂等朝夕相處,互相爭論,雖各論不一,相異甚大,甚至針鋒相對者亦有之,但這對蒙文通佛學研究益發登堂入室有極為重要的作用。
在長期的“閑話”與“爭辯”中,蒙文通得以旁及各學派立論的根基及其論證的過程,從而使自己的體系益發精密、嚴整,以致在佛學研究上當時少有人能及。歐陽竟無由此而寄希望于蒙文通,希望他繼承衣缽專研佛學。“改好刻竣(《中庸傳》),先寄此。此惟我弟能知,個中人談其事,欲其速達也。……全恃觀行,一絲九鼎;繼續大難,德孤鄰寡,亦可悲矣!”“孔學,聊發其端,大事無量,甚望我弟繼志述事。”蒙文通離開“支那內學院”后,歐陽竟無己又常致函問訊,希望“共剪西窗燭、共作刻入談”,“奈何經年不遺我一字!”
不負歐陽竟無重望,蒙文通在佛學研究上相繼取得重大突破。歐陽竟無看完他所撰的《中國禪學考》、《唯識新覺羅》后,大喜過望,竟又重閱一遍,時而憤筆于原稿之間,時而揮墨于稿紙之上。之后,蒙文通所撰兩篇皆被刊于院刊《內學》創刊號上,緊接于歐陽竟無的《佛法》、《心學》二文之后。
在經史文學上,蒙文通早在四川存古學堂便顯示出深厚的根基。蒙文通于1914年所著的《孔氏古文說》,筆觸深入舊史與六經的根基,由此辨其差別進而解開以后學者在二者上爭論的癥結。蒙文通獨特的見地深得其師廖平的贊譽:‘文通文如桶底脫。佩服!佩服!后來必成大家。”之后,蒙文通又相繼撰述《近二十年漢學之平議》、《經學抉源》、《天問本身》、《周秦民族史》、《中國史學史》、《考古甄微》、《儒家政治思想之發展》、《墨學之流變及其原理》等專論。
有別于陽翰笙寫歷史劇《天國春秋》借古以諷今,蒙文通治學專務學問本身。他常筆觸探幽,從其本源尋找立論的根基進而撰述歷代的變遷過程,逐條分源各派進行深人剖析,辨其前后承接及延續,從而使時分不經意的思想、詞條都歸人相應的淵源。由此廖平稱其為“如桶底脫”。對于經史,蒙文通一向視之為歷史的經緯,二者與文學互相交疊共同組成歷史的洪流。他的著述論證也常以經治史,以史注經二者相互疊交,相互出人而輝映成趣。1968年蒙文通所著的《越史叢考》一書即詳細引用一百三十余種古文獻資料,有經有史,經史互證。文章從十二個角度探究越南的起源、發展、擴張、削弱的過程,論證謹嚴,資料詳實,極具說服力。80年代初期,越南當局授意其國內學者著《越南古代史》,以期為侵略我國尋找輿論借口。1984年,中華書局即將蒙文通所著《越史叢考》資料整理出版,《越南古代史》一書產生的輿論效果由此而消失。
蒙文通所著、所講魏晉南北朝及隋唐斷代史為當時國內權威。湯用彤先生曾在1957年的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會上發言提及蒙文通的專長:“現在很多人知道蒙文通是個史學家,并且是個上古史學家,但很少有人知道蒙文通在中國思想史方面也有特長,因為研究中國思想史特別離不開經學和佛學。此外,他對唐宋思想史的發展也極有研究,特別注意了過去向未被人注意的那些思想家。”因此,當胡適不再延聘蒙文通時,錢穆曾言:“文通所任,乃魏晉南北朝及隋唐兩代之斷代史。余敢言.以余所知,果文通離職,至少三年內,當物色不到一繼任人選。”后來蒙文通離職北大,隋唐史一門先由陳寅恪先生擔任。還未教一個月,其夫人就威脅說:“若不辭職北大,即不再過問其三餐。”隋唐史只得由各學者分授,學生甚為不滿,胡適為此也大傷腦汁,卻也拉下下學者的臉面到天津去延聘蒙文通,授課一事也只好敷衍了事。
文如其人,蒙文通生性剛直而不輕易茍同于人。他先后執教于重慶府聯中、重慶第二女子師范學校、成都大學、中央大學、河南大學、北京大學、天津第一女子師范學校、四川大學、華西大學等校。任教期間,蒙文通不僅學術迥異于人,而且脾性也有剛氣。1931年四川軍閥為節省教育經費以挪至他用,強行將成都大學。成都師范大學、公立四川大學合并為國立四川大學。蒙文通憤而辭去職務以示抗議,后執教于河南開封;在河北女子師范校期間,日偽政府多次強“邀”其撰寫類似《越史叢考》之類的政治學術文章,并以重金相誘。蒙文通雖一家七口,經濟拮據,加之抗日戰爭爆發,家計日益困頓,仍對來者嚴辭相拒。后來舉家遷往四川,執教于川大。而他對胡適的態度則近乎有幾分“牛”氣。在北大期間他竟一次也沒有前往胡適家拜訪,錢穆先生亦稱“此亦稀有之事也”。這事弄得胡適十分難堪,胡適以至置北大隋唐史無人授課一事于不顧也不再續聘蒙文通,蒙文通也處之泰然,仍我行我素,后轉至天津一女師,與徐錫予及其他人交往依然如故。
從河北女子師范大學轉至四川大學后,蒙文通應郭有守之邀,出任四川省圖書館館長。新中國成立伊始,蒙文通又兼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員和學部委員。此期蒙文通猶喜撰述從未被人注意的思想家,辨其本源,考其流變,進而論其在歷史中的影響,同期而地域、傳說的注重較前期大為提高。在巴蜀史的研究中,蒙文通的研究也貫穿了他由經人史、經史兼治的學風。
1968年,蒙文通撰完《越史叢考》的初稿后便與世長逝享年七十四歲。
<來自: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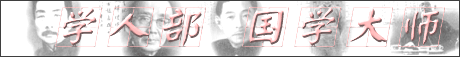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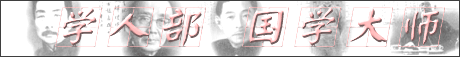


mailto:guoxue@guoxue.com
![]() 010-68900123
010-68900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