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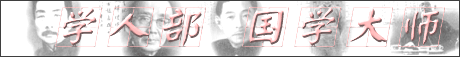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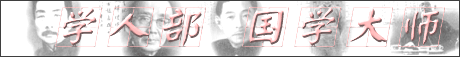 |
|
|
|
||
|
|
大師生平|著作年表|著述索引|作品選讀|大師研究|研究著述|書品推介|研究學(xué)人|相關(guān)鏈接
|
|
|
蒙文通對今文經(jīng)學(xué)的貢獻(xiàn) |
|||||||
陳德述 |
||||||||
| 今年是國學(xué)大師蒙文通(1894—1968)先生誕辰110周年紀(jì)念。蒙文通是近代著名經(jīng)學(xué)家廖平的學(xué)生,他知識淵博,學(xué)術(shù)貢獻(xiàn)十分廣泛。本文只就蒙文通對今文經(jīng)學(xué)研究的貢獻(xiàn)作一些介紹、分析和評述,指出他對廖平經(jīng)學(xué)的修正、發(fā)揮與發(fā)展,突現(xiàn)他對今文學(xué)家的理想制度及其思想實(shí)質(zhì)的揭示和闡釋等等。 一、對今文學(xué)內(nèi)部派別的修正與發(fā)展 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dú)尊儒術(shù)”之后,中國的學(xué)術(shù)思想史,特別是儒學(xué)的歷史是在經(jīng)學(xué)的模式中發(fā)展的。經(jīng)學(xué)是對儒家的經(jīng)典進(jìn)行解釋、引伸和加以發(fā)揮的學(xué)問,是中國學(xué)術(shù)文化史上特有的現(xiàn)象,占據(jù)著從漢代到清代兩千多年的中國學(xué)術(shù)思想史,因此,不研究經(jīng)學(xué)就不知道儒學(xué),因而也不知道中國學(xué)術(shù)思想發(fā)展的內(nèi)涵、歷史過程和特點(diǎn)。 歷史上,漢代的經(jīng)學(xué)分為今文經(jīng)學(xué)和古文經(jīng)學(xué)。以什么標(biāo)準(zhǔn)來劃分今文經(jīng)學(xué)與古文經(jīng)學(xué),長期以來眾說紛紜,有以文字的不同而分今古者;有以師說的不同而分今古者;有以是否立于學(xué)官來分今古者等等。近代著名今文經(jīng)學(xué)家廖平首倡以“禮制”的不同來區(qū)分今古學(xué)。這一理論超越了以往一切劃分今古學(xué)標(biāo)準(zhǔn)的說法,把今古學(xué)劃分的標(biāo)準(zhǔn)置于科學(xué)的地位上。為此,被蒙文通謄為是:清代學(xué)術(shù)史上的“三大發(fā)明”之一,“為百世不易之論”,具有“劃分時代”的意義(蒙文通:《蒙文通文集》第三卷,第101頁、第116頁、第142頁,巴蜀書社,1995。以下凡引《蒙文通文集》者,只注卷數(shù)和頁碼。) 廖平的經(jīng)學(xué)是經(jīng)學(xué)史上的高峰,他為之做出了獨(dú)特的貢獻(xiàn)。按照蒙文通的看法,廖平的學(xué)術(shù)貢獻(xiàn)在于:“廖師獨(dú)造之學(xué),尤在《春秋》,初蓋專精於《春秋》,而后偶悟於禮制,故其廖師之學(xué),以禮言,則為守兩漢之壁壘,俾今古不相淆”;“蓋其說禮固能明兩漢之學(xué),曉然於今古之辨,突過前儒,至若究明《春秋》,則已決蕩周秦,棄置兩漢今古學(xué)而不屑道也。然其發(fā)明兩漢今古學(xué)之功人知之,其破棄今古直入周秦,人未有能知之者。”(第三卷,第134頁)即廖平的學(xué)術(shù)貢獻(xiàn)有兩個方面,一個是學(xué)術(shù)界已經(jīng)知道的以“禮制”分今古學(xué)的理論,另一個是學(xué)術(shù)界還不知道的“破棄今古直入周秦”的理論。蒙文通作為廖平的學(xué)生,不只是繼承了廖平的學(xué)說,更重要的是進(jìn)行了修正、發(fā)揮和發(fā)展。但是,蒙文通對廖平提出的、具有“劃分時代”意義的以“禮制”區(qū)分今古學(xué)的理論始終沒有改變,只作了一些修正和補(bǔ)充。他反復(fù)高度評價廖平關(guān)于以“禮制”分今古學(xué)的理論,他說:“先生依許、鄭《五經(jīng)異義》以明今古之辨在禮制,而歸納於《王制》、《周官》,以《王制》、《谷梁》魯學(xué)為今學(xué)正宗。不分江河,若示指掌,千載之惑,一旦冰釋。先生《春秋》造詣之微,人不易知,由《春秋》而得悟於禮制,遂不脛而走天下。皮氏(錫瑞)、康氏(有為)、章氏(炳麟)、劉氏(師培)胥循此軌以造說,雖宗今宗古之見有殊,而今古之分在禮制,則皆決於先生說也。”(第三卷,第140—141頁)蒙文通還引證劉師培的話來旁證廖平以“禮制”分今古學(xué)的理論,劉師培說廖平“長於《春秋》,善說禮制,洞澈漢師經(jīng)例,魏晉以來未之有也。”(轉(zhuǎn)引自《蒙文通文集》第三卷,第105頁) 蒙文通指出,廖平因提出以“禮制”分今古學(xué)的理論,成了學(xué)術(shù)史上“劃時代的人物”。“自先生今古之辨明,天下蓋莫之能易。然《六經(jīng)》儒家之學(xué),何由而有二派之殊,則人各異論,先生固亦屢變其說而莫可定,然終以《王制》、《周官》為之主,則未始有異,則先生之說雖變,而謂之不變亦可。”“先生於《今古學(xué)攷》以今為改制,古為從周;古為孔子壯年之學(xué),今則晚年素王之制,此一說也。繼疑《周官》為劉歆偽書,而今學(xué)乃孔子嫡派,作《古學(xué)攷》,此二說也。及尋諸《大戴》、《管子》,與所謂《刪劉》之條,皆能符證,則斥為歆偽之論不可安,於是以今古為孔子小統(tǒng)與大統(tǒng)之殊,此三說也。三變之說雖殊,而皆以《王制》、《周官》為統(tǒng)歸。”(第三卷,第142頁)蒙文通說:“自井研廖先生據(jù)禮數(shù)以判今古學(xué)之異同,而二學(xué)如冰炭之不可同器,乃大顯白”,廖平的經(jīng)學(xué)前三變與劉師培“著論,以為東西二周,疆理則殊,雒邑、鎬京,禮文復(fù)判,此劉釋今古之微意,而未大暢其說者也。四說雖立意不同,而判今古為不可相通之二學(xué)則一也。”今古學(xué)不可相通之處在于“禮數(shù)”(禮制),“依禮數(shù)以判家法,此兩師之所同,吳師亦曰:‘五經(jīng)皆以禮為斷',是固師門之緒論僅守而勿敢失者也。”(第三卷,第46頁)可見,蒙文通對廖平以“禮數(shù)”、“禮制”分今古的理論的評價是很高的。 蒙季甫是蒙文通的堂弟和學(xué)生,在蒙文通作古多年之后說:“禮制是通群經(jīng)的,從某種意義上講,也可說是經(jīng)學(xué)的骨架。”“先兄從廖氏學(xué)經(jīng)學(xué)時,廖氏正大倡小大、天人之說,但兄所承受于廖氏者只是以禮制判今、古這一核心。”還說“先兄講經(jīng)學(xué),最推崇廖季平。推崇廖氏以禮制判今古,從而使?jié)h儒在禮制上的分歧,大部分可以從今、古學(xué)派的不同得到解決,是近世經(jīng)學(xué)上的一大貢獻(xiàn)。”(引自蒙默編:《蒙文通學(xué)記》第61頁、第60頁、第62頁,三聯(lián)書店,1993。)可見,廖平以“禮制”分今古學(xué)經(jīng)學(xué)的“骨架”和“核心”的理論,蒙文通是加以繼承的。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蒙文通把廖平關(guān)于“禮制”分今古學(xué)的發(fā)明,看成是“固守不敢有所掉失”的師門“緒論”,是不能超越的“百世不易之論”。蒙先生之子蒙默教授在《論經(jīng)學(xué)遺稿三篇·后記》中說過,“先君之說前后亦三變”,但是以“禮制”分今古學(xué)的理論始終沒有改變,他對今文學(xué)的“井田”等五種制度的分析和闡釋也證明了這一點(diǎn)。如果說蒙文通另立一個區(qū)分今古學(xué)的標(biāo)準(zhǔn),他不但否定了廖平經(jīng)學(xué)的貢獻(xiàn),而且也否定了自己,從而也挖掉了廖平經(jīng)學(xué)的基礎(chǔ)。 蒙文通在講到自己的學(xué)術(shù)貢獻(xiàn)時說,“到得近世井研廖先生著一部《今古學(xué)攷》,真是平分江漢,劃若鴻溝,真是論今、古學(xué)超前絕后的著作”。“我敢說,石渠議后莫有可和他比擬的。近來講今文的,談古文的,何嘗出得他的范圍。或者采取他的說法,或者攻擊他的說法,無論他們?nèi)绾屋p侮這位老人家,他們都是在《今古學(xué)攷》的范圍里打轉(zhuǎn)。現(xiàn)在我拿出我的見解來討論今古兩家的究竟,我也還是出不了《今古學(xué)攷》的范圍。我的意見自然有些和他不同,說我是脫離這部書在宣告獨(dú)立也可。說近來的今文家、古文家和我的這篇文字的主張,都是《今古學(xué)攷》一書下面的三個修正派亦無不可。”(第三卷,第12--13頁)蒙文通在這里說的不論是他對廖平學(xué)說的“修正”也好,還是“獨(dú)立”也好,都沒有超過廖平在《今古學(xué)攷》中所提出來的以“禮制”分今古學(xué)的理論。但是,他沒有在廖平的學(xué)說中踏步不前,而是對廖平經(jīng)學(xué)做出了許多的新的發(fā)揮和發(fā)展,做出了他自己特有的貢獻(xiàn)。 蒙文通對廖平今古學(xué)分派的學(xué)說進(jìn)行了修正和發(fā)展。廖平在《今古學(xué)流派表》中說:“今魯派,今齊派,今韓派,今緯派,今《易》、《尚書》、《詩》、《孝經(jīng)》、《論語》派。古《周禮》派,古《國語》派,古《左傳》派,古《孝經(jīng)》派,古《易》、《尚書》、《詩》、《論語》派。”(李耀先主編:《廖平選集》(上)第47頁,成都,巴蜀書社,1998。)從這里可以看出,廖平對今文學(xué)主要是以地域分派,對古文學(xué)主要是以典籍分派,他的劃分是不夠科學(xué)和規(guī)范的。為此,蒙文通修正了廖平區(qū)分今古學(xué)派別的說法。 蒙文通認(rèn)為,漢代官方的十四博士學(xué)(即今文學(xué))是“不完全一樣”的,除遵從的“禮制”相同以外,其余有許多不同的地方。“皇帝不愛的書,便不能立博士,博士也就排斥他們。他們的學(xué)問只好傳授於民間,也就不必跟著皇帝說,后來便與博士的學(xué)問分成兩派,便分了個今文、古文的差別。”(第三卷,第15頁)為何皇帝愛好今文學(xué)而厭惡古文學(xué)呢?是因?yàn)椤安┦拷裎闹畬W(xué),固一遵朝廷之制者也。”(第三卷,第66頁)在這個漢代統(tǒng)治者推崇的今文學(xué)內(nèi)部,也有相反異的地方。在蒙文通看來,是因?yàn)榻裎膶W(xué)內(nèi)部有派別不同的緣故。“今文學(xué)是兩部分學(xué)問混合組成的,一部分是魯學(xué),一部分是齊學(xué),又混進(jìn)去了一個內(nèi)學(xué),便組成了今文學(xué)。”(第三卷,第22頁)可見,今文學(xué)由魯學(xué)、齊學(xué)和內(nèi)學(xué)三派組成的。古文是在晉國流傳的學(xué)問,魏國是古文家的發(fā)源地。“三晉的學(xué)問正是和孔子背道而馳的”,古文家的書是古代流傳的史傳,“到了漢代,那一批古文家,把一些古史傳記一齊混入經(jīng)來”(第三卷,第19頁),這樣古文家便成了儒家的一個學(xué)派。古文學(xué)源于晉學(xué)。古文學(xué)不是純?nèi)鍖W(xué),“晉國的學(xué)問,根本是古史,孔子的弟子后學(xué)如像子夏、李克、吳起一般人,都顯重於魏,孔子的學(xué)問自然也就傳到魏國去,二者化合起來,這一派的孔學(xué),便又不是純正的孔學(xué),孔子的學(xué)問里邊混入了許多古史的說法。”蒙文通認(rèn)為,在古文學(xué)的組成中晉學(xué)占了大部分,此外還有壁中書和流傳于民間的學(xué)問。 蒙文通指出:《六藝》是魯人之學(xué),《谷梁》是魯學(xué),魯學(xué)是《六經(jīng)》的正宗,是孔子學(xué)說的嫡派,是謹(jǐn)守舊義的、謹(jǐn)守師傳的、純正的儒學(xué)。《伏生尚書》、《夏侯尚書》、《田何易》、《梁丘易》、《魯詩》、《后氏禮》都是魯學(xué)。 在西漢的十二博士中公羊?qū)W是占統(tǒng)治地位的,董仲舒是公羊?qū)W大師。《公羊》是齊學(xué),齊學(xué)源于稷下學(xué),稷下學(xué)為百家之學(xué),駁雜而不純。“《六經(jīng)》不是齊國的學(xué)術(shù)。在齊襄王時,齊國的稷下學(xué)很發(fā)達(dá)。在稷下學(xué)中有陰陽家、有儒家、有墨家、有名家、有法家、有道家。蒙文通說,孔子的《六經(jīng)》在稷下中只好占個小部分。這一小部分的《六經(jīng)》,和百家學(xué)術(shù)在這里就混合起來,百家諸子的學(xué)說里面混有了孔子的理論。孔子《六經(jīng)》里面自然也有諸子百家的理論,齊國以后傳出的《六經(jīng)》自然就沒有魯國傳出來的純粹了。”(第三卷,第26頁)“孔氏之學(xué),於時遂流入於齊,別為齊學(xué),與魯人六藝之學(xué)有異”。“就漢世言之,魯學(xué)謹(jǐn)篤,齊學(xué)恢宏,風(fēng)尚各異者,正以魯韓太固儒學(xué)之正宗,而齊乃諸子所萃聚也。”(第三卷,第90頁)魯國的孔子之學(xué)傳到齊國后,齊國人固然以百家學(xué)說為主旨來吸取孔子的學(xué)說,齊學(xué)會聚了諸子之學(xué),于是孔子的義理就被鄒衍的方術(shù)之學(xué)所浸淫,儒家的禮制被淳于髡的學(xué)說所糅雜,這樣齊學(xué)就雜而不純了。《施氏易》、《孟喜易》、《歐陽尚書》、《齊詩》、《韓詩》屬齊學(xué)。齊學(xué)雜而不純,是因?yàn)榛烊肓酥T子百家之學(xué)。孔子的《六經(jīng)》到了燕國后,也和諸子百家混合起來,與燕國自身的學(xué)術(shù)融合起來,形成了燕學(xué)。燕學(xué)與齊學(xué)是不同的,它們混合諸子百家之說卻是相同的,所以蒙文通說燕學(xué)可以附屬于齊學(xué)。齊學(xué)還有一個特征,就是把海上的神仙方術(shù)混入了《六經(jīng)》,好言災(zāi)異,因而使齊學(xué)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 蒙文通說:“《公羊》齊學(xué),既雜以淳于髡、鄒衍之言,如說襄公滅紀(jì)為復(fù)九世之仇等事,尤為袒齊之明效;《谷梁》魯學(xué),言禮則與孟子符同,正以孟子為魯學(xué)之嫡派也。魯以六藝為正宗,齊為百家所聚萃,持百家之語比之孟氏所陳,而后魯學(xué)之陳義足珍,乃更昭然顯著也。”(第三卷,第91頁) 蒙文通認(rèn)為,漢代今文學(xué)中除了魯學(xué)和齊學(xué)這兩個派別外,還有一個內(nèi)學(xué),即讖緯之學(xué)。蒙文通在這里說的“內(nèi)學(xué)”,主要是指“緯書之學(xué)”。今文學(xué)家為了服從于統(tǒng)治者的需要,屈服于統(tǒng)治者,把今文學(xué)的斗爭性和革命性都抹殺掉了,背叛了今文學(xué)的宗旨,在這樣的情況下,今文學(xué)分為“公開”的和“秘密”的兩種方式傳播,“秘密”傳的內(nèi)容才是今文學(xué)的真諦。蒙文通說: “今文學(xué)本是富有斗爭性的,而董仲舒放棄了這一點(diǎn)。降低了儒家的理想要求,因而對專制君主沒有危害反而有益,所以董仲舒的儒學(xué)是妥協(xié)的、讓步的了。這就無怪乎漢武帝不但能接受反而加以推崇。所以像趙綰、王臧、眭孟、蓋寬饒那些堅決斗爭的人,必然以身殉道。在這種高壓之下,一部分人變節(jié),放棄了主張,入於利祿之途;一部分人只能隱蔽起來,秘密傳授,所謂‘以授賢弟子',公開講是表面的一套,秘密講的才是真的一套。這就是后來的所謂‘內(nèi)學(xué)'。同時又不能不用陰陽五行為外衣當(dāng)煙幕,這就成為后代緯書(不是讖記)的來源。在博士官的學(xué)者,就入到了‘分析文字,煩言碎辭'的章句之學(xué)。今文學(xué)從這里就分為二了。傳內(nèi)學(xué)的自負(fù)為‘微言大義',傳外學(xué)的(博士)‘於辟雍、巡狩、封禪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源',所以今文大義也就從此湮滅了。到了石渠、白虎兩次會議,專論禮制,由皇帝稱制臨決以后,就成為御用品了。”(第三卷,第160頁) 由此可見,蒙文通看來,漢武帝獨(dú)尊的儒學(xué),不是真正的儒學(xué),已經(jīng)是變了味的了。這種儒學(xué)拋棄了儒家的理想和孔子學(xué)說的真諦。傳授儒家真正理想的的人是有生命危險的,他們只能進(jìn)入秘密狀態(tài)進(jìn)行傳播,于是就形成了漢代的緯書之學(xué)。但是,今文學(xué)的傳播并沒有絕跡,儒家的“微言大義”逐漸由秘傳轉(zhuǎn)入到了躬行實(shí)踐,今文學(xué)的《齊詩》和京房《易傳》中講的“革命”思想進(jìn)入了道教,成為黃巾起義的指導(dǎo)思想了。蒙文通指出: “到成帝時,齊人甘忠可造《天官歷包元太平經(jīng)》十二卷,以教夏賀良、丁廣寬、郭昌諸人,於是解光、李尋也竭力宣傳這一套學(xué)說,這些人都是今文學(xué)家。后來也因此而遭到誅殺或滅死一等的處分。《太平經(jīng)》的思想,對于漢末的農(nóng)民起義實(shí)質(zhì)上起了極大的作用,可說《太平經(jīng)》是倡導(dǎo)農(nóng)民起義的巨著。”(第三卷,第161頁) 也就是說,今文學(xué)的革命思想被甘忠可的《天官歷包元太平經(jīng)》所吸收,通過《太平經(jīng)》把今文學(xué)的革命思想傳給農(nóng)民。農(nóng)民起義的領(lǐng)袖張角號稱黃巾,創(chuàng)立“太平道”,提出“蒼天已死,黃天當(dāng)立”的口號,號召農(nóng)民起來推翻漢代統(tǒng)治者,所以今文學(xué)的思想不只是秘密傳授,而是真正付諸實(shí)踐的。 以上是蒙文通在廖平學(xué)說的基礎(chǔ)上,對今文學(xué)內(nèi)部流派的內(nèi)容所作的“修正”與發(fā)展,這些修正與發(fā)展,是蒙文通對今文學(xué)研究所做出的新貢獻(xiàn)。蒙先生的貢獻(xiàn)仍然在堅持以“禮制”劃分今古學(xué)的理論的基礎(chǔ)進(jìn)行的。但是,他也作了一些修正,蒙文通說:“井研先生以今文學(xué)統(tǒng)乎王,古學(xué)帥乎霸。齊、魯為今學(xué),燕、趙為古學(xué)。詳究論之,趙魏三晉為古學(xué),三晉為晉文霸制,齊學(xué)為齊桓霸制。”(第三卷,第95頁)今古學(xué)之間的界限確是“禮制”的不同。同時,在今文學(xué)內(nèi)部有齊學(xué)和魯學(xué)之分,也是因?yàn)椤岸Y制”有差異而不盡完全相同的緣故。蒙文通說:“各國禮制,本自不同。齊、魯之學(xué),因之以異。《公羊》言‘歲則三田';《谷梁》言‘四田'。《王制》與《公羊》同,與《谷梁》異。《王制》言‘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公羊》以‘伯子男同一爵。'是《王制》為今文“禮制”之宗,而或取齊,或取魯,左右采獲以為書。故俞蔭甫謂《王制》與《公羊》同,廖師又謂其與《谷梁》同,則今文學(xué)為糅合齊魯兩學(xué)而成者也。”(第三卷,第90--91頁)即漢今文學(xué)是魯學(xué)與齊學(xué)混合的產(chǎn)物。 二、從理想制度中闡釋今文經(jīng)學(xué)思想的內(nèi)涵和革命意義 蒙文通對今文經(jīng)學(xué)研究的最大貢獻(xiàn)是:他把今文學(xué)的主要制度歸納為五種,并且詳盡地進(jìn)行了分析,深刻地揭示了今文學(xué)思想的實(shí)質(zhì)和意義。從上面的分析中,我們知道蒙文通認(rèn)為,漢代今文學(xué)有內(nèi)學(xué)和外學(xué)之分,內(nèi)學(xué)中蘊(yùn)含著儒家的“微言大義”,外學(xué)不但背叛了今文學(xué)的革命思想,也不研究“禮制”,對禮儀制度是“幽冥而莫知其源”,陷入了“分析文字,煩言碎辭”的煩瑣哲學(xué)之中,這種學(xué)風(fēng)在歷史上產(chǎn)生了深遠(yuǎn)的極壞的影響。為此,蒙文通批評康有為說:“清末康有為專講《公羊》,尊崇董仲舒,也不是今文學(xué)的全面,所以他結(jié)果只能言變法,卻不能從禮家研究‘一王大法'的具體制度,從學(xué)術(shù)上講,他只能算是董仲舒派的今文學(xué)而已。”(第三卷,第160頁)蒙文通沒有走康有為的路子,而是沿著廖平的學(xué)術(shù)方向往前走,他著重去分析今文學(xué)的理想制度,通過其理想制度的分析來揭示今文學(xué)思想的革命性和進(jìn)步性,從而大大豐富了今文學(xué)思想的內(nèi)涵。 蒙文通認(rèn)為,“今文學(xué)思想,應(yīng)當(dāng)以《齊詩》、《京易》、《公羊春秋》中的‘革命'、‘素王'學(xué)說為中心,禮家制度為其輔翼。”“革命”思想導(dǎo)源于孟子的“民本主義”。(第三卷,第166頁)所謂“革命”就是“易姓改代”,誅伐暴君,革除其統(tǒng)治權(quán),但是今文學(xué)家的這些革命思想,都被“曲學(xué)阿世之流”的董仲舒等人給以了歪曲,甚至篡改,因而今文學(xué)的革命內(nèi)容被抹殺而成為統(tǒng)治階級手中的工具了。孔子為“素王”,三代損益的制度又是“孔子素王的制度”,“革命”思想、“禪讓”和“素王”的理論是密不可分的。素者,空也。漢代今文家說孔子是有德的,他可以為“王”。但是,他只是“有德無位的素王”,即“空王”。孔子寓王法于《春秋》,所以也稱為“《春秋》素王”,在《春秋》中寄寓了孔子的“理想制度”。“‘素王'說是必須以‘革命'論作為根據(jù)的”,通過“革命”的手段推翻當(dāng)權(quán)的統(tǒng)治者,經(jīng)過“禪讓”選舉的辦法使有德的“素王”成為“新王”。(第三卷,第172頁) 蒙文通認(rèn)為,今文學(xué)的這些革命思想來源于孔子,“為兆民”是孔子思想的“主腦”、“根本”和“最高原則”。“孔子把讓天下當(dāng)成小事,把為兆民認(rèn)為是大事,這是何等精透的識見。今文學(xué)正是從這一原則擴(kuò)充出去的,把這一學(xué)說發(fā)揮得最完備,以至於千頭萬緒,這自然不是孔子所能達(dá)到的程度,也不是秦漢儒生那一個人獨(dú)力所能作到的,而是在長時間的封建社會嚴(yán)酷統(tǒng)治下,在許多人的思想啟示下才達(dá)到的。這也不是儒家學(xué)者就能這樣高明,而是儒家吸取周秦諸子百家之長,卻又以孔子思想為中心,加以豐富才發(fā)展起來的。”(第三卷,第164頁)就是說,漢代儒學(xué)是集許多人的共同智慧,吸收了先秦諸子的長處而發(fā)展了的儒學(xué)。 今文學(xué)的上述“革命”思想要得以實(shí)現(xiàn),必須要有一套具體的理想制度,“革命”思想雖然是進(jìn)步的,能推動歷史前進(jìn)的,但它只是一種觀念,只有把它轉(zhuǎn)化為制度,成為實(shí)施方案,才有可能變成現(xiàn)實(shí)。為了說明今文學(xué)的革命思想如何存在于它的制度學(xué)說中,必須對漢代今文學(xué)的理想制度進(jìn)行分析,從中發(fā)現(xiàn)今文學(xué)的制度和其中包含的革命意義。蒙文通說: “‘素王'是寓王法於《春秋》,今文學(xué)家又常說《春秋》為漢制作。但所謂‘王法'究竟是甚么呢?所謂‘制作'究竟又是甚么呢?很顯然,今文學(xué)家必還有一套和‘革命'、‘素王'思想一貫的具體的典章制度存在。但這在現(xiàn)存的資料中,卻不能找到明確的答案。學(xué)者有‘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等‘三代損益'的說法來作解答的。但是,這也只不過是所謂‘《春秋》新王大法'的擬訂原則而已。還不能完全解決問題。對于這個問題,我們應(yīng)當(dāng)這樣來理解:正是由於這套制度是和革命、素王的理論相一貫,所以它同樣是王朝統(tǒng)治者所不容忍的。當(dāng)時學(xué)者迫於統(tǒng)治權(quán)威的壓力,只好托之於三代,以寄托其理想。這樣,雖然把理想的制度保全了,但卻把真正的三代古制度搞得混亂了。所以漢代的經(jīng)師們在講授同一經(jīng)籍時候,卻講出了各種不相同的制度,其所以不同的根源,就在於此。因此。我們就必須仔細(xì)分析漢代經(jīng)師所講的各種制度,清理出哪些制度是歷史的陳跡,哪些制度是寄寓的理想,然后才能觀察出理想制度所體現(xiàn)的思想實(shí)質(zhì),然后才能看出經(jīng)學(xué)家思想的深遠(yuǎn)恢宏。”(第三卷,第176頁) 要從漢代經(jīng)師們所講的制度中去識別哪些是“三代古制”留下的“陳跡”,哪些是今文學(xué)家們寄寓的“理想制度”,是一件十分困難的工作。蒙文通經(jīng)過分析、對比,歸納出了五種制度:井田、辟雍、封禪、巡狩、明堂,通過對這五種制度的分析,從迷茫的文獻(xiàn)中,挖掘出了今文學(xué)家的革命思想,對今文經(jīng)學(xué)的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貢獻(xiàn)。 關(guān)于今文學(xué)的制度問題,廖平在《今古學(xué)攷》中,把今文學(xué)與古文學(xué)不同的制度列了15種,相同的列了10種。他認(rèn)為,今文學(xué)的制度“大綱”是:爵祿、選舉、建國、職官、食貨、禮樂之類,未對今文學(xué)制度中所包含的思想進(jìn)行分析。蒙文通認(rèn)為,今文學(xué)的革命、禪讓、明堂、選舉等制度,是今文學(xué)的“大義”。顯然,蒙文通提出的今文學(xué)的這五種制度更具有歸納性和概括性,更能說明了今文學(xué)的進(jìn)步性,從而更具有學(xué)術(shù)價值。 蒙文通最早提出今文學(xué)的五種制度,是在1938年寫成的《儒家政治思想之發(fā)展》一文中,此文是由《漢儒之學(xué)源於孟子考》、《非常異義之政治學(xué)說》、《非常異義之政治學(xué)說解難》修改合并而成,公開發(fā)表于1942年出版的《志林》雜志上。蒙文通于1961年刊載于《孔子討論文集》上的《孔子和今文學(xué)》一文中,再次分析今文學(xué)的五種制度。蒙文通在這兩篇論文中所討論的今文學(xué)的五種制度,幾乎沒有多少區(qū)別。時隔23年之后仍然堅持自己的觀點(diǎn)不變,說明蒙文通對今文學(xué)的五種制度的分析論述和對今文學(xué)的革命思想的分析是成熟的,是定型了的。關(guān)于這五種制度,蒙默教授在《論經(jīng)學(xué)遺稿三篇·后記》進(jìn)行了歸納:“今文學(xué)家所講之‘一王大法'乃萬民一律之平等制度,既與貴賤懸絕之周制不同,亦與尊獎兼并之秦制相異,而為當(dāng)時儒生之理想制度,故今文師說所陳禮制多有精深大義,如井田以均貧富,辟雍以排世族,封禪以選天子,巡狩以黜諸侯,明堂以議國政,殆皆所謂‘非常異義可怪之論也'。”(第三卷,第155頁) 下面我們對今文學(xué)的理想制度:“井田、辟雍、封禪、巡狩、明堂”等,一一加以介紹、分析和評述: 第一,井田。蒙文通指出,歷史上三代的田制是不同的,夏為貢法,殷為助法,周為徹法。孟子所說的“井田”是周制。周代在天子的疆域內(nèi)有“王畿”、“六鄉(xiāng)”和“六遂”之分。“王畿”為國中,即京城之內(nèi);“六鄉(xiāng)”在“王畿”附近,“六遂”離“王畿”較遠(yuǎn),為鄙野。“周人居國中,而放逐殷人于野。”在“六鄉(xiāng)”的居民稱為“民”、“君子”。在“六遂”居住的是被流放的殷人,稱為“野民”。“六鄉(xiāng)”實(shí)行“徹法”,“六遂”實(shí)行“助法”,“徹法”為什一之稅,“助法”為九一之稅,“助法”重于“徹法”,納稅是不平等的。居住在“六鄉(xiāng)”的君子、民可以當(dāng)兵,其子弟可入學(xué)校接受教育;“六遂”之人不但要繳納九一之稅,不能當(dāng)兵,也沒有受教育的權(quán)利。今文學(xué)家說的井田與周代井田還有其不同點(diǎn),周代的井田制農(nóng)民是不能離開土地的,今文家講的井田制農(nóng)民是可以離開土地的,這樣農(nóng)民就不是君主的私有財產(chǎn)而獲得了一定程度的人身自由。“今文家所論井田,通國皆助,通國皆出兵出車,亦通國立學(xué),而君子、野人之隔泯矣。則今文家之論井田,既以夷周人貴賤之殊,亦以絕秦人貧富之隔,所謂‘一王大法'者。”(第一卷,第173頁)今文家井田制的實(shí)質(zhì)是什么呢?蒙文通說:“今文學(xué)家所謂的井田制是一種經(jīng)濟(jì)平等思想的反映,和周的種族歧視及秦的豪強(qiáng)兼并”(第三卷,第180頁)都是完全不相同的。 第二,辟雍。蒙文通指出,“辟雍”就是學(xué)校,按《周官》記載:周代的制度,“人民在受教育的權(quán)利是不平等的,這不僅是由於財富的差別,更是在制度上就存在一種不平等的規(guī)定。”(第三卷,第180頁)當(dāng)時的所謂“國學(xué)”是教育貴族子弟的,“六鄉(xiāng)”之民雖然不能進(jìn)入貴族學(xué)校,但是可以進(jìn)入鄉(xiāng)校,即“庠”、“序”,接受教育,也可以做官。“六遂”之民不但沒有受教育的權(quán)利的,更是不能做官,表現(xiàn)出周代的教育的不平等性。蒙文通指出,今文學(xué)家講的教育完全是另一回事,他首先引證今文學(xué)的經(jīng)典《禮制·王制》、《尚書大傳》和《白虎通義·辟雍》中的教育制度后說:“在這個教育制度中,鄉(xiāng)的秀士、選士可以迭升而至國學(xué),和貴族子弟受同樣的教育,授官命爵是在國學(xué)中選拔,庶民子弟也就和貴族子弟有了同等的機(jī)會。”還說:“在這些制度中,學(xué)校已是普遍設(shè)立在鄉(xiāng)里,人民已經(jīng)能普遍受到教育。”(第三卷,第183頁)從這里看出,所謂“辟雍排世族者”,就是主張“民”、“野民”應(yīng)該和“世族”一樣都能受到教育,企圖打破只有世族才能接受教育的特權(quán)。 第三,封禪。蒙文通指出,“封禪”是“禪讓”的禮制,“禪讓”說體現(xiàn)在“禮制”上就是“封禪”。“家天下”、“封建”為“小康”,“官天下”、“禪讓”為“大同”。“大同”社會要“選賢與能”,他引用墨子的話說“選賢與能”就是“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為天子,又選擇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為三公。”(第一卷,第178頁)他說:“官天下傳賢,就是‘天下為公,選賢與能';家天下傳子,就是‘天下為家,大人世及'。”(第三卷,第186頁)就是說“傳賢與世襲”是區(qū)別“天下為公”與“天下為家”的一種標(biāo)志。所謂“封禪”的實(shí)質(zhì)就是“異姓受命”,就是今文學(xué)家說的“革命”,可見,漢代今文經(jīng)學(xué)家說的“革命”不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階級的“革命”,而“是以‘素王'為目標(biāo)的‘禪讓'。禪讓就是由皇帝求索天下德若舜、禹的賢人,把帝位禪讓給他,讓他接受天命。”(第三卷,第148--185頁) “《韓詩》、《魯詩》、《公羊》、《禮運(yùn)》都講禪讓,禪讓是今文經(jīng)學(xué)家的普遍學(xué)說,今文經(jīng)學(xué)家莫不用禪讓來解釋封禪。由于“封禪”是“禪讓”的禮制,所以,“封是受命之禮,是開始;禪是成功之禮,以傳賢人,是結(jié)束。”(第三卷,第187頁)今文學(xué)家所倡導(dǎo)的“易姓受命”、“選賢與能”的“禪讓”制度,“要想要求坐在金鸞寶殿上的統(tǒng)治者退位讓賢,這無異乎是與虎謀皮,是絕對不可能實(shí)現(xiàn)的,”(第三卷,第185頁)只能是一種不能實(shí)現(xiàn)的幻想而已。 第四,巡狩。蒙文通認(rèn)為,今文經(jīng)學(xué)家講的“巡狩”與周代的“巡狩”是不同的。《孟子·梁惠王下》說:“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是類似於檢查工作的制度。《禮記·王制》、《白虎通義·巡狩》講的“巡狩”有選賢、黜陟的意義。蒙文通引《禮記·王制》說,經(jīng)過巡狩,如果發(fā)現(xiàn)“不敬不孝”的諸侯“削以地”、“黜以爵”;“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為叛,叛者君討;有功德于民者,加地進(jìn)律。”(第三卷,第189頁)周初所封立的諸侯主要是血緣宗族的,根本沒有選賢的,并且是世襲的,沒有廢黜的。今文學(xué)家提倡的巡狩制度,“不僅主張選賢以為諸侯,同時還有對諸侯的恁獎制度——黜陟。”(第三卷,第188頁)“選諸侯之說,始見于《荀子》。”“黜諸侯之義,莫備於巡狩。”(第一卷,第180頁)蒙文通還引證《尚書大傳》、《白虎通義·考黜》等文獻(xiàn)上的話來證明今文學(xué)的“巡狩”,是一種“選諸侯”和“黜諸侯”的制度。這只是今文學(xué)家的一種理想之制度,在三代的制度中是沒有的。 第五,明堂。廖平說“今學(xué)不言明堂”(《廖平選集》(上)第100頁)。蒙文通卻大講“明堂”,并且認(rèn)為,周代的“明堂”與今文學(xué)所設(shè)的“明堂”是不同的。他指出,周代明堂就是大學(xué)。在周代學(xué)校是可以“議政”的,所以鄭國有“毀鄉(xiāng)校”的記載。按《周官》規(guī)定“明堂”有“議政”的職能,是一種外朝“致萬民而詢焉”的制度。蒙文通說: “外朝是對內(nèi)朝而言,內(nèi)朝以朝群臣,處理經(jīng)常事務(wù)。而外朝則以朝萬民,處理國家重大事件,如國危、國遷、立君之類。在朝見時,三公、孤、卿、大夫、公、侯、伯、子、男、群士、群吏、州長、眾庶、罷民、窮民等。都各有一定的部位。朝士則專門負(fù)責(zé)維持朝時的秩序,禁止不嚴(yán)肅、亂部位、交談等現(xiàn)象。”(第三卷,第193頁) 由此可見,周代的“明堂”雖然有“詢於芻蕘”、“謀及庶人”、“詢國危”、“詢國遷”、“詢立君”等等制度,但是,周代“以朝萬民”是一種族歧視的政治權(quán)利不平等的制度,它只限于“國人”,而“野人”是不能參加的。周代的大學(xué)是培養(yǎng)貴族子弟的學(xué)校。所謂“大學(xué)議政”,只不過是貴族子弟的課程習(xí)實(shí)而已。即是這樣一種具有極大局限性的“明堂”制度,也不適于漢代皇帝專權(quán)的需要,所以在漢武帝即位之初,王臧、趙綰請求立“明堂”,漢武帝不同意而被迫自殺,河間獻(xiàn)王因大談明堂制度而遭忌妒,抑郁而死。河間獻(xiàn)王劉德是漢景帝之子,因?yàn)榇笳劇懊魈弥贫取倍荚馐艿狡群Γ@說明“明堂”制度與當(dāng)時統(tǒng)治者的根本利益是矛盾的,是相沖突的。蒙文通指出: “今文學(xué)家強(qiáng)調(diào)明堂制度,其意義正在‘明堂議政'這一點(diǎn)上”。“我們曾經(jīng)指出過,周代的大學(xué)和今文學(xué)家理想的大學(xué)不同”。今文學(xué)理想的大學(xué),“它已經(jīng)不完全是貴族子弟的學(xué)校了,滲入了從王朝領(lǐng)地和諸侯領(lǐng)地所選來的大量秀選之士,這批人是從農(nóng)村、從鄉(xiāng)校選拔出來的優(yōu)秀份子。富有廣泛的代表性。這樣的太學(xué)議政便不再是貴族子弟的課程實(shí)習(xí),而是具有全國性的對政治的‘獻(xiàn)可替否'(獻(xiàn)善而止不善)。今文學(xué)家所稱頌的接受禪讓的天子既曰虞舜”,“就是從事農(nóng)業(yè)手工業(yè)的生產(chǎn)者。這樣,從天子以至太學(xué)生,都來自畎畝之中,同在明堂議政,這種理想就高了。根據(jù)典籍記載,天子朝諸侯是在明堂,頒布政令是在明堂,養(yǎng)老尊賢是在明堂,而斷獄、獻(xiàn)俘也在明堂,王朝的國家大事幾乎完全集中在明堂了。”(第三卷,第192頁) 可見,“明堂”制度是何等的重要。周代的“明堂”有兩大局限性,一是一種不平等的“種族歧視政策”,不給以被征服民族在明堂議政的權(quán)利。“六遂以下所居的被征服的民族,沒有當(dāng)兵、受教育的權(quán)利,當(dāng)然就更不會給予他們以討論國家大事的權(quán)利了。周代之‘致萬民而詢焉'的制度乃是一種種族歧視的政治權(quán)利不平等的制度。”(第三卷,第194頁)二是“六鄉(xiāng)”之民也不是都能參加議政的,只限于工商兵農(nóng)中的有產(chǎn)者,即在“國”中和“六鄉(xiāng)”中能交納“什一自賦之人。”周代的明堂制度雖然有它的局限性,但不能否定它仍然是一種先進(jìn)的制度,“今文學(xué)家根據(jù)這一制度的精神,擴(kuò)大了太學(xué)議政的范圍,而集中了來自全國各地鄉(xiāng)學(xué)的、沒有種族差異的各成員來議政,以繼承這一種原始民主制度的傳統(tǒng)”(第三卷,第195頁),大學(xué)議政即明堂議政。今文學(xué)所設(shè)的“明堂”與周代“明堂”差別之根本所在,就是擴(kuò)大了議政的范圍,企圖弘揚(yáng)原始社會氏族制的民主傳統(tǒng)。 蒙文通指出:“明堂、辟雍、封禪、巡狩等制度,一直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制度,是儒生講論的重要內(nèi)容”,后來,這些制度“幽冥而莫知其原”和《春秋》“微言大義”不敢著於文字,是迫于“君主專制的淫威”和“當(dāng)世君主的威權(quán)勢力。”(第三卷,第196頁)今文學(xué)家講的制度是創(chuàng)新的理想制度,與古文學(xué)講的帶有歷史陳跡的制度有著根本的不同。今文學(xué)家所講的這種理想的制度,與當(dāng)時漢朝統(tǒng)治者所實(shí)行的制度是根本矛盾的。蒙文通說: “井田制度和當(dāng)時的豪強(qiáng)兼并相矛盾,辟雍選賢和當(dāng)時的任子為郎相矛盾,封禪禪讓和當(dāng)時家天下傳子相矛盾,大射選諸侯和當(dāng)時以恩澤封侯相矛盾,明堂議政和當(dāng)時的專制獨(dú)裁相矛盾。像這樣處處與時代相矛盾的制度,正是一種反抗現(xiàn)實(shí)的意識形態(tài)。而當(dāng)時的儒者又不敢鮮明地提出來作為反抗綱領(lǐng),而托之於古賢先賢以避難免禍。這樣做雖可使理想的制度不致遭到扼殺,但卻無法避免要和真實(shí)的歷史陳跡在某些部份發(fā)生矛盾。西漢末年和東漢時期長時間在經(jīng)學(xué)所存在的今古文學(xué)之爭,便是這一矛盾的總爆發(fā)。”(第三卷,第197頁) 由于今文學(xué)講的是理想制度,古文學(xué)講的是歷史的陳跡,它們又都在《六經(jīng)》的旗幟下,這就必然發(fā)生矛盾和沖突。由于今文學(xué)借《六經(jīng)》來發(fā)揮自己的理想制度,古文學(xué)以舊史為依據(jù)來批評今文學(xué)是“信口說而背傳記”,“怪舊藝而善野言”,而恰好就在這些“背傳記”的“口說”和“野言”中,包含著今文學(xué)的“微言大義”,包含著今文學(xué)思想的革命性和進(jìn)步性。 以上是蒙文通對今文學(xué)的五種制度中所包含著的思想內(nèi)容、實(shí)質(zhì)和歷史價值進(jìn)行了深刻的、詳盡的分析,使我們對“今文學(xué)是哲學(xué),古文學(xué)是史學(xué)”的論斷有了深刻的認(rèn)識。由此也看出,蒙文通雖然沒有“尊今抑古”的傾向,也批評了古文經(jīng)為劉歆偽造的說法,論證了《六經(jīng)》未嘗亡缺,充分肯定了古文學(xué)的價值和歷史地位,但是他傾心于今文學(xué)的態(tài)度十分明顯,對今文學(xué)大加贊賞。蒙文通做出總結(jié)說: “綜合上面所論,我們認(rèn)為今文學(xué)的理想是一個萬民一律平等的思想:井田制度是在經(jīng)濟(jì)上的平等,全國普遍建立學(xué)校是在受教育和作官機(jī)會上的平等,封禪是在出任國家首腦上的權(quán)利的平等,大射巡狩是在封國爵土上的平等,明堂議政是在議論政治上的平等。在這一律平等的基礎(chǔ)上,而后再以才德的高下來判分其地位,才德高的人可以受命而為天子,其次可以為諸侯、卿、大夫、士,其不稱職者可以黜免,同時又還有輔助政府的議政機(jī)構(gòu)。從形式上看,應(yīng)當(dāng)說這是一個氣魄雄偉、規(guī)模宏大的、有理論的、有具體辦法的、比較完善的思想體系。但無論如何也無法擺脫歷史對他們的局限:他們無法認(rèn)識在階級社會中,任何要一律平等的理想都只能是幻想。同時他們也無法認(rèn)識周代井田制度的崩潰是歷史發(fā)展的必然。”(第三卷,第198頁) “由上之說觀之,今文之義,原為理想,其恣為異論,托之三代,制益歧而義益精。”(第一卷,第200頁) 蒙文通的以上總結(jié),對今文學(xué)思想的實(shí)質(zhì)和它的幻想特征性進(jìn)行了較為全面的分析,在充分肯定它的進(jìn)步性的同時,也指出它的歷史局限性。他說:“今文學(xué)家的思想雖然是帶有幻想性,不徹底的、軟弱的、迷信氣氛濃厚的學(xué)術(shù)體系,然而卻不能因此而抹煞了在專制統(tǒng)治時代提出‘革命'的進(jìn)步性,不能因此而抹煞了在階級對抗異常尖銳的時代提出‘一律平等'的進(jìn)步性。”(第三卷,第199頁) 我們知道,今文學(xué)和古文學(xué)的根本不同在于禮制。古文學(xué)遵從的是歷史上有過的制度,今文學(xué)的制度則是一種托之三代而加以創(chuàng)新的理想制度。這些制度,如井田、學(xué)校、封禪、巡狩、明堂等,正是所謂“一王大法”,是“素王之制,為一代理想之法。”這些理想之法,“不以禮家之說考《春秋》,誠不免於‘非常可怪'之論;不以周、秦之史校論‘一王大法',則此‘非常異義'者。”這些制度是不能用禮家之說和周秦的歷史來考校的,因?yàn)樗鼈冎皇墙裎膶W(xué)的理想,不是歷史上的事實(shí)。為此,蒙文通還說,“誠以周之治為貴族,為封建,而貴賤之級嚴(yán);秦之治為君權(quán),為專制、而貧富之辨急;‘素王革命'之說,為民治,為平等。”(第一卷,第189頁、190頁)這就是周代政治、秦代政治與今文學(xué)家理想的政治之不同。也就是說,今文學(xué)是漢代的新儒學(xué),為民治、為平等的學(xué)說。魯學(xué)派是孔子的嫡傳是純正的儒學(xué),他們所提出的理想政治思想具有極大的進(jìn)步性。齊學(xué)是當(dāng)時官方的學(xué)術(shù),它已經(jīng)背離了今文學(xué)的“革命”宗旨,已成了為統(tǒng)治者服務(wù)的工具了。 三、今文經(jīng)學(xué)的進(jìn)步思想主要來源于墨家和法家 歷史上任何學(xué)說的發(fā)展都不是孤立的,它除了受當(dāng)時社會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傳統(tǒng)的影響外,還要受當(dāng)時的各種學(xué)派、各種學(xué)說的相互影響。相生相克、相互斗爭,在斗爭中生存,在斗爭中發(fā)展。在我國的漢代,接續(xù)了戰(zhàn)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學(xué)術(shù)繁榮景象,更是在漢初實(shí)行“清凈無為”政策之時,人們的思想沒有受到禁錮,為新的學(xué)術(shù)研究和創(chuàng)新提供了好的條件。加之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需要新的社會思想來適應(yīng)新的社會需要,歷史發(fā)展的客觀要求,需要進(jìn)行學(xué)術(shù)創(chuàng)新。任何創(chuàng)新都離不開已有的文化傳統(tǒng)。在經(jīng)過實(shí)踐、比較、篩選之后,被改造過的、創(chuàng)新的儒家學(xué)說,即今文學(xué)滿足了時代的需要。 那么儒家學(xué)說為何能夠滿足當(dāng)時社會的需要呢?蒙文通認(rèn)為,這是漢代儒生對孔孟學(xué)說進(jìn)行綜合、改造和創(chuàng)新的結(jié)果。對儒學(xué)的改造一是吸收墨家的思想,把孔子和孟子的思想,改造成主張“一律平等的思想”,提出了一整套的理想制度。在先秦諸子百家中,主要的是儒、道、墨、法四家,“各家都起自戰(zhàn)國時期,在長期并存的歲月里,彼此之間不斷的斗爭、辨難,及至戰(zhàn)國晚期,各家在長期的斗爭中相互影響、相互吸收,都改變了其原始的面貌。”(第三卷,第201頁)如法家、道家本來是反對仁義的,可是它們的后繼者也吸收了仁義的思想。《易》為顏氏之儒所傳,吸收了孔子的“性與天道”的思想,又受道家思想的影響等等。總之,各家相互影響、相互吸收、相互融合,使各自的學(xué)說都發(fā)生了變化。雖然如此,蒙文通認(rèn)為,對今文學(xué)影響最大的是墨家和法家。 首先,今文學(xué)家的進(jìn)步思想深受墨家思想的影響,其影響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今文學(xué)家的“平等思想”來源于墨家。墨家“學(xué)說以兼愛和尚賢為主,兼愛以反對世襲貴族的血緣性的經(jīng)濟(jì)地位,尚賢以反對世襲貴族的血緣性的政治地位。兼愛之極不別親疏一律平等,尚賢之極則至於選天子。他主張一律平等,甚至主張君主和人民在工作和生活上都不應(yīng)有差別。”“但是,他卻又把這一律平等的思想說成是天的意志(天志),給他披上了神學(xué)的外衣。儒家則只吸取了這一律平等的思想而拋棄其天志學(xué)說。”(第三卷,第202--203頁)就是說,今文學(xué)的“一律平等”的思想是吸收墨家的“兼愛”和“尚賢”思想并加以改造而形成的。 第二,今文學(xué)家理想制度的的中心“明堂”,也來源于墨家。蒙文通指出:“漢代今文學(xué)理想制度以明堂最為重要,而明堂制度則源於墨家。《漢書·藝文志》說:‘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yǎng)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尚賢,宗祀嚴(yán)父是以右鬼,順?biāo)臅r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尚同,此其所長也'。”所以,蒙文通說,墨家的“清廟就是明堂,墨家的各項大義都出於明堂”。“明堂”是今文學(xué)家理想制度的總綱,“今文家不僅以明堂為議政之所,禪讓行之於明堂,巡狩黜陟告歸於明堂,大射選侯於明堂,辟雍選賢也在明堂,是今文家的理想制度可以明堂制度統(tǒng)之。儒家正是吸取以墨家思想的中心成為儒家思想的中心。”(第三卷,第203頁)這是儒家善于吸取別人之長,把墨家的中心思想吸取、改造成為自己的中心思想。在先秦諸子中,對“明堂”闡釋得最詳細(xì)的應(yīng)當(dāng)是尸子,“尸子很可能是一位《谷梁》先師,墨家明堂理論可能就是通過尸子而傳給漢代今文學(xué)家的。”(第三卷,第204頁)蒙文通上面的論述,把今文學(xué)家“明堂”制度的淵源和中介都講得十分清楚了。 第三,今文學(xué)家吸取墨家最顯著的是《禮運(yùn)》中的大同說。蒙文通認(rèn)為“官天下傳賢,就是‘天下為公,選賢與能';家天下傳子,就是‘天下為家,大人世及'。”“選賢與能”就是選天下之賢者為天子、為三公,這是今文學(xué)家“禪讓”的重要內(nèi)容。蒙文通說:“《禮運(yùn)》的思想來自墨家。他引用著名墨家學(xué)者伍非百的《墨子大義述》中的話來證明自己的觀點(diǎn),伍非伯認(rèn)為,“《禮運(yùn)·大同》之說,頗與儒家言出入,學(xué)者或疑其非孔氏書,或以為學(xué)老、莊糝入之。實(shí)則墨子之說而援之以入儒耳。”伍非百還說,《大同》篇的思想與《墨子》書中的意義很相符合,文句也沒有太大的差別。認(rèn)為“總觀全文”,《大同》篇是拾摭《墨子》之文而形成的,“其為墨家思想最為顯著。”(第三卷,第205頁)對于伍非伯的觀點(diǎn)蒙文通不但完全贊同,而且認(rèn)為是“分析得最為透徹”的。就是說,今文學(xué)家吸取了《禮運(yùn)·大同》中的墨家思想,企圖通過五種理想制度來建構(gòu)一個理想的大同社會。 第四,“素王”說導(dǎo)源于墨家。蒙文通說,“‘素王'說在漢初以《公羊》持之最力”。“‘素王'雖為今文學(xué)家的主要學(xué)說,然而這一學(xué)說當(dāng)導(dǎo)源於墨家。墨家尚賢,主張賢人政治,尚賢的極致便主張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為天子”,“又選擇天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為三公”,這些思想又“成為尚同說的基礎(chǔ)。墨家的巨子制度,就是墨家尚賢、尚同學(xué)說的實(shí)踐。”(第三卷,第172、173頁)“‘巨子'就是墨家理想的應(yīng)當(dāng)立為天子的圣人。”墨家的“巨子制度”為儒家所接受,“巨子”即是“素王”,所以說今文學(xué)的“素王”說也是導(dǎo)源于墨家的。今文學(xué)家還吸取《殷本紀(jì)》中“素王”之說來謚孔子,是儒家“從殷而取‘素王'之名”(第一卷,第231頁),法家效法殷代的法律文化,這說明今文學(xué)家的“素王”學(xué)說也來源于法家。 第五,《孝經(jīng)》思想也來源于墨家。《孝經(jīng)》為十三經(jīng)之一,它也有今文和古文之分。《孝經(jīng)》的作者和成書的年代,到目前學(xué)術(shù)界沒有定論。但是它與孔子、孟子、荀子以及《禮記》中所講的“孝”已有很大的不同。《孝經(jīng)》中的“孝”的思想很系統(tǒng),提出“以孝治天下”的思想,是《孝經(jīng)》的最大特點(diǎn)。《孝經(jīng)》的出現(xiàn)標(biāo)志著“孝道”的形成。為此,蒙文通認(rèn)為,《孝經(jīng)》是承繼了墨家的“以孝視天下”的思想而形成的。在孔、孟、荀的思想中,“孝”是個人行為,把它和政治聯(lián)系起來,提出“以孝治天下”的思想,卻是《孝經(jīng)》的發(fā)明。蒙文通說:《孝經(jīng)》把“孝”作為一切德目的總綱,“漢代《緯書》載:‘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jīng)》'”,把《孝經(jīng)》和《春秋》并列,說明漢代人對孝的重視。“墨家法夏,而《孝經(jīng)》多用夏法;并且又說:‘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第三卷,第204頁),顯然,這都是今文家吸取了墨家“以孝視天下”思想的結(jié)果。 墨家在戰(zhàn)國時是“顯學(xué)”之一。韓非子說:“世之顯學(xué),儒、墨也”。(陳奇猷:《韓非子集釋》(下)第1080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孟子也說:“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說明墨子的學(xué)說,很有勢力。為此孟子加以嚴(yán)厲的批判,說“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認(rèn)為,讓墨子的“邪說”橫行來欺騙毒害民眾,并阻止了儒家仁義思想的傳播,就等于放任禽獸來吃人。孟子說,他深為此而感到恐懼,于是他主動承擔(dān)了“閑先圣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陳良年:《孟子譯注》第139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的歷史任務(wù)。捍衛(wèi)先圣的準(zhǔn)則,抵制楊朱、墨翟的學(xué)說,批判他們的錯誤言論,讓楊墨的邪說不得興起和流行。既然墨家學(xué)說在戰(zhàn)國時有如此大的影響,為何到了漢代就突然銷聲匿跡了呢?這是因?yàn)樗?“兼愛”、“尚賢”、“尚同”、“非攻”、“非樂”的學(xué)說,代表了平民的利益,與統(tǒng)治者的利益是根本的沖突,因而不可能受到重視和傳播。以后墨子學(xué)說的保存與傳播,一說它被道教吸收,保存在道教思想中;按蒙文通的說法,墨子的思想被漢代今文學(xué)家吸收,成了今文學(xué)“微言”的一部份,經(jīng)過今文學(xué)這個中介而進(jìn)入道教。到底是道教直接吸收了墨子的思想,還是經(jīng)過今文學(xué)這個中介,需要進(jìn)一步的研究。總之,今文學(xué)吸收了墨家的“中心思想”,與儒家的以“仁愛“為主體思想熔鑄成一體,從而豐富和發(fā)展了儒家的學(xué)說。 其次,蒙文通還認(rèn)為,漢代今文學(xué)還吸收了法家的思想。蒙文通說:“《子思》二十三篇,除《禮記》中收錄的《中庸》、《表記》、《坊記》、《緇衣》為純?nèi)寮宜枷胪猓湟婌吨T書所引佚文則頗多法家思想。”《漢書·袁紹傳注》引的“兔走於街,百人追之”等話,“和《慎子》、《商君書》不僅是思想一致,且文字也大同小異。”《孔叢子》中的《記問》、《抗志》篇中的有些思想與《韓非子·有度》篇中的思想相同;還有《孔叢子》中的《公儀》、《居衛(wèi)》篇中的“重才不重德的思想,也正是法家思想的反映。”(第三卷,第208頁)《子思子》中有一段談?wù)摗傲x利”關(guān)系的文字,在《孔叢子·雜訓(xùn)》篇中也有。為此,蒙文通指出,儒家在《孟子》以后,吸取了各家的學(xué)說,而最為顯著者則是法家思想。漢代“今文學(xué)家之大量吸取法家思想當(dāng)正是以子思之儒為先導(dǎo)”(第三卷,第209頁)的。 今文學(xué)家吸取了法家的什么思想呢?蒙文通說:“法家擯貴族,《公羊》因之以譏世卿。”(第一卷,第190頁)“譏世卿” 是《春秋公羊傳》的重要思想,它是用來反對“世襲貴族”的,“反對世襲貴族可以說是法家思想的主要一面”,但是,“法家是站在擴(kuò)張君權(quán)的基礎(chǔ)上來反對世襲貴族”,它和墨家所不同的是,“墨家是站在一律平等的基礎(chǔ)上來反對世襲貴族”的。就是說,今文學(xué)家吸收了法家反對“世襲貴族”的思想,因?yàn)槭酪u制度是與“一律平等“的思想相對立的;其次,還吸收了法家“大一統(tǒng)”、“尊王”等方面的思想。 從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漢代今文學(xué)吸收了墨家和法家的學(xué)說。墨家效法和吸取夏代的原始民主文化的遺風(fēng),法家效法和吸收殷代的法律文化。商鞅之法是根據(jù)殷代的法律來制定的,申、商、韓非所傳的法律都是殷代的法律。“今文學(xué)家所說的法夏、法殷就是兼取墨家、法家”。“從戰(zhàn)國晚期到漢初這段時間,儒家的思想發(fā)生了一次巨大的變化”,“它吸取了先秦諸子各家的思想”,“在思想內(nèi)容上豐富了,宏大了”,“使它在理論上較各家為全面,它重視了三古的典章制度,使它在方法上較各家為具體。”(第三卷,第210頁、211頁) 我國的學(xué)術(shù)思想,在戰(zhàn)國末期和秦漢之際形成了相互采獲,相互融會的潮流。正是由于這樣的綜合、融合、創(chuàng)新才促進(jìn)了學(xué)術(shù)的發(fā)展,而漢代的今文經(jīng)學(xué)正是這種綜合的結(jié)果,孔孟原始儒學(xué)才因之而成為新儒學(xué)。蒙文通說: “蓋周秦之季,諸子之學(xué),皆互為采獲,以相融會。韓非集法家之大成,更取道家言以為南面之術(shù),而非(指韓,引者注)固荀氏之徒也。荀之取於道、法二家事,尤至顯。鄒生晨曦謂:‘莊書有詆詈孔氏者,為漆園之本義,《雜篇》中乃頗有推揖孔氏者,為后來之學(xué),有取於儒家',亦篤論耶!《呂覽》、《管書》,匯各派於一軌,《準(zhǔn)南子》沿之,其旨要皆宗道家;宗道者綜諸子以斷其義,純?yōu)榭昭裕蛔谌逭呔C諸子而備其制,益切於用。自宗儒之經(jīng)術(shù)繼宗道之雜家而漸盛,遂更奪其席而代之,於是孔氏獨(dú)尊於百世。罷黜百家,表彰《六經(jīng)》,仲舒之說,建元之事其偶然耶!竊嘗論之,《六藝》之文,雖曰鄒魯之故典,而篇章之殘缺,文句之異同,未必即洙泗之舊。將或出於后學(xué)者之所定也。故經(jīng)與傳記,輔車相依,是入漢而儒者於百家之學(xué)、《六藝》之文,棄駁而集其醇,益推致其學(xué)於精渺,持義已超絕於諸子,獨(dú)為漢之新儒學(xué)。”(第一卷,第238頁) 由此可見,在這個綜合的過程中,有一個顯著的特點(diǎn)就是:一是吸收和綜合墨家和法家東西更具體,受其影響也最大;二是重點(diǎn)綜合了諸子的制度,“宗儒者綜諸子而備其制,益切於用。”儒家綜合了諸子的“禮制”,即政治制度,也就是說漢代的儒家“詳於制度”,從而使新儒學(xué)不像孔孟學(xué)說那樣“迂闊無用于世”,而是“益切於用”了。 蒙文通認(rèn)為,漢代儒家能夠把先秦時代的孔孟學(xué)說,作為其官方的統(tǒng)治思想,不是偶然的。諸子在理論創(chuàng)樹時忽視傳統(tǒng)文獻(xiàn),“儒家則既重理論又重文獻(xiàn)。諸子以創(chuàng)樹理論為經(jīng),儒家則以傳統(tǒng)文獻(xiàn)為經(jīng)。”(第三卷,第211頁)《六藝經(jīng)傳》是儒家思想的發(fā)展,因此,漢代經(jīng)學(xué)(主要指今文學(xué))自有其自己的體系,它和先秦時代的思想比較起來其重點(diǎn)各有不同。蒙文通指出: “先秦重在理論,漢代詳於制度。只有理論而沒有制度,理論就是空談;只有制度而沒有理論,制度就會失去意義。故理論和制度必須綜合起來研究,而后才能認(rèn)識其思想全貌”。“漢代經(jīng)學(xué)是先秦儒家和諸子的發(fā)展和總結(jié)。雜家《呂覽》、《準(zhǔn)南》是以黃老為中心來總結(jié),《六藝經(jīng)傳》是以儒家為中心來總結(jié)。”(第三卷,第213頁) 所以,在蒙文通看來,由于今文學(xué)經(jīng)過吸取了各家的思想,發(fā)展和總結(jié)了先秦儒家和諸子的思想,其中最顯著的是吸收了墨家和法家的思想;在創(chuàng)樹理論時,重視制度,詳于制度。因而使今文學(xué)的思想更豐富、更宏大、更全面、更具體,從而適應(yīng)了當(dāng)時社會歷史的要求,滿足當(dāng)時統(tǒng)治者的需要。這不僅有其歷史發(fā)展的必然,也有其內(nèi)在的邏輯依據(jù)。 蒙文通還認(rèn)為,儒學(xué)在漢代獲得了獨(dú)尊的地位,與吸取墨家和法家的長處有很大的關(guān)系,“儒家者流取法家之所長,而輔儒家之不足”,“自儒家之能取於法,而法亦因之以合於儒。”儒家與法家,“其始也,相攻如寇讎;其卒也,調(diào)和如昆仲,而學(xué)術(shù)以漸入於統(tǒng)一”,至儒家兼取法家和墨家的長處之后,“各家相爭之跡熄,而恢宏卓絕之新儒以形成,道術(shù)遂定於一尊也。”(第一卷,第309頁)儒家以自己學(xué)說為中心,吸取法家和墨家學(xué)說的長處,從而使儒、法、墨三家融合為一體,形成了與先秦儒學(xué)不同的,為能獲得獨(dú)尊創(chuàng)造了條件。 但是,獲得獨(dú)尊地位的儒學(xué)已經(jīng)是變了味的董仲舒公羊派儒學(xué),它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蒙文通在《儒家政治思想的發(fā)展》一文對董仲舒公羊派的儒學(xué)提出嚴(yán)肅的批評,他說: “儒者之說,始亂於仲舒,易革命為改制,易井田為限田,選天子之說廢,而教天子之說隆,明堂議政之義隱,而諍官諷諫之義張,學(xué)校與考試相代興,封建與守相相錯雜,其蛻變固可考也。既亂於學(xué)官博士之術(shù),再亂於佚經(jīng)古文之說,章句訓(xùn)故,秕塵極目,而大義晦,微言絕。”(第一卷,第193頁) 蒙文通還在1961年寫的《孔子和今文學(xué)》一文中,再次批評董仲舒儒學(xué): “自董仲舒出來以后,變‘素王'為‘王魯',變‘革命'為‘改制',變‘井田'為‘限田',以取媚於漢武帝;又高唱‘《春秋》大一統(tǒng)'以尊崇王室,因而攪亂了今文學(xué)思想。自武帝、宣帝立今文學(xué)各家博士官以后,學(xué)術(shù)統(tǒng)帥在政權(quán)下面,今文學(xué)中一部份比較尖銳的思想——如革命、禪讓等理論,就不敢公開講了,從而今文學(xué)思想漸趨枯萎。”(第三卷,第213頁) 思想內(nèi)容豐富的、宏大的、全面的、進(jìn)步的今文學(xué),經(jīng)過董仲舒的篡改、歪曲,使之大義乖背,微言斷絕,對禮制也“幽冥而莫知其原”,加上只“分析文字,煩言碎辭”的治學(xué)方法和“專己守殘,黨同伐異”的學(xué)術(shù)態(tài)度,從此今文學(xué)就衰微了。 歷史證明,任何一個昌明的時代必須要有學(xué)術(shù)思想上的創(chuàng)新,才能適應(yīng)那個時代的需要。漢代的今文學(xué)就是那個時代的新的學(xué)術(shù)思想。在階級社會、乃至在任何社會中,對社會的控制不能只用道德,還必須用宗教和法律來進(jìn)行社會控制與管理。有人說,漢代獨(dú)尊的儒術(shù),實(shí)為荀子之說。荀子主張用建立在“性惡論”基礎(chǔ)之上的“隆禮重法”的理論來管理社會,漢代獨(dú)尊的儒學(xué)實(shí)則是內(nèi)儒外法之學(xué)。道德自律與法律強(qiáng)制是治理社會不可缺少的東西。漢代董仲舒的公羊派今文學(xué),在儒學(xué)重道德的基礎(chǔ)上,吸收了法家的思想,緯書學(xué)派神化了孔子,使孔子成為“生知前知”的教主,儒學(xué)實(shí)際上成了準(zhǔn)宗教,這樣它就具有了宗教、道德和法律的社會控制功能,再輔之以道教和后來的佛教,這就為儒學(xué)成為官方意識形態(tài)奠定了理論的基礎(chǔ),這就是儒學(xué)統(tǒng)治了中國思想幾千年的重要原因之一。 以上是我運(yùn)用“述而不作”方法,介紹、分析和評述了蒙文通對今文學(xué)研究的貢獻(xiàn)。從中可以看出,蒙文通在繼承廖平經(jīng)學(xué)的基礎(chǔ)上,對之進(jìn)行了“修正”,有所發(fā)展,有自己“獨(dú)立”于廖平的東西,這些“修正”和“獨(dú)立”的部份,就是蒙文通對今文經(jīng)學(xué)研究所做出的貢獻(xiàn)。由于經(jīng)學(xué)在我國有幾千的歷史,漢代今文學(xué)有理論創(chuàng)新,近代有今文學(xué)運(yùn)動;加之蒙文通學(xué)識淵博,他在經(jīng)學(xué)研究上有自己的獨(dú)創(chuàng)之處,只有對整個經(jīng)學(xué)以及今文學(xué)進(jìn)行深入的研究,才能進(jìn)入蒙文通經(jīng)學(xué)、特別是今文經(jīng)學(xué)的堂奧,這個問題只有待來者去完成,我深信在不久的將來會有可喜之成果問世的。 為了表示對先賢、先輩誠摯的敬意和深切的緬懷,我于2004年10月23日至24日在成都召開的“蒙文通先生誕辰110周年及學(xué)術(shù)討論會”上,寫了一首題為《閃耀在華夏文化史上》的詩,現(xiàn)在附之于后:“從浩瀚的文化典籍中探寶/探掘出了黃燦燦的金子/金子閃爍著耀眼光輝/又被深埋在學(xué)術(shù)寶庫里//從白發(fā)蒼蒼的學(xué)者/乃至年輕的教授博士/再到寶庫中去尋找/尋找那被深埋的金子//金子依然閃爍著光輝/金光照亮了來者的心底/那閃閃發(fā)光的金子啊!/豐富了華夏的文化史。”蒙文通先生的學(xué)術(shù)貢獻(xiàn),必將永存于華夏文史上,啟迪來者的智慧。 <來自:四川省社會科學(xué)院> |
||||||||
 |
國學(xué)網(wǎng)站,版權(quán)專有;引用轉(zhuǎn)載,注明出處;肆意盜用,即為侵權(quán)。
mailto:guoxue@guoxue.com
![]() 010-68900123
010-68900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