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中國地名學史分期及其特征
縱觀中國地名學的發展歷程,可以清末民初為界明顯地劃分為前、后兩大階段,即在此之前是漫長的傳統地名學階段,而在此之后則是現代地名學的興起階段。中國地名學從傳統邁向現代是一個漸變過程,不存在突變。
傳統地名學依其發展的性質可劃分為先秦的萌芽、秦漢的奠基、魏晉南北朝的深入、隋唐的成熟、宋元的承前啟后和明清的繁榮鼎盛六個時期
。
一、先秦時期的萌芽
先秦時期,中國地名學尚處于孕育期的萌芽狀態。追尋地名的起源,的確非常久遠,而從甲骨文記載的地名來看,殷商時的地名表達形式已相當完整。《詩經》、《左傳》等文獻中不乏地名的記錄,《尚書·禹貢》對后世地名學產生了至為深遠的影響,所以上古時代即已產生了專門釋地的典籍《八索》、《九丘》
,可惜早已亡佚了。春秋、戰國時代,產生了中國歷史上非常重要的地名通名——郡和縣,而近年于甘肅天水放馬灘出土的秦國地圖,則向人們展示了先秦民間地名的風采。這一時期,中國地名的專名完成了由單名向雙名、多名的過渡,然而對地名淵源僅有零星的解釋。
二、秦漢時期的奠基
如果說秦漢時期西漢處于國力最為強盛時代的話,那么為中國地名學奠定基石的應是東漢。東漢明、章之世,班固著成了我國第一部具有地名學研究意義的地理志書——《漢書·地理志》。靈帝、獻帝時代,又有應劭《漢書集解》、《地理風俗記》、《十三州記》、圈稱《陳留風俗傳》等一系列地名學著作誕生。這些著作包含了頗具價值的地名學思想、地名命名原則和地名淵源解釋內容,應劭著作的地名淵源解釋還首次超過了百數。隨著大量地名的產生和應用,人們認識到一系列地名的共同特征,《爾雅》、《說文解字》、《釋名》對地名通名均作了系統的總結和升華。這一切都為中國地名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三、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深入
魏晉南北朝是個離亂紛紛的年代,政區地名進入了歷史上最為繁復、最為混亂、最令人目眩的時期。然而,就是這么一個時代,《漢書》注家筆下出現了色彩斑瀾的地名淵源解釋,地名學史上產生了像杜預《春秋釋例·土地名》、京相璠《春秋土地名》、張華《博物地名記》、郭璞《山海經注》、常璩《華陽國志》、盛弘之《荊州記》、沈約《宋書·州郡志》、劉昭《續漢書郡國志注補》、顧野王《輿地志》、闞骃《十三州志》等這樣著名的地名學家和地名學著作,因而地名學在各個方面均有了深入和提高,成績也堪稱卓著;而像北魏酈道元《水經注》這樣的地名學著作,地名淵源解釋首次超過千數,釋名率達6.7%,不但使北魏、而且使整個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地名學發展達到了頂點。
四、隋唐時期的成熟
隋唐時期的地名學在地名命名原則的總結與運用、地名淵源解釋、地名“標準化”、地名用字與讀音等方面都取得了一系列新的進步,涌現了像《括地志》、《大唐西域記》、《元和郡縣志》這樣的地名學著作,敦煌地理文書也頗具地名學價值
,甚至皇帝的詔書中也提出了一些地名命名、改名的原則 。這些均是傳統地名學成熟的標志。特別要指出的是,唐代地名學承南北朝以來之余緒,《通典》等著作最終完善了“因水為名”的原則、《元和郡縣志》最早完整地總結了年號地名的命名等原則;并且《元和郡縣志》地名淵源解釋數量(931處)在五代以前的文獻中僅次于《水經注》,而釋名率則高出《水經注》近兩倍,在地名學上取得了從南北朝到隋唐的巨大進展,并為兩宋乃至元、明、清的地名學發展開辟了道路。
五、宋元時期的承前啟后
中國古代的地名學發展到宋元時期,發生了明顯的轉變:一方面,地名淵源解釋越來越多,個體的、局部的地名考釋越來越精細,蘇東坡為了探究石鐘山的得名原委而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聆聽那悅耳的窾坎鏜鞳之聲;同時,地名學著作的篇幅也越來越宏富,一百卷《太平寰宇記》中的地名淵源解釋超過兩千處,二百卷的《輿地紀勝》則超過三千,假使一千三百卷之巨的《大元大一統志》能完整保存至今的話,則其地名淵源解釋數量很可能在五、六千處以上。另一方面,地名學規律的總結卻相對較少,無論是宋代的五部地理總志,還是元代的“一統志”,抑或宋元筆記、《通鑒》胡注,既沒有《水經注》那樣豐富的地名學思想,也沒有《元和郡縣志》那樣眾多的地名命名規律的繼承與總結,局部領域雖有創新,總體進展卻不太顯著。這兩個方面說明,宋元時期的地名學在承襲秦漢以來優良傳統的同時,又開啟了明清及其以降注重個體的、局部的地名研究的風習,實處于承前啟后的時期。
六、明清時期的繁榮鼎盛
明清時期,中國傳統地名學的發展達到了鼎盛時期。郭子章著成了我國第一部專門解釋地名淵源的著作《郡縣釋名》,顧祖禹以個人之力完成了不朽之作《讀史方輿紀要》,李兆洛主持編成了第一部歷史地名詞典《歷代地理志韻編今釋》;既產生了偉大的地理學家徐霞客,又培育了重于考據的乾嘉學派,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明編《大明一統志》的基礎上,清代三修《一統志》,其中最后成書的《嘉慶重修一統志》質量最高
,從而成了歷史地名的淵藪。考據學派對歷代地名沿革、定位、地名典籍進行了大量的、艱苦的考證與研究,從而把傳統地名學推向了頂峰。
不過,我們也應該看到,清人治學重于考據,征實多而空論少,對地名沿革、地名淵源、地名定位、地名讀音、地名用字等方面貢獻尤著,然于地名命名與更名規律的歸納相對貧乏,理論總結的起點更低。這正是傳統地名學的一大特點。直到時代進入了民國,地名學理論才有所建樹,這種狀況才有所改觀。
現代地名學依其發展的性質可劃分為民國年間的確立、1949年后至“文化大革命”前的成長發育和“文革”以來迄今的成熟三個時期。
一、 民國年間的確立時期
地名學作為一門科學,是十九世紀后期首先在歐美諸國發展起來的。
晚清以降,因受歐風美雨的熏陶,西方先進的地學知識逐漸傳入中國,其中翻譯西方地學著作是主要的傳播渠道之一。據研究,清末翻譯和出版了三十八部外國自然地理學著作和四十三部外國人文地理學著作
,從而引進了一大批漢語的學科新名詞,如“地文學”、“地勢學”、“人生地理學”等,但未見有“地名學”一詞。
辛亥革命以后,西方地學知識繼續輸入中國。據目前所知,“地名學”一詞最早出現于1928年正月初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綜合英漢大辭典》中,該書第2747頁將英文toponomy譯成漢語作“地名學”。
民國年間中國現代地名學的確立,主要表現在地名學理論的探索、地名分類的闡述、地名辭書的編纂、統一地名譯名的討論四個方面,在這些方面有所建樹的學者有金祖孟、葛綏成、徐松石、錢穆、臧勵龢、劉鈞仁等先生。
二、成長發育時期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迄于“文化大革命”開始前夕,地名工作和地名研究獲得了新的發展,地名學步入了良好的成長發育時期,主要體現在六個方面,即頒布了一系列整頓和管理地名的批示和規定、清除對鄰國含有大國沙文主義和外國人強加于我的地名、更改了一批帶有歧視侮辱少數民族性質和以人名命名不適宜保留的地名、更改了53處字面生僻難認難讀的縣級及其以上地名、對19處容易引起混淆的異地同名進行了調整、制定了若干少數民族語地名的漢字譯音規則。
三、成熟時期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雨過天晴,科學迎來了春天,地名學研究的熱潮也迅速興起,現代地名學獲得了健康的發展,步入了它的成熟時期,主要成績有:
1. 建立管理、研究地名的機構。
1977年成立了中國地名委員會,各省、市、自治區的地名機構及各市、縣地名組織也相應建立起來。1979年、1980年召開了兩次全國地名工作會議,確定在全國范圍內開展地名普查。整個普查工作是在中國地名委員會的指導下,在各省、市、自治區地名機構的領導下進行的。通過地名普查,為實現我國地名的標準化提供了豐富資料。1986年1月23日國務院頒布了《地名管理條例》。1988年,成立了中國地名學研究會。1992年7月,在原國家測繪局測繪科學研究所地名研究室的基礎上,成立了地名研究所。同時,民政部也建立了地名研究所。
2. 進行中國地名拼寫的標準化
1958年的《漢語拼音方案》正式公布后,如何以它來取代漢語的外來各種拼音形式,從而正確統一地拼寫我國地名,不僅是個技術問題,而且還關系到國家的尊嚴。1977年8月,在雅典舉行的第三屆聯合國地名標準化會議上通過了中國代表提出的《用漢語拼音拼寫中國地名作為羅馬字母拼法的國際標準》提案。次年9月,國務院批轉了關于改用《漢語拼音方案》作為我國人名地名羅馬字母拼寫法的統一規范的報告。于是,從1979年元旦起,我國對外文件、書刊中的人名、地名羅馬字母拼寫,一律改為漢語拼音。與此同時,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和國家測繪總局制定了《中國地名漢語拼音字母拼寫法》和《少數民族語漢語拼音字母音譯轉寫法》,按照這一規定,蒙、維、藏語地名可直接從原文音譯轉寫。這些工作不僅推動了中國地名的標準化,而且便利了民族往來和國際交往。
3. 參加國際會議與學術交往
在聯合國恢復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席位之后,1975年中國應聯合國秘書長的邀請派代表參加了聯合國地名專家組第6次會議。此后參加了歷屆聯合國地名專家組會議和地名標準化會議。1979年,中國代表在出席了聯合國地名專家組第8次會議后順訪了美國地名委員會(The
United States Board On Geographic Names),交換了情況,互贈了地名資料。此后與日本地名研究所、英格蘭地名學會(English
Place-name Society)均有交往。從此,中國開始了地名工作方面的國際友好交往。我國參加國際地名會議和國際地名學術交流,使我國地名科學的發展納入了世界地名科學發展的軌道,推動了中國相對落后的現代地名科學研究趕超世界先進水平的進程。
4. 開展地名學研究,出版了若干定期刊物和一批學術論著。
中國地名委員會成立后,各省區相繼出版了一些地名學刊物,其中大家熟悉的有山西《地名知識》(1979年創刊)和遼寧《地名叢刊》(1984年創刊),前者自1993年起更名為《中國方域》,后者自1991年起改名為《中國地名》,其它尚有云南的《地名集刊》、《江蘇地名》、《內蒙古地名》等。這些公開的和內部的刊物共同成為發表地名科學研究成果和交流地名工作經驗的陣地。同時,發表了一批學術界有影響的論文、專著和文集,代表了中國現代地名學研究的新水平,標志著中國現代地名學的完全成熟。這樣的論文有曾世英等《試論地名學》、杜祥明《地名學概述》、史念海《論地名的研究和有關規律的探索》、陳橋驛《論地名學及其發展》、鄒逸麟《譚其驤論地名學》、劉伉《略論地名的起源與演變》、史為樂《談地名學與歷史研究》、周振鶴等《古越語地名初探》、尹鈞科《論歷史地名在地名學研究中的地位》、韓光輝《中國地名學的發展》、王際桐《中國地名標準化雛論》等,專著與文集有曾世英《中國地名拼寫法研究》、《曾世英論文選》及其續篇、史念海主編《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第二輯、中國地名委員會辦公室編《地名學文集》、褚亞平主編《地名學論稿》、邱洪章主編《地名學研究》(一、二集)、王際桐主編《地名學概論》、王際桐主編《實用地名學》、王際桐著《王際桐地名論稿》、褚亞平等著《地名學基礎教程》、史為樂主編《中國地名考證文集》、李如龍著《漢語地名學論稿》、馬永立主編《地名學新探》、孫冬虎與李汝雯合著《中國地名學史》和《中國山名論稿》、華林甫著《中國地名學源流》、劉南威著《中國南海諸島地名論稿》、吳光范著《云南地名探源》、牛汝辰著《新疆地名概說》、吳郁芬等編《中國地名通名集解》等。與此相應,還編纂出版了一批高水平的地名工具書,如《辭海》的世界地理、中國地理、歷史地理三個分冊、《中國大百科全書》的地理學、中國地理與世界地理三卷、《中國歷史地圖集》(八冊)、《世界地名語源詞典》、《中國地名語源詞典》、《中國地名詞典》、《中國歷史地名詞典》、《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中國歷史大辭典》歷史地理卷,以及正在編纂出版中的31卷本《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名詞典》(已出19卷)和史為樂先生主編的《新編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即出)。
鑒于地名學研究的累累碩果,有的學者早就樂觀地指出:“中國地名學的研究已經趕上或接近于世界先進水平”
。不管這個結論的準確性如何,自“文革”結束以來我國地名學得到了驚人發展則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其成果之豐盛,超過了民國以來至“文革”開始前夕所有成果的總和,可以說是地名學發展的黃金時期。
匆匆回顧中國地名學史的歷程,筆者感到并不必急于用簡潔的幾句話或幾個方面來概括它的主要特點。這是因為,首先對于任何專門史而言,概括得越簡練則距離錯綜復雜的歷史真實越遠;其次,中國的地名學史研究剛剛起步,現在僅僅是個開端,過早地總結它的“幾大特征”未免操之過急,反而可能會束縛這一領域的繼續深入;再次,地名學史是學術發展史中的一個組成部分,體現著學術史的共性,過于強調地名學史的“特點”未必恰當,因為任何一種特點在其它領域也都有可能找到。所以,中國地名學發展史特征的全面總結,還有待于地名學史各方面專題研究的進一步深入。
話雖這么說,中國地名學的發展歷史卻表明它并非沒有任何特征,這種特征是否具有共性還有待于進一步的探討,筆者在此只提一點自己粗淺的看法,供大家討論,并希望得到專家的指教。
從《漢書·地理志》到《大清一統志》、從《水經注》到《郡縣釋名》、《今縣釋名》這些中國傳統地名學典籍中的地名學思想與地名淵源解釋,均是因具體某個或幾個地名而發,從來沒有單獨論述地名學的篇章,也就是說中國傳統地名學對地名的研究,只偏重于具體的、個別的地名記載與解釋,而把地名作為整體看待、從而探討其發展和分布的普遍規律是非常零星的,更是不成系統的。這是中國傳統地名學最顯著的特征。
傳統地名學的這種非系統性與它沒有獨立的地位有很大關系。傳統學術上的地理典籍隸屬于史部,所謂“地名學典籍”實質上是指經學、史學、輿地學、小學著作于地名學有所貢獻者,地名學內容分散于這些著作之中,而真正的地名學著作僅有《郡縣釋名》、《今縣釋名》等極少數幾種,正如史念海先生所寫的那樣:“地名學和歷史地理學在那時不僅不能獨立自成科學,就是這樣的名稱也從來未曾見到有人提過;歷史地理學稍勝一籌,還能以沿革地理之名為那時學者所齒及,地名學連這一點也是難于談到的”。
不過,我們也應該看到傳統地名學擁有汗牛充棟的具體的地名研究,擁有與世無比的地名沿革、地名淵源解釋的考證成果,從而為現代地名學的發展提供了雄厚的基礎和廣闊的前景。現代地名學理論之傳入中國并能扎下根來,與此也不無關系。
回顧中國現代地名學的發展歷程,它受國際學術發展的影響比較明顯,連“地名學”一詞都是從外文toponymy一詞翻譯過來的,金祖孟、葛綏成更是汲取當時國際地名學最新成果的弄潮兒。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在外國地名的漢譯方面投入了較多力量,1962年曾世英等向地理學會年會提交的論文題目為《地名學的國際現狀與研究方向》。我國地名國際標準化的研究,得力于聯合國地名標準化會議和與日俱增國際交往的推動,地名信息系統的研究則更是學習國外先進技術的結果。
任何一門獨立的學科都應有理論、應用、學史三個基本組成部分
。中國現代地名學研究從一開始就表現出較強的實用性,學術服務于實踐的特點非常突出,因而應用地名學十分發達,而理論地名學研究相對較少,地名學史研究則更為薄弱。如何糾正這種偏差,使地名科學各個部分同步、健康地協調發展,這是日后中國地名學發展應該注意的大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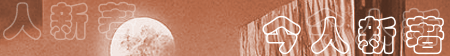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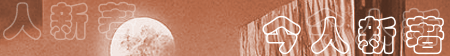
web@guoxue.com
![]() 010-68900123
010-68900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