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清代考據學派的地名學成就
第三節 結語
筆者在此對清代考據學派的地名學成就僅僅作了一個鳥瞰式的概括,其貢獻的內涵遠非筆者的三言兩語所能道盡。總而言之,他們對政區地名的沿革、水體地名變遷的考證取得了長足的進展,其研究范圍之廣是前所未有的,從上古三代直至清朝,從中原到邊疆,幾乎所有見于記載的重要地名、山川以至名勝古跡都有人作了考證;他們對古代的地名學著作進行了全面的整理和研究,使很多珍貴的資料得以保存和流傳,從《禹貢》、《漢書·地理志》、《水經注》到宋元總志與方志,差不多都作了校勘、輯佚、辨偽和疏證,包含了很多超越前人的成就
。所有這一切,既是中國古代地名研究的高水平總結,也是現代地名學發展的堅實基點。
考據學派對古代大量地名所作的考證與研究,貢獻是巨大的,影響是深遠的,遺澤后人不淺。近代以來,歷史地理學研究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除了有新的學科理論指導以外,主要得力于考據學派為后人提供了一筆豐厚的地名考證遺產。
雖然如此,考據學派在地名學上的不足也是很明顯的。盡管這些瑣碎的考證邏輯嚴密、論證清晰,解決了一個又一個的實際問題;但見樹不見林,理論上的歸納、升華實屬鳳毛麟角,規律性、系統性更是無從談起,正如譚其驤先生所指出的那樣:“清代的地理學研究只是舊的總結,而不可能成為新的開端”
。
另外,在具體的地名考證中,“乾隆中葉后士人習氣:考證于不必考之地,上下務為相蒙” ,“執今水以求故瀆、據后城以定前地” 的現象也屢見不鮮,當時學者便認識到這是“言地理之公患也”
,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結論的科學性。
(本章原發表于《中華文史論叢》2001年第2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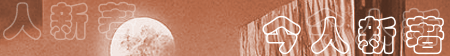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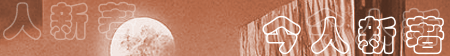
web@guoxue.com
![]() 010-68900123
010-68900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