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清代考據學派的地名學成就
第二節 分
論
清代考據學派在地名學上所取得的具體成就,以地名方位考證為核心,在地名沿革、地名含義、地名用字、地名讀音、地名典籍考證與辨誤等各個方面均取得了豐碩的成果,蔚為大觀,而規律性的總結反而少見。現各撮舉一二以說明之。
一、關于地名方位
清代學者的輿地著作,幾乎都涉及地名方位問題,絕大部分內容均是地名的具體方位考定。今試舉閻若璩、江永、程恩澤、李兆洛、楊守敬五人的輿地著作為例。
閻若璩(1636~1704年)字百詩,號潛邱,祖籍山西太原,至五世祖時遷居江蘇淮安府山陽縣(今江蘇淮安市)。其考證《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中地名的專門之作叫《四書釋地》,本編加上續、又續、三續共有六卷。
《四書釋地》本編一卷,共57條,所釋地名則有蓋、嬴、雪宮、石門、闕里、武城、泰山北海、淇河西、漯滄浪、南陽、華岳、海濱、水滸、莘、匡、汶沂、晝、東山、任、滕、薛、轉附朝儛、棠、溫泉、平陸、靈丘、畢郢、虞虢、溱洧、陽城箕山之陰、幽州、崇山、屈邑、傅巖、莒父中牟、南山、淇、邦畿千里、周舊邦、垤澤之門、范、魯昌平鄉陬邑、微箕、河河內、首陽,共45條。其中大部分地名方位的考辨頗具學術價值。例如“雪宮”,閻氏云:“齊宣王見孟子于雪宮,解者謂:‘雪宮,孟子之館,宣王就見于此’,因夸其禮遇之隆……《元和郡縣志》:‘齊雪宮故址在青州臨淄縣即齊故都東北六里,《晏子春秋》所謂齊侯見晏子于雪宮’。然則先孟子,雪宮又為晏嬰館舍耶?蓋齊離宮之名、游覽勝跡。宣延見孟子于其地,非就見之謂。益信地理宜究”。閻氏通過雪宮位置的考訂,將人們誤以為宣王赴雪宮看望孟子糾正為宣王召見孟子于雪宮;雪宮原來是齊國離宮之名,而非孟子居所。可見地名方位考證是多么的重要!
《四書釋地續》一卷,因釋地而牽涉人名,共80條,所釋地名有汶水、泰山、川上、柳下、休、鄹、海隅、東蒙等46條。例如“休”,閻氏云:“孟子致為臣而歸,歸于鄒也,中間經過地名‘休’者,少憩……故休城在今兗州府滕縣北一十五里,距孟子家約百里。《路史·國名紀》:休在潁川,或云介休。介在膠西,并非”。
《四書釋地又續》兩卷,因釋地名、人名而及物類訓詁典制,共163條,所釋地名有闕里、闕黨、四海、少梁、句繹、召陵等24條。例如“四海”,胡渭(朏明)據《爾雅》認為九夷八狄七戎六蠻為四海,閻氏云:“按古書所稱四海,皆以地言,不以水言,故《爾雅》此條系《釋地》、不系《釋水》……自宋人拋棄舊詁,直以海為海水,而古書所稱四海之義始有不可得通者矣。余曾以書往質《孟子》‘放乎四海’、‘禹以四海為壑’,此得謂不以水言耶?朏明不覺欣然。大抵四海之義有二,有宜從今《爾雅》解者,四海遏密八音是卻少;有宜從康成《周禮注》,四海猶四方也”。其最終結論是:“四海即天下字面也”。
《四書釋地三續》兩卷,系閻氏其它解釋經義者,共126條,但地名考證成份不多,僅有湍水、闕里闕黨、湯居亳與葛為鄰三條。
總計《四書釋地》及其續編共426條,其中詮釋地名118條。有人問閻若璩:《四書釋地》中的說法為什么與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不同?閻氏回答:“吾老矣,著書冀以垂后,豈必同于應考諸生?”他認為,朱子可以正孟子,則后人未嘗不可以正朱子。正因為閻氏治學嚴謹,因而李慈銘認為“所著書自當以《四書釋地》為最,故此書所論地理亦多確核”。
江永(1681~1762年)字慎修,徽州府婺源縣江灣村(今江西婺源縣東北江灣鎮)人,一生雖僅以明經終老于家,卻對皖派學術影響甚大。所著《春秋地理考實》四卷,是一部關于《春秋》及《左傳》地名的考證之作,涉及古今地名方位、沿革,雖多承襲前人之說,而又多所補正,“核其虛實,精者益精,詳者益詳”
。該書體例是先出《春秋》地名,繼標所在文句,然后列杜注、孔疏及《春秋傳說匯纂》,再加自己的“今按”,是者從之,非者辨之。茲于前三卷各舉一例:
卷一莊公三十一年:“薛,[經]筑臺于薛。[杜注]魯地。[匯纂]今兗州府滕縣東南有薛城。[今按]薛國在滕縣南四十里,魯豈筑臺于其國?當是魯地有名薛者耳”。
卷二宣公八年:“舒蓼,[經]楚人滅舒蓼。[傳]楚為群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杜注]舒蓼,二國名。[疏]舒蓼二國名者,蓋轉寫誤,當為一國名。《釋例土地名》有舒、群舒、舒蓼、舒庸、舒鳩,以為五名,則與文五年滅蓼同。蓋蓼滅后,更復故,楚令更滅之。劉炫以杜為一國而規之,非也。[匯纂]今廬州府廬江縣故舒城是也。[今按]杜于文十四年注云:舒蓼即群舒,此言二國,非也。然二國亦非轉寫之誤。劉炫規之不得,謂其非此舒蓼,與文五年之蓼不同。彼蓼在安豐,此舒蓼在舒城,《疏》合為一,亦誤”。
卷三定公四年:“容城,[經]許遷于容城。[今按]《水經注》:容城即華容縣,今荊州府監利縣也”。
該書卷四則為“王朝列國興廢說”,詳細敘述了周王朝和魯、蔡、曹、衛、滕、晉、鄭、吳、燕、齊、秦、楚、宋、杞、陳、薛、邾、莒、小邾、許二十個諸侯國的興衰變遷,其中注出了列國國都的今地。
書名雖為《春秋地理考實》,而實際上考實《左傳》的地名大大多于《春秋》。據筆者統計,全書前三卷考實《春秋》地名316處,考實《左傳》地名達1029處,后者是前者的三倍多。其考《左傳》地名,亦依前例釋地。茲于前三卷亦各舉一例說明之:
卷一隱公元年:“費,[傳]費伯帥師城郎。[匯纂]魯大夫費,
父之食邑,讀如字,與季氏費邑讀如秘者有別。魏武封費亭侯,即此。今魯臺縣西南有費亭。[今按]費伯者,費 父也,見隱二年;郎亦在魚臺縣,故知此費為其食邑。陸德明《釋文》:音秘。非也。季氏之費,見僖元年”。該書同卷僖公元年“費”下云:“[今按]費音秘,今山東沂州府費縣也”。
卷二宣公十二年:“滎澤,[傳]及滎澤。[杜注]在滎陽縣東。[今按]此即《禹貢》濟水溢為滎者也。今無水,滎陽人猶謂其處有滎澤”。
卷三昭公十二年:“鮮虞,[傳]假道于鮮虞。[杜注]白狄別種,在中山新市縣。[匯纂]今直隸真定府新樂縣西南有新市故城,俗名新城鋪。其地有鮮虞亭,《史記索隱》曰:中山,古鮮虞國,姬姓也。[今按]如《索隱》說,則鮮虞非白狄別種。真定府今改正定府,新樂屬本府之晉州”。
清四庫館臣認為,江永《春秋地理考實》于經、傳地名“皆確指今為何地,俾學者按現在之輿圖,即可以驗當時列國疆域及會盟侵伐之跡,悉得其道里、方向”,“于名同地異、注家牽合混淆者,辨證尤晰”,從而得出了“其訂訛補闕,多有可取,雖卷帙不及高士奇《春秋左傳地名考》之富,而精核較勝之矣”
的結論。
程恩澤(1785~1837年)字云芬,號春海,安徽歙縣人。嘉慶十六年進士,官至戶部右侍郎。傳世著作有《國策地名考》二十卷。
《國策地名考》專考《戰國策》中出現的地名,于每一地名下先列原文,次列原注,次加案語,次詳眾說,次列當時的“今名”。全書以地名所地各諸侯國國別為序,詳細情況見下表:
表4-4 《國策地名考》中的地名考證
| 卷次 |
國別 |
地名數 |
| 一 |
周 |
22 |
| 二、三 |
秦 |
92 |
| 四、五 |
齊 |
87 |
| 六、七 |
楚 |
92 |
| 八、九 |
趙 |
90 |
| 十、十一、十二 |
魏 |
138 |
| 十三、十四 |
韓 |
68 |
| |
燕 |
31 |
| |
宋 |
7 |
| 十五 |
衛 |
11 |
| |
中山 |
6 |
| 十六 |
諸小國 |
21 |
| |
諸夷國 |
16 |
| 十七 |
諸國隙地 |
26 |
| |
諸國姓氏地 |
58 |
| 十八 |
古國 |
38 |
| 十九、二十 |
古邑 |
61 |
| 總計 |
|
864 |
書中有少許地名是重復的,故所考地名不及表中統計的864條之多,程氏在該書的自序里說有七百多條,大致與實際情況相合。
該書考證地名頗為詳確,今可舉孟津、蒲坂二地名為例。卷一周朝“孟津”條:“《秦策》謂秦王曰:‘章驅十二諸侯,以朝天子于孟津’。原注:在河內河陽縣南。恩澤案:孟津與孟津縣非一地。孟津縣在河南,漢為河陰縣,今屬河南府;孟津在河北,漢為河陽縣,今為孟縣,屬懷慶府;中隔大河,相距約七十里。孟津與河陽又非一地,河陽故城在今孟縣西三十五里,孟津在今孟縣南十八里。《尚書正義》曰:孟是地名,津是渡處,在孟地置津,謂之孟津,蓋即《左傳》盟地。《書》所云東至于孟津、師畢渡孟津皆是也。《后漢書·光武紀注》:俗名冶戍津,即此。《十三州記》云:‘河陽縣治河上,即孟津也’。以孟津為河陽。《元豐志》從之,非是;《方輿紀要》以孟津為漢平陰縣,即以孟津縣為孟津,亦非”。
又,卷一一魏國“蒲坂”條云:歷代學者以為見于《楚策》中的“蒲坂”在河東。作者認為作為舜都的河東蒲坂系魏國地名,當時存在著另一叫“蒲坂”的秦國地名,他論述道:“蒲坂在唐虞時已有此名,不始于春秋戰國間。若垣與蒲坂本是兩地,何得相混?然《正義》云:前秦取蒲坂,復以與魏,魏以為垣,今又取魏垣,以為蒲坂、皮氏,其后又歸魏,魏復以為垣(俱本《史記》)。是當時實屢經更名,并非無因。蓋垣為今長垣縣,本衛之蒲邑,秦嘗取之,后既歸魏,而又歸秦,故秦人以為蒲反,而魏則仍其故名曰垣。此自為一地,與舜都全不相涉。《國策》所云蒲坂,蓋即指此……自漢以來,俱列之河東郡,則其名稱之相混久矣”。
正因為該書對列國地名有如此詳細的考證,所以書前所附《戰國輿地總圖》及周、秦、齊、楚、趙、魏、韓、燕、宋、衛、中山等國的12幅歷史地圖中地名定位也大都準確。楊守敬《歷代輿地圖》中的“戰國疆域圖”圖組,亦全賴此書繪出。
阮元評價《國策地名考》時,指出像孟津、蒲坂這樣的條目考證“皆確不易”
。有的學者稱:該書自“胡朏明《禹貢錐指》、全謝山《地理志稽疑》后,此其盛業矣” 。
以上所舉閻若璩、江永、程恩澤三人的輿地著作,均以考證先秦典籍中的地名方位見長。像這樣的輿地著作,清儒所撰還有許多,已見上文表4-1中。隨著地名方位考證的日趨增多,成果日積月累,時代呼喚著有系統、有條理也便于檢索的地名著作的誕生。于是,由李兆洛主編的第一部歷史地名辭典——《歷代地理志韻編今釋》,于道光十七年(1837年)問世了。
李兆洛(1769~1841年)字申耆,號養一,常州府陽湖縣大寧鄉三河口(今江蘇武進市東三河口鄉)人。師從著名學者盧文弨。嘉慶十年(1805年)進士。據其弟子蔣彤記載:“先生自幼年即留意地輿之學,凡史部有涉地理者無不備致,尤得力于顧氏書(指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
,并且“備購各省通志,較五千余年來水地之書,證以正史” 。
清朝“自乾隆中葉后,海內士大夫興漢學,而大江南北尤甚”
,漢學昌盛、考據發達,李兆洛有感于“歷代地理建置沿革,變亂紛總,名實訛淆,或同地而異名,或同名而異地,南北相乖、東西易向”的復雜情況,集門下十余弟子“編錄古來史書中地志所載郡縣之名,以韻次之,分別時代,條其同異,鉤稽今代所在之處,以著其實,閱史者易于尋檢焉”
。二十卷的《歷代地理志韻編今釋》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編成的,編纂工作自道光二年李兆洛到暨陽書院講學始、至道光十七年完成,艱苦地持續了16年,“雖非日日致力于此,而暇日之力則無不致焉,可謂勞矣”
。
《歷代地理志韻編今釋》收錄地名的對象是歷代正史《地理志》中的政區地名,即漢、續漢、晉、宋、南齊、(北)魏、隋、新唐、新五代、(趙)宋、遼、金、元、明十四部正史《地理志》中所載全部州、郡、府、縣和唐、宋、金、元、明各志中的鎮、堡、羈縻州郡、長官司之類以及南北朝有實地可考的僑置州郡。歷代所無而清代新置的政區,也一并收錄,下加“本朝”二字,以示區別。全書地名依平水韻106個韻部編排
,在1667個同韻字下編排了一萬個左右的地名,全都注出了今地。這個數量是空前的,也是地名方位研究的一次大總結。
《歷代地理志韻編今釋》詮釋地名具有精、全、明三個特點,即釋文盡量用簡潔的文字,包含盡量可能多而全的內容,并且敘述簡明、條理清晰,是一部頗具學術價值的地名工具書。茲舉卷十八入聲“屋”
韻下“福”字為例:
祿福:[西漢]縣,酒泉郡,(今)甘肅肅州治。
永福:[北魏]縣,徐州蕃郡,(今)山東兗州府滕縣東南一百二十。●[隋]縣,揚州江都郡,(今)安徽泗州天長縣西北。●[唐]縣,嶺南道桂州,[宋]縣,廣南西路靜江府,[元]縣,湖廣省靜江路,[明]縣,廣西省桂林府永寧州,(今)廣西桂林府永福縣治。●[宋]縣,福建路福州,[元]縣,江浙省福州路,[明]縣,福建省福州府,(今)福建省福州府永福縣治。
延福:[隋]縣,雍州雕陰郡,[唐]縣,關內道綏州,(今)陜西綏德州東南。
安福:[隋]縣,豫州淅陽郡,(今)湖北襄陽府均州西。●[隋]縣,揚州廬陵郡安復之訛。●[唐]縣,江南道吉州,[宋]縣,江南西路吉州,[元]縣,江西省吉安路,[明]縣,江西省吉安府,(今)江西吉安府安福縣治。
福:[唐]州,江南道,[五代]州,(今)福建福州府閩縣東北。●[唐]州,羈縻,江南道,[宋]州,羈縻,夔州路紹慶府,(今)闕。按:當在貴州思南府境。●[宋]州,福建路,[元]州、路,江浙省,[明]州、府,福建省,(今)福建福州府閩縣治。●[遼]州,上京道,(今)闕。按:當在盛京境。
建福:[宋]縣,廣南東路韶州,(今)廣東韶州府曲江縣東南。
正因為《歷代地理志韻編今釋》收錄并詮釋方位的地名比以往著作為多,在歷史地名研究方面跨上了一個新臺階,故而一百多年以來備受贊譽。毛岳生在序中說:該書“取諸史,郡縣分隸韻書,以今為本,推諸前代,或地名皆同,或同名異地,與今昔增損有無殊異,皆列其疆域廣袤所在”,使讀者“不出戶庭而時代之遷嬗、裔徼之荒遼,源流俱在,其絕舛馳何如哉!”李鴻章盛贊此書:“每閱乙部,于郡縣疑名輒用檢視,應手可得,覺向者肝膽楚越,忽如盧醫之遇長桑,飲以池上水,盡見癥結”,因而于同治十年(1871年)在直隸總督任上將李兆洛著作匯刻為《李氏五種》,并作了一篇長序,“重付剞劂,冀永其傳”
。譚其驤先生稱此書為“空前之創著,與讀史者以一大便利,誠所謂嘉惠后學者不淺” 。
地名方位的考證既可以用文字敘述,也可以用地圖表達。在歷史地圖研制方面,清末楊守敬的成就最為突出。
楊守敬(1839~1915年)字鵬云,號惺吾,晚年自號鄰蘇老人,湖北宜都(今宜都市陸城鎮)人。學問通博,于歷史地理、版本目錄、金石書法均有精深造詣,友人潘存謂其“妙悟若百詩,篤實若竹汀,博辨若大可,尤精輿地之學”,謂其學問為“曠世絕學,獨有千古”
。羅振玉視楊守敬的地理學與王念孫段玉裁的小學、李善蘭的算學“為本朝三絕學” ,今方志學家朱士嘉也說:“楊惺吾先生崛起楚北,竭數十年精力于此,遂集諸家之大成,蓋近百年來治歷史地理者無能出其右焉”
。在他八十三種著作之中,最享有盛譽的為《歷代輿地圖》和《水經注疏》。前者便是用地圖表示歷史地名方位考證成果的杰出的代表之作。
《歷代輿地圖》可分為兩大部分,前一部分為《歷代輿地沿革險要圖》,共71幅,系楊守敬先于同治二年(1863年)與鄧承修、后于光緒五年(1879年)與饒敦秩合作繪成,主要是歷代疆域形勢圖、四裔圖等,性質相當于總圖。后一部分為歷代《地理志》圖,始繪年代已不可考,熊會貞出力尤多,最終完成于宣統三年(1911年),共繪出春秋、戰國、嬴秦、前漢、續漢、三國、(西)晉、東晉、前趙、后趙、前燕、后燕、南燕、北燕、前秦、后秦、西秦、前涼、后涼、南涼、北涼、西涼、夏、后蜀、劉宋、南齊、蕭梁、陳、北魏、北齊、西魏、北周、隋、唐、后梁、后唐、后晉、后漢、后周、宋、遼、金、元、明總計四十四組地圖,性質相當于分幅圖。春秋圖組畫出《左傳》地名,戰國圖組畫出《戰國策》地名,漢代以后各圖以相應的各史《地理志》為主畫出各朝政區和山川形勢,最多的元朝圖組由91幅圖組成,最少的西秦圖組也有5幅地圖。整套圖集共有1714幅地圖,分裝成三十四冊。這是我國歷史上朝代最為完整、內容最為詳細的一套大型歷史地圖集,譚其驤先生稱:“這是歷史地圖繪制史上的里程碑”
。
《歷代輿地圖》采用朱墨套印,朱圖即是作為底圖的胡林翼《大清一統輿圖》,墨圖即清代以前的歷代各圖,是楊守敬博考群書、為歷代正史《地理志》中地名確定方位、里距后上圖的。如果每幅地圖的地名承載量平均以二十個計,則這套地圖集共收有地名三萬四千多個。我國歷史悠久、疆域遼闊,大大小小的山川地名成千上萬,而郡縣的遷徙、地名的改易、水道的變遷十分復雜;為了考證每一個地名的確切位置、弄清每一條河流的變遷過程,楊守敬往往翻檢許多典籍,甚至對《水經注》、歷代正史《地理志》作了詳盡的疏證,這方面的傳世著作便有《漢書地理志補校》(2卷)、《三國郡縣表補正》(8卷)、《隋書地理志考證附補遺》(9卷)、《水經注疏》(40卷)等。所以應該說,《歷代輿地圖》以地圖的形式表達地名方位,是楊守敬畢生考證歷史地名的結晶。
有些清人的學術著作,即使不以輿地作書名,內也多含地名方位考證的內容,今可舉顧炎武、沈垚二人的著作為例。
顧炎武(1613~1682年)系清朝的“開國儒宗”
,江蘇昆山人,代表性著作為《日知錄》(32卷)。《日知錄》是一部體大思精、內容龐雜的著作,作者自稱“平生之志與業皆在其中”
,但卷三一具體考證了向、韓城、四海、九州、南武城、夏謙澤、綿上、箕、唐等古地名的含義和位置。例如《春秋》隱公二年“莒人入向”,杜預注:“譙國龍亢縣東南有向城”;宣公四年“公伐莒、取向”,杜預注:“向、莒邑,東海丞縣東南有向城”。《日知錄》卷三一“向”條寫道:“按《春秋》,‘向’之名四見于經,而杜氏注為二地,然其實一‘向’也。先為國,后并于莒,而或屬莒、或屬魯,則以攝乎大國之間耳。丞縣今在嶧”。顧氏先辨“向”之名,然后考“向”之實,考證了“向”地地名的來龍去脈。又如夏謙澤,見于《晉書·載記》及《通鑒》卷一0九,顧炎武考證道:“胡三省注:夏謙澤在薊北二百余里,恐非。按《水經注》:‘鮑丘水東南流,徑潞城南,又東南入夏澤。澤南紆曲渚一十余里,北佩謙澤,眇望無垠也’……今三河縣西三十里,地名夏店
,舊有驛,鮑丘水徑其下,而泃河自縣城南至寶坻,下入于海。疑夏店之名因古夏澤,其東彌望盡陂澤,與《水經注》正合” 。在這里,顧氏的地名方位考證還結合了他在京東作實地考察的體會。再如,關于綿上、箕、唐的位置,傳統認為分別在山西介休、陽邑、晉陽,《日知錄》卷三一“晉國”、“綿上”、“箕”、“唐”諸條從晉國疆域逐漸擴展而作出論證,“吾于杜氏之解綿上、箕而不能無疑,并唐叔之封晉陽亦未敢以為然也”,認為綿上、箕“必在近國都之地”
,“必其近國之地也”,“竊疑唐叔之封以至侯緡之滅,并在于翼(今山西翼城縣)”。這些觀點,不失為一家之言。
沈垚(1798~1840年)字子敦,浙江省烏程縣南潯鎮(今屬湖州市)人。“喜研金元輿地掌故之學”,“尤精輿地之學”
,可惜懷才不遇,在京師貧病而死,年僅43歲。遺稿零落,好友張穆編為《落颿樓文稿》四卷。書中有許多內容是考證地名方位的論文,如卷一的《六鎮釋》、卷四的《<西游記>金山以東釋》等。
《六鎮釋》是一篇考釋北魏六鎮地名的文章,認為北魏初年為防御柔然而設置的六鎮是指沃野鎮、懷荒鎮、懷朔鎮、武川鎮、柔遠鎮、撫冥鎮,而不包括御夷鎮,并且一一考定了其中五鎮的具體位置,只是“不知撫冥鎮在今何地”。在沈垚考定六鎮確數之前,錢大昕還犯過“當時名為六鎮、實不止六矣”的錯誤。
《<西游記>金山以東釋》則是沈垚的代表作,撰成于去世前兩年。《西游記》是《長春真人西游記》的簡稱,金山即今阿爾泰山。長春真人姓丘名處機,金朝末年從山東登州到燕京(今北京),然后北出西游去中亞謁見成吉思汗。《西游記》所記多為蒙古族聚居區的地名,蒙、漢文字、讀音均異,地名歧議頗多,加以北徼懸遠,交通不便,流傳至清時人們對丘處機所經過的地方已不甚清楚,甚至對大蒙古帝國的首都和林也不知所在了。沈垚憑藉他的“地學之精”
和勇于探索的精神,著成此文,詳細考證了《西游記》燕京至金山之間的道路、山脈、河流、湖泊、驛站、城鎮、關隘等古今地名,使游記中的地名處處有著落,成為研治西北邊疆地理的重要文獻。該文共分九節,第一節所釋地名野狐嶺、翠帡口、會河堡、得勝口等,均在當時直隸西北部;第二節所釋地名蓋里泊、昌州,在內蒙古南部;第三節所釋地名魚兒濼則在今內蒙古巴林左旗西北沙漠中;第四節詮釋了地名臚朐河(今克魯倫河)、土兀剌河(今蒙古國土拉河);第五節所釋地名“和林”,在和林川之東,為大蒙古帝國首都(今有哈喇和林遺址),辨明建都始于太宗而非太祖;第六節所釋地名契丹城,認為就是遼鎮州城,位于和林東北;第七節所釋地名唐古河疑為哈瑞河(今哈綏河)、駐夏之地窩里朵疑在齊老圖河(今楚魯滕河)側近;第八節所釋地名杭海,認為即是杭愛山;第九節所釋地名鎮海城,亦名稱海,因鎮海(1169~1252年在世)所筑而得名,位于外蒙古科布多之東。由此往南即達金山。沈垚分節考釋長春真人西游經過蒙古地區的具體線路、山脈、河流和地名,使蒙古地區歷史地理輪廓清晰,從而成為繁榮的清代西北史地之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程恩澤對沈垚的考證十分佩服,張穆轉述道 :“程春海侍郎嘗讀《西游記》,擬為一文,疏通春廬中丞跋所未盡;及見子敦跋,嘆曰:地學如此,遐荒萬里,猶目驗矣,我輩粗才,未足語于是也”。
考據學派大量地理類論文中的地名方位考證,真可謂多如牛毛,如全祖望《祁連山考》
、陳遹聲《涂山考》 、沈登瀛《原鄉非孝豐地辨》 、張澍《曲江在廣陵考》 、舒潤《五月渡瀘今地證》 、莫與儔《漢且蘭縣故地考》
、曾朝佑《楚地今名考》 、汪之昌《旸谷明都昧谷幽都今地釋》 、蔣湘南《大 山在成皋說》 等文,一望選題便知其研究對象是地名的方位。對于同一地名的方位,不同學者或有異說,例如張澍《涂山考》認為禹娶于涂山的方位在蜀之巴縣(今屬重慶直轄市)、《首陽山考》
認為夷齊不食周粟而餓死的首陽山在甘肅渭源縣,然陳遹聲《涂山考》認為涂山在安徽懷遠,金鶚《首陽山考》 認為首陽山在平陽府(今山西臨汾市)。類似的論文很多,例繁不備舉。
二、 關于地名沿革
考據學派對地名沿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歷代政區地名沿革方面,錢大昕、洪亮吉、陳芳績、段長基、楊丕復的著作可作代表。
錢大昕(1728~1804年)系乾嘉考據學大師,字曉征,一字及之,號辛楣,又號竹汀居士,太倉州嘉定縣(今上海市嘉定區)人。乾隆十六年(1751年)特賜舉人,三年后考中進士。歷任翰林院庶吉士、《一統志》纂修官、詹事府少詹事、廣東學政等職,晚年長期執教于鐘山、婁東、紫陽等書院。他“深于經史之學”,“不專治一經而無經不通,不專攻一藝而無藝不精”,被后人視為“開國以來蔚然一代儒宗”。
錢氏總結了考證政區地名沿革應遵循的普遍原則,其《秦四十郡辨》
開篇有云:“言出于古人而未可信者,非古人之不足信也;古人之前尚有古人,前之古人無此言,而后之古人言之,我從其前者而已矣”。在這個理論指導下,他認為秦郡數目當以班固《漢書·地理志》為據,而闞骃和《晉書》的秦四十郡說均系后出,不足信
。與此同理,他論述了《水經注》可否補漢初侯國地名問題。有人問:漢初功臣封侯者一百四十余人,封邑所在班固已不能言,酈道元《水經注》始考得十之六七,可否補孟堅之闕?錢氏答道:“此史家之謹慎,即其闕而不書,益知其所書之必可信也;酈氏生于后魏,距漢已遠,雖勤于采獲,未必皆可盡信。”接著他列舉了九個實例,如劉蒼封安成侯,《贛水篇》以為長沙之安成,而《汝水篇》以為汝南之安成;又如劉拾封建成侯,《贛水篇》以為豫章之建成,而《淮水篇》以為沛之建成;更有甚者,酈道元以東晉僑置之山陽郡當作漢劉荊所封山陽公之邑,從而認為“班氏得古史闕文之遺意矣”,而酈注“其誤更不待辨矣”
,因而在漢侯國地名記載方面,錢大昕的結論是:“《水經注》難盡信”。
錢氏在進行政區地名沿革的考證中,有兩大重要發現。一是晉僑置州郡無“南”字。他在深入鉆研東晉南朝僑置政區的基礎上,發現晉室南渡后在南方僑置的州郡并非如《晉書·地理志》所說的那樣冠有“南”字,僑置政區地名前加“南”字實始于永初受禪(公元420年6月)以后。唐初修《晉書》不察,遂有此誤,至錢氏始正之。他說:“唐初史臣誤認宋代追稱為晉時本號,著之正史,沿訛者千有余年,至予始覺其謬”,從而認為“史家昧于地理,無知妄作,未有如《晉志》之甚者”
。二是闡發《宋書·州郡志》去京水陸里程的含義。他論述道:“案休文志州郡,于諸州書去京都水陸若干,唯州所治郡不云去京都水陸若干者,已見于州也。南徐州領郡十七,南東海為州所治,此外則南瑯邪、晉陵、義興皆有實土,故有水陸里數;南蘭陵以下十三郡,有戶口而無水陸里數者,僑寓無實土也。諸州皆仿此”
。這一發現,為后人根據《宋書·州郡志》所載水陸道里判斷州郡是否僑置、僑置是否割實提供了重要依據。
就具體的地名沿革而言,可舉漢廬江郡為例。當時,姚鼐的觀點是:“夫廬江者,其水出陵陽東南,而西北流經彭蠡,以入于江,至今猶命彭蠡之山為廬山云”;到了漢武帝時,“江南遂無廬江名矣,其后改衡山郡曰廬江,然后廬江之名遂移于江北也,然則衡山之為廬江,其昭、宣間乎?”
據其所考,廬江郡初在長江以南,漢武帝后此名移植到了長江以北,移置時間推測為昭、宣年間。此論一出,反應甚大,然則錢大昕頗有疑義,他寫信給姚鼐說:“廬江之為郡,在孝景初,自后別無廢省之人。伍被說淮南王安云:南收衡山以擊廬江。是衡山與廬江絕非一地。今欲并而合之,難矣”。就在這封信中,錢大昕結合漢廬江郡的考證,闡述了進行地名沿革考證的一條重要原則:“讀史之病,在乎不信正史,而求之過深、測之太密。班孟堅志郡國沿革,精矣;間有未備,以紀傳考之,無不合也。孟堅所不能言,后儒闕其疑可矣。謂漢初之廬江在江南,武帝時已罷,昭、宣之間改衡山為廬江,皆孟堅所未嘗言。所據者僅廬江出陵陽一語,然陵陽乃鄣郡之屬縣,非淮南故地,恐難執彼單辭以為定案也”
。
洪亮吉(1746~1809年)字君直,又字稚存,號北江,晚號更生居士。常州府陽湖縣(今江蘇常州市)人。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中舉,十年后考中一甲第二名進士。歷任翰林院編修、貴州學政、上書房行走等職。嘉慶四年(1799年)因直諫而被論死,從寬發落,遣戍伊犁,次年詔諭釋回。晚年執教于旌德洋川書院。他完全生活在乾、嘉時代,自己謙稱“粗知湛濁,稍別方輿”
,史稱“洪氏深于地理之學” ,“經、史、注、疏、說文、地理靡不參稽鉤貫” 。所著沿革地理著作,即有《補三國疆域志》、《東晉疆域志》、《補十六國疆域志》等。
眾所周知,《三國志》無志,正如洪亮吉所說:“其尤要而不可闕者,惟地理一志”
。補作三國的地理志,既要克服資料不足的困難,也要分辨前人舛誤,他博考群書,花了兩年功夫,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撰成《補三國疆域志》兩卷。該書仿《宋書·州郡志》體例,上卷為魏國司、豫、兗、青、徐、涼、秦、冀、幽、并、雍、荊、揚十三州,下卷為蜀漢益州和吳國荊、揚、交、廣四州。此書的編成,令錢大昕“嘆其奇絕”,錢氏認為該書“勝仆數倍”,因而放棄了“留意三國疆域有年、常欲作志”的打算
。這是清人補作《地理志》之始 。
洪亮吉認為,歷代正史《地理志》各有得失,“其最舛者則惟晉史地理志”,該志“惟詳泰始、太康,而永嘉以后僅掇數語”,所以“止可稱西晉之地志,而于江左則尚無預焉,此東晉疆域之不可不作也”
,因而也用了兩年時間,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在畢沅幕中纂成了《東晉疆域志》四卷,十年之后刊刻行世。該書前三卷為實州郡縣,輯考了揚、北徐、兗、豫、北青、司、荊、湘、江、梁、益、寧、廣、交十四實州所轄162實郡、882實縣共凡1058個政區地名的沿革;卷四則探討了荊、益、揚三個實州所轄12僑郡,徐、秦二僑州所轄7實郡,遙立北雍、東秦、司、并四州所轄17郡以及豫、徐、兗、幽、冀、青、并、司、雍、秦、梁11僑州所轄61僑郡,即自序所謂“僑州至十數、僑郡至百、僑縣至數百”等政區地名的沿革。此書的編成,極為錢大昕贊賞,親自為此書作序,認為“其才大而思精,誠史家不可少之書也”,“稚存生于千載之后,乃能補苴罅漏,抉摘異同,搜酈、樂之逸文,參沈、魏之后史,闕疑而慎言,博學而明辨,俾讀者了然,如聚米之在目前,詎非大快事哉!”
。錢序雖可能溢美,書中問題亦復不少,然亮吉纂輯此書,對地名沿革的考辨是下了很大功夫的。
《十六國疆域志》與《東晉疆域志》相輔而行,共有16卷,即每國一卷(卷一二后燕附有西燕),詳考各國州、郡、縣等政區地名沿革,即使赫連勃勃以城名代替郡縣地名也照錄不誤(見卷一六)。此志補成后,洪亮吉總結了補撰《地理志》同時也是研究歷史政區地名沿革所面臨的十大困難。
陳芳績字亮工,清初江蘇常熟人,康熙六年(1667年)撰成《歷代地理沿革表》四十七卷,道光十三年(1833年)始得刊行。該書分為部表(3卷)、郡表(15卷)、縣表(29卷)三部分,部表首列虞十二州及交州,每州下列自唐虞至明代轄境內之州、國、道、路、府、省等地方區劃;郡表首列秦四十郡,每郡下列自秦至明歷代轄境內之郡、州、路、府、軍、衛等地方區劃;縣表按《漢書·地理志》次序,列舉自秦至明各縣之置廢,并旁注其沿革年、月。“自古至今,凡添設、并省、更名、徙治之類,纖悉具載”
,因而后人稱贊“是讀一書而九州之疆土、古今之名號、城邑之變遷了如指掌,誠前此未有之書也” 。清代類似的著作還有段長基的《歷代沿革表》和楊丕復的《輿地沿革表》。河南偃師人段長基,于嘉慶十九年(1814年)撰成《歷代沿革表》三卷,以當時的府縣為綱,每一地名下依次考其先秦至明代的沿革,與陳芳績的做法相近。湖南常德人楊丕復(字愚齋)系嘉慶十二年舉人,其四十卷的《輿地沿革表》大約成書于道光年間。梁啟超曾將陳芳績、楊丕復兩書作了比較:“陳書按古以察今,楊書由今以溯古;陳書以朝代為經、地名為緯,楊書以地名為經、朝代為緯”,結論是:“兩書互勘,治史滋便”
。此言得之。
清人有關政區地名沿革考證的單篇論文,數量也很可觀,除上文提到的之外,具有代表性的還有劉師培《秦四十郡考附秦郡建置沿革考》
、沈家本《漢豫章郡名考》 、黃以周《漢縣道考》 、洪頤煊《漢淮陽置郡考》 、汪士鐸《三國廬江郡考》 、陳壽祺《唐置建州辨》
、鄒漢勛《貴陽沿革》 、江藩《六安州沿革說》 、劉恭冕《沔陽州沿革考》 、繆荃孫《江陰沿革考》 等,恕不一一詳細介紹。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本文將地名學的成就分為幾個方面,不是絕對的,這些方面之間并不是孤立的,而是有機地聯系在一起的。例如上文提及的李兆洛、楊守敬著作,這里也可看作是用地名辭典、歷史地圖的形式來表現的政區地名沿革;下文將要齒及錢大昕在地名典籍考證與辨誤方面的貢獻,其實也是有關地名沿革的考證;而本節有關洪亮吉的政區地名沿革著作中,也不乏地名定位、用字、讀音等的考證性內容。
三、 關于地名含義
清儒關于地名含義的討論,要數“三江”問題最為典型。
《尚書·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此處“三江”的含義到底是什么?漢代以來論爭紛起,群言淆亂,迄無定論。程瑤田早就感嘆:“三江為解經者之一大惑也久矣!欲辨其惑,言人人殊”
。蕭穆也說:“前人之說地理,言人人殊、不能劃一者,莫過于《禹貢》之三江” 。清人考證“三江”的論著,多至三十余種,歸納起來主要有六種觀點:
(1) 主班固《漢書·地理志》北、中、南三江說者,
有朱鶴齡《禹貢三江辨》 、錢塘《三江辨》 、許宗彥《禹貢三江說》 、張澍《三江考》 、張海珊《三江考》 、蕭穆《禹貢三江說》
、汪士鐸 《三江說》 、胡薇元《三江說》 、黃家辰《三江既入解》 、鄒漢勛《三江彭 蠡東陵考》 等十余文。王鳴盛《尚書后案》、阮元《浙江圖考》亦持此觀點。
(2)主鄭玄以岷江、漢水、彭蠡諸水為三江者,有程瑤田《荊州江漢揚州三江異名同實說》、《三江辨惑論》
、陳一麒《禹貢三江解》 、管世銘《彭蠡三江說》 等文,以及胡渭《禹貢錐指》、金榜《禮箋》等著作。
(3)主韋昭以松江、錢唐江、浦陽江為三江者,見趙一清《答禹貢三江震澤問》
。
(4)主郭璞以岷、松、浙為三江者,見顧炎武《日知錄》卷二“三江”條。
(5)另出別說,以中江、北江、九江為三江,見李紱《三江考》
、黎庶昌《禹貢三江九江辨》 等文。
(6)亦另出別說,以松江、蕪湖江(永陽江)、毗陵江《孟瀆河》為三江,見
楊 椿《三江論》。
由上所述可知,當以主班固說者居多。雖然,北江、中江之名已見于班固《漢書·地理志》,卻獨不見“南江”一名,大多推論“有北、有中,則有南可知”,邢澍《南江考》維護傳統觀點,還具體考證了從皖南經蘇南入太湖的所謂“南江故道”
,程廷祚《禹貢南江辨》則以洞庭湖為南江 。然而,推論代表不了事實,王舟瑤《論近人考<禹貢>南江之失》一針見血地指出:“《禹貢》三江,中、北見于經,而南江無明文,近金輔之、錢溉亭、阮文達、邵二云、洪稚存諸人皆據《漢書·地理志》‘分江水首受江、東至余姚入海’者以當《禹貢》之南江,自以為根據班志、《水經》、《說文》等書,實則以意牽合,而終無明證也”
。
經過清代學者的不懈努力,現在學界對此大致取得了共識。顧頡剛先生認為:《禹貢》三江“其實是江、湖分歧錯雜的意思”,“并不必確指其地”
。李長傅先生也認為:“《禹貢》中之三、九等數字,只不過是公式數字,表示多數與次數多之意義;三江,大概是指長江三角洲之支流而言,并不專指哪三條江;若一定要考出三條江之名稱及經流,恐難得出定論”
。
四、 關于地名用字
在清人論述中,沒有關于地名用字的專門著作,只是在一些論著中涉及到這個問題,其中顧炎武、胡渭、錢大昕、吳卓信的著作較為典型。
顧炎武論述了“嶗山”、“濰水”等地名的用字。《日知錄》卷三一“勞山”條謂:“勞山之名,《齊乘》以為‘登之者勞’,又云一作‘牢丘’,長春又改為‘鰲’,皆鄙淺可笑。按《南史》:‘明僧紹隱于長廣郡之嶗山’。《本草》:‘天麻生太山、嶗山諸山’。則字本作‘嶗’”
。同書“濰水”條則云:“其字或省‘水’作‘維’,或省‘系’作‘淮’,或又從‘心’作‘惟’,總是一字。《漢書·地理志》瑯邪郡朱虛下、箕下作‘維’,靈門下、橫下、折泉下作‘淮’,引《禹貢》‘惟甾其道’又作‘惟’,一卷之中,異文三見。《通鑒·梁武帝紀》:‘魏李叔仁擊邢杲于惟水’,胡三省注:‘惟’當作‘濰’。古人之文或省,或借其旁,并從‘鳥隹’之‘隹’則一爾。后人誤讀為‘淮沂其乂’之‘淮’,而呼此水為槐河,失之矣”。
胡渭考證了《漢書·地理志》“ 哉水”實為“涐水”之誤,《禹貢錐指》卷九“和夷底績”句下:“渭按:《水經注》引鄭說云:和夷,和上夷所居之地。和水即涐水,和、涐聲相近,字從而變。《地理志》云:‘青衣縣,《禹貢》蒙山溪大渡水東南至南安入
哉。 哉水出汶江縣徼外,南至南安,東入江,過郡三,行三千四十里’。‘ 哉’乃‘涐’字之誤。《說文》:涐水出蜀汶江徼外,東南入江。從水、我聲。徐鉉音五何切。故知‘
哉’當作‘涐’,和夷者,涐水南之夷也……道元敘涐水甚略,自《漢書·地理志》‘涐’誤作‘ 哉’,而師古曰音哉,世遂不知有涐水,且不知
哉水之所在,徒以其下流與南安之沫水號為大渡者,合而入江,因目涐水曰大渡河”。在這里,胡渭論證了《漢書·地理志》“ 哉水”實為“涐水”之誤
。此說得到了錢大昕、王紹蘭、《大清一統志》、吳卓信、徐松、楊守敬的同意和肯定 。然而,今《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二冊仍從《漢書·地理志》誤字作“
哉水”。
錢大昕對正史《地理志》中的地名用字發表過一些精辟的見解。《續漢書·郡國志》河東郡垣縣“有王屋山,兗水出”,《廿二史考異》卷一四:“兗,即流字,古人從水,字或橫寫如
、 之類, 作兗亦是以立水為橫水,隸省為六爾,兗州本以 水得名,非兩字也”。《晉志》武威郡有揖次縣,《廿二史考異》卷一九:“當作揟次,漢隸胥、揖二字多相亂,故訛為揖;隋開皇初改廣武縣曰邑次,又因揖、邑同音而訛也”。《魏書·地形志》南青州州治作“國城”,《
廿二史考異》卷二九:“國城,《通鑒》作圂城,胡三省云:圂城,當在唐沂州沂水縣界;圂,戶困翻。予按:《高閭傳》以本官領東徐州刺史,與張讜對鎮團城;《劉休賓傳》亦云東徐州刺史張讜所戍團城,領二郡。則‘國城’當為‘團城’之訛,或作‘圂城’亦誤”。《隋書·地理志》渤海郡有滴河縣,《廿二史考異》卷三三:“滴當作滳,讀如商”。
吳卓信字立峰,號頊儒,蘇州府昭文縣何家市(今江蘇常熟市東何市鎮)人,生活在乾、嘉年間,道光三年(1823年)去世時享年六十余歲
。一生著書甚多,可惜大部分均已散佚,惟103卷之巨的《漢書地理志補注》因李兆洛的保存而得以流傳至今。吳卓信恐怕是清代學者中對地名用字發表意見最多的學者,在此僅舉二十例:
《漢書·地理志》京兆尹新豐有驪山,《補注》卷一:“按驪字,或作麗、作酈,又作離,古通用”。
《漢書·地理志》左馮翊有鄜縣,《補注》卷二:“按《說文》作鄜
,《始皇本紀》有 公,應劭曰: ,秦邑。考秦邑別無名‘ ’者,當即此 字。古 、 二字本通用”。
《漢書·地理志》弘農郡弘農縣下有燭水,《補注》卷四:“按
灟即燭字,據《水經注》燭入門水、門水入河水也。《太平寰宇記》所謂鴻臚澗,即顏注所云洪溜澗,聲之轉也”。
《漢書·地理志》太原郡有界休縣,《補注》卷六:“按界休本因介子推死而名,當作介,隋開皇十八年始改界休為介休,至今因之。然界、介二字古實通用”。
《漢書·地理志》東郡有茬平縣,《補注》卷一0:“按‘茬’字,《續志》、《晉志》、《水經注》并作‘茌’,宋祁曰:當作茌。今俗皆作茌,讀若治”。
《漢書·地理志》汝南郡有吳房縣、常山郡有房子縣,《補注》卷一三:“按《史記·項羽本紀》、杜預《左傳注》并作吳防,房、防古通用”;卷二四又云:“按《后書光武紀》作防子,注云:防與房同,古字通用”。
《漢書·地理志》江夏郡有 縣,《左傳》、《史記·信陵君傳》作冥,《淮南子》作澠,《補注》卷一六:“按古字
、冥聲相近, 與澠亦通用”。
《漢書·地理志》山陽郡有湖陵縣,《補注》卷一九:“按《說文》作胡陵,《史記》諸紀傳亦作胡陵,湖、胡古通用”。
《漢書·地理志》清河郡有 縣,《補注》卷二五:“按
,史表作俞,如淳曰:俞即 也,蓋古通用”。
《漢書·地理志》平原郡有瑗縣,《左傳》作轅,《水經注》作援,《補注》卷二八:“按古瑗、援、轅三字并通用”。
《漢書·地理志》千乘郡有 沃縣,《補注》卷二九:“按諸書引者皆作漯沃或隰沃,不知何故,其實此三字皆有意義,不可混也”。
《漢書·地理志》泰山郡蛇丘縣下有隧鄉,《補注》卷三一:“按隧當作遂,《春秋》、《史記》、《郡國志》并同,此真是流俗之訛,而顏氏不能正之,反曰‘隧音遂,可謂謬極”。
《漢書·地理志》桂陽郡有含洭縣,《補注》卷四一:“按洭水,即桂陽縣下誤作匯水者也,《集韻》洭本作
,隸省作 ,亦有作 者,蓋因避(宋)太祖諱”。
《漢書·地理志》武陵郡鐔成縣下有潭水,《補注》卷四二:“按潭當作鐔,縣所名也”。
《漢書·地理志》蜀郡湔氐道下有崏山,《補注》卷四六:“按岷山,本志作崏,《說文》作
,省作岷,漢人隸書皆作汶,蓋古字通用也”。
《漢書·地理志》犍為郡 縣,《補注》卷四七:“按《晉書·地理志》作存
,《水經》亦作存。據《說文》,本無 字,則存字是也。 ,今《玉篇》、《廣韻》俱訛為鄢,《廣韻》并兩載郁鄢、 二縣,尤誤”。
《漢書·地理志》天水郡冀縣下引《禹貢》有朱圄山,《水經注》、《通典》、《元和郡縣志》、《大清一統志》俱作朱圉山,《補注》卷五五:“按圄、圉,古通用,《說文》及本書《東方朔傳》囹圄皆作囹圉”。
《漢書·地理志》北地郡直路縣下有沮水,《補注》卷六一:“按沮水,《說文》作
,水出北地直路,從水、 聲;沮水出漢中房陵,從水、且聲。今概從省文作沮,而北地之 與漢中之沮并無分別。據《史記索隱》云:沮水,《地理志》無文,《水經》以為
水,此可見唐時《水經》亦作 水,與《說文》合也”。
《漢書·地理志》漁陽郡有路縣,《補注》卷七一:“按路當從《續志》及《水經注》作潞,蓋縣以潞水得名也”。
《漢書·地理志》中山國有新處縣,《補注》卷八七:“按《表》作薪處,又作辛處,又作宣處,古字薪、辛、宣皆通用”。
在考據學派有關地名用字研究的單篇論文中,也不乏高見,可舉伊雒、朐忍二地為例。段玉裁《伊雒字古不作洛考》
云:“今學者作伊雒字皆作洛,久無有知其非者矣。古豫州之水作雒字,雍州之水作洛字,載于經典者劃然。漢四百年未嘗混淆,至魏而始亂之”。他查考了《詩經》、《周易》、《春秋》、《左傳》、《逸周書》、《淮南子》等古文獻,最后得出的結論是:“字一作洛、一作雒,亦分別皎然,與《周禮》合。是亦見古二水二字之分矣”。
又,漢巴郡有朐忍縣(治所在今重慶直轄市云陽縣城附近),《漢書·地理志》、《續漢書·郡國志》均作“朐忍”,但后代多誤作“朐
”、“朐 ”,段玉裁《朐忍考》 認為:“《郡國志》作朐忍,而《吳漢傳》、《劉焉傳》作朐 者,因朐字從肉而誤增也”。他分析道:“《吳漢傳》注引《十三州志》:朐音春,
音閏。闞骃在唐以前,不宜有誤,蓋注《十三州志》者見忍既訛 、朐又訛朐,不知改正,妄為此音,而章懷引之。自后杜佑《通典》上字此順切、下字如尹切,讀如蠢閏,又誤以為地屬漢中。宋徐鉉等校《說文》,肉部增‘
’二字,而仍其音,且仍屬漢中之誤。至《廣韻》則上字音蠢、下字音閏。總之,承訛襲謬,上字形、聲俱舛,下字聲近似而形實舛也”。由此感嘆“六書不明,論古之難非一日矣!”
陳漢章《朐忍 辨》一文 ,列出十條證據證明作“朐忍”者是、作“ ”者非。例如第二條證據是:“《樊毅修華岳齋亭碑》、《巴郡太守張納功德敘》、《郃陽令曹全碑》、《趙國相雝勸闕碑》皆作‘朐忍’,至《晉書·宣帝紀》、《地理志》‘忍’字始沿‘朐’之肉旁,誤作‘
’”。第三條證據是:“維時‘忍’雖誤‘ ’,而‘朐’尚未誤‘ ’。《晉書》紀、志而外,《宋書·州郡志》、《隋書·地理志》注皆作‘朐
’。《后漢書·吳漢傳》注雖引《十三州志》讀為蠢閏,而章懷先有‘劬忍’二音,可見其字亦本作‘朐’矣”。第十條證據是:“《水經·江水注》引《華陽記》曰:朐忍縣出靈龜;又曰:常璩曰朐忍縣在巴東郡西二百九十里;又云:彭溪水徑朐忍縣西六十里,江水右徑朐忍縣南。是晉、魏人仍作‘朐忍’”。經過這樣深入的探討,“朐忍縣”地名用字已得到圓滿的解決。
五、 關于地名讀音
清人著作中也沒有關于地名用字的專門著作,即使在論著中涉及這個問題,也是筆墨不多,但發表的意見都很重要。可舉顧炎武、錢大昕二人著作為例。
顧炎武詳細注明了“徐州”、“東 ”的讀音。《史記·魯世家》:“頃公十年,楚伐我,取徐州”。《日知錄》卷三一“徐州”條原注:“《索隱》曰:徐音舒,徐州,齊邑薛縣是也,非九州之徐”,并且說:“《說文》:‘
,邾之下邑,在魯東’。又《竹書紀年》云:‘梁惠成王三十一年,邳遷于薛,改名曰徐州’。則徐與 并音舒也。今讀為《禹貢》徐州之‘徐’者誤。《齊世家》:‘田常執簡公于徐州’,《春秋》正作‘舒州’!”漢陳留郡有東
縣(治今河南蘭考縣北),而山陽郡有東緡縣(治今山東金鄉縣),“ ”、“緡”二字形近易混,《日知錄》卷三一“東 ”條特別注明:“屬陳留者,音
;屬山陽者,音旻”。并且指出:“《水經注》引《王海碑辭》曰:‘使河堤謁者山陽東 司馬登’,是以‘緡’為‘ ’,誤矣”。
錢大昕在地名讀音方面發表的意見較多。《漢書·地理志》千乘郡
沃,《廿二史考異》卷七:“ 當作濕,音它合反”;齊郡鉅定,《廿二史考異》卷七:“《水經注》作巨淀,定有澱音,語之轉也,后人又加水旁”。《續漢書·郡國志》卷縣有垣雝城,或曰古衡雍,《廿二史考異》卷一四:“垣、衡聲相近”;陳留郡封丘有桐牢亭,或曰古蟲牢,《廿二史考異》卷一四:“古音蟲如同,《詩》‘蘊隆蟲’,徐仙民:音徒冬反,《韓詩》亦作烱烱,故蟲牢轉為桐牢也”。《魏書·地形志》太原有靡溝,《慕容白曜傳》作糜溝,《廿二史考異》卷二九:“靡、糜,音相近”。《舊唐書·地理志》歙州黟縣:“漢縣,屬丹陽郡,晉同醫縣”,《
廿二史考異》卷五八:“按晉無同醫縣,當是‘音’字之訛,謂黟音近醫耳,‘縣’字衍”。
錢大昕發明的“古無輕唇音”之說,在地名讀音上也有四例:(1)“古讀文如門,《水經注》漢水篇:文水即門水也。今吳人呼蚊如門。《書》:岷嶓既藝,岷山之陽,岷山導江,《史記·夏本紀》皆作汶山。《漢書·武帝紀》文山郡注,應劭曰:文山,今蜀郡崏山”。(2)“古讀汾如盆,《莊子·逍遙游篇》‘汾水之陽’,司馬彪、崔譔本皆作盆水”。(3)“古讀房如旁,《廣韻》:阿房,宮名,步光切。《釋名》:房,旁也,在堂兩旁也。《史記·六國表》:秦始皇二十八年為阿房宮,二世元年就阿房宮,宋本皆作旁。旁、房古通用”。(4)“古讀望如茫,《釋名》:望,茫也,遠視茫茫也。《周禮·職方氏》:其澤藪曰望渚……即宋之孟渚,古音孟如芒”。
錢大昕也探討過音譯地名問題,認為譯音地名無定字。例如蒙古語地名“插漢”,《明史李成梁傳》作“叉漢”,《張學顏傳》作“察罕”,《大清一統志》又作“察哈爾”
。又如北朝時北方有一強悍的少數民族政權柔然,他說:“按柔然,北方之國,不通中華文字,史家據譯音書之,或稱茹茹,或稱芮芮,其實即柔然二字之轉也。柔然、茹、芮,同屬日母。明元(帝)易茹為蠕,不過借同音字寓蚩鄙之意,元非改其國號”。
清人單篇論文論述地名讀音的,可舉汜與氾、陽狐與陽孤二例。王舟瑤有《辨氾汜二水》
一文,大意是說:氾、汜本是二水,氾水故道在山東曹州府定陶縣界,顏師古注《漢書》音敷劍反;汜水在河南開封府汜水縣境,讀如祀;氾、汜二字形近易訛,古文獻中多互為混淆,但是“二水本別,許書(指《說文》)氾從
聲,汜從巳聲,則音亦別也”。由此他判定張晏注《漢書》云汜水在濟陰界、司馬貞《史記索隱》標氾音似,皆誤。又如,《資治通鑒》卷一周安王元年:“秦伐魏,至陽孤”,《史記·六國年表》與《魏世家》俱作“陽狐”,《水經·河水注四》又作“陽壺”。汪之昌《陽孤、陽狐、陽壺辨略》
一文在引證大量文獻后寫道:“狐駘可作壺駘,與陽狐之或作陽壺同是地名,尤堪引證;若狐與孤,雖同以從瓜得聲,然易混淆,經傳罕見通假”,但是“同音通假,經傳恒例,據諸書之作‘壺’,即可決魏地之是陽狐,而非陽孤”。在這里,汪之昌據同音通假之例考證出一處《通鑒》地名之誤。
六、 地名典籍考證與辨誤
典籍考證是清人治學的重點之一,所以考據學派在地名典籍的考證與辨誤方面成績顯著,許多著作都涉及到這個問題(詳見表4-1),其中以顧炎武、錢大昕、吳卓信、趙紹祖、楊守敬五人的成就較為突出。
顧炎武旅居山東十余年,對齊魯大地了如指掌,他說:齊地東環大海,海岸之山莫大于勞、成二山。《史記·秦始皇本紀》:“自瑯邪北至榮成山”,《正義》:“榮成山即成山也”。顧氏論證道:“按史書及前代地理書并無‘榮成山’,予向疑之,以為其文在瑯邪之下、成山之上,必‘勞’字之誤。后見王充《論衡》引此,正作‘勞成山’,乃知昔人傳寫之誤,唐時諸君亦未之詳考也,遂使勞山并成之名、成山冒榮之號。今特著之,以正史書二千年之誤”。
對于《大明一統志》,顧炎武重點指出了十處錯誤
,言辭比較激烈,今舉其三:
《大明一統志》:“楊令公祠在密云縣古北口,祀宋楊業”。顧氏查考了楊業一生行跡,結論是:“是業生平未嘗至燕,況古北口又在燕東北二百余里,地屬契丹久矣,業安得而至此?且史明言雁門之北口,而以為密云之古北口,是作志者東西尚不辨,何論史傳哉!”
漢樂浪郡有朝鮮縣,箕子所封,故地在今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平壤特別市的大同江南岸。顧氏云:“慕容氏于營州之境立朝鮮縣(今遼寧義縣北),魏又于平州之境立朝鮮縣(今河北遷安縣東北),但取其名,與漢縣相去則千有余里。《一統志》乃曰:‘朝鮮城在永平府(治今河北盧龍縣)境內,箕子受封之地’。則是箕子封于今之永平矣!當日儒臣,令稍知今古者為之,何至于此?為之太息”。
《明一統志》登州府名宦下云:“劉興居,高祖孫……封東牟侯,惠澤及于邦人,至今廟祀不絕”。顧氏考證了劉興居事跡,寫道:“興居之侯于東牟僅三年,其奉就國之令至立為濟北王相距僅五月,其曾到國與否尚不可知,安得有惠澤及人之事歷二千年思之不絕者乎?甚矣,修志者之妄也!”
錢大昕考證地名,用力最勤、研究最深的當推各正史的《地理志》,指正政區地名錯誤、不當、衍脫及釋疑等情況共有895處,茲統計如下:
表4-5 錢氏考證中的地名訂誤與釋疑
| 地理志名稱 |
訂誤與釋疑條目 |
出 處 |
| 《漢書·地理志》 |
96 |
《廿二史考異》卷七、《三史拾遺》卷三 |
| 《續漢書·郡國志》 |
199 |
《廿二史考異》卷一四、《三史拾遺》卷五 |
| 《晉書·地理志》 |
52 |
《廿二史考異》卷一九、《諸史拾遺》卷一 |
| 《宋書·州郡志》 |
49 |
《廿二史考異》卷二三、《諸史拾遺》卷二 |
| 《南齊書·州郡志》 |
6 |
《廿二史考異》卷二五 |
| 《魏書·地形志》 |
82 |
《廿二史考異》卷二九、卷三0 |
| 《隋書·地理志》 |
93 |
《廿二史考異》卷三三 |
| 《新唐書·地理志》 |
17 |
《廿二史考異》卷四四、《諸史拾遺》卷二 |
| 《舊唐書·地理志》 |
97 |
《廿二史考異》卷五八 |
| 《五代史·職方考》 |
46 |
《廿二史考異》卷六五 |
| 《宋史·地理志》 |
55 |
《廿二史考異》卷六九、《諸史拾遺》卷四 |
| 《遼史·地理志》 |
7 |
《廿二史考異》卷八三 |
| 《金史·地理志》 |
12 |
《廿二史考異》卷八四、《諸史拾遺》卷五 |
| 《元史·地理志》 |
84 |
《廿二史考異》卷八八、八九及《諸史拾遺》卷五 |
至于錢大昕指正正史《地理志》地名不當甚至錯誤之處,那更是俯拾皆是,茲于各正史《地理志》均僅舉一例,列表說明如下:
表4-6 錢氏地名訂誤舉例
| 書 名 |
原 文 |
訂 誤 舉 例 |
| 《漢書·地理志》 |
漁陽郡白檀縣:洫水出北蠻夷。注:洫音呼貝鳥反。 |
《考異》卷七:“按《水經注》:濡水流逕漁陽白檀縣故城,《地理志》曰:濡水出縣北蠻中。蓋酈道元所見之《漢書》本作濡水,不知何時訛濡為洫,師古不能正也”。 |
| 《續漢書·郡國志》 |
樂安國,高帝西平昌置,為千乘。 |
《三史拾遺》卷五:“前撰《考異》,指此條‘西平昌’三字衍,西平昌縣名當屬上文平原郡,誤脫竄入于此。今檢《魯峻碑陰》有門生‘平原西平昌王端子行’一人。此以漢人述漢郡縣,尤可信吾言之非妄”。 |
| 《晉書·地理志》 |
其后又立巴渠……等十郡。 |
《考異》卷一九:“蓋《晉志》敘江左僑置州郡,多不可信”。 |
| 《宋書·州郡志》 |
徐志有邊城兩,領雩婁、史水、開化、邊城兩縣 |
《考異》卷二三:“此上、下‘兩’字皆誤。詳其文義,謂立邊城郡,領雩婁等四縣也。上‘兩’字疑是‘郡’字之訛,下‘兩’字疑‘四’字之訛。” |
| 《南齊書·州郡志》 |
有平陽石鼈,田稻豐饒,所領惟平陽一郡。 |
《考異》卷二五:“據下文,當為‘陽平郡’轉寫顛倒耳,《周山圖傳》亦云于石鼈立陽平郡”。 |
| 《魏書·地形志》 |
幽州宣都城。 |
《考異》卷二九:“按幽州無宣都城,一本作宜都,亦誤。當是軍都之訛。” |
| 《隋書·地理志》 |
后置魯州。 |
《考異》卷三三:“永安中,置廣州于魯陽,而齊、周因之。史未見魯州之名,當為廣州之誤也”。 |
| 《新唐書·地理志》 |
思唐州武朗縣。 |
《諸史拾遺》卷二:“郎當作朗,史臣避宋諱缺筆,后人訛為郎耳。《元和郡縣志》正作武朗。 |
| 《舊唐書·地理志》 |
晉置泰州,北齊為泰州。 |
《考異》卷五八:“泰,當作秦州“。 |
| 《五代史·職方考》 |
乾州,李茂貞置,治奉先縣。 |
《考異》卷六五:“奉先,當作奉天。《唐志》京兆奉天縣,乾陵在北五里。乾寧二年,以縣置乾州,蓋州以乾陵得名,非同州之奉先縣也”。 |
| 《宋史·地理志》 |
句容,天禧四年改名常寧。 |
《考異》卷六九:“案《景定建康志》,初無改句容為常寧之事,但云天禧元年置常寧鎮于句容縣,又云以鎮置寨耳。此志誤”。 |
| 《遼史·地理志》 |
北安州興化軍領縣一,利民縣。 |
《考異》卷八三:“遼之北安州有興化縣,無利民縣,惟金承安中嘗升利民寨為縣,未久旋廢。作《遼史》者乃以金所置之利民為遼時舊縣,而不及興化,誤矣”。 |
| 《金史·地理志》 |
薊州縣五,舊又有永濟縣,大定二十七年,以永濟務置,未詳何年廢。 |
《考異》卷八四:“案元至元七年,孫慶瑜撰《豐閏縣記》云:金大定間改永濟務為縣,大安初避東海郡侯諱,更名曰豐閏,史不知豐閏即永濟之改名,而分而為二,乃以豐閏為泰和間置,又謂永濟已廢,而未得其年,皆誤之甚也”。 |
| 《元史·地理志》 |
建德路,唐睦州,又為嚴州,又改新定郡。 |
《考異》卷八九:“案唐時為睦州,天寶初為新定郡,乾元初仍為睦州,宋初亦為睦州,宣和中平方臘之亂,始改睦為嚴。志云:唐為嚴州,誤之甚矣”。 |
除此之外,錢氏因考《通鑒》胡注地名之誤而著有《<通鑒注>辨正》兩卷,指正胡注地名72處錯誤;又因參加《鄞縣志》的編纂而指出了小江湖非西湖、甬橋非甬水橋等三則地名錯誤
。
錢大昕在古代地名問題上發現前人這么多錯誤,其目的并不是為了挑剔前人,而是讓它們更加完善,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訂訛規過,非以訾毀前人,實以嘉惠后學”
,“去其疑,乃能堅其信;指其瑕,益以見其美;拾遺規過,匪為齮龁前人,實以開導后學” 。
前賢對吳卓信成就的認識不足。其實,吳氏在地名研究方面很有遠見卓識,上文已略有述及,下面所論亦說明了這一點。
吳卓信針對前人論述地名的錯誤,在《漢書地理志補注》中時時指正。即如《漢書·地理志》本文,他就指正了十二處:
(1)《漢書·地理志》京兆尹南陵縣下有沂水,《補注》卷一:“按今本《漢書》京兆尹南陵縣下,‘浐水’并作‘沂水’,師古曰:沂音先歷反。據《說文》則作‘浐水’,而《水經注·浐水篇》首尾再引班志,是‘沂水’即‘浐水’無疑,不知何以誤‘浐’為‘沂’。
(2)《漢書·地理志》右扶風鄠縣下有燏水,《補注》卷三:“按本志作燏水,誤也,據《說文》乃是澇水,然唐本已誤為燏,故顏師古音決”。
(3)《漢書·地理志》上黨郡泫氏縣下云:“楊谷,絕水所出,南至野王入沁”。《補注》卷七:“按泫水合丹水始入沁,在高都縣,非野王也,本志誤”。
(4)《漢書·地理志》河內郡山陽縣下云:“東太行山在西北”。《補注》卷八:“按‘東’字疑衍,孔氏《書正義》及《詩譜正義》并引本志此文皆無‘東’字”。
(5)《漢書·地理志》泰山郡蓋縣下有臨樂于山,《補注》卷三一:“按《說文》及《水經》并作臨樂山,無‘于’字,故后世地志多宗之。則‘于’字當衍”。
(6)《漢書·地理志》:“北海郡益縣,莽曰探陽”。《補注》卷三三:“舊作探陽,誤。按《后書·劉盆子傳》有王莽探湯侯田況,章懷注:莽改北海益縣曰探湯,則知舊本‘陽’字之誤矣”。
(7)《漢書·地理志》蜀郡下有《禹貢》桓水,《補注》卷四六:“按《禹貢》桓水即廣漢郡甸氐道之白水,亦即墊江水;蜀郡之桓水,自別是一水入南海者,孟堅以當《禹貢》之桓水,實誤”。
(8)《漢書·地理志》蜀郡有汶江(縣級政區),《補注》卷四六:“按《續志》、《華陽國志》、《水經注》并作汶江道,縣有蠻夷謂之道,今本《漢書》脫‘道’字耳”。
(9)《漢書·地理志》:“張掖郡,故匈奴昆邪王地”。《補注》卷五七:“按張掖非昆邪王所屬,志誤也,《武帝紀》明言‘分武威所置’是矣”。
(10)《漢書·地理志》代郡且如縣下云:“于延水出塞外,東至寧入沽”
。《補注》卷六九:“按上谷郡有寧縣、有廣寧縣。據《水經注》:于延水東至廣寧入治,則本志作‘寧’誤也”。
(11)《漢書·地理志》上谷郡且居縣下有樂陽水,《補注》卷七0:“按樂陽水,當從《水經注》作陽樂為是,遼西郡有陽樂縣,此水所出也”。
(12)《漢書·地理志》漁陽郡白檀縣下有洫水,《補注》卷七一作濡水,并云:“舊作洫水,今改正。按洫當作濡,濡水即遼西肥如之水,今之灤河也。《水經注·濡水篇》引本志亦作濡水而不別出洫水,可知即濡水矣”。
以上除第(5)、(11)兩處標點本已改正,第(7)、(9)兩處屬一家之言,第(8)一處指出脫字之外,其余第(1)、(2)、(3)、(4)、(6)、(10)、(12)七處地名錯誤今中華書局標點本《漢書·地理志》既未改正,又未出校勘記。看來標點本《漢書·地理志》吸收前人成果似尚不足。
吳氏指正其它學者或地名典籍之誤的,書中也隨處可見,今僅舉十例:
(1) 應劭之誤。《漢書·地理志》泰山郡有肥成縣,《補注》卷三一:“按應仲遠謂肥成即古肥子國。據本志真定國綿蠻縣注云:故肥子國。又杜氏《左傳注》:肥子國在巨鹿下曲陽縣西南,今有肥纍城。則肥子國屬真定者為是。《元和郡縣志》復主應氏之說,非也”。
(2) 《續漢書·郡國志》之誤。《漢書·地理志》瑯邪郡有不其縣,《補注》卷三五:“按《續郡國志》作不期,非是。伏湛封不其侯,不作期也”。
(3) 《水經注》之誤。《漢書·地理志》會稽郡有山陰縣,《補注》卷三八:“按《續志》云:會稽郡,秦置,本治吳,立吳郡乃移山陰。然則《水經注》謂山陰縣秦會稽郡治者,誤也”。
(4) 顏師古之誤。《漢書·地理志》張掖郡角樂得縣下顏師古注:“角樂得,匈奴中地名,縣取其名耳”。《補注》卷五七:“按角樂得,本匈奴地,為去病所取乃置郡縣,非取其名也,顏說誤”。
(5) 李賢《后漢書注》之誤。《漢書·地理志》勃海郡有重平縣,《補注》卷二七:“按今濟南府德平縣西北亦有重平故城,乃后魏孝昌中所改置,非漢縣也。《后漢書注》及《太平寰宇記》、《方輿紀要》諸書所言皆誤”。
(6) 《史記正義》之誤。《漢書·地理志》桂陽郡有臨武縣,《補注》卷四一:“按《史記·樊噲傳》:漢王賜爵為列侯,號臨武侯。《正義》曰:即桂陽臨武縣。考戰國、秦時之際,趙亦有臨武君,未必遠取桂陽之臨武也”。
(7) 司馬貞之誤。《漢書·地理志》武陵郡有義陵縣,《補注》卷四二:“按《功臣侯表》:義陵侯吳郢,高祖九年以長沙王柱國封,即此。徐廣云:一作義陽。司馬貞遂謂義陽縣在汝南,誤矣”。
(8) 《太平寰宇記》之誤。《漢書·地理志》上郡有膚施縣,《補注》卷六二:“按《太平寰宇記》謂,耆老云:佛書言昔尸毘王割身肉飼鷹,后人言膚施即其地。據《史記》,膚施乃戰國時趙地,秦以為縣,其時未有佛書也。荒唐附會,不足與辨。今膚施為延安府附郭縣,出城東北里許為清涼山,上有尸毘巖。予于嘉慶乙丑(1805年)秋過此,土人猶指以為證,可哂也”。
(9) 顧祖禹之誤。《漢書·地理志》泰山郡有東平陽縣,《補注》卷三一:“按魯有兩平陽……顧宛溪、高江村于‘宣八年城平陽’并引哀二十七年盟越后庸事,是誤以鄒縣之西平陽為即此東平陽矣”。
(10) 閻若璩之誤。《漢書·地理志》平原郡高唐縣下有漯水,《補注》卷二八:“按閻百詩謂漯水有二,一出東武陽,一出高唐。析一水而二之。甚矣,其妄也”。
吳卓信《漢書地理志補注》指出他人之誤,雖屬一已之見,未必全都正確,但都是經過縝密考證后得出的結論。
趙紹祖(1752~1833年)字繩伯,號琴士,安徽涇縣人。著作等身,《通鑒注商》為其代表作之一。該書18卷,依《通鑒》編年順序對胡三省的注提出商榷,共731條,前人評價說:此書“視顧炎武《日知錄》所列及陳景云之《舉正》,不啻倍蓰,一一有成處可核”
。
表4--7 清儒有關《通鑒》胡注著作一覽表
| |
作 者 |
指正胡 注誤處 |
其中正地 名之誤 |
備 注 |
| 《日知錄》 |
顧 炎 武(1613~1682) |
16 |
6 |
見黃汝成集釋本卷二十七。 |
| 《通鑒胡注舉正》 |
陳 景 云(1669~1747) |
63 |
18 |
影印《四庫全書》本。原 為十卷,今僅存一卷。 |
| 《通鑒注辨正》 |
錢 大 昕(1728~1804) |
140 |
72 |
《潛研堂全書》本,共二卷。 |
| 《通鑒注商》 |
趙 紹 祖(1752~1833) |
731 |
365 |
《安徽叢書》本,共十八卷。 |
胡注詳于地名,因而趙氏的商榷也以地名居多,或糾胡注地名之誤,或補胡注地名之疏。全書前17卷中指出的胡注地名疏誤,秦漢時期31處、三國兩晉時期33處、南北朝59處、唐時期40處、五代時期15處,共計178處,占前17卷指出胡注疏誤544處的三分之一。下面將每個時期各舉一例以說明之:
(1)《通鑒》卷四二漢光武帝建武八年:“田弇、李育保上邽”。胡注:“上邽縣屬天水郡”。《注商》卷二:“余按《續漢書·郡國志》:漢陽郡,本天水郡,明帝時改名,其屬縣有上邽,故屬隴西。則此時上邽屬隴西也”。
(2)《通鑒》卷九三晉成帝咸和二年:“(桓)彝退保廣德”。胡注:“何承天曰:廣德,漢舊縣。沈約曰:二漢志并無,疑是吳所立,屬宣城郡。《桐川志》:后漢置廣德縣,晉并入宣城。今廣德軍是也”。《注商》卷五:“余按《晉志》:宣城郡有宣城縣,又有廣德縣,未嘗并廣德于宣城,《桐川志》不足據也。且胡氏既引沈志以為吳立,何又引《桐川志》以為漢置耶?”
(3)《通鑒》卷一四三齊東昏侯永元二年二月戊戌:“魏以彭城王勰為司徒,領揚州刺史,鎮壽陽”。胡注:“壽陽自東漢以來為揚州治所,宋始為豫州治所,今復其舊”。《注商》卷九:“余按魏非能盡得揚州之地也,但以新得壽陽,故假揚州刺史之名以鎮之耳;而胡氏曰‘今復其舊’,不思之甚也”。
(4)《通鑒》卷一九六唐太宗貞觀十七年:“太子曰:‘當率萬騎獵于金城西’”。胡注:“金城,恐當作金河”。《注商》卷一三:“余按《承乾傳》本作金城,《地理志》延州敷政縣:本因城,武德二年更名金城,天寶元年曰敷政。是此時為金城也”。
(5)《通鑒》卷二八二后晉高祖天福四年:“康化節度使兼中書令楊珙稱疾,罷歸永寧宮”。胡注:“康化軍亦吳于統內所置節鎮,或南唐置之,其地今無考”。《注商》卷一七:“余按陸放翁《南唐書》云:昇元二年六月甲申,升池州為康化軍”。
趙紹祖還曾考證了《通鑒》原文地名之誤和《通鑒考異》中的地名錯誤。例如《注商》卷一五指出《通鑒》卷二四九南詔國“拓東”為“柘東”之誤,卷一六又指出:《通鑒》卷二五0唐咸通四年七月“復置安南都護府于行交州”句下《通鑒考異》以為無“郡州”這一政區亦誤,“溫公偶失考耳,胡氏亦未之舉正”。這種發現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隋書地理志考證附補遺》(九卷)是楊守敬研究歷代正史《地理志》諸多著作中成就最高的一種。早在年青時,楊守敬研讀《隋書·地理志》就發現該書錯漏甚多,加之后世傳抄之訛,誤、脫、衍、倒時有發生,于是下決心詳加考證。他廣集史料,多方考核,在熊會貞的協助下,經過三十多年的辛勤努力,終于完成了《隋書地理志考證》這部著作,光緒甲午(1894年)刻成,刊刻時每卷均附有《補遺》。書末跋云:“溯自草創之初,迄今繕寫之日,稿凡五易,時閱卅年”。該書體例上是按《隋書·地理志》逐條書寫的。在考訂各條內容之前,他先用宋版《隋書》對當時流行的各種版本作了校勘,然后廣泛引用《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通典》、《太平御覽》、《輿地廣記》、《輿地紀勝》、《方輿勝覽》、《天下名勝志》、《方輿紀要》、《大清一統志》及正史紀傳和金石文字等各種史料,對《隋書·地理志》加以考證。其記載無誤的,舉諸書為證較簡;其記載有誤的,則舉諸書訂誤較詳;有可疑而不可決者,則姑且存疑。綜觀楊守敬考證《隋書·地理志》之成績,約有六個方面:一是糾正因字形相似而產生的訛誤,二是糾正總管為西魏置之誤,三是訂正《隋書·地理志》記各州郡縣置廢時間的舛誤,四是補脫文、刪衍文,五是乙正《隋書·地理志》中多處倒文,六是補充《隋書·地理志》缺漏之州、郡、縣
。經過楊守敬這一番考證和訂誤,《隋書·地理志》不但內容較以前翔實可信,地名大多有了著落,并且文義不通之處也大大減少了。
但是,楊守敬在考證《隋書·地理志》地名沿革時,犯過以封爵補政區的錯誤,并為后人所承襲 。對此筆者已有專文論及 ,茲不贅述。
七、 規律性總結
相對于上述十分豐富的具體地名考證與研究而言,清代學者對地名學的規律性總結很是稀少。這種重實證、輕理論的特點,本身就是傳統地名學的顯著特征之一。
筆者孤陋寡聞,所見僅顧炎武、胡渭、王鳴盛、錢大昕、吳卓信等人在這方面有一些零星的論述。
顧炎武、王鳴盛總結了漢代區別異地同名地名的規律。《日知錄》卷二0“史書郡縣同名”條指出:“漢時,縣有同名者,大抵加‘東’、‘西’、‘南’、‘北’、‘上’、‘下’字以為別”。《十七史商榷》卷一七“《漢書》十一”則云:“郡國縣邑名同者,則加‘東’、‘西’、‘南’、‘北’、‘上’、‘下’或‘新’字以別之”。比顧氏多總結出一“新”字。錢大昭、吳卓信對此也有所論述
,不過其總結的規律不及顧、王二氏嚴密。
胡渭總結了山名相同而以大小(太、少)相區別的規律,他說:“山有名同而系之以大小者,如大別、小別、太華、少華、太室、少室之類是也,古書太、少與大、小通用”
。
錢大昕關于譯音地名無定字、古無輕唇音的規律性總結,以及在地名沿革研究方面的兩大發現,均已見上文,恕不復述。
吳卓信指出了地名用字的同音通假之例。《漢書地理志補注》卷四五于廣漢郡下寫道:“按《華陽國志》繩鄉,《水經注》作乘鄉,繩、乘字同音假借用耳”。具體地說,汪之昌還根據同音通假這一“經傳恒例”,考證出先秦魏地作“陽狐”者是,《通鑒》卷一作“陽孤”者非
。
晚清學者阮惟和(今上海市奉賢縣人),在其所著《元祕史地理今釋》
的自序中總結了蒙語地名漢譯的四大弊端,而從本文角度來看則是總結了地名譯名的四條原則,其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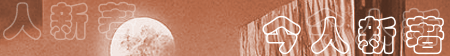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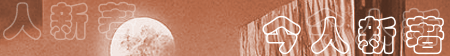
web@guoxue.com
![]() 010-68900123
010-68900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