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ڶ��� �Ї��v�������YԴ��ጵİl(f��)չ
����(ji��) �������
�����Ї��v�������YԴ��ጵİl(f��)չ���ğo���С��ij��١���ǧһֱ��ͻ��һ�f���P(gu��n)���V�����Ї������W(xu��)�l(f��)չʷ�ϵĹ��xƪ�¡���������ЌW(xu��)�g(sh��)�����l(f��)չ��ԭ��Ҳ�����(hu��)���������ء�
���������īI(xi��n)���ػ��Ժpʧ�O���(y��n)�أ��������h���꣬���īI(xi��n)�dz�ȱ�����h��ەr(sh��)���������z�Ĺ��£��Ҳ�����̫ʷ����
�����͵�������ԣ���ʷ�w��ӛ�������������ѡ� ���������hĩ��,����째���У��Ⱥ�����ż��ŵõ��˺ܺõ��������˺��īI(xi��n)��u�S�����������H��(sh��)�������ˣ���(n��i)��Ҳ�䌍(sh��)�ˡ��Ե����伮���ԣ���(j��)��̡��h����ˇ��־��������(y��ng)�롶�hˇ��־���C����Ҧ���ڡ��h��ˇ��־ʰ�a(b��)��������
��ǰ�hˇ��־ע�������h�]�����ĵ������ֻ��ǰ��������ġ���ؕ���͡�ɽ����(j��ng)�������˖|�h����������EȻ���࣬ε����^������a(b��)��h��ˇ��־�����������9�N���
�����a(b��)��h��ˇ��־�����������33�N��Ҧ���ڡ���hˇ��־���������H�ں��A(ch��)���������������4�N������߀�ѵ���ֳɌm���(hu��)��־֮�١��ݿ�֮�١���o(j��)֮�١��sӛ֮�����T����ȥ��؏�(f��)�ģ��t��Ҧ������䛵ĵ�����īI(xi��n)�_(d��)37�N֮�ࡣ�@Щ�����īI(xi��n)�T��ࡢ��(n��i)���·f�����в��������YԴ��ጵă�(n��i)�ݣ���ǰ����(y��ng)ۿ�������L(f��ng)��ӛ������ʮ����ӛ���ȣ��S�ܵġ�����ӛ�������Ϳ����f����������־������������־���t���˖|�x��賡��Aꖇ�־����ጵ����YԴ�ā�Դ֮һ��
�������������һ�T��Ҧ���ڷQ���ݿ�֮�ٵą^(q��)���Ե�־����(j��)���������(j��ng)��־�����ƣ�����h���䣬ʼ�t������L(f��ng)�ף����桢���o�����f��(ji��)ʿ֮�������]�����������t֮ٝ������֮�������Ƕ��������|�h�Ŀ���֮�����С�����L(f��ng)�ׂ�����Ȧ�Q������L(f��ng)�ׂ�����3�������Rֲ�������L(f��ng)��ӛ������
���o(j��)������ؕ���o(j��)�����w�������l(xi��ng)��ӛ�������Ϳ��D��(j��ng)�������ݡ��V�꿤�D��(j��ng)���ȣ���ϧȫ��������Ȧ�Q�ġ�����L(f��ng)�ׂ������Hه��ˮ��(j��ng)ע���������ű�����һ�[��צ�������Ŀ���Ȧ�Q�˕��漰�����m�H���һ�����s������Lԫ�����x��ξ�ϡ����ء����ᡢӺ���ᗗ�����ϡ����h������ʮ��(g��)�h���ĜYԴ���ɴ��Ɯy������֮�����@�(n��i)�ݲ��٣���������Ҳ�y�Q��ȫò�ˡ�
�������ܰ�̽�ጵ����YԴ��Ӱ푺��d��ע�⡶�h����֮�L(f��ng)��Ҳ�ǵ����YԴ��ጵ��l(f��)չ�����C(j��)�����h���������������꣬���|�hĩ�����Б�(y��ng)ۿ��עጡ�����h������(y��ng)ۿ��������������������ʮ��ƪ���ּ��⡶�h�������Ԃ��ڕr(sh��)������(y��ng)ۿ������ԏ������ƶȵ����֣������h�����и��N�������~���н�ጣ��磺
�������ٹٹ�����������ⵓ�ס�����(y��ng)ۿע�����⣬��Ҳ��������Ҳ���ף���Ҳ����
����������־�������S�۵����£��S�����x��Ҋ������(y��ng)ۿע�����x�������Ҳ���S�����£��ʵ�Ҋ����
������ʳ؛־�������ܾ����r(sh��)���X�p�������T���X������(y��ng)ۿע���������f�X����r(ji��)��Ҳ����
�������Y��־����(y��ng)ۿע�����������ܪz��Ҳ����
������ꐄق��������ٹ���ˌ�܊�γ����n�^܊������(y��ng)ۿע�����r(sh��)܊�����������Ի�n�^����
��������Ԫ������������ʸҹ�⡱����(y��ng)ۿע��������Ҳ��������ʸ���xҲ�в�������Ի��ʸ����
������Ҋ���������ģ��������������N�����ƶ���������ԏጣ�ԏጷ����漰���h�������еļo(j��)������־������������־����(d��ng)ȻҲ�����С����ԣ���(y��ng)ۿԏጡ��h��������־�������YԴ�䌍(sh��)����ע��������h��������Ҫ�M�ɲ���֮һ�����������x���ꏈ�̡��紾���Ͽ����f�ѡ��������x�Ƶ���עጡ��h��������ጵ����YԴ������������^��
�������������(j��ng)��־�����L�ƣ����������Ե���ة������ʹ�����M�lӛ�L(f��ng)�ף������֮��������־�������݇����hɽ�����U(xi��n)�r(sh��)��֮������(j��ng)��֮�֡��L(f��ng)���������^(q��)��֮�V������֮?d��ng)?sh��)�������������c�š���ؕ�������ܹ١���ӛ�������Ǻ��d�P֮ʿ���ܸQĩ�W(xu��)�����ܼ��h(yu��n)����ӛ�ݿ�֮�����ѡ�������@��Ԓ���õ����˵����W(xu��)�l(f��)չ�Č�(sh��)�|(zh��)����̡��h��������־���ь�60̎�������˜YԴ��ጣ���(y��ng)ۿ���L(f��ng)��ͨ�x�����������L(f��ng)��ӛ�����ܲ��f�������M����̵�Ӱ푣����˶���Ҳ���Ǒ�(y��ng)ۿ�ĵ����W(xu��)ؕ�I(xi��n)���ڡ�
�����������������(j��ng)��־�������У�����ʷ�����u�@Щ���ģ�°�̵ġ��d�P֮ʿ���ǡ��ܸQĩ�W(xu��)��������������R�����ݿ�־������κ��������־�����fҲ�S���ǡ���ӛ�ݿ�֮�����ѡ������������(sh��)�������������������W(xu��)���������f��δ��̫������(sh��)�ϣ���̡���(y��ng)ۿ�z�L(f��ng)�������������a(ch��n)������̵�Ӱ푣����挢�����ǰ�����YԴ��ጳ��^ʮ̎�ĵ����W(xu��)�Ҽ�������W(xu��)�����б��y(t��ng)Ӌ(j��)���£�
��2��10
�����ǰ�����YԴ��ጰl(f��)չ�Ĕ�(sh��)���y(t��ng)Ӌ(j��)
| |
| �����W(xu��)�� |
�r(sh��)�� |
�����W(xu��)���� |
�YԴ��ጔ�(sh��)�� |
| �� �� |
�| �h |
���h��������־�� |
60 |
| ��(y��ng) ۿ |
�|�hĩ |
���h�����⡷���������L(f��ng)��ӛ������ʮ����ӛ�� |
168 |
| Ȧ �Q |
�|�hĩ |
������L(f��ng)�ׂ��� |
10 |
| �f �� |
������ |
���h��ע���������ǿ���־���������Zע�� |
12 |
| Ԭ������ƽ������ |
��x�g |
��Խ�^���� |
43 |
| �� �� |
���x�� |
��̫����ӛ�� |
13 |
| �� �Y |
�� �x |
������Ҫӛ�� |
13 |
| �� � |
�| �x |
������ע������ɽ����(j��ng)ע�����������ӂ�ע�� |
21 |
| �� � |
�| �x |
���Aꖇ�־�� |
33 |
| ʢ��֮ |
�ϳ��� |
���G��ӛ�� |
21 |
| �� �� |
�ϳ��� |
���m(x��)�h������־ע�a(b��)�� |
17 |
| �Ұ�� |
�ϳ�� |
��ݛ��־�� |
72 |
| �R �S |
ʮ���� |
��ʮ����־�� |
34 |
| �B��Ԫ |
�� κ |
��ˮ��(j��ng)ע�� |
1052 |
| �� ̩ |
�� �� |
������־�� |
75 |
| �� �� |
ʢ �� |
��ɳ�ݶ������D��(j��ng)�� |
21 |
| ��� |
�� �� |
��Ԫ�Ϳ��h־�� |
931 |
�����ı�2��10��֪����̡���(y��ng)ۿ�_��(chu��ng)�Ľ�ጵ����YԴ֮�L(f��ng)������������W(xu��)�Ҙ����˰�ӣ�����Ė|�hĩ�굽��������������YԴ��ጲ��^��|������10̎���σ�(n��i)�ݵļ���Ȧ�Q���f�ѡ���̫����ӛ������Խ�^���������Y����象���賡�ʢ��֮�����ѡ��Ұ�����R�S���B��Ԫ����̩����ɳ�ݶ������D��(j��ng)�������ʮ��ң������B��Ԫ��ˮ��(j��ng)ע����������־֮��ɣ��YԴ��ጔ�(sh��)�����^һǧ�������Ԫ�Ϳ��h־��Ҳ�ӽ�ǧ��(sh��)��
����κ�x�ϱ��������YԴ��ጵ����࣬�ܵ�־�W(xu��)��ʷע�w�l(f��)�_(d��)��Ӱ�Ҳ��ԭ��֮һ����־�W(xu��)�İl(f��)�_(d��)��κ�x�ϱ����r(sh��)��ʷ�W(xu��)���c(di��n)֮һ
���|�xʮ�������ϱ����L�ڵķ��ѡ�����(zh��n)��������(hu��)��(d��ng)ʎ�������˿ڵĴ�Ҏ(gu��)ģ�w�ƣ��e������֮�y�Ժ�����ԭ�ϵ���������������ԭ���S������������ˌW(xu��)ʿ�������w��ʷ�Q�������Ժ��Җ|�w���¹ڱ��y��������ֹ����������ʿŮ�܁y������ʮ���ߡ�
������һ����Ѯ�(d��ng)�r(sh��)���M(j��n)���Ļ��������L�����齭������һ����Ҳʹ�������_�۽磬���L�˵���֪�R(sh��)�����ӿ�F(xi��n)�˔�(sh��)���ٔ�(sh��)�ĵ����������Ķ���(d��o)���˵���W(xu��)���������W(xu��)�İl(f��)չ����(j��)���������(j��ng)��־���d���ϳ��Rꑳ΅R����160�ҵ���־�����ɡ��������149���������ΕP��ꑳεĻ��A(ch��)�������a(b��)��84�ң����ɡ���ӛ��252��,�t�H�˶�����Ҋ��־����240��N��Ȼ�Ƅ�֪�ס�ʷͨ����־ƪ���q�ƣ����������R��ˮ������̎��w�L(f��ng)��������Տ��һ�壬���Ե�������ꑳμ����y�M��������?y��n)���ˣ��ϳ�������������־�������O(sh��)һ�T���D�V־�����o(j��)���D��
�����F���ǣ������@Щ�锵(sh��)�����ĵ�־�������˴����ĵ����YԴ��ጃ�(n��i)�ݡ�
�����l(f��)�_(d��)�ĵ�־�W(xu��)�cʷע�w�o��ɡ�κ�x�ϱ�����ʷע�d���_�صĕr(sh��)��
��ԓ�r(sh��)�ڵĵ����W(xu��)�īI(xi��n)�У����h�����ı���ע�ҡ���象�����ע������ɽ����(j��ng)ע�����������ӂ�ע�������ѡ��m(x��)�h������־ע�a(b��)�����B��Ԫ��ˮ��(j��ng)ע������ʷע�w��ʷע�����˴����ĵ�־�īI(xi��n)��ʹ�ØI(y��)��ʧ���Ĺż�������һ�[��צ���P�߽y(t��ng)Ӌ(j��)�˄���ע���m(x��)�h��������־�����õĵ�־�īI(xi��n)����Ҫ�У����[���x�ص�ӛ�������A������ӛ��������֮������ӛ�������R����ӛ�������|���x�������Q�ע�������ϡ�����ӛ���������o�S�D�����������P(gu��n)��ӛ���������־������Խ�^�������ϡ�����ӛ���������Rӛ�������G��ӛ�������϶��x������������f�������_��������ӛ�������Iꖿ�ӛ������ʼ����ӛ������ʼ�d��ӛ��������|ӛ���������dӛ������ԥ��ӛ������ԥ���f־�������V־�������|�ӛ�������Aꖇ�־��������ӛ������ԥ������ӛ���������x���������hӛ�������ٮa(ch��n)������ӛ����������ӛ����ʮ���N��ͬ�ӣ��B��Ԫ��ˮ��(j��ng)ע��Ҳ�����˱���ĵ�־�īI(xi��n)����(j��)ꐘ��A�����y(t��ng)Ӌ(j��)��109�N
������ʷע������־�īI(xi��n)������(g��)�e�N���浽����֮�⣬�^�־���������������������r���@Щ�����ĵ�־�īI(xi��n)�����ИO�䌚�F�ĵ����YԴ��ጃ�(n��i)�ݡ�
����κ�x�ϱ����r(sh��)�ڔ�(sh��)�����^�ĵ�־�w�������ˡ�Ԫ�Ϳ��h־�����Y�ρ�Դ֮һ������@Щ��־��ӛ����˽�ģ��S���@������IJ������࣬�������u������^�ɡ����������(j��ng)��־����������������I(y��)�����t�����T�����l���L(f��ng)����a(ch��n)�؈D�������Е���������С��T����a(ch��n)����ӛ��һ����ʮһ�������^(q��)��D־��һ�ٶ�ʮ�ž������T�݈D��(j��ng)����һ�پ�������ӛע�������������Ƴ��������D��(j��ng)�����γɹ̶��ƶȣ�ǰ���ǡ����؈Dί�ݸ�������һ�죬�c�弮����ʡ��
������Ԫ�꣨780�꣩�Ժ�Ո�݈Dÿ����һ�������������һ�x�ͣ����ݿh�Є�(chu��ng)�켰ɽ�Ӹ��ƣ�����������֮�ޡ� ���@�����f�ġ��؈D�������݈D�����ڄe��ʷ���ﱻ�������D��(j��ng)��
���䌍(sh��)����(d��ng)�r(sh��)���^���؈D�������݈D�������D��(j��ng)������һ���£����Ǽ��е؈D�����������f�����硶̫ƽ���[����������ꖵ؈D�������L���D���������݈D�������Gɽ�D����������D�����������D�������_�݈D���ȣ���H�������f�����؈D�������y�Ա���������ˡ��҂��x��ʷ���r(sh��)�����Կ������˵ġ��D��(j��ng)������Ԫ��С����������D��(j��ng)��
����𡶲轛(j��ng)���������С�����D��(j��ng)���������ΈD��(j��ng)��������ꎈD��(j��ng)����������D��(j��ng)�����ػ��z�����С�ɳ�݈D��(j��ng)���������݈D��(j��ng)������ɳ�ݶ������D��(j��ng)���������n����������Ѧ�ܡ��_�[�����С����ܡ��R����Ԋ��Ҳ�ᵽ���D��(j��ng)��
����̫ƽ���[����䛵ġ��D��(j��ng)�����_(d��)��ʮ�˷N���^�ֶ������ƕr(sh��)�ڵģ��@Щ���D��(j��ng)��Ҳ���������YԴ�Ľ�ጡ�ֵ��ע����ǣ��@Щ�I(y��)�������˵ġ��D��(j��ng)������Щ�����YԴ�Ľ�ጣ�ֱ�Ӟ顶Ԫ�Ϳ��h־�����^�У�Ո�������2��11�Č��գ�
��2��11 ��Ԫ�Ϳ��h־�������YԴ��ጵā�Դ
| ���� |
�D ��(j��ng) |
Ԫ�Ϳ��h־ |
| ��ɽ |
������^(q��)��D־���ƣ���̫���M�ڣ���ĺ�ɽ����ɽҲ������̫ƽ���[���ز�һ0����ɽ�l������ |
��һ��������ɽ�h����ɽ��һ����ɽ���ڿh����ʮ������U(xi��n)�^��������֮˒������̫�M�ڣ���ĺ�ɽ����ɽ���� |
| ��ɽ |
������D��(j��ng)��Ի��ɽ�����ς�Իκ�r(sh��)��ɽȺ�I����Ȳ������L��ֱ����̖��Q���������^֮�ƹ��������^֮�����r(sh��)���\����ɽ�����Ԟ���������̫ƽ���[���ز�һ0����ɽ�l������ |
��һ��������ɽ�h������ɽ�ڿh���ϰ���hĩ��ɽȺ�I���w��Ȳ������L��ֱ����̖��Q���������^֮�ƹ��������^֮�����r(sh��)�����\���ˣ����Ԟ������� |
| ����ɽ |
������D��(j��ng)��Ի����ɽ�����������ɽ�����Ƽq���ȸ��ڴˣ������������̫ƽ���[���ز�һ0������ɽ�l������ |
��һ���l(w��i)����ꖿh��������ɽ���ڿh������ʮ������Լq���ȸ��ڴˡ��� |
| ����ɽ |
������D��(j��ng)��Ի��ɽ�������Σ���������ɽ������Σ�^��ɽ��ж�Ȫ����κ��s�y�����ձ�����ɽ��������֮������̫ƽ���[���ز�һ0������ɽ�l������ |
��һ�ߺ��ݫ@¹�h������ɽ����������ɽ������κ��s֮�y��������ɽ���ٶ��������Ԟ������� |
| ��ɽ |
����κ���D��(j��ng)��Ի����ɽ����Ҳ�����^֮��ɽ�����h�ɵەr(sh��)�ӛQ��̣��w�ڴ��\(y��n)�������ӣ��H�ܮ�(d��ng)�r(sh��)���ģ����^֮��ɽ������̫ƽ���[���ز����ˡ���ܤ�l������ |
��һ��κ���F�l(xi��ng)�h�������ߣ�������ɽ���ڿh������ɵەr(sh��)�ӛQ��̣��ӵ�ʹ��������ļ����֮���w�\(y��n)������֮̎������ܮ�(d��ng)���飬���^֮��ɽ���� |
| �R�mɽ |
������ꖈD��(j��ng)��Ի���R�mɽ�ڿh����ʮ���ɽ�϶��аײݣ��b����������˺���R���R�m������̫ƽ���[���ز��š��R�mɽ�l���� |
�����`���`��h���R�mɽ���ڿh����ʮ���ɽ�И�ľ��ף�������R�����˺����R�m���� |
���������������У������@���Կ������ஔ(d��ng)һ���֡�Ԫ�Ϳ��h־���ĵ����YԴ��ጁ�Դ�����ƕr(sh��)�ڵġ��D��(j��ng)�������ǣ���������ġ��D��(j��ng)���H�H��Ƭ��ֻ�Z���ʌ�(sh��)�H�ϡ�Ԫ�Ϳ��h־�����á��D��(j��ng)��֮̎�϶����@���ࡣ���@�����x���f����Ԫ�Ϳ��h־����������������@һ�������ݡ����������˱���������������ȫ�����؈D��(j��ng)�����ɵġ����Λr����Ԫ�Ϳ��h־������Ҳ��һ���D��(j��ng)�w�������������ԭ�����f����֔(j��n)�ϡ�Ԫ�Ϳ��h�D־�����������M�]�ҵ�������ʮ���(zh��n)������ʮ����ÿ�(zh��n)�ԈD��ƪ�ף����ڔ���֮ǰ����ֻ�ǣ�ÿ�(zh��n)ƪ�ĵ؈D�ڱ��κ�ȫ�����ˡ�
������(d��ng)Ȼ�������ƴ�����־���Ĵ�������������Ԫ�Ϳ��h־������ǧ̎�������˜YԴ��ጣ���(sh��)���^���˝hκ�ԁ������������@����Ă��y(t��ng)������
�����ƴ��Ժ�ݛ��֮�W(xu��)�õ����L��İl(f��)չ�������YԴ���Ҳ�ij��^��ǧ����ǧ����(j��ng)�v���^��ǧ����ǧ�����峯һ�S��ͻ��һ�f���P(gu��n)���ơ�Ԫ�Ϳ��h־���H����ʮ�������Ρ�̫ƽ���ӛ���EȻ�U(ku��)չ��һ�پ������Ρ�ݛ�ؼo(j��)�١��U(ku��)���ɰپ�����Ԫһ�y(t��ng)־�����Ƕ��_(d��)һǧ�����ϣ��Ď��^���u�r(ji��)��̫ƽ���ӛ���r(sh��)�f�����w����֮����ӛ�d���Ǖ���ʼԔ��
��־��Ҏ(gu��)ģ�ĔU(ku��)�����ă�(n��i)�݄ݱظ����S����ʣ������YԴ���Ҳ��Ȼ�E��������Ԫ�����������������M(f��i)����������������Ҏ(gu��)ģ�T��o��ġ�һ�y(t��ng)־�����e���峯���ޡ�һ�y(t��ng)־�������H��ȫ��ʡ�������h�������^(q��)�ط�־��(n��i)�ݵľ��A���������M(j��n)ȥ�����Ҳ����˸����ط������ψ�(b��o)�Ĵ��������Y��
����������YԴ��ጰl(f��)չ���峯�����^�f��(sh��)��(d��ng)Ȼ��������µ����ˡ�
���������YԴ���e�����ࡢ�I(l��ng)��ĔU(ku��)չ��Ҳ����ȡ�þ�l(f��)չ��ԭ��֮һ���|�h�_��(chu��ng)�ĵ����YԴ���֮�L(f��ng)����κ�x�ϱ����r(sh��)�õ��˰l(f��)�P(y��ng)��YԴ��ጵ�e����u���ࡢ��(n��i)�����U(ku��)������څ�����ƣ�֔(j��n)�б��f�����£�
��2��12�������YԴ���e�Ľy(t��ng)Ӌ(j��)
| �����W(xu��)�� �����(sh��)��e |
��(y��ng)ۿ |
��� |
ʢ��֮ |
�Ұ�� |
�R�S |
�B��Ԫ |
| ��ˮ���� |
25 |
7 |
�� |
8 |
4 |
70 |
| ��ɽ���� |
11 |
8 |
3 |
2 |
4 |
69 |
| ����� |
8 |
�� |
�� |
�� |
�� |
53 |
| ��(sh��)�ֵ��� |
2 |
2 |
�� |
3 |
�� |
44 |
| ֲ����� |
2 |
2 |
4 |
3 |
4 |
33 |
| ������ |
1 |
�� |
3 |
�� |
�� |
21 |
| ��(d��ng)����� |
�� |
1 |
�� |
3 |
1 |
19 |
| �V����� |
2 |
�� |
2 |
�� |
�� |
18 |
| �ɫ���� |
�� |
�� |
�� |
3 |
�� |
15 |
| �������� |
�� |
�� |
�� |
�� |
1 |
6 |
| ����������� |
13 |
3 |
�� |
11 |
1 |
131 |
| ����� |
49 |
2 |
1 |
2 |
9 |
105 |
| ʷ�E���� |
�� |
�� |
�� |
11 |
�� |
97 |
| ���Q���� |
9 |
�� |
�� |
�� |
�� |
74 |
| ������� |
�� |
3 |
3 |
8 |
�� |
63 |
| �~�x���� |
9 |
�� |
2 |
3 |
3 |
50 |
| �ʇ����� |
17 |
3 |
�� |
�� |
3 |
29 |
| ��Ԓ���f���� |
�� |
�� |
3 |
4 |
�� |
29 |
| �ٔ�(sh��)������� |
8 |
2 |
�� |
�� |
�� |
22 |
| ��Ը������� |
6 |
�� |
�� |
1 |
�� |
15 |
| ������� |
4 |
�� |
�� |
6 |
1 |
13 |
| �ZӞ���� |
�� |
�� |
�� |
�� |
�� |
13 |
| ��(f��)�ϡ��������������� |
�� |
�� |
�� |
�� |
3 |
12 |
| �֮����� |
�� |
�� |
�� |
3 |
�� |
�� |
| ���M���� |
2 |
�� |
�� |
1 |
�� |
6 |
| �� Ӌ(j��) |
168 |
33 |
21 |
72 |
34 |
1007 |
�������Ͻ�ֹ���ϱ�����ֹ�������YԴ��ጵ�e����25����Εr(sh��)����������̖������ȡ�ŕ����x�������Ԫ����������r(sh��)�����н�ͨ��������̖����������������˾�������µ�e��
�����c��ͬ�r(sh��)�������YԴ��ጵ��I(l��ng)��Ҳ�ڲ����?c��i)U(ku��)������60̎�����YԴ����59̎�����^(q��)�������鑪(y��ng)ۿ��ጜYԴ��168̎������Ҳ��150̎�����ǿ����h���������������x���꡶�h����ע�ҹP�µ�24̎�����YԴ����У����^(q��)������20̎�������x�Ժ����YԴ����ڱ������^(q��)����ռ����(sh��)��ͬ�r(sh��)�����I(l��ng)���ڲ����U(ku��)����[�������������������A������ӛ����������̫����ӛ�������Y������Ҫӛ������������䛵���־������象�����ע������ɽ����(j��ng)ע�����������ӂ�ע�������[���x���ص�ӛ������賡��Aꖇ�־����Ԭɽ�ɡ��˶�ɽ��ӛ����̽���ĽY(ji��)��ʹ�x�������YԴ��ጵ��I(l��ng)��U(ku��)��Ȫ���ϡ�ͤ�����l(xi��ng)��ԭ������ꀡ��ǡ�Ѩ���ޡ��ɡ������ء�ܩ���_(t��i)��ڣ���w���T������İ������ʢ��֮��ꑳΡ����ѡ��Ұ����Ŭ��ʹ�ϳ������YԴ����I(l��ng)���ڕx�����A(ch��)����?j��n)Uչ�������Y���r��Ϫ�������ڡ������X��ʯ�������ʵ���͡������ı�κ�B��Ԫ�ڡ�ˮ��(j��ng)ע���н����1052̎�����ĜYԴ�������^(q��)����֮�⣬�ں�������߀���������ӡ������^��������ˮ�ڡ��ٲ�����ɽ����߀�����X���塢�n���{�ȡ��r�¡���Ѩ�ߣ��Լ����龮Ȫ��������ɡ��P(gu��n)����·���ݿ��h�ǡ��l(xi��ng)����桢���^�������m����w���@Է��Ĺ�ȵ����ĜYԴ����(sh��)�����N��࣬���B��Ԫ��ǰ�κε����������o���ġ������YԴ����I(l��ng)��ĔU(ku��)���o�Ɇ�����չ�˵����YԴ��ጵĔ�(sh��)����
�������^�������Ժ�ĵ����YԴ��ጲ���hκ�r(sh��)���ǘ��Խ�����^(q��)�����ĜYԴ����������ɽ�������ĜYԴ���ռ�����L(f��ng)���ɱ�2��7��֪��������һ�y(t��ng)־���㽭ʡ���֣��H��ɽ����һ�Tӛ�d�ĵ�����1393̎����ռ���d��������(sh��)��2291̎����60��8������ɽ�����T�����ĜYԴ��ጣ�369̎������ռ�˵����YԴ��ጿ���(sh��)��451̎����81��8�����ɱ�2��8��֪�����Αc����һ�y(t��ng)־����Ӹ��ݡ�ɽ����һ�T���d��������1314̎�����^���d��������(sh��)��2600̎���İ딵(sh��)����ጵ����YԴ����ɽ�����T��353̎���tռ���˿���(sh��)��546̎����64��7�����ı�2��9���Կ��������Αc����һ�y(t��ng)־��ӛ�d���㽭ʡ3810̎�������H��ɽ����һ�T����2027̎��ռһ�����ϣ�ɽ�������ĜYԴ��ጣ�619̎��ռ�˵����YԴ��ጿ���(sh��)��964̎����64��2��������ʡ���mδ�ض����_(d��)���@��(g��)����������(y��ng)�c�㽭ʡ��r��ȥ���h(yu��n)����(g��)�eʡ��߀�п��ܸ߳��@��(g��)������������֮���Ї��v�������YԴ��ጵ����c(di��n)�����ɝhκ�r(sh��)��ע�ؽ�����^(q��)�����ā�v����ȫ�D(zhu��n)�Ƶ�����r(sh��)���Խ��ɽ�������ĜYԴ���������^(q��)���������ģ���������ɽ��������(sh��)��Ҫ������ö࣬�����YԴ��ጵ����������^(q��)������u�D(zhu��n)�Ƶ�ɽ�����������ǚv�������YԴ��ጵ���ȡ�ó��m(x��)����(w��n)���l(f��)չ����Ҫԭ��
�������⣬�����YԴ��ጔ�(sh��)���ڵ�������(sh��)����ռ�ٷֱȣ��ɷQ֮�顰����ʡ�������u��ߣ�Ҳ�ǵ����YԴ��ጵ��l(f��)չ��ԭ��͘�(bi��o)־֮һ����̡��h��������־����ጵ����YԴ60̎��ռ���h��������־������4500̎��1��3������(y��ng)ۿ�����h��������־�������ĜYԴ�����152̎��ռ���h��������־������4500̎��3��4�����Ȱ�̷���һ���ࡣ�B��Ԫ��ˮ��(j��ng)ע����1052̎�������˜YԴ��ጣ�ռȫע1��5�f̎������6��7�����ȑ�(y��ng)ۿ��������һ���������Ԫ�Ϳ��h־����931̎�������˜YԴ��ጣ�ռ���dȫ������4800̎��19��4�����@��(g��)�������B��Ԫ�Č������������㽭ʡ�����ġ�����һ�y(t��ng)־������ʞ�19��7�������w�c��Ԫ�Ϳ��h־����ƽ�����Αc����һ�y(t��ng)־����Ӹ��ݵ�ƽ���������21��0�����㽭ʡ���ֵ��������25��3�����@����ζ��ԓ�����d�ĵ���ƽ��ÿ�����傀(g��)��(d��ng)�б���һ̎�YԴ��ጡ��@��(g��)�����mȻ�����ϵ����YԴ��ጵČ��T���������h������c����h��������քe��89.1%��85.3%�������ڷnj��T�����Єt������һָ�ġ��@Ҳ�������˂������ʲô������һ�y(t��ng)־�����@����ă�(n��i)���܉�ͻ��һ�f���P(gu��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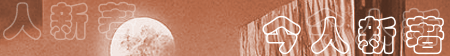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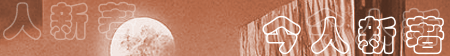
web@guoxue.com
![]() 010-68900123
010-68900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