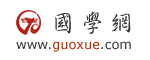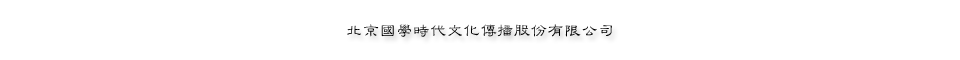第一節 春秋至兩漢:圍棋逐漸普及
圍棋誕生之后,直到春秋時代(公元前770~前476),一直未有確切的文字記載,這一段時間圍棋發展和流行的情況,我們不得而知。值得欣慰的是,從后人的一些記載以及民族學和民俗學的一些資料中,可以大略地勾畫出一個輪廓。
圍棋在古代除了娛樂競技之外,還有一個十分重要的功用,即“一枰之間,方罫之內,勝負視乎多寡,所以商度而計較者。”(焦循《孟子正義》)也就是說,下圍棋可以培養一定的算術知識和計算能力,有發蒙益智的特殊功用。
張華《博物志》“或云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圍棋以教之”的說法,以及《孟子·告子》“今夫弈之為數,小數也”的觀念,分別從正面和側面證明古人是很重視圍棋的這種功用的。數即算術,在周代是六藝之一。《周禮·地官·大司徒》載:“六藝:禮、樂、射、御、書、數。”這六藝是周王室及貴族子弟的必修課程,事關德行教養,意義非同小可。《玄玄棋經》禮卷歐陽玄序說:“古者人生八歲入小學,比及弱冠而禮、樂、射、御、書、數六藝之事偏習矣。他日因射之余意為投壺,且寓禮焉,因數之余意為弈,且寓智焉。”晏天章也說:“弈之為數,即六藝之數也。”可見古人在圍棋與數和圍棋與六藝關系上的看法,是相當一致的。20世紀初,日本學者青木文曾旅居西藏學習喇嘛教義。他在參觀為未來的僧官和俗官而建立的貴族子弟學校時發現,那里的學生就是靠藏棋——一種與圍棋極其相似的棋藝游戲,用擺放棋子的方法來學習和練習算術的。我們有理由相信,這些文字資料和民族民俗學的資料是在告訴我們,圍棋正式誕生后,其娛樂性、趣味性和競技性還沒有被人們很好地認識時,它的流傳相當程度上是有賴于它的教化益智的功用,而且流行范圍較窄,主要是在王室和貴族子弟中。其流傳方式,除自學外,至少在西周時,還有設課教習的可能。平王東遷以后,周王室逐漸衰微,禮崩樂壞。緊接著的春秋、戰國(公元前475—前221)時期,諸侯爭霸,列國稱雄,戰爭頻仍;社會生產工具進一步改進,出現了牛耕和鐵器,生產力得到更快的發展,社會生活水平得到提高,開始了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的過渡。在這個時期中,人們的思想意識也發生著劇烈的變動,漸趨活躍,最后造成了戰國時期諸子之學百家爭鳴的局面。這樣的社會環境,促使圍棋跳出宮廷娛樂和教化益智的狹小范圍,開始流傳到民間,并逐漸傳布開去。
到春秋時期,圍棋在諸侯士大夫中已流行得比較廣泛了。《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載:“衛獻公自夷儀使與寧喜言,寧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曰:‘嗚呼……今寧子視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弈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這是歷史上第一次可靠的涉及圍棋的記載,時間是公元前548年。人們在談話中使用比喻,都是選擇互相之間比較熟悉的事物作喻材,這樣才能使自己要表達的意思更為形象,更為明白,對方也才能準確無誤地領會。大叔文子用圍棋作比喻絕非偶然,說明在衛國的宮廷和士大夫中,圍棋已有相當程度的開展,是人們非常熟悉的事物。衛國只是當時十多個諸侯國之一,地處當今河南濮陽一帶。而這十多個諸侯國互相之間的聯系,以及與周王室的聯系都比較密切。這說明圍棋在各國開展流行的程度可能有所不同,但至少是都有所開展了。
“舉棋不定,不勝其耦”,實際上是一種早期的樸素的圍棋理論,具有基本的指導意義。它總結前人下棋積累的經驗,概括了一個制勝之道:下圍棋時,每落一子,必須深思熟慮而又要當機立斷。若猶豫不決,拿不定主意,就戰勝不了對方。盡管在今天看來,這只是一個十分淺顯的道理,可它卻是當時人們對數百年圍棋經驗的精辟總結。從此后它成了棋手時刻必須注意的警句格言,也成了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廣泛應用的一句成語。
隨著圍棋在社會上特別是社會上層人士中的逐漸流行,它與人們的文化娛樂生活的聯系也越來越緊密。但任何事物都有其兩面性,圍棋也不例外。一方面它可以開拓人的思維,培養計算能力、判斷能力和敏捷的反應,帶來無窮的趣味和愉悅;另一方面它又因耗時費日影響人的其他活動,或者使人沉迷其中難以自拔。因此,在這一時期開始出現了對圍棋褒貶不一的議論。《論語·陽貨》有這樣一段話: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禮”,是“仁”,而要達到這種境地,必須學“道”。他上面這番話就是基于這種思想向弟子們講的,意思是如果人飽食終日,于學“道”無所用心,則很難安排自己,必然要生淫欲以打發日子。不是有博和弈一類的游戲嗎?如果從事這些游戲,還勝過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而生淫欲。在他看來,博和下圍棋當然不能和學“道”相提并論,但也不是什么大逆不道的,如果能從事博和圍棋,就會得到一定的快樂和滿足,阻止淫欲邪念的萌生。他的觀點和傾向性很明確,與《左傳》中大叔文子的話毫無褒貶之意有所不同。
還有一部叫作《關尹子》的書,傳為周人尹喜所作,原書已佚,今本是宋人所輯,書中有不少談及圍棋的地方,如“道雖絲紛,事則棋布”,“兩人弈,相遇則勝負見”等。其中還有這樣的話:“習射、習御、習琴、習弈,終無一事可以息得者。”他是為了說明什么事都要堅持不懈才能達到目的,舉學習射、御、琴、棋為例,指出這些技藝沒有哪一樣是不經過長期學習就可以學到手的。宋人輯佚此書不知是否有可靠的依據,但從所舉的事看,都是周代六藝之一,可能也并非完全杜撰。這段文字本身雖無褒貶之意,但以圍棋直接代表“數”藝,而且與其他幾藝相提并論,其褒揚的意思就再明顯不過了。戰國時齊處士尹文撰有《尹文子》一書,原書已佚,今本是東漢人偽托,其中講道:“以智力求者,譬如弈棋,進退取與,攻劫收放,在我者也。”認為圍棋是智者的游戲,褒揚之意更為明確。
戰國時期,出現了對圍棋貶斥得十分尖銳的言論。《孟子·離婁下》載:“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肢,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弈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善事父母為孝,古人對孝極為重視,被視為人倫之大節,孔子就有“弟子入則孝,出則悌(敬兄)”(《論語·學而》)的訓導。將圍棋列為五不孝的行為之一,足見世上一些人對圍棋已到了深惡痛絕的地步。孟子是鄒(今山東鄒縣東南)人,曾游歷齊、宋、魏等北方諸國。五不孝的說法既然是“世俗所謂”,足見在北方一些國家的社會下層中,圍棋已經流行開來了,而且以錢財作注賭棋的風氣也開始出現,以至于有的人沉迷圍棋而不顧奉養父母。
隨著圍棋的流行和發展,著名的圍棋高手開始出現,第一位見于文字記載的圍棋高手,是戰國時齊國的弈秋。《孟子·告子上》載:
今夫弈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為聽;一人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非然也。
古代有許多因技藝杰出而傳名于世的人,都是以其技藝加稱其名。弈秋便是這樣。因為他名秋,圍棋下得好,在齊國冠絕一時,所以稱他“弈秋”。至于他的本姓則無人知曉了。中國古代沒有專業圍棋和業余圍棋的概念,也沒有專業棋手和業余棋手的概念。我們今天只有以是否靠以棋為生來予以辨別。從《孟子》的話看,弈秋是在課業授徒,而且聲名甚顯。這表明戰國時期,在社會生活中圍棋已出現了專業化的趨勢,而弈秋就是第一個留下姓名的專業棋手。這件事的出現,具有深遠的意義,它標志著圍棋已開始成為人們社會生活的一個重要內容,而棋藝精湛的高手必然會得到人們承認和一定程度的尊重。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滅齊,統一了中國。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建立起一個疆域空前的中央集權制的封建大帝國。秦王朝的建立,對社會的統一和社會生產的發展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它在中國文化的發展上,卻造成了空前的大劫難。秦始皇為保證嬴氏江山得以萬代相傳,防止諸生以其所學惑亂民眾,采納丞相李斯的建議,實施嚴刑峻法和文化禁錮政策。規定除秦記和醫藥、卜筮、種樹的書之外,其它如《詩經》、《尚書》等典籍,以及諸子及百家之書統統都得燒掉;世人有相對聚語議論這些書的,處以死刑,而借用這些書以古非今的誅滅九族。圍棋這時在大多數人眼中只是一種微藝末技,也沒有出現專門的棋藝著作和棋藝理論著作,但因為它同天文、數學、陰陽、軍事知識有關,經戰國之后又很容易同縱橫家學說聯系在一起,再加上圍棋至少是兩人相聚,若是下注賭棋還會招來更多的人,所以雖然沒有明令查禁,但人們為免招是非,也不敢下圍棋了。另外,秦王朝設博士官職掌官學,嚴禁私學,因此也不可能有人課業授徒教授圍棋。在這樣的環境下。民間的文化娛樂根本無法談起。本來就缺乏理論、還不夠發達的圍棋好似雪上加霜,完全喪失了活力,除能在極小的范圍內,如宮廷內部的一些人中勉強生存外,幾乎絕跡了。
秦始皇的萬世之夢,不過兩世就被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徹底打破了。漢王朝建立后,采取休養生息政策,社會生產力迅速恢復并快速地發展起來。文化上,較靈活、開放,在儒家文化空前發展的同時,道家文化也得到發展,佛教文化、西域文化等外來文化也開始傳入和被消化吸收。這樣,在西漢(公元前206—公元25)二百年間及東漢(公元25—220)的大部分時間里,文學、史學、音樂、藝術和自然科學等都非常繁榮發達,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頁。
良好的文化藝術環境,給圍棋帶來了勃勃生機,圍棋出現了復興局面,并有了新的發展。
兩漢時期,宮廷中盛行圍棋,許多帝王都愛好圍棋。西漢的創立者漢高祖劉邦,就是著名的圍棋愛好者。晉代葛洪《西京雜記》卷三:“戚夫人侍高帝。……八月四日,出雕房北戶,竹下圍棋,勝者終年有福,負者終年疾病。取絲縷就北辰星求長命,乃免。”他們二人圍棋行樂竟形成宮中習俗,而且出現什么勝者終年有福,負者終年疾病,要取絲縷拜求北辰星才能免疾的神秘傳說,可見圍棋影響之大。戚夫人多才多藝,擅長鼓瑟擊筑,曾擊筑伴和劉邦唱《大風歌》,又會弦管歌舞,還會圍棋,自然深得劉邦寵愛。為此,劉邦幾次想廢太子(呂后所生),立戚夫人之子趙王如意為太子,后因呂后阻撓,張良設計請來四皓輔佐呂后之子而未成。呂后對此深深忌恨,劉邦死后,便將戚夫人和趙王如意害死了。戚夫人死后,她身邊的宮女都被逐出宮。這些宮女在宮中或耳濡目染,或身體力行,自然都會下圍棋,出宮之后,將棋藝帶至民間,對圍棋普及倒不無作用。漢宣帝劉詢也很喜歡下圍棋,而且水平還不低。據《漢書·宣帝紀》所載,他“師受《詩》、《論語》、《孝經》,操行節儉,慈仁愛人”,與劉邦不同,是一個知書識禮的天子。他未作皇帝前,同杜陵人陳遂十分要好,陳遂也是一個圍棋愛好者,二人經常在一起下棋。陳遂棋藝略遜一籌,常常輸棋,欠劉詢不少棋注。劉詢當皇帝后,準備擢用陳遂為太原太守,曾賜璽書一封:“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厚,可以償博進矣。妻君寧時在旁,知狀。”意思是太原太守官職不小,奉祿豐厚,這下可以償還你當年輸的棋注了。你妻子當時在旁邊,那些事她完全清楚,可以作證人。結果陳遂深知為臣之道、今昔之別,不敢領此厚愛,婉言辭謝了。陳遂雖未受官,但此事亦算是歷史上第一個圍棋賜官的例子。漢宣帝還常與王褒等放獵,縱情享樂,辭賦為歡,朝中多有非議,他便借孔夫子的話說:“‘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辭賦比之,尚有仁義風諭,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于倡優博弈遠矣。”(《漢書·王褒傳》)
除了皇帝外,在劉氏諸王中,愛好圍棋的也不少,如廣川王劉去、淮南王劉安即是代表。劉去通諸經,史稱“好文辭、方技、博弈、倡優。”劉安“為人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喜歡方士,也極好圍棋。他那著名的《淮南子》中,就常常提到圍棋。如“行一棋不足以見智,彈一弦不足以見悲”、“圍棋擊劍,亦皆自然”等,說明他是深諳棋理的。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帝王中的圍棋之風在文人士大夫中也得到響應。前面提到的陳遂,即是一例。到東漢時期,愛好圍棋的文人士大夫就更多了。像桓譚、班固、馬融、李尤和黃憲等,都是著名的愛好者。
桓譚(公元前?—公元56),字君山,沛郡(今安徽濉縣)人。博學多通,遍習五經,官至議郎給事中,是著名的經學家和哲學家。他著有《新論》,其中涉及到一些圍棋的基本理論和實戰理論,認為圍棋與兵法相類;更視帝不懂兵法猶如不懂棋,結果使別人死棋得生、自己功敗垂成。
班固(32—92)。字孟堅,扶風安陵(今陜西咸陽)人,先任蘭臺令史,后轉遷為郎,典校秘書,是著名的史學家和文學家。他喜愛圍棋,對圍棋的深奧道理和豐富的文化內容作了嚴肅的探討,曾撰《弈旨》一篇,第一次對圍棋作了全面的論述,對圍棋的特點多有發掘,是一篇劃時代的圍棋理論文章。
李尤(約55—135后),字伯仁,廣漢雒(今四川廣漢)人,累官蘭臺令史、諫議大夫、樂安相,是當代的辭賦家,被譽為有司馬相如、揚雄之風。他有一首《圍棋銘》:“詩人幽憶,感物則思。志之空閑,玩弄游意。局為憲矩,棋法陰陽。道為經緯,方錯列張。”精煉地概括了圍棋的特點和陶冶性情的作用,嗜棋之情溢于言表。
馬融(79—166),字季長,扶風茂陵(今陜西興平東北)人,官至南郡太守,著名的經學大家,生徒數以千計。他十分愛好圍棋,認為圍棋源于兵法,作有《圍棋賦》,抒發自己一介書生在三尺之局的戰場上,縱橫馳騁的愉悅之情。
這時期,民間的圍棋也得到恢復和發展。揚雄《方言》對地方語言研究頗深,所謂圍棋“自關而東,齊魯之間,皆謂之弈”,本身就說明了中原地區民間圍棋活動流行的程度。另據葛洪《西京雜記》卷二載:“杜陵杜夫子善弈棋,為天下第一。人或譏其費日,夫子曰:‘精其理者,足以大裨圣教。’”杜陵在今西安南,屬京兆尹。杜夫子名不詳,既被稱為夫子,或因學識過人,或因棋藝超群,沒有頻繁的交流比賽,他是不可能得到“天下第一”這樣的稱號的。這至少說明,長安附近及其周圍地區的圍棋活動是相當盛行的。由于古代棋手的地位很低,圍棋總的來說還沒有得到朝廷的重視,因而棋手的姓名是很難見諸史乘的。一個“天下第一”的著名棋手的事跡都僅有幾十字的記載,其他棋手就可想而知了。那些被湮沒了姓名的棋手,雖然不能傳名后世,但他們為兩漢時期圍棋復興所做出的貢獻,是不容抹殺的。
兩漢圍棋的發展推動了圍棋的理論研究,也促進了棋譜的收集和整理。棋譜的記錄留存起源于何時,尚難以考定,但兩漢時期是肯定已經比較流行了。一些優秀的對局譜,經收集整理后成為棋家珍藏之物,對推動圍棋水平的提高,起了巨大的作用。至少是從兩漢后收集整理棋譜便成了棋藝研究的重要方法,幾千年來一直為棋手所沿用。可惜的是,漢代棋譜現已無處可尋,唯從成書于北周的敦煌《棋經》的“漢圖一十三勢”一句話中,才知道他們在唐以前還廣為流傳,為棋手們所推崇。
從當時棋手和圍棋愛好者的籍貫和游歷看,圍棋活動在長江南北,即今天的河南、山東、陜西、河北、四川、江蘇、湖南等地區都開展起來。而且根據一些資料推斷,圍棋還可能流傳到了發羌、唐旄地區,即今天的西藏地區。西藏有一種藏棋,叫做“密芒”,意思是“多眼”,故又稱為“多眼戲”。它的制式和規則除個別地方外,與兩漢時期的圍棋極為相似。圍棋的歷史早于藏棋,完全有可能是兩漢時期或稍晚時候流傳到西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