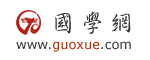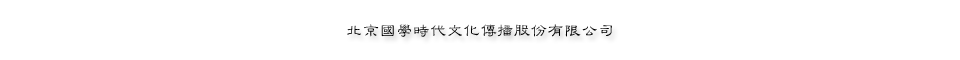第四章 宋代宰相的職權
諸葛憶兵
第四節 宰相代行用人權
在“人治”的封建社會,各級官吏的任命和使用的權力,關系到一個王朝的興亡盛衰。元祐年間,翰林學士梁燾說:“政事之本,在于用人”(《長編》卷468)。皇帝的中央集權,總是以控制用人權為主要目的之一。用人決策權是中央決策的最主要組成部分,所以,這里單獨討論。
宋代中央政府的用人權大概可以分為三個層次:皇帝冊授高級和要害部門官員、宰相除授朝廷次要官員、吏部差注全國基層官員。元祐初,呂陶奏章中說明三者之間的大致區分云:
自兩府而下至侍從官,悉稟圣旨,然后除授,此中書不敢專也;自卿監而下及已經進擢,或寄祿至中散大夫者,皆由堂除,此吏部不敢預也;自朝議大夫而下,受常調差遣者,皆歸吏部,此中書不可侵也。(《長編》卷370)
這三個層次用人權的劃分,也是言其大概,實際操作中并不能如此界線分明。但無論哪一個層次,宰相或唱主角、或唱配角,都參預其中,而且發揮越來越多的影響,作用越來越重要。以下分別討論。
1、皇帝控制用人權。
宋代君王汲取唐代君主失柄、用人權歸于下的歷史經驗教訓,試圖將用人權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臺諫也時常提醒皇帝注意用人權的有效利用,慶歷八年(1048)三月,御史中丞魚周詢對仁宗說:“臣愿陛下聽政之外,選材識之臣,獨對便殿,訪諸臣能否,曰某人宜何用,某人不足用,然后廣詢博采,參驗異同,俟其得實,則行進退。”(《長編》卷163)對此,皇帝有系列得力的措施。
① 高層或要害部門官員的任命。
皇帝的用人決策權,主要體現在高層官員的任命方面。唐代,“凡諸王及職事官正三品以上,若文武散官二品以上,及都督、都護、上州刺史之在京師者”,都由皇帝親自除授(《通典》卷15《選舉》)宋代承繼唐人做法,以制度的形式確定高層官員的任命必須由皇帝發布制書,《宋史》卷162《職官志》云:凡“拜宰相、樞密使、三公、三少,除開府儀同三司、節度使,加封,加檢校官,并用制。”此外,凡“執政、侍從、臺諫、給舍之選,與三衙、京尹之除,皆朝廷大綱所在,故其人必出人主之親擢,則權不下移”(《宋史》卷401《柴中行傳》)。皇帝的親自提拔和任用,稱為“特旨除授”,或稱“御筆除授”、“上批”、“中批”、“御批”、“內降”、“直筆”、“旨授”等等。皇帝的特旨用人,在宋代是很頻繁的,如二府宰輔的任命,經常出自皇帝獨裁,二府大臣的榮辱進退,與帝王的賞識與否休戚相關。嘉祐五年(1060)四月,樞密副使程戡罷,“宰臣進擬”繼任者名單,仁宗說:“朕欲用舊人”,因此任命孫抃(《長編》卷191)。徽宗即位,執政闕員,皇帝親自一一篩選進擬的名單,最后確定為韓忠彥、李清臣、黃履三人(《長編》520)。《老學庵筆記》卷9載:“王冀公自金陵召還,不降詔,止于茶藥合中賜御飛白‘王欽若’三字,而中使口傳密旨,冀公即上道,至國門,輔臣以下皆未知。政和中,蔡太師在錢塘,一日中使賜茶藥,亦于合中得大玉環,徑七寸,色如截肪。京拜賜,即治行。后二日,詔至,即日起發。”又,《朝野雜記》乙集卷8載云:
孝宗初政,命相多不以次。史(浩)文惠自宗正少卿再閱月而執政,又五閱月而為相,相四閱月而罷。洪(適)文惠自太常少卿九閱月而執政,又五閱月而相,相三閱月而罷。魏(杞)文節自宗正少卿期年而執政,又九閱月而相,相未一年而罷。
孝宗登基后亟欲有所作為,所以不次命相,稍不如意又匆匆更替,任用大臣,隨心所欲,將皇帝的用人權表現得淋漓盡致。孝宗任用二府大臣沈夏時,與宰相梁克家的一段討論,也充分說明了皇帝用人的主動權。孝宗賞識沈夏,問宰相梁克家說:“侍郎有過政府例否?”梁克家回答說:“陛下用人,何以例為?”孝宗因此特除沈夏為簽書樞密院事(詳見《癸辛雜識》別集下)。這一系列任命中,皇帝的旨意體現的十分明顯。
兩宋時期,“一代天子一代臣”的現象十分突出,新皇帝登基或親政,總是要大批更換二府和其它要害部門的大臣,以起用自己信賴或與自己政見相同的臣下。兩宋還沿襲唐代一條不成文傳統,即皇帝去世,以首相為山陵使,喪葬事畢,宰相便“堅請去位”,依例皆得新即位的皇帝同意。元豐末年神宗去世、哲宗登基,首相蔡確沒有依上述傳統行事,便成為政敵攻擊他的主要理由之一(詳見《長編》卷362)。這種傳統,事實上不過是為新即位的皇帝起用自己信賴的大臣提供一種便利。得新皇帝信賴的舊宰輔,也總是能以種種籍口留任。可以說,在兩宋多數時間里,帝王把握住高層或要害部門的用人決策權。
② 其他官員的任命。
皇帝精力有限,原則上不過問具體部門和地方官員的任命。然而,有時皇帝為了顯示自己的明察秋毫,或對某一任命特別感興趣,同樣可以插手其他各級官吏的任命或升遷,有時直接下達指示。這種出自“宸斷”的決策方式,并不算違制,被朝野所接受。開寶七年(974)二月,軍校史珪進讒言,誣陷權知德州梁夢升,太祖明察其奸,“曰‘夢升真清強吏也。’取所記紙召一黃門令赍付中書,曰:‘即以夢升為贊善大夫。’既行,又召還,曰:‘與左贊善大夫,仍知德州。’”(《長編》卷15)太祖的決斷,可以不必咨詢任何部門的意見。景德二年(1005)正月,真宗分別任命了定州、鎮州、大名府等十余名知州、知府,真宗錄任命名單付中書,中書宰相立即要求施行(《長編》卷59)。天圣四年(1026)九月,以“王博文為兵部員外郎、戶部副使。時三司闕官,中書議除人”,仁宗以為“博文饋軍有勞,此可用也”,故得任命。
為了在用人權上取得主動地位,使人盡其才,宋代帝王花費了更多的心思,注意臣下的賢愚、才干等。《涑水記聞》卷1載:“太祖聰明豁達,知人善任使,擢用英俊,不問資級。察內外官有一材一行可取者,密為籍記之。每一官缺,則披籍選用焉。”太宗平日發現有才干者,總是“記其名于御屏”(《長編》卷34),用人之時就可以發表自己的意見。如淳化四年(993)七月,太宗“御筆飛白書(向)敏中及虞部郎中鄄城張詠姓名付宰相,曰:‘此二人,名臣也,朕將用之。’左右因稱其材。”(同前)太宗曾對臣下說:“朕每日后殿自選循吏,候選及三二百人,天下郡縣,何愁不治?迂懦因循之人,并與諸州副使、分司西京。或且給俸祿,不與差遣,然此輩又如何消國家祿食也?”(《長編》卷36)太宗不但掌握著高級官員的任命權,甚至過問地方下層官吏的任命,在兩宋帝王中是一個十分極端的例子。
其他帝王作為,如《長編》卷96載:
(呂)夷簡治開封,嚴辦有聲,上(真宗)識其姓名于屏風,意將大用之也。
《長編》卷117載:
太子中允、知淮陽軍梁適,亦上疏論朱全忠乃唐之賊臣,今錄其后,不可以為勸。上(仁宗)是其言,記適姓名于禁中,尋召為審刑院詳議官。
《朝野雜記》甲集卷5載:
紹興初,樓仲輝(炤)資政有左史請命:“從官舉可為監司者,令中書籍記姓名,遇闕除授。”上從之。已而,謂輔臣曰:“朕亦當書之屏風,以時揭貼。其不任職而無他過者,以自陳公觀與之。”乾道初,孝宗新創選德屏于御座后,作金漆大屏,分畫諸道,各列監司、郡守為兩行,以黃簽標識居官者職位、姓名,其背為《華夷圖》云。
③ 皇帝用人決策時與宰輔的合作。
在用人的決策方面,宋代許多帝王與宰輔之間有較好的協調合作關系。皇帝重視宰輔的人選推薦,宰輔則在用人問題上,尤其是在高層官員的任用方面,特別尊重皇帝的意見,推尊皇帝的最終決策權。真宗朝宰相王旦得病久不愈,真宗問天下事可付誰,王旦答云:“知臣莫如君,惟明主擇之。”(《長編》卷84)英宗時,宰相韓琦、曾公亮欲用歐陽修為樞密使,歐陽修以為不可,說:“二三大臣自相位置,何以示天下?”韓、曾服其言。(《長編》卷205)《湘山野錄》卷中記載著這樣一段政壇、文壇佳話:
呂申公(夷簡)累乞致仕,仁宗眷倚之重,久之不允。他日,復叩于便座,上度其志不可奪,因詢之曰:“卿果退,當何人可代?”申公曰:“知臣莫若君,陛下當自擇。”仁宗堅之,申公遂引陳文惠堯佐,曰:“陛下欲用英俊經綸之臣,則臣所不知。必欲圖任老成,鎮靜百度,周知天下之良苦,無如陳某者。”仁宗深然之,遂大拜。后文惠公極懷薦引之德,無以形其意,因撰《燕詞》一闋,攜觴相館,使人歌之曰:“二社良辰,千秋庭院,翩翩又見新來燕。鳳凰巢穩許為鄰,瀟湘煙暝來何晚? 亂入紅樓,低飛綠岸,畫梁時拂歌塵散。為誰歸去為誰來,主人恩重朱簾卷。”申公聽歌,醉笑曰:“自恨卷簾人已老。”文惠應曰;“莫愁調鼎事無功。”
這里,君臣之間在用人問題上有很好的合作,后任宰輔則深感前任薦引之德。可以這樣說,在兩宋絕大多數時間內,皇帝都沒有失去用人的主動權。
帝王在理論上、同時也是在實際中掌握著高級和要害部門官員的任用權,在這一方面,宰輔享有參議權,提出候選人名單供皇帝抉擇,或對皇帝決定的人選提供個人意見,皇帝也常常主動征詢宰輔的看法。皇帝征詢宰輔的意見之做法,大約也分成三種,一是事先要求宰輔推薦合適人選,以供選擇,如:
(太宗淳化五年十一月)詔(呂)蒙正以下至知制誥,各舉有器業可任以事者一人。(《長編》卷36)
(真宗天禧元年六月)上封者言:“邊鄙雖寧,武備難闕。望令群臣各舉將帥之才。如邊上未有員闕,即且于內地州軍差遣,緩急足副推擇。”乃詔王旦等各舉所知三兩人,具名以進。已而,樞密院又請令宰相以下,各于京朝、幕職等官及閤門祇候已上,舉堪任將帥者各三兩人。(《長編》卷90)
(哲宗元祐二年七月)手詔付呂公著等,令于文臣中擇有才行風力、兼知邊事、堪大用者三五人,具姓名親書實封進入。(《長編》卷403)
二是拿自己的任命意見去咨詢宰輔,以彌補缺失。《長編》卷59載真宗景德二年(1005)正月事云:
上以河北守臣宜得武干善鎮靜者,乙卯,命西上閤門使馬知節知定州,孫全照知鎮州,刑部侍郎趙昌言知大名府,給事中馮起知澶州,洺州團練使上官正知貝州,莫州團練使楊延朗知保州,滁州刺使張禹珪知石州,崇儀使張利涉知滄州,供備庫使趙繼昇知邢州,西上閤門副使李允則知雄州,供備庫副使趙彬知霸州。上親錄其姓名付中書,且曰:“朕如此裁處,當否?卿等供詳之。”畢士安曰:“陛下所擇,皆才適于用,望付外施行。”
三是否定宰輔們的推薦,提出自己的人選;或在宰輔議論用人時,直接提出自己的意見。《長編》卷105載:
(仁宗天圣五年正月)命樞密直學士、禮部侍郎劉筠權知貢舉。中書初議擇官,上曰:“劉筠可用也。”筠時在穎川,遂驛召之。
在上述的用人過程中,中書或樞密院僅僅有向皇帝推薦合適人選的職責,決策權卻掌握在皇帝手中。二府推薦的人選,如不合皇帝之意,一般說來要依照皇帝的旨意辦理。如:
(康定元年九月)己未,右正言、知制誥葉清臣為龍圖閣直學士、起居舍人、權三司使事。中書進擬三司使,清臣不在選,帝(仁宗)曰:“葉清臣才可用。”遂以命之。(《長編》卷128)
紹興初,劉大中以監察御史宣諭諸路回,宰臣以其稱職,擬除殿中侍御史。太上皇帝(高宗)云:“且令除秘書少監。”宰臣啟其所以,太上曰:“大中所至多興獄,尚有未決者。一除言路,外方觀望,恐累及無辜。”(《揮麈前錄》卷1)
反過來,帝王決意要重用的人選,臣下的反對是無濟于事的,哪怕是舉朝反對。慶歷四年(1044)九月,仁宗欲選拔陳執中為參知政事,《長編》卷152載:
(仁宗)謂宰相曰:“執中在青州久,可召之。”遂召執中參知政事。于是諫官蔡襄、孫甫等爭言執中剛愎不學,若任以政,天下不幸。上不聽。諫官爭不止,上乃命中使赍敕告即青州賜之,且諭意曰:“朕用卿,舉朝皆以為不可,朕不惑人言,力用卿爾。”明日,諫官上殿,上作色迎謂之曰:“豈非論陳執中耶?朕已召之矣。”諫官乃不敢復言。
2、宰相的用人權。
宋代皇帝雖然握有用人決策權,但是,無論以何種方式貫徹皇帝的意志,都必須通過中書宰相,包括宮廷賓妃的冊命。通例,“凡制詞既授閤門宣讀,學士院受而書之,送中書結三省銜,官告院用印,然后進內。”(《長編》卷165)皇帝的接觸面、視野、精力都是有限的,在用人問題上許多時候只是起象征性的決策作用,主要依賴臣下的推薦或決斷。二府宰輔是皇帝身邊的輔佐大臣,是皇帝依賴的主要對象,所以,宋代帝王往往是將用人權委諸宰輔,如仁宗要求“中書門下其采端實之士,明進諸朝”(《長編》卷192)。宋代任選官員的基本做法是“中書日進呈差除,退即批圣旨,而同列押字”(《春明退朝錄》卷下)。即中書草擬任選方案,得皇帝同意,為制詞頒布。宋初,太祖就強調“京朝官將命出入,及受代歸闕者”,由中書派人“考校勞績,及銓量材器,候有闕,中書類能以授之”(《宋朝事實》卷9《官職》)。中書用人具體表現為“堂除”、“部注”兩種方式。“堂除”就是政事堂直接的除授;“部注”則是通過人事主管部門吏部經辦的除授,同樣置于宰輔的領導之下。其中以“堂除”的方式更直接地體現了宰輔的用人意志。
① “堂除”范圍的膨脹。
“堂除”制度由來已久,“堂除之說,天子托大臣以選擇人才,無資格之拘,無關鍵之限”(《古今源流至論》別集卷6《堂除》)。唐代中央政府次一級的官員就由“宰相商議奏可,而除拜之”。宋代“堂除”制度屢有變化,一種總的趨勢是:隨著相權的強化,宰相將越來越多的用人權攬到自己手中,“堂除”的范圍也越來越開闊。
北宋初年,兵荒馬亂,制度不健全,“除授皆由中書,不復由吏部”(《長編》卷22),用人主要是以“堂除”方式。太平興國八年(983)八月,太宗特別詔曰:“自今應臨軒所遣官吏,并送中書門下,考其履歷,審取進止。”(《長編》卷24)如此可以比較靈活主動,易于應付各種復雜緊急情況。太平興國末年以后,朝廷行政管理逐漸正規化,中央先后設立差遣院、考課院、審官院等,掌握不同層次官員的任選,宰相的人事權受到一定限制。但是,皇帝還是經常將更多的信任給予宰輔,對關鍵地區地方長官的任命,要求中書直接過問。嘉祐五年(1060)九月詔曰:“齊、登、密、華、邠、耀、鄜、絳、潤、婺、海、宿、饒、歙、吉、建、汀、潮凡十八州,并繁劇之地,自今令中書選人為知州”(《長編》卷192)。神宗年間,皇帝企圖更多地將權力攬歸己有,對“堂除”的限制逐漸嚴厲,甚至有廢除的想法和詔令(詳說見后)。然而“堂除”作為一項制度,始終沒有真正退出歷史舞臺。哲宗年幼即位,宰相在中央機構中的作用得以加強,“堂除”侵占吏部闕額的事情經常發生,對此朝廷中爭論不斷。元祐元年(1086)三月,“詔自今堂差不得沖吏部已注授人”(《長編》卷371),對“堂除”加以限制,不過奏效甚微。同年六月,又“詔:新復州縣知州、軍并堂除選,余吏部選。”(《長編》卷379)欲對“堂除”范圍做一些劃分。元祐二年(1087)八月,詔令大臣討論確定制度,使堂闕和部闕“兩不相妨”,結果是將104個知州闕歸堂除,98個知州闕歸吏部,堂除知州數比仁宗時增加了近一倍。這種劃分并不能遏制堂除膨脹的勢頭,元祐三年(1088),右正言劉安世說:“近來堂除差遣多取吏部之闕”(《盡言集》卷11《論堂除之弊》),同年十一月只得再度劃分堂除和部注的范圍,三省言:
在京堂除差遣,累有增改,尚書吏部闕少官多。今裁定:門下、中書省正言,尚書省左右司、六曹郎中,御史臺監察御史,秘書省正字,館職校理以上,寺監長、貳、丞,太常博士,太學博士、正、錄,侍講、說書,開封推判官、府司錄,開封府祥符、咸平、尉氏、陳留、襄邑、雍丘知縣,登聞鼓院、檢院,王府翊善、侍讀、侍講、記室、小學教授,知大宗正丞事,諸王府講書、記室,睦親、廣親宅講書,左藏庫、三京留司御史臺、商稅院、進奏院,并中書省差。寺監主簿,太常寺太祝、奉禮,光祿寺太官令,元豐庫、牛羊司,京東排岸司,諸宮院教授,太康、東明、考城、長垣知縣,并吏部差。(《長編》卷417)。
太皇太后同意三省的詳細劃定。元祐六年(1091)六月又詔曰:“見今堂除闕內,單、利、耀、溫州知州,石州、霸州、順安軍通判,并送吏部差注。”(《長編》卷460)
元祐年間一次又一次地限制“堂除”的努力,正說明了“堂除”范圍的不斷膨脹。元祐臣僚的做法,為北宋末年以來權相濫用人事權開了先路。
哲宗以后,皇帝不斷發布各種詔令,限制堂除,卻沒有實際效果。到南宋紹興年間,堂除知州軍89處,吏部僅27處,甚至“京官知縣并堂除”(《中興圣政》卷9),此外,諸路監司的屬官、坑冶監官等也被收為堂闕。孝宗時以至“知州軍闕盡歸于堂,而吏部更無知州軍一闕以待孤寒資格之人”(韓元吉《南澗甲乙稿》卷9《集議繁冗虛偽弊事狀》)。南宋后期皆權相當政,用人如同囊中取物,更加隨心所欲。
② 宰輔以用人為己任。
皇帝在任用官員時對二府宰輔的依賴過多,就往往將用人權不知不覺地轉移到二府宰執的手中。在任用官員的問題上,無論是哪一層次的,皇帝主動發表意見的時候總是比較少見,經常性的是二府大臣做出推薦并決斷。然而,更多的時候,皇帝是有意將用人的決策權委之于宰輔,發揮相權的中樞調配作用,皇權只是做一種宏觀調控。大中祥符九年(1016)九月,中書請以盛度權知開封府,真宗回答說:“可更問王旦”,事后證明了咨詢的必要性,真宗評價說:“王旦銓量才品極當,必使人各得其所,此豈可不問也?”(《長編》卷88)熙寧年間,神宗特別信任宰相王安石,曾令參知政事馮京傳諭王安石說:“自今進用人,或不可于意,但極論。”(《長編》卷237)此時,皇權和相權是相輔相成的。從理論上到實質上,皇帝都沒有失去用人的決策權,在實際操作中,又是宰輔把握著用人決策權。皇權和相權,在宋代有著很好的協調合作關系。
宋代在任命高級官員時的一般程序如下:首先由二府進擬準備任用者的名單,以供皇帝決斷,得到皇帝最后首肯,中書依據所授予的詞頭,轉入起草詔書之類的第二步具體工作。如果二府進擬名單不合皇帝意,就需要做再三的修訂,以協調君臣的意見。例如,仁宗天圣元年(1023)八月,朝廷任命陜西轉運使,“先是,宰相連進數人,不稱旨。”最后,所擬的名單中有權開封府判官、侍御史俞獻卿,“上曰:‘此可矣。’即命獻卿往。”(《長編》卷101)《宋會要·職官》1之16言:“朝廷有除拜,中書吏赴院納詞頭;其大除拜,亦有宰相召舍人面受詞頭者。”中下層官員的任命,就更加簡化,不必征求皇帝意見,“凡所除授,先由大臣進擬,而后下于中書、門下兩省,臣僚無異論,則命詞省審授之。”(《宋會要·職官》1之48)在這一系列任命官員的運作過程中,中書宰相起著承上啟下的關鍵性作用。此外,中央和地方上各級官員的任用和升遷,也都必須經過二府審核這一道關卡。大中祥符三年(1010)四月,真宗詔曰:中央和地方官員才干“如實有可取,即送中書、樞密院,再加考核取裁”;或“先送中書、樞密院參詳,別與引見”(《長編》卷73)。天圣七年(1029)九月,“詔審官院,自今定差知州軍,令中書審視,若懦庸老疾不任事者,罷之”(《長編》卷108)。
這種“委任責成”的方式,也固定為制度,使宰相將進退官吏、選拔賢能視為自己份內之事。宰相呂蒙正對太宗說:“臣備位宰相,可以進退百官。”(《長編》卷36)右正言魯宗道則說:“審官之任,本宰相之責,宜妙選英哲以委之。”(《長編》卷90)元祐初宰相司馬光說自己“備位宰相,遴選百官,乃其職業。”(《長編》卷382)元祐末執政梁燾論蘇頌說:“頌為宰相,理會差除,可謂稱任矣。”(《長編》卷482)他們所說的“百官”,應該是各個層次的官員任用。承認皇帝有用人最終決策權和委任于宰輔,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二者并不沖突。宋代帝王和士大夫對此已有共識。
③ 宰輔插手高層和要害部門官員的任用。
皇帝雖然直接掌握高層和要害部門官員的任用權,但是,他們的決策往往得自宰輔的推薦,許多時候更是由宰輔代替行使決策權。甚至宰相闕任,也由現任宰相或樞密使等推薦。天圣六年(1028),宰相張知白去世,中書闕員,“宰相王曾薦呂夷簡,樞密使曹利用薦張士遜”,太后劉氏最終用張士遜為相(《長編》卷106)。宰輔插手這些方面的官員任選,表現方式是多樣的,主要有以下三種:
其一,堅持自己的正確用人主張,迫使皇帝聽從。
宰輔有時推薦的人選,不合皇帝之意,被屢屢駁回。然宰輔認定自己的選擇是正確的,便一而再、再而三地堅持,最終獲得君王的首肯。這種決策方式,從表面上來看依然是帝王最后拍板,但實際上的決策是由宰輔做出。當然,這時候必須是一位明智、有納諫容量的帝王在位。
(趙普)嘗欲除某人為某官,不合上(太祖)意,不用。明日,普復奏之,又不用。明日,又奏之,上怒,裂其奏投諸地,普顏色自若,徐拾奏,歸補綴。明日,復進之,上悟,乃可其奏。后果以稱職聞。又有立功者當遷官,上素嫌其人,不與,普力請與之,上怒曰:“朕故不與遷官,將奈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之通道也。且刑賞者,天下之刑賞,非陛下之刑賞也,豈得以喜怒奪之。”上弗聽,起,普隨之。上入宮,普立于宮門,良久不去,上卒從其請。(《長編》卷14)
它日,上(太宗)欲使人遣朔方,諭中書選才而可以責以事者。(呂)蒙正退,以名上,上不許。他日又問,復以前所選對,上亦不許。他日又問益急,蒙正終不肯易其人。上怒,投其手奏于地曰:“何太執耶!必為我易之。”蒙正徐對曰:“臣非執,蓋陛下未諒爾。”因固稱:“其人可使,余不及。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同府皆惕息不敢動,蒙正搢笏,俛而拾其書,徐懷之而下。上退,謂親信曰:“是翁氣量我不如。”既而卒用蒙正所選,復命,大稱旨。(《長編》卷35)
王珪嘗三薦(張)璪,不用。珪曰:“璪果賢,陛下未嘗用以為不賢,讒也。臣恐士弗得進矣。臣為宰相,三薦賢三不用,臣失職,請罷。”上(神宗)喜曰:“宰相當如是。朕姑試卿德不回,朕復何慮?”(《長編》卷311)
趙普、呂蒙正都以直言著稱。王珪則是北宋有名的“三旨宰相”,“以其上殿進呈,云‘取圣旨’;上可否訖,又云‘領圣旨’;既退,諭稟事者,云‘已得圣旨’故也。”(《長編》卷356)連王珪如此阿諛圣意的宰相,有時在用人問題上也要堅持己見,原因是宋代宰相將薦人、用人視為自己的當然職責。熙寧年間,王安石為相,朝廷任命大臣,神宗意見多次與王安石相左,反復討論爭議,最終采納的總是王安石的用人方案。寇準嘗自言用人標準:“宰相所以器百官,若用例,非所謂進賢退不肖也。”(《長編》卷62)寇準在中書時,因此大膽破格用人,在這一方面,宰相有決定性的發言權。
其二,宰輔雖然是用人的最后決策者,卻將恩德歸諸帝王。
在用人推薦與決策過程中,宰輔默默地做實際工作,皇帝享受“用人之明”的稱譽,對外維護了皇帝用人之決策權。宰輔這樣謙和的行為和態度,維持了皇帝用人決策權表里的諧和,避免了帝王可能生發的嫉妒之心,使得帝權和相權處于一種融洽的關系之中。
(李)昉居中書日,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材可取,必正色拒絕之,已而擢用。……子弟問其故,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于上。”(《宋史》卷265《李昉傳》)
(王)旦為相,賓客滿堂,無敢以私請。察可與言及素知名者,數月后召與語,詢訪四方利病,或使疏其言而獻之。觀才之所長,密籍其名,其人復來,不見也。每有差除,先密疏四三人姓名以請,所用者帝以筆點之。……旦凡所薦,皆人未嘗知。旦沒后,史官修《真宗實錄》,得內出奏章,始知朝士多旦所薦云。(《宋史》卷282《王旦傳》)
(王)曾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嘗問曾曰:“明揚士類,宰相之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耳。”曾曰:“夫執政者,恩欲歸己,怨使誰歸?”仲淹服其言。(《宋史》卷310《王曾傳》)
(范)純仁凡薦引人材,必以天下公議,其人不知自純仁所出。或曰:“為宰相,豈可不牢籠天下士,使知出于門下?”純仁曰:“但朝廷進用不失正人,何必知出于我邪?”(《宋史》卷314《范純仁傳》)
其三,權相當政時,用人權成為他們結黨運私的一種主要手段。
權相當政時,往往采取多種方法蒙騙君王,使帝王的用人決策權成為一句空話。《長編》卷96云:“自寇準貶斥,丁謂浸擅權,至除吏不以聞。”在類似情況下,相權對帝權產生離心作用,二者之間矛盾加劇,同時帶來政局和社會的動蕩。以至“競進之徒,趨走權門,經營捷徑,靡所不至。是恩命未出于上,而請托已行于下矣。”(《長編》卷121)或者“丞相不進賢者為將來之資,但用不如己者為自固之計。”(《長編》卷139)這種情況大多發生在北宋末年或南宋年間。例如:
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仲淹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為序遷,如此為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況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宋史》卷314《范仲淹傳》)
附己者立與擢用。自其獨相,至死之日,易執政二十八人,皆世無一譽。……然甫入即出,或一閱月,或半年即罷去。(《宋史》卷473《秦檜傳》)
南宋后期權相韓侂胄、賈似道當政時,門生、故吏、仆夫皆躋身朝廷顯貴,用人尺度已被敗壞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如“陳自強則以侂胄童子師,自選人不數年致位宰相,,而蘇師旦、周筠又侂胄廝役,亦皆預聞國政,超取顯仕。……惟所欲用,三省不預知也。”(《宋史》卷474《韓侂胄傳》)賈似道則憑賄賂授人以官職,“吏爭納賂求美職,其求為帥閫、監司、郡守者,貢獻不可勝計。”(《宋史》卷474《賈似道傳》)
這種權相任人唯親的現象,甚至發展到逐步把持科舉考試。《續宋編年資治通鑒》卷6稱:紹興二十四年(1154)三月,“親試舉人,考官以秦檜孫秦塤為第一,……同榜三百三十余人,檜之親黨居多,天下為之切齒。”
但是,兩宋這種權相操縱用人權的特殊情況,時間即短,皇帝的最終決策權也沒有被完全侵奪。皇帝只是過于依賴某一宰相,或過于懦弱、昏庸。如果皇帝想發揮作用,權相立即退居其次。如徽宗曾輕易地將蔡京貶謫出朝,高宗輕易地從秦檜手中取回權力等等。這與其他朝代成為傀儡的皇帝,雖個人有才干,且“有心殺敵”,卻“無力回天”的情形有天壤之別。所以說,宋代皇帝始終從理論到實質上都握有用人的最終決策權。
3、中下層官員的任用。
中下層官員的任選,歸吏部負責,所注授的官闕稱“部闕”。無論是元豐改制以前還是以后,這類吏部審官機構都是宰相的下屬單位,歸宰相領導,所以,宰相對其依然可以過問,“部注”人選,依然要通過中書審核。如熙寧四年(1071)十一月詔:“審官東院每季具知州軍、通判闕,及合入知州、通判人姓名、功狀赴中書,委中書審問,主判官詳察人材,不以次選差。”(《長編》卷228)只不過宰相不直接插手中下層官員的任選,而是一種間接領導。以下對吏部的任選官員的機構做一簡介。
北宋前期設吏部尚書銓(簡稱尚書銓),掌七品以下文臣選授。建隆三年(962),代之以吏部流內銓(簡稱流內銓、吏部銓、吏部流內選等)。淳化四年(993)五月考課院并入后,并掌選人奏舉與考核。元豐三年(1080)八月,改名為尚書吏部;元豐五年(1082)五月改制,再改為吏部侍郎左選。又設流外銓,歸屬吏部,掌在京師百司人吏考試與奏差。
此外,掌管中下層官吏的選用、磨勘、考核、升遷的,還有吏部南曹:掌選人履歷驗審,將按吏部格式可以敘資遷調的選人材料送往流內銓,經流內銓注擬遷資的選人,再由南曹發給歷子。這是流內銓的一個輔助性機構,熙寧五年(1072)七月并入流內銓;差遣院(京朝官差遣院):始置于太平興國六年(981)九月,淳化四年(993)五月并入審官院,掌考核、比較少卿監以下京朝官任滿歸朝待命者,據中書所下員缺,量材錄用,授以新官;磨勘院(磨勘京朝官院):淳化三年(992)十月始置,次年二月改名審官院,掌考核京朝官,以定黜陟;考課院:淳化四年(993)二月,由磨勘幕職州縣官院改名(淳化三年十月始置),同年五月并入流內銓,掌幕職州縣官(選人)的奏舉及歷任有過失人的考察等;審官院:淳化四年(993)二月,改磨勘京朝官院為審官院,又將差遣院并入,熙寧三年(1070)五月改為審官東院,考核六品以下京朝官殿最,排列其爵名、秩位,提出相應的內外職務任命方案,上報待批,神宗改制后,并入吏部尚書左選。審官西院:熙寧三年(1070)五月始置,元豐五年(1082)五月改為尚書省吏部尚書右選,掌閤門祇候、大使臣以上武臣磨勘、差遣。這些部門,在不同的時期內職能有所交叉或取代。
元豐改制,審官機構經過演變、合并,確立為“吏部四選”,即吏部尚書左選、右選和吏部侍郎左選、右選,其具體分工為:
文臣之(寄)祿官自朝議大夫、職事官自大理正以下,非中書省敕授者,歸尚書左選;武臣外朝官自皇城使、職事官自金吾街仗司以下,非樞密院宣授者,歸尚書右選;自初仕至州縣幕職官,歸侍郎左選;自借差、監當至供奉官、軍使,歸侍郎右選。(《宋會要·選舉》23之1)
四選制度確立后,宋代中下層官員的管理、任選機構從此定型,一直綿延到南宋末年。
4、皇帝和宰輔之間用人權的相互控制。
宋代皇帝和宰輔在用人方面基本上能協調一致,如上所述,同時又有矛盾之處。兩者既相輔相成、相互依賴,又有相互控制的一面。
① 皇帝對宰輔用人權的控制。
首先,好猜忌的皇帝并不能對臣下完全放心,他們要耍弄各種權術,以達到控制宰輔用人權的目的,使自己處于一種主動的地位,或有更多的發言權。這種情況一般發生在君王(包括垂簾的太后)對自己和二府大臣沒有信心的時候。
章獻太后智聰過人。其垂簾之時,一日,泣語大臣曰:“國家多難如此,向非宰執同心協力,何以至此?今山陵了畢,皇親外戚各已遷轉推恩,惟宰執臣僚親戚無有恩澤。卿等可盡具子孫內外親族姓名來,當例外一一盡數推恩。”宰執不悟,于是盡具三族親戚姓名以奏聞。明肅得之,遂各畫成圖,粘之寢殿壁間。每有進擬,必先觀圖上,非兩府親戚姓名中所有者,方除之。(《默記》卷上)
章獻是宋代第一位垂簾的母后,她生恐臣下不服或欺瞞,就使詐以操縱用人權。
而且,帝王也一再公開告戒宰輔用人要出自公心,不要任用私人。太宗曾對宰相李昉等說:“中書、樞密,朝廷政事所出,治亂根本系焉。且天下廣大,卿等與朕共理當各竭公忠,以副任用。人誰無姻故之情,茍才不足稱,不若遺之財帛耳。朕亦有舊人,若果無取,未嘗假以名器也。卿等其戒之。”(《長編》卷26)太宗登基素有“燭影斧聲”之說,所以,對人、對環境多疑忌之心,與宰輔之間的用人矛盾也因此產生。然而,宰執不可用其親戚、子弟,也成為慣例。元祐元年(1086)五月,朝廷除平章軍國重事文彥博之子文及為右司員外郎、門下侍郎韓維之侄韓宗師直秘閣,既引來臺諫的一致攻擊,文及和韓宗師不久因此罷去。元祐二年(1087),文彥博向朝廷推薦呂大臨、楊國寶,侍御史王巖叟進諫說:“楊國寶、呂大臨二人,是見任執政之親,士大夫口語籍籍,以為不平。”要求“養之以重其名實”。(《長編》卷396)在正常情況下,宰輔用其親戚或子弟,必定會遭到言官的彈劾。
皇帝對用人權的控制,還典型地表現在對宰相“堂除”用人的限制上。相對來說,宰相比較喜歡采用“堂除”的方式用人,將人事權直接操縱在自己手中。“堂除”的范圍雖一定之規,但并不嚴格,因人因時而異。神宗時,皇帝與宰相曾為此有過爭執,《宋會要·職官》1之18載:
(熙寧)二年,宰臣曾公亮欲知州皆選于中書,上曰:“中書數人,所總事已多矣,知州材否,何暇盡詳。且中書,三公職事,在于論道經邦。”公亮曰:“今中書,乃六卿冢宰之職,非三公也。”上曰:“冢宰固有冢宰之職。唐陸贄言宰相當擇百官之長,知審官是也。今不擇知審官人,而但堂選知州,所選人不精,徒令中書事更煩,況非國體也。”王安石曰:“誠如陛下所諭。”
根據神宗意見,宰相不應該直接插手下面地方人事任免,“堂選”范圍不應該過于寬泛,宰相應該將精力投注于“擇百官之長”,關注中央高層的人事任用。對于“百官之長”,宰相則僅有推薦權,決策在皇帝,所以,進一步連“堂除”也可以廢除。元豐四年(1071)八月一日詔:“中書自今堂選并歸有司”。同年十一月六日詔:“自今堂選、堂占悉罷,以勞得堂除者,減磨勘一年。”(《宋會要·職官》1之19)不過,“堂除”并沒有因為一紙詔書而廢罷,在兩宋選官制度中依然盛行“堂除”方式。元祐三年(1088)十二月,三省因“在京堂除差遣累有增改,而吏部闕少官多”,具體裁定“中書省差”和“吏部差”的界限(詳見《宋會要·職官》3之9、10)。皇帝為了控制“堂除”用人,又規定“堂除簿每月一次進納,逐名下聲說出身、歲月、歷任、資序,如有功過,即述其要,仍具系與不系宰執有服親”(《宋會要·職官》8之7)等,以便皇帝審閱瀏覽。“親屬,其舊法不系堂除”(同上)。
在監督過程中,皇帝還可以隨時糾正宰相“堂除”過程中“任人唯親”的傾向或做法,《齊東野語》卷1載:
舊法,未經任人,不許堂除。時相欲示私恩,則取部闕而堂除之。上(孝宗)知其故,遂令根刷姓名進呈。降旨云:“宰執當守法度,以正百官。梁克家違戾差過員數最多,候服闕日落職,曾懷可降觀文殿學士。”
朝廷多次立法,抑制任用宰輔子弟。熙寧四年(1071)三月八日,“詔在京官不得舉辟執政官有服親。以御史知雜舒亶言:近論蒲宗孟不當薦舉同知樞密院韓縝侄宗弼,乞立奏舉法故也。”(《宋會要·職官》1之19)其意圖也是抑制“任人唯親”的做法。
皇帝對宰相用人權控制的極端就是剝奪其權力,這樣的事例在南宋也曾發生過。理宗時的參知政事崔與之曾描述當時用人的情況說:“宰相進擬多沮格不行,或除命中出,而宰相不與知。”(《宋史》卷406《崔與之傳》)皇帝破壞“委任責成”的模式,意味著朝綱已亂。南宋寧宗時宰相余端禮就曾意識到這一點,他說:“除從官中書不知,朝綱已紊,禍根已滋。”(《宋史》卷398《余端禮傳》)這些不正常態,多數發生在南宋。
② 宰輔對皇帝用人的諍諫。
從宰輔的角度出發,則要求帝王用人不能獨斷獨行,隨心所欲,上面曾舉例宰相在用人時的堅持己見。當宰輔被不同程度地剝奪用人權時,他們就要提出抗議意見。右補闕田錫在上書時指出太宗的處事不當,其一是“宰相不得用人”,建議“宰臣若賢,愿陛下信而用之;宰相非賢,愿陛下擇可用而任之”(《長編》卷25)。總之,應該充分發揮宰相的職能作用,將用人權放心地交到宰相手中。
皇帝“內降”用人,這種做法往往是為了酬謝私情,更多的時候是為宵小打開方便之門,在兩宋時期雖然比較少見,但臣下依然要對此提出抗議,要求君主改正。慶歷元年(1041)五月,左正言孫沔對仁宗說:“天圣之間,多有內降,莫測夤緣,盡由請托,蓋頗邪之輩,巧宦進身,求左右之容,僥榮濫賞,假援中闈,實玷朝直。”“近歲以來,此路復起,未知以何事跡達于聰明?妨公起謗,無甚于此。”“伏望特發宸衷,止絕內降,如有合自中出之事,令兩府及諸司依公執奏,勿使阿諛上累圣明。”(《長編》卷132)慶歷二年閏九月,直集賢院尹洙上疏說:“近時貴戚、內臣以及士人,或因緣以求恩澤,從中而下,謂之‘內降’。臣聞唐氏衰政,或母后專制,或妃主擅朝,結恩私黨,名為‘斜封’。今陛下威柄自出,外戚、內臣賢而才者,當與大臣公議而進之,何必襲‘斜封’之弊哉!”(《長編》卷137)元祐元年(1086)閏二月,左司諫王巖叟告誡垂簾聽政的太皇太后說:“斜封墨敕,不宜于今日有,自古此事盡出于外人交結宦官、女謁,遂賣官鬻獄,無所不至,不可不防微”(《長編》卷386)。“與大臣公議”是用人的唯一正常途徑,“公議”的結果往往是宰輔代行用人決策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