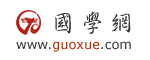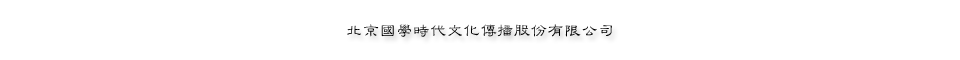第二章 宋代的三省制
諸葛憶兵
第二節 三省的建構
宋代自始至終分設三省。然在神宗改制前,三省僅有虛名,沒有或很少有實際職權。《山堂考索續集》卷30《官制門》云:“宋初三省,雖曰沿唐,而實異于唐。蓋三省為空官,而以平章為宰相者,宋初制也。”朝廷于皇城之外設尚書省、中書省和門下省,中書省和門下省又稱中書、門下外省(下省),僅“存其名”,不預聞中央政務。神宗改制后,三省才各自得以獨立,行使職權。但是,很快許多機構功能又趨于合一。可以說,宋代沿襲唐中葉以來三省制的發展變化,名義上保留三省制,實際上向一省制趨向發展。其間雖有神宗改制的反復,但這個大的發展趨勢沒有改變。
1、中書省
北宋前期,中書省僅僅是皇城外掛牌機構,不參與政務,“中書省判省事一人,以舍人充,掌供郊祀及皇帝冊文、幕職州縣官較考、齋郎室長諸司人年滿復奏、并受文官改賜服章、僧道紫衣師號、舉人出身、寺觀名額、正宣之事”(《宋會要·職官》3之1)。神宗改制后,中書省成為宰輔機構的核心部分,宰輔的權力行使大體上體現為中書省的機構運作過程。神宗改制前,在“中書門下”機構中,宰相的核心權力是原來屬于中書省的起草和發布詔令的職能部分,這也是“中書門下” 簡稱“中書”的原因;改制以后,中書省始終處于權力的中心位置。
① 職掌和職官。
《宋史》卷161《職官志》載:
掌進擬庶務,宣奉命令,行臺諫章疏、群臣奏請與興創改革,及中外無法式事、應取旨事。凡除省、臺、寺、監長貳以下,及侍從、職事官,外任監司、節鎮、知州軍、通判,武臣遙郡橫行以上除授,皆掌之。
即中書省職掌范圍是處理日常政務,起草詔令并取旨,任命中下層職官等。設官十一:有令、侍郎、右散騎常侍各一人,舍人四人,右諫議大夫、起居舍人、右司諫、右正言各一人。中書令官高不除,改制后,以右仆射兼中書侍郎行中書令之職,另置中書侍郎以為副職。南渡后,只設左、右丞相,不設本省長官,逐漸恢復到神宗改制前的狀況。
② 機構設置。
最初設八房:吏房,“主行除授、考察、升黜、賞罰、廢置、薦舉、假故、一時差官、及本省雜務”;戶房,“主行廢置升降郡縣、調發邊防軍須、給借錢物”;兵禮房,“主行郊祀陵、廟典禮,后妃、皇子、公主、大臣封冊,駙馬都尉、內命婦官封,科舉考官,外夷書詔”;刑房,“主行赦宥、契勘刑獄,除授官貶降敘復”;工房,“主行計度營造、開塞、河防”;主事房,“主行受發文書”;班簿房,“主行百官名籍及具員之事”;制敕庫房,“執行編錄供檢敕令格式及架閣庫”。元祐以后,析兵禮房為二,增加催驅房和點檢房。催驅房,“主行催驅在省諸房行遣文字稽違之事”;點檢房,“專點檢諸房文字差失之事”(均見《宋會要·職官》3之3、4、5),共有十一房。后又改主事房為開拆房。其中兵房僅“掌行除授諸蕃國王爵、官封。”軍政之事歸樞密院管理。
③ 中書省獨尊的位置。
中書省獨尊局面,由來已久。《石林燕語》卷3說:“自兩漢以來,謂中書為政本。蓋中書省出令,而門下省復之,王命之重,莫大于此。”唐代,“中書之權獨重,宋朝亦最重中書。蓋以造命可否,進退皆由之也。”(《山堂考索別集》卷18《人臣門》)北宋前期中書門下,統領百官,總攬大政,所行使的職權大都同于中書省。宋真宗對宰相呂蒙正等說:“中書事無不總,賴卿等宿望,副朕意焉。”(《長編》卷48)
神宗改制,有所變易。《老學庵筆記》卷4稱:“舊制,兩省中書在門下之上,元豐易之。”改制后,雖置中書省于門下省之下,但中書省因為是朝廷政令所出之地,事實上仍然凌駕尚書、門下二省之上。《長編》卷327敘述三省制后說:“三省分班奏事,各行其職令,而政柄盡歸中書。”當時,王珪以左仆射兼門下侍郎,蔡確以右仆射兼中書侍郎。蔡確善心計、好攬權,“已而,確果獨專政柄。凡除吏,珪皆不與聞。”(《長編》卷327)“王珪以左相在門下,拱手不復校”(《長編》卷358)。甚至,蔡確試圖在三省來往文書之間也顯示出中書省獨尊的地位,《長編》卷327又載:“蔡確既為右仆射且兼中書侍郎,欲以自大,乃議尚書省關移中書,當加‘上’字以重之。”此說雖然未得神宗首肯,但蔡確有此想法,也是當時中書省實際位置的一種體現。中書與門下二省侍郎之間,也是中書侍郎權大。“兩省侍郎,由中書過門下,雖名為遷,實抑其權。”(《山堂考索續集》卷30《官制門》)
哲宗即位初,曾試圖改變中書獨尊的局面。元豐八年(1085)九月,“詔三省合取旨事及臺諫章奏,并同進擬,不專屬中書”(《長編》卷359)。然在實際運作中,中書省由于處在“擬旨出令”的有利位置,獨尊的情況一直得以延續。元祐元年(1086)五月,殿中侍御史呂陶奏曰:“朝廷差除,雖云三省同奉圣旨,其根本次序、擬議、進呈皆出中書”(《長編》卷377)。同年十一月,呂公著奏曰:“今雖分三省,事多同呈,然機務之本并在中書。”(《長編》卷391)元祐六年(1091)正月,御史中丞蘇轍言及范純禮任職之事時說:“竊緣舊例,從官出入,盡系三省商量,然后進呈取旨行下。今中書獨專其事,中外莫不驚怪。”(《長編》卷454)中書獨尊的局面就使得三省權力的分配,有了輕重主次之分,也為三省的重新合一奠定了基礎。
2、門下省
門下省前期名存實亡。《宋會要·職官》2之2言:“用兩制以上官一員判門下省事,其通進、銀臺司及門下封駁事,又離為別司,而領于他官,名具實廢,散無統紀。”《長編》卷107載群牧判官司馬池天圣七年(1029)三月轉對之言說:“唐制:門下省,詔書出有不便者,得以封還。今門下雖有封駁之名,而詔書一切自中書下,非所以防過舉也。”此時的門下省,僅是皇城外保留的掛牌機構,“主乘輿八寶、朝會位版、流外較考”(《宋會要·職官》1之17)。門下省原來職掌的部分封駁權,歸于通進、銀臺司,銀臺司下面專設“封駁房”。然宋初門下省承襲制度傳統,封駁權并未完全失去,偶爾仍有類似職責的履行,太祖乾德五年(967)三月,門下省言:“今流內銓以前進士開封李肅擬保順軍節度掌書記,有違元制,準格下。”(《長編》卷8)開寶八年(974),“戶部員外郎、知制誥王祜判門下省,與判吏部流內銓侯陟不協。陟所擬注,祜多駁正。”(《長編》卷16)天圣元年(1023)十月,“門下省言:吏部流內銓注擬選人,請如舊制過堂押定。”(《長編》卷101)這些都是明顯的門下省封駁事例。
門下封駁之職,在北宋初期若有若無。太宗淳化四年(993)六月,“以右諫議大夫魏庠、知制誥柴務成同知給事中事,凡制敕有所不便者,宜準故事封駁。”同年九月即詔“停廢知給事中封駁公事”(《宋會要·職官》2之42)旋設旋廢,制度還十分不穩定。真宗咸平四年(1001)五月,以吏部侍郎陳恕知通進、銀臺封駁司,陳恕言:“封駁之任,實給事中之職,隸于左曹,雖別建官局,不可失其故號,請為門下封駁司,隸銀臺司。”得皇帝同意(《長編》卷48)。同年九月,“知封駁司陳恕請鑄本司印,詔:如有封駁事,取門下省印用之。因遂改知封駁司為兼門下封駁事。”(《長編》卷49)此后,通進、銀臺司長官時常兼門下封駁事①,門下封駁權逐漸得以恢復。嘉祐四年(1059)四月,何郯同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再次強調“此司實代給事中封駁之職”,要求“凡有詔敕,并由銀臺司”,得仁宗同意(《長編》卷189)。于是,這個部門有直接被簡稱為“門下”的,如嘉祐五年(1060)七月,以“知諫院唐介知荊南”,“敕過門下,知封駁事何郯封還之”(《長編》卷192)。神宗即位初,范鎮知通進銀臺司,范鎮上言:“故事:門下封駁制敕、省審章奏、糾舉違滯,著于所授敕,其后刊去,故職寢廢。請復之,使知所守。”得神宗同意(《蘇東坡集》卷39《范景仁墓志銘》)改制后,罷銀臺司,通進司隸屬門下省,以左仆射兼門下侍郎為門下省長官,居首相位置。其實際權力常常不如中書右相,但已經是朝廷兩宰相之一。
① 職掌和職官。
元豐改制以后,門下省也成為實權宰相機構,職掌范圍與職官設置也有了明確說法,《宋史》卷161《職官志》載:
受天下之成事,審命令,駁正違失,受發通進奏狀,進請寶印。凡中書省畫黃、錄黃,樞密院錄白、畫旨,則留為底。及尚書省六部所上有法式事,皆奏復審駁之。給事中讀,侍郎省,侍中審。進入被旨畫聞,則授之尚書省、樞密院。即有舛誤應舉駁者,大者論列,小者改正。凡文書自內降者,著之籍。章奏至,則受而通進,俟降布,分送所隸官司。凡吏部擬六品以下職事官,則給事中校其仕歷、功狀,侍郎、侍中引驗審察,非其人則論奏。凡遷改爵秩、加敘勛封、四選擬注奏鈔之事,有舛誤,退送尚書省。復刑部、大理寺所斷案,審其輕重枉直。不當罪,則以法駁正之。
《宋會要·職官》2之4載元豐五年(1082)十二月二日詔曰:
門下省,凡中書省、樞密院文字應復駁者,若干事體稍大,入狀論列;事小,即于繳狀內改正行下。若事不至大,雖不足論列,而其門曲折、難于繳狀內改正者,即具進呈,以應改正。事送中書、樞密院取旨。
門下省主要工作是審核上發之詔令、下呈之奏章、六部任命、斷案等等,并保留檔案。所謂“審而復之”。設官十一:侍中、侍郎、左散騎常侍各一人,給事中四人,左諫議大夫、起居郎、左司諫、左正言各一人。侍中官高不除,改制后,以左仆射兼門下侍郎行侍中之職,另置門下侍郎以為副職。南渡后,只設左、右丞相,不設本省長官,逐漸恢復到神宗改制前的狀況。
改制以后,朝廷有意識地加強門下省的獨立作用,元豐五年(1082)十二月,“詔門下省:凡本省事,從本司取旨”(《長編》卷331)。門下省長官由首相尚書省左仆射兼任,依據制度,其位序在中書省長官之上,然實際中卻反處其下。至元豐八年(1085)五月,左仆射王珪去世,右仆射蔡確遷左仆射,才有意識地加強左相的權勢,如改“百官差除”“盡歸中書”為“三省合班取旨”(《長編》卷363)等等。有時左仆射也會因為首相的位置和個人的作用,權力超越中書右相,如章惇紹圣年間為左仆射,以首相的身份,“文字合送中書省取旨者更不送中書省,便于尚書省將上取旨畫定,指揮簽書,押送中書省降敕。”(《宋會要·職官》1之29)同僚對此雖有意見,卻也無可奈何。但整體上仍然不能改變中書權重的格局。
門下省中,正副長官既然都是朝廷宰相、副宰相,行門下封駁之職的往往就是給事中了。如元豐六年(1083)六月,鄧綰試禮部侍郎,“于是給事中陸佃、韓忠彥封駁綰命,言綰奸回頗僻,使典邦禮,恐玷清選。詔罷之”(《長編》卷335)。
② 機構設置。
門下省所設機構與尚書、中書二省對應,初共有九房:吏房、戶房、禮房、兵房、刑房、工房,“皆視其房之名而分尚書省六曹二十四司所上之事,以主行之,惟班簿、本省雜務則歸吏房”;開拆房,“主行受發主事”;章奏房,“主行受發通章奏事”;制敕庫房,“主行供檢編錄敕令格式,及擬官爵、封勛、黃甲,與架閣庫”(均見《宋會要·職官》2之2)。元豐八年(1085)門下外省增設催驅房,掌檢查、催促本省諸房文書按期限發送;元祐三年(1088)增設班簿房、點檢房,掌百官名籍、檢查諸房文書有無失誤。
3、尚書省
尚書省前期名存實亡,掌管朝廷部分禮儀之事。“尚書省尚書、侍郎至諸司郎中、員外,止為正官,以敘位祿,皆不職本司之事。”(《宋會要·職官》4之1)名義上,朝廷規定“國家每有大事,必集議于尚書省”,然往往流于形式,赴議者多為一些官職不重要者,“本省官自三司副使已帶職者,多移牒不赴”(《宋朝事實》卷9《官職》)。官署舊址在典國坊梁太祖舊第,太平興國中遷往利仁坊孟昶舊第。
宋代官與差遣分離,尚書省六部基本上也是虛設、沒有職能的機構,但又不可一概而論。尤其是宋初,沿襲唐五代制度,尚書省六部與后來設置的差遣重疊并行,官制設置比較紊亂,六部也仍保留一定的行政職能,例如:建隆三年(962)三月,控鶴右廂都指揮使尹勛擅斬部屬,兵部尚書李濤“以病臥家”,“力疾草奏,乞斬勛”,家人勸其不要過問,李濤說:“我為兵部尚書,知軍校無辜殺人,豈得不論?”(《長編》卷3)又,同年同月,太祖下令說:“諸州自今決大辟訖,錄案聞奏,委刑部詳覆之。”(同前)又,《長編》卷5載乾德年間事說:張昭“為吏部尚書領選事,凡京官七品以下又屬銓。及昭致仕,始用它官權判,頗更舊制。”上述幾例,都說明六部仍是具有一定行政職能的部門。只是隨著北宋社會的逐漸穩定和差遣制度的逐漸完善,六部的行政職能才漸漸被完全剝奪,機構完全虛化。
① 恢復尚書省的要求及付諸實踐。
北宋前期,中央政府機構設置重疊,行政效率低下,許多官員將弊病歸結到尚書省的有名無實,提出恢復尚書省的要求。至道二年(996)二月,王炳上書論尚書省職能,言“尚書六曹,名雖存而其實亡矣。”然王炳要求恢復的僅僅是尚書省“藏載籍、興治教”的功能。宋初,大臣也曾提出全面恢復尚書省的建議。端拱元年(988)十二月,著作郎羅處約上疏討論三司制度時,要求全面恢復尚書省二十四司制度(詳見《長編》卷29)。淳化二年(991)九月,御史中丞王化基獻《澄清略》言五事,首言“復尚書省”,具體建議說:
臣今請廢三司,止于尚書省設六尚書分掌其事;廢判官、推官,設郎官分掌二十四司及左右司公事,使人掌一司;廢孔目、勾押前行后行為都事、主事、令史、書令史;廢勾院、開拆、磨勘、憑由、理欠等司,歸比部及左右司。如此,則事益精詳,且盡去其州郡職局鄙俗之名也。(《長編》卷32)
嘉祐三年(1058)十二月,知制誥劉敞等上條奏說:
尚書二十四司既為虛名,所以官冗員眾,蠹財害政。即欲改正官制,當罷三司,復二十四司及九卿官,使有定員,其郎官不在本省治職事者,并以前資及散官處之。……大理寺決天下獄,刑部復之,于事已足,又加審刑院,則為駢衍。即欲裁損官制,當廢審刑院。一吏部尚書、侍郎、郎中分領銓事,則當差次輕重,分別流品。今審官院掌京朝官磨勘,而尚書銓惟典州縣幕職官,體制不倫。即欲裁損官制,當罷審官院,以其職事歸尚書銓。群牧司、提舉司、糾察司之類,皆古無此官。即欲裁損官制,悉當省罷,還屬尚書九卿,此所謂裁損者也。……中書出制敕,唐制并經門下審核,然后尚書出告身,經歷三省。比來唯于中書發敕,虛置三省官名,今欲申明復此制。(《長編》卷188)
大中祥符九年(1016)三月,真宗對宰輔們言及尚書省制度時也說:“言事者屢請復二十四司之制,楊礪嘗言行之不難。”(《長編》卷86)此外,咸平中楊億提出“文昌會府宜復其舊”,至和中吳育認為“尚書天下之大,有司當漸復之”(《山堂考索續集》卷29《官制門》),可以說,要求恢復尚書省制度,在神宗改制前,幾乎已在朝野達成普遍共識。
神宗改制后,大臣們的建議得以付諸實踐,尚書省六曹二十四司轉為職能單位,尚書省也成為名義上的宰相機構,且以尚書省都堂為政事堂, 宰相們議政、決策于此,徽宗曾賜尚書省手詔曰:“尚書,政事之本”(《宋會要·職官》4之15)。神宗又于元豐五年,在大內之西建尚書新省,“自令、仆廳事下至吏舍,為屋四千楹有奇。”神宗夸耀說:“新省宏壯,甚與官制相稱。”(均見《宋會要·職官》4之8)有都省、令庭、左仆射庭、右仆射庭、左丞庭、右丞庭,三省辦公處所皆在于此。這一年的五月,還詔曰:“如聞官制新行,諸司不知所屬,可一切申尚書省。”(《長編》卷326)尚書省成為總理朝政的機構。不過,尚書省長官由中書、門下二省長官兼任,尚書省不免與中書、門下二省呈現合而為一的傾向。如元豐八年(1085)三月和元符三年(1100)正月詔:“尚書省官權于門下、中書省治事。”(《長編》卷353、520)就是這種傾向的一種體現。
② 職掌和職官。
元豐改制后,尚書省有了相當的職掌和機構設置,《宋史》卷161《職官志》載:
掌施行制命,舉省內綱紀程式,受付六曹文書,聽內外辭訴,奏御史失職,考百官庶府之治否,以詔廢置、賞罰。……凡天下之務,六曹所不能與奪者,總決之;應取裁者,隨所錄送中書省、樞密院。事有成法,則六曹準式具鈔,令、仆射、丞檢察簽書,送門下省畫聞。審察吏部注擬文武官及封爵承襲、賜勛定賞之事。朝廷有疑事,則集百官議其可否。凡更改申明敕令格式、一司條法,則議定以奏復,太常、考功謚議亦如之。季終,具賞罰勸懲事進奏院,頒行于天下。大祭祀則誓戒執事官。
尚書省屬下的六部,是中央政令的具體實施和執行機構,神宗總結其職能便是“尚書省承而行之”。 設官九位:尚書令,左、右仆射,左、右丞,左、右司郎中,員外郎各一人。尚書令官高不除;左、右仆射兼門下、中書二省長官,為宰相;左、右丞為副宰相。
③ 機構設置。
尚書省機構設置有十房:吏房、戶房、禮房、兵房、刑房、工房,“各視其房之名分掌六曹諸司所行之事”;開拆房,“主受發文書”;都知雜房,“主行進制敕目、班簿、具員賞功罰罪、都事以下功過遷補、及在省雜務”;催驅房,“主行鉤考六曹稽失”;制敕庫房,“主行編類供檢敕令格式、簡納架閣文書”(均見《宋會要·職官》4之4)。后增設點檢房、奏鈔班簿房等。各房之上,設尚書省左右都司,“掌受付六曹諸司出納之事,而舉正其稽失,分治省事。左司治吏、戶、禮、奏鈔、班簿房,右司兵、刑、工、案鈔房,而開拆、制敕、御史、催驅、封椿、知雜印房則通治之。”(《宋會要·職官》4之19)
① 如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三月,"命吏部尚書王欽若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天禧二年(1018)五月,以御史知雜事呂夷簡同勾當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皆見《宋會要輯稿·職官》2之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