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 《竟陵詩選》
詩總集,十三集,清熊士鵬編選。士鵬字兩溟,一字莼灣。天門(今屬湖北)人。嘉慶乙丑(1805)進士,武昌府教授,喜培植孤寒,提倡風雅,獎掖后進,著有《兩溟詩集》。竟陵本是湖北一隅,并非文化昌盛之地,竟陵詩因明末鐘惺、譚元春選《詩歸》提倡“幽深孤峭”之詩而享大名。然而明末、清初,詩壇主流和統治者視此派詩為“詩妖”和“亡國之音”,從而受到壓制,甚至他們的部分作品被列為禁書。熊士鵬編此書雖意在表彰鄉先賢,也有提倡詩學,示人矩之意。
全書共選詩八百一十五首,第一卷首選唐張祜等人詩作二十二首,他們并非竟陵人,只是曾到此仕宦、流寓、游覽送別于此,因此錄之以備覽。第二卷起正式選本邑人之作,首列魯鐸,此人字振之,明弘治會元,科舉名次雖高,但卻是位道學色彩很濃的詩人。第三、第四卷為鐘惺、譚元春之詩,每人選詩近百首,此為全書之骨干,編者認為:“鐘、譚別開風氣,故最著。”作者也反對人們“轉相仿效,惟知尚聲調、崇浮華,卒不見所為性情之真、氣韻之妙,則亦無殊乎內土木而外冠裳也”。他還認識到詩人各有所長,故此編只取所長,不求全責備。擺脫門戶之見,有善必錄。因而能使此書成為“羅五侯以成鯖,貢九牧而鑄鼎,四美具,二難并”(見編選者自《序》)的選本。五卷以后則多為清代竟陵人的詩篇。亦以表現性靈者為多。
有清道光癸未(1823)鵠山小隱的刊本。
197 《清代北京竹枝詞》
竹枝詞總集,十三種,今人路工編纂。
“竹枝詞”本為唐代巴渝一帶的民歌,劉禹錫采錄改造竹枝之聲辭,使之成為富有民歌特色的一種詩體,他創作的十一首竹枝詞也給后代文人以示范作用。唐朝以后竹枝詞發展很快,成為泛詠風土、描寫愛情、記事抒情的一種通俗的聯章體的七言絕句。
此書所收十三種竹枝詞內容更是豐富,它們都是描寫從清初到清末的北京風土人情、名勝古跡、社會生活的。比較真實地顯示了二百余年間的北京風貌。
1.《燕九竹枝詞》,孔尚任等撰。記錄北京“燕九雅集”(每年正月十九日,北京士人聚會紀念元代著名道士丘長春仙去)花會之盛。孔氏首唱十首,蔣景祁等八人各和十首。
2.《都市竹枝詞》,凈香居主人(楊米人)撰。描寫乾隆、嘉慶間北京各階層人們的生活、好尚以及百業百工情況。
3.《燕臺口號一百首》,查揆撰。詩中多寫嘉慶之初京師各行各業情況及風土人情。
4.《都市竹枝詞》,作者佚名。描寫嘉慶間京師異事新聞,分十類:街市、服用、時尚、京官、候選、考試、教館、胥吏、內眷、觀吏,每類十首。
5.《草珠一串》,作者碩亭。共一百零八首,分總起、文武各官、兵丁、商賈、婦女、風俗、時尚、飲食、市井、名勝、瀏覽、總結。
6.《續都市竹枝詞》,作者學秋氏(張子秋),共一百首。如作者序中言此書“詼諧間作,或寫之狀,或操市井之談,或抒過眼之繁華,或溯賞心之樂事”。多是發生在嘉慶間事。
7.《都市雜詠》,作者楊靜亭,共一百首。全書分風俗門、對聯門、翰墨門、古跡門、技藝門、時尚門、服用門、食品門、市廛門、詞場門等十門寫道光間情況。
8.《燕臺竹枝詞》,作者何耳,共二十首。寫咸豐間風俗細事。
9.《增補都市雜詠》,作者李靜山,共六十三首。系選本。分風俗、對聯、翰墨、古跡、技藝、時尚、服用、食品、市廛、詞場等十一門,多系同治間事。
10.《都門記變百詠》,作者西復儂氏,青村杞廬氏。記庚子之變、義和團事。
11.《京華百二竹枝詞》,作者蘭陵憂患生,共百二首。寫宣統間清統治者推行所謂“新政”在北京所形成的新異景象。這一組詩注文較為詳盡。
12.《京華慷慨竹枝詞》,作者吾廬孺,共一百首。諷刺宣統間清統治者推行“新政”的情景。多詼諧之語,中寫了對當時來說還是新生事物的“志士”“鼠疫”“議員”“帝國統一黨”“國民”“巡警”等,實為一組政治諷刺詩。
13.《百戲竹枝詞》,作者李振聲。描寫康熙間京師百戲情況。此書有北京出版社1962年排印本。
198 《揚州風土詞萃》
揚州風土詩詞總集,十七種,揚州古舊書店搜集。
揚州自古繁華,南朝時有“腰纏十萬貫,騎鶴下揚州”之說。富有、成仙和生活在揚州被視為人生三大美事。唐代除了東西二京之外,就是“揚一益二”。揚州的繁榮,至清尤盛,其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都得到長足的發展,因之許多詩人用詩詞從多方面描寫過它,此書便是清代詩人以通俗詩詞記錄揚州風土民情的一部叢書。包括:1.《廣陵古竹枝詞》,作者闕名;2.《揚州畫舫詞》,作者韓日華;3.《廣陵秋興》,作者王雪洲;4.《揚州夢香詞注》,作者費執御;5.《揚州竹枝詞》,作者董恥夫;6.《董竹枝逸稿》,作者董恥夫;7.《續揚州竹枝詞》,作者林蘇門;8.《邗江三百吟》,作者林蘭癡;9.《邗江竹枝詞》,作者署集英書屋;10.《小游船詩》,作者辛漢清;11.《續揚州竹枝詞》,作者臧毅;12.《赤湖雜詩》,作者阮先;13.《淥湖竹枝詞》,作者阮充;14.《揚州竹枝詞》,作者孔劍秋;15.《望江南百調》,作者黃惺庵;16.《揚州雜詠》,作者臧?;17.《揚州辛亥歌謠》,作者闕名。
這部叢刻中值得注意的是:
一、董恥夫的《揚州竹枝詞》《董竹枝逸稿》。董是康熙雍正間人。名偉業,字恥夫,號愛江,沈陽(今屬遼寧)人,寄籍揚州。因其所寫竹枝詞盛傳一時,外號“董竹枝”。此編中二集共收竹枝詞一百四十四首。其筆觸深入到揚州社會各個角落。詩中農、漁、商、儒、優、僧、道、巫、尼、娼、官、紳,三教九流,七十二行無所不有。每一首記錄一個具體事物,保存了大量民間資料,而且微言多諷。開篇第一首就是“只栽楊柳蓮花埂,不種桑麻芍藥田”這種帶刺的詩句。因此李斗在《揚州畫舫錄》中說到董恥夫的詩“無和平忠厚之旨,論者少之”。這種諷刺詩自然不為達官貴人所看好;只有具有叛逆性格、“揚州八怪”之一的鄭板橋贊賞其詩“如銘如偈,有警世之用”。
二、林蘇門的《邗江三百吟》《續揚州竹枝詞》。林字嘯云,號蘭癡,揚州甘泉人,生活于乾隆間,為阮元之母舅和老師。林氏之詩以贊美、描寫揚州風俗為主,特別是其《邗江三百吟》每詩前均有小序,后有注文,對揚州風俗掌故記錄頗詳,如年節習俗、新異衣飾以及日常生活中的種種小事都有詳細的描寫。
三、《邗江竹枝詞》署名“儀征函璞集英書屋”,撰人不詳。全編對揚州的吃、喝、玩、樂諸方面的情形作了具體而生動的描繪。
四、《續竹枝詞》。臧?字宜孫,號雪溪,自號種菊生、菊隱翁、菊叟,揚州人,道咸間進士。他的詩主要記錄太平天國軍隊三次攻克揚州、給揚州帶來的滅頂之災和滄桑巨變。臧是這場災難的目擊親歷者,形諸于詩,頗感人,更富于史料價值。
五、《揚州辛亥歌謠》。作者不詳,此集為《十古怪歌》,描寫大革命前夕揚州各界的“古怪”現象。
此編為揚州古舊書店所影印,無序跋。未說明書編纂過程,書中筆墨一致,恐為今人過錄本。多缺字,漏字,借字,也無編纂體例,應該對此書作進一步整理,以便閱讀。
有揚州古舊書店1961年影印本,分裝十二冊。
199 《詩淵》
類書,不知編者,《文淵閣書目》曾著錄此書。其成書年代大約與《永樂大典》相同,或稍偏后。此書恐未刊刻,只有手稿本流傳。
全書共分天、地、人三大部分,天部已佚,地、人二部分也不全,現存殘本分裝二十五冊,近三百萬字。從收錄情況來看可能為明初人所編。
書中所收作品上自魏晉六朝,下至明初,共約五萬多首。收錄唐以前作品少一些,但多為名家之作。唐、宋、元三代收錄較多,其中宋最多,是目前所見到的收輯宋詩最為豐富的總集之一。其中約有十分之二三不見于傳世的各種別集、總集,還包括了一些名家的佚作、中小作家的佚集以及大量聲聞不彰的詩人的作品,許多詩歌作者僅見于此書。收錄詩歌的內容也極豐富,題材廣泛,天、地、人的事物無所不及。另外還收錄詞近千首,其中有一半左右不見他本流傳,今人孔凡禮的《全宋詞補遺》主要依據此書。《詩淵》所依據的是宋、元、明初的版本或寫本,其距作者時代較近,也比較近真,因之可以用之校正現在流傳本之誤,或流傳本之闕。另外,編者態度嚴肅認真,忠實原文,不輕易改動原作面貌,因此亦可以補某些古籍的脫訛。此書編輯者文化水平不高,可能是應書坊之邀而編,后來不知因何未能出版,由于收錄詩多而被皇家的“文淵閣”所收錄,得以稿本傳世。宋元書坊編輯詩文總集為了便于讀者使用(主要是學詩的過程中摹擬),多用“分門纂類”的方法,本書也是如此。全書分若干“門”,于“門”下再分“類”,然后編排所錄入詩。由于編輯水平有限,而分類標準往往只根據詩題,收錄次第十分混亂。據今人陳尚君考證(見《文獻》1995年第1期《〈詩淵〉全編求原》),本書原應有十七門,包括天文、地理、時令、花木、鳥獸、宮室、器用、人物、身體、聲色、衣服、珍寶、飲食、文史、數目、方隅、人事。全佚者六門:天文、時令、人物、聲色、數目、方隅。殘者為地理、文史兩門。本書在書的編排和我們了解古代文獻的編纂情況方面,為研究我國古代詩歌和整理古代詩總集、別集方面提供了豐富的、可信賴的資料。
有書目文獻出版社影印本(分裝六冊)。
200 《名教罪人》
清詩總集,一卷,清雍正時宮廷詞臣編纂。
此集之詩皆為奉雍正皇帝之命作,其內容為指斥唾罵被雍正斥為“名教罪人”的錢名世。錢氏為康熙四十二年一甲進士,曾任翰林編修,很有詩名。康熙末至雍正初權臣年羹堯曾一度深受雍正的倚重,雍正六年任命他為撫遠大將軍。雍正皇帝還對他恩寵有加,在短短一二年中他受到多次賞賜,如賜爵、賜金、賜第、賜園、賜世職。年羹堯也是氣焰熏天,群僚趨附,成為朝廷的第一紅人。誰也沒有想到這只是雍正為確立和鞏固自己地位的手段,待帝位穩固后,便迅速翦除年羹堯及年黨。處置年羹堯時發現了錢名世有投贈贊頌年羹堯的詩歌(可以想見寫這種詩的決非錢氏一人),觸怒了雍正。雍正偏狹而好名,又為了警誡其他臣子,他沒有殺錢名世,并在諭旨中說:“其人玷辱名教之人,死不是蔽其辜,生更以益其辱,是以不即正典型褫職遞歸。”所以不殺錢名世之頭,押送回鄉,令地方官管制,并親書“名教罪人”四字,令地方官制成匾額,張掛在錢所居之宅。他還下令“在京現任官員,由進士舉人出身者,仿詩人刺惡之意,各為詩文,紀其劣跡,以儆頑邪。并使天下讀書人知所激勸,其所為詩,一并匯齊,繕寫呈進,俟朕覽過,付給錢名世”。而且下令說:“凡文學正士,必深惡痛絕,共為切齒。”此書便是當時在京大小臣工奉旨表示義憤唾罵錢名世之“詩”的總集,共三百余首,詩的內容千篇一律,枯燥無味,有的罵他“瞯然人面,無恥之至”;有的說他“慚愧須眉事善柔,媚奸附惡不知羞”。質木無文,至此為甚。其實當時參加罵錢名世者,有的便是剛從文字獄解脫出的,如方苞,也有的不久也遭文字獄之害,如查嗣庭。因此這部書雖無文學價值,但從中可看出為人們所艷稱的康、雍、乾“盛世的”文化面貌,展示清代統治者思想文化統治上的手段和殘酷。
有民國間故宮博物院的《文獻叢書》本。卷前有雍正皇帝上諭,諭中敘述了錢案的過程, 和他之所以如此處理錢氏的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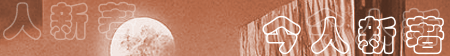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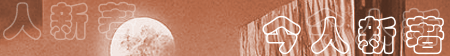
![]() web@guoxue.com
web@guoxue.com ![]() 010-68900123
010-68900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