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 《國朝詩乘》
清初詩選集,十二卷,清劉然編選。然字簡齋,一字文江,號西澗,諸生,好與名流往來,江寧(江蘇南京)人。大約生活在順治、康熙時期,生平仕履不詳。有《西澗初集》行世。
此集選錄清初詩一千余首,作者二百余人,不拘先后。據劉氏稱此選“著名稱雄者或闕焉,而加意表彰幽隱之士”(見自《序》)。書中評語頗多,或評論品藻文字,或分析標舉格律,也多有得之語。首卷論詩,編者友人徐秉義為之作《序》,言此編“殫精研思于六義之正變,諸家之派別,五七言之源流,古樂府之聲辭離合,罔不臚列縷析,粲然如指諸掌。其用意可謂勤矣。至于持擇謹嚴,議論高闊,直欲靡濟南、竟陵之壘而拔其幟,又無論鐘嶸、高等輩。是豈不欲其言之既立,為學詩者通億載之津哉!”這些雖不無夸誕之詞(從中可見時風之溺人,徐秉義眼中只有李攀龍所選的《古今詩刪》、鐘惺所選的《詩歸》一類當時流行的詩歌選本,把它們看成當時選家的最高標準;鐘嶸的《詩品》、高的《唐詩品匯》反而不在他眼內),但劉然的批點評論還是很認真的。他強調詩人首先要有高尚的思想品質:“詩人志芳行潔,不以名位動其心,乃與風雅二字合,不然筆補造化,皆余緒也。”并結合唐代有名詩人作品作了深入的論述。
劉然對于生活在下層的詩人的辛酸有著深刻的理解:“獨古慧心文人艱辛刻苦,僅以數首詩博身后名,顧使其生少知音,得歸湮沒,此亦仁人所深悲極痛也。”這說明編者也是沉淪不偶的士人,為人作嫁也頗不易,為使書板能繼續刊刻,他在最后呼吁詩人們集資刊刻,在首卷中還講明一塊板書刻兩面需要多少銀兩(可作出版之史料),即使如此,劉然也未能編刻成此書,赍志而亡。賴有摯友朱豫等人據遺稿再加編綴,捐資刊刻。徐秉義《序》中言:“朱子以寒素,擅高才,寢食漢唐,貫穿經史,豈不足以自成一家言,而必為之訂殘補闕,以終劉子未竟之緒。其所以不死其友者,未有若斯之篤者也。”本書刊成也有朱豫很大功勞,他不僅出了錢,而且再“遍搜諸名家詩,拔萃取尤,多則數十首,少則數首,評跋付刊,匯為十二卷,卷七八十葉,可作數十卷”(見蘇《序》)。書以“乘”為名“取諸無所不載之意”。
有康熙間拙真堂刊十卷本,后有玉谷堂增刻本,為十二卷。
177 《清詩別裁》(國朝詩別裁)
清詩選本,本三十六卷,經翰林院刪訂為三十二卷。清沈德潛編纂。德潛編有《古詩源》,已著錄。
此書選錄從清初到乾隆初年已亡故詩人九百九十六人,詩三千九百五十二首。始于錢謙益,終于潘廷瞷(計算到三十卷)。三十一卷為“閨秀”,三十二卷為“方外”。全書編排基本上以時代先后為序。
沈氏論詩主“格調說”,選詩以“和性情、厚人倫、匡政治、感神明”為宗旨,認為詩歌作品只有“原本性情、關乎人倫日用及古今成敗興壞之故者,方為可存,所謂其言之有物也”。盡管編者是從封建主義立場看待這些問題,但能貫徹這些主張的作品必然與社會現實有較多的聯系。
書中選錄了許多頗能反映現實生活于民間疾苦的作品。如此書所選吳偉業作品三十二首,幾乎都與明朝覆亡和清初重大事件密切相關,甚至有些民族情緒特別強烈的作者如屈大均(選十五首)、陳恭尹(選十二首)也有較多的作品選入。這些詩中多有怨憤之音。如屈大均的《魯連臺》(一笑無秦帝)、《吊雪庵和尚》(一葉離騷酒一杯),陳恭尹的《讀秦紀》(謗聲易弭怨難除,秦法雖密亦甚疏),都是有為而作(雍正八年,廣東巡撫就密奏說屈大均的詩歌作品中“多有悖逆之詞,隱藏抑郁不平之氣”。屈氏雖死,但也兩度受到過文字獄的追究)。此書入選詩人很多,大部分沒有專集行世,他們的詩歌也賴此書以傳。沈氏深于詩學,是清代著名的詩學理論家,并有較高的藝術鑒賞力,所選作品大多具有可讀性,以含蓄蘊藉、風調音節近于唐音者為多。編者也要通過這個選本反映清初詩壇之概貌,因此,清初虞山、云間、婁東三派代表人物都有一定量的代表作品入選(“云間”派最重要的代表陳子龍的作品選入沈氏另一個詩歌選本———《明詩別裁》之中)。浙派、神韻派也有足以知人論世的數量的作品入選。
沈德潛是乾隆時期詩壇領袖,操詩壇選政多年,他選詩最壞的習慣是為入選者改詩,視入選者如其弟子。本書也是如此。如錢謙益為一代名家,其詩遠勝于沈,而此編選錢詩三十二首也多有改篡。如《送福清公歸里》原詩為:“閩海爭傳岳降神,匝天弧矢護生申。契丹使亦知元老,回紇占應見大人。代許孤忠留一柱,帝思耆德撫三辰。吳門咫尺鄰閶闔,珍重東山五畝身。”而本編選入此詩首二句改為“鶚立超端領縉紳,飄蕭鬢發見風神”。原詩是賦兼比興,“閩海”而有“岳神”之降,用以象征“福清公歸里”。其氣魄之大可以想見。而改后的則只是“賦”,太寫實、平板。書前“凡例”言選詩時只對個別用錯的字詞作了些調整,如不復核原詩,很難發現沈氏選本這一特點。
此編初創于乾隆十年(1745),成于二十三年(1758)。曾請序于乾隆皇帝。當時乾隆指出此書有三點需要改正之處:“謙益諸人為明朝達官,而復事本朝,草昧締構,一時權宜,要其人不得為忠孝,其詩自在,聽之可也,選之以冠本朝諸人則不可。錢名世者,皇考所謂‘名教罪人’,更不宜入選。慎郡王(允禧)朕之叔父也,朕尚不忍名之,德潛豈宜直書其名。至于世次前后倒置,益不可枚舉。”(見《清史稿·沈德潛傳》)“因于御制文內申明其義,并命內廷翰林為之精校去留,俾重鋟板以行世。”(見《文字獄檔案》第七冊)沈氏奉旨在原編內刪去錢謙益、王鐸、吳偉業、方拱乾、張文光、龔鼎孳、曹溶、陳之遴、趙盡美、高珩、許承欽、周亮工、彭而述、孫廷銓、李雯、宋之繩、梁清標、王崇簡等十八人,因為他們都在明代有功名并降清為官,被乾隆皇帝定為“貳臣”。另外在“凡例”中涉及錢謙益的文字也被刪去。于乾隆二十六年刊刻為“定本”。二十四年、二十五年兩次刻本皆被定為禁書。乾隆四十一年(1776),皇帝再度追究此事(此時德潛已去世七年),十分生氣。后又因為徐述夔詩集《一柱樓集》中有“悖逆語”,而德潛曾為徐述夔作傳,稱其品行文章皆為可法。被清廷議罪。后被奪死后贈官,“罷祠削謚,仆其墓碑”。未作修改的《國朝詩別裁》雖經數度追繳,仍未絕跡于人間。
乾隆二十四年(1759)所刊三十六卷本及乾隆二十六年所刊教忠
①參照拙文《〈欽定熙朝雅頌集〉和旗人的詩歌創作》,見《文學遺產》1992年第五期。
堂三十二卷本,皆傳于世。1973年中華書局據教忠堂本縮小影印出版,為線裝本,1975年又出版了平裝影印本。
178 《欽定熙朝雅頌集》
清詩總集,一百三十八卷,清鐵保編纂。保(1752~1824)字冶亭,一字鐵卿,號梅亭,舊譜稱覺羅氏,自稱趙宋之裔,后改棟鄂,隸滿洲正黃旗。乾隆三十七年(1772)進士,累官吏部侍郎、山東巡撫,嘉慶九年(1804)進所編選之《八旗詩集》,賜名《熙朝雅頌集》,后以洗馬致仕。
此編所收是王公貴族、文人武士以及八旗中閨閣之詩作。滿洲本是以弓馬游獵起家,后來兼并諸部,進而統一中國。清朝建立以后,滿洲八旗分派住在各地,成為鎮壓各地漢族百姓反抗的主要力量,因此他們的主要任務就是要學習弓馬騎射,但隨著國家的安定與旗人生活有著國家俸祿為保障,八旗子弟無所事事,有一部分棄武從文逐漸漢化者越來越多。乾隆皇帝在位時借整頓旗務多次加以制止。他曾傳喻八旗子弟“務崇敦樸舊觀,毋失先民巨?;倘有托名讀書,無知妄作,侈口吟詠,自蹈囂陵惡習者,朕必重治其罪”。① 可是制止者本人———乾隆皇帝就是一位“無知妄作,侈口吟詠”的最多的“詩人”,而且產量居古今詩人之冠。因此,皇帝號令雖嚴,也屬一紙空文。旗人寫詩作文之風,越來越盛。旗人詩家出專集者越來越多,清統治者定鼎中原也有一百余年,然而,卻不見滿洲詩人的總集或選本出現,其原因就在于最高統治者對此采取了壓制的態度,誰也不敢冒險編纂這類書籍。《熙朝雅頌集》之編纂,標志著壓制滿人漢化政策已經失敗。此書得到嘉慶皇帝的承認和作序可以視為滿洲上層人士與文人公開融合于漢族文化的一個標志。此時距乾隆皇帝去世僅有五年,不過在嘉慶的序文中對于旗人寫作漢詩是吞吞吐吐承認的:“夫言為心聲,流露于篇章,散見于字句者,奚可不存?非存其詩,存其人也。非愛其詩律深沉,對偶親切,愛其品端心正,勇敢之忱洋溢于楮墨間也。是崇文而未忘習武,若逐末舍本,流為纖靡曼聲,非予命名‘雅頌’之本意。知干城御侮之意者,可與之言詩。徒耽于詞翰,侈言吟詠太平,不知開創之艱難,則予之命集得不償失,為耽逸惡勞之作俑,觀其集者應諒予之苦心矣。”從這些文字看來,最高統治者還是要把這種漢化限制在自己允許的范圍之內,也就是,旗人可以在不影響其作為鎮壓工具的前提下作有限度的漢化。實際上這是不可能的,滿族統治者的漢化過程也就是滿族統治的衰落過程。旗人的生活、風俗都與漢人有別,這些在收入本集的作品中有不同程度的反映。這是在其他清詩總集中難以見到的。
旗人詩歌的風格以近白居易者為多。編者編選此集是十分謹慎的。滿族統治者之間的斗爭特別尖銳復雜,而且許多事情關系著最高統治集團的核心機密,因此,在選錄作者與作品上就頗費斟酌,稍有偏差,關系著身家性命。編者在“凡例”中言其編選此書,入選作者是以朝廷所肯定的《皇清文穎》為圭臬的。“故于《文穎》所載之人,其詩未見于他編者,僅一一登載,不敢稍為遺漏”。清室的天潢貴胄,另編首集,以爵位高低為序。其他則參照《國朝詩別裁》順序,以若干年為一段,一般作者以科名先后編入其中。此書多采之諸家本集,無本集者則從伊福納《白山詩鈔》、卓奇圖《白山詩存》以及各種選本中擇入。《隨園詩話》的批者滿洲人某說:“鐵冶亭輯八旗人詩為《熙朝雅頌集》,使時帆(法式善)董其事。其前半部,全是《白山詩選》,后半部則竟當作買賣做。凡我旗中有勢力者,其子孫為其祖父要求,或為改作,或為代作,皆得入選。竟有目不識丁,以及小兒女子,莫不濫廁其間。”(見1982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隨園詩話》后附“批本隨園詩話批語”)明清兩代詩文選本為標榜聲氣而編者不少,但如此貶斥此集,復核本書,似言之過甚。因為滿洲許多人關系高層的政治斗爭,完全做成“買賣”是不可能的。
全書分首集二十六卷,共收五十六人作品;正集一百零六卷,收作者五百三十余人,余集二卷收十六人。
此書有清嘉慶間內務府刻本,甚精美。
179 《湖海詩傳》
清詩總集,四十六卷,清王昶編纂。昶(1724~1806)字德甫,號蘭泉,又號述庵,江蘇青浦(上海市松江縣)人。早有詩名,與王鳴盛等合稱“吳中七子”。乾隆十九年(1754)進士,歷官內閣中書、刑部右侍郎,參與纂修《大清一統志》,工詩詞,著述甚富。
王氏交游廣泛,游宦四方,與文人墨客多有往來,常以詩文相贈,如其《自序》云:“予弱冠后出交當世名流,及?登朝寧,鰎歷四方,北至興桓,西南出滇蜀外,賢士大夫之能言者,攬環結佩,率以詩文相質證,披讀之下,注錄其最佳者,藏之篋笥名曰《湖海詩傳》。”《湖海詩傳》是繼《清詩別裁》而編選。
全書收錄作者六百余人,起自康熙五十一年(1712),止于嘉慶八年(1803),前后近百年,絕大部分是《清詩別裁》所不及收錄的。此期間為清詩中衰期間,著名作者不少,“性靈”“格調”“肌理”三派亦風行于此時,但從反映社會內容的廣泛,思想感情的深沉和藝術風格的多樣等方面來看是不如明末清初的,而王氏又是沈德潛門生,錄其衣缽尊崇唐音,以“格調派”眠光為去取標準,以己律人,而不能各隨人之所長,故所取者往往膚庸平弱,徒存聲調,土偶衣冠。
書中編排以作者科第為序,其間布衣韋帶之士則以年齒約略附之,人不求全,詩不求備,意在借詩存史,俾有益于論世知人。故在每人姓名之下各附小傳,間記有關詩人之遺聞佚事,或詩話評論。其所著《蒲褐山房詩話》體裁全仿朱彝尊《靜志居詩話》,逐條附在每位詩人之后,其史料極為豐富,九十年間的朝野文獻多賴之以存。《湖海詩傳》中所收錄的江浙人十居八九,而其他地區的作者則收錄較少,作為一代總集則為不足。
此書最早刻本為嘉慶癸亥(1803)三茆漁莊刊本。常見者有商務印書館民國間排印《國學基本叢刊》本,此版有1958年重印本。
180 《清詩鐸》(國朝詩鐸)
詩清詩選集,二十六卷,清張應昌編。應昌(1790~1874)字仲甫,號寄庵,浙江錢塘(浙江杭州)人。嘉慶十五年(1810)舉人,官至內閣中書舍人。
張氏處于內憂外患深重的時代。太平天國起義曾席卷多半個中國,英法聯軍曾攻入北京,清政府曾多次與帝國主義侵略者簽訂喪權辱國的條約。階級矛盾、民族矛盾刺激了他,他編選這部比較能反映從清朝建立以來全面的社會情況的詩集,以供清統治者采擇,并用以警醒世人。
全書所選上自清初,包括明遺民,下至清同治間,共錄詩五千余首,作者九百五十一人。張氏《自序》云:“嘗讀子美《潼關吏》《石壕吏》諸篇及香山、文昌、仲初《新樂府》,洵所謂言易知、感易入者。當今之世,不少子美、香山、文昌、仲初之詠,散見于各集中。爰就所見,選輯匯編,名曰《國朝詩鐸》。以為遒人之警路,以是佐太史之陳風,覽者茍興起好善惡惡之心,豈曰小補哉。”可見張應昌重視類似杜甫、白居易、張籍、王建等能夠正視現實和勇于反映現實的作品。他選錄大量的富于社會內容的詩篇,如《田家》《稅斂》《科派》《炎荒》等類目中有不少真實反映老百姓所遭受的苦難和階級矛盾尖銳對立的作品,使詩歌起到“通諷諭而抒下情”的作用。其實這些作品所展示的社會現實正是聲勢浩大的太平天國社會運動產生的根本原因。
全書所收錄作品按照所寫的內容分為一百五十二類,如“歲時”“輿地”“總論政術”“善政”“財賦”“水利”“催科”“刑獄”“鬻兒女”“民變”“酷吏”“風俗”“商賈淘金”“采礦”等,這些分類雖然基于編者選錄宗旨,但也過于瑣碎。有些分類滲透封建觀念,如“會匪”“捻匪”等。
集中也選錄了不少鴉片戰爭時期的作品,記錄了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侵略斗爭的業績,另外還有一些同情深受封建主義壓迫的婦女和揭露迷信陋俗的作品入選。其中有些詩章藝術上比較粗糙,因此這部詩集史學價值、社會學價值大于文學價值。
編者選此書下功力很大,工作始于咸豐六年(1856),終于同治八年(1869),前后共十四年,他突破大家的圈子,搜采到一些不引人注意的詩人及作品,采用了幾百種詩集和詩話,許多現已難找到。卷首所附詩人的姓名爵里、著作目錄,為研究清詩提供了線索。
本集初刻為同治八年(1869)永康應氏秀野堂刻本。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60年據此本排印出版,后附作者姓名筆畫索引,以便翻檢。
過瑣屑。不過這也是宋代書坊刻分類詩文時特有的風格。集中所收詩逾千,宋代一些題畫詩賴此以存。并可以“因詩而知畫,因畫而知詩”。北宋蘇軾“少陵翰墨無形畫,韓丹青不語詩”(《韓馬》)。張舜民“詩是無形畫,畫是有形聲”(《跋百之詩畫》)。南宋錢鍪“終朝涌公有聲畫,卻來看此無聲詩”(《宋詩紀事·次袁尚書巫山詩》)。此書名即用此意。
有清康熙間曹寅刊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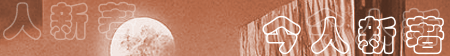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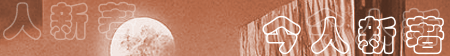
![]() web@guoxue.com
web@guoxue.com ![]() 010-68900123
010-68900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