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 《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
古詩總集,五十四卷,近人丁福保編纂。福保(1874~1952),字仲祜,號疇隱居士,江蘇無錫人。畢業于南菁書院,后學醫,中西貫通,以西醫為業,喜藏書刻書,曾輯《歷代詩話續編》《說林解字詁林》等書。
此書上起西漢,下至隋代收作者七百余人。全書分《全漢詩》《全三國詩》《全晉詩》《全宋詩》《全齊詩》《全梁詩》《全陳詩》《全北魏詩》《全北齊詩》《全北周詩》《全隋詩》等,依時代先后和地理位置(先南后北)編次為十一集。
丁氏編此書只以馮惟訥《古詩紀》為依據,參酌馮舒之《詩紀匡謬》,刪去馮書中的前集、外集和別集(詩論、詩評、品藻、雜解以及考證等)并增入了唐許朝宗所輯《文館詞林》殘卷中所載各詩,其他則一仍其舊,沒有吸取清楊守敬為補馮書之不足而作的《古詩存目》中的成果。有些地方不僅沒有訂正馮書之失反而又增加了新的錯誤。如馮書錄吳均《古意》七首,其中五首原出于《玉臺新詠》的《和蕭冼馬子顯古意》六首。馮書未能根據《玉臺新詠》而全部收入,丁氏據此刪去馮書之《古意》七首,錄入《玉臺新詠》六首,遂使吳集增入一首而脫去兩首。諸如此類例子還有一些。但此書搜羅還是較馮書完備,又系排印,卷帙稍簡,故較流行。
有中華書局1959年排印本。
47 《先秦漢魏南北朝詩》
古詩總集,一百三十五卷,今人逯欽立編纂。欽立(1910~1973)字卓亭,筆名祝本,山東省鉅野人。1942年畢業于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一度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解放后一直在東北師范大學任教。
此書是上起上古下至隋代的詩歌總集(《詩經》《楚辭》不錄)。在馮惟訥《古詩紀》基礎上糾正了馮書搜輯、考訂不審之失。全書以時代先后為次,各代之中先諸家、次謠諺、再次郊廟歌辭,最后為釋道鬼神之詩。此書充分運用了新發現的資料,包括國內已佚的古籍(如從日本傳回的唐許朝宗《文館詞林》殘卷)、地下發掘物和敦煌石室中的遺卷(如漢簡中的《風雨詩》、敦煌石室中《老子化胡經》的玄歌等),并從碑帖、方志、釋、道經藏、類書輯出許多為馮氏和丁福保所遺漏的詩歌謠諺,大大豐富了馮書,并訂正了馮書一些錯誤。如把宋王令的《於忽操》誤作龐德公的作品(此詩假托龐德公之歌),把晉應亨的《四王冠詩》誤編排在漢朝等。書中所錄之詩均注出處,并作了多方面的考證。對作品真偽、作者、時代、題目、體裁、時間、順序以及作品的完整與否等問題都作了詳盡的考訂,以確保提供資料的可靠性,編者在輯詩時掌握偏嚴,使一些作品可以錄入而未錄入,則是此書不足之處。另外一些難于確定時代的可作附錄處理,以給研究者檢尋之便。
有中華書局1983年排印本。
48 《古今詩刪》
古至明詩的流派選本,三十四卷,明李攀龍編選。攀龍(1514~1570)字于鱗,號滄溟,歷城(山東省濟南市)人。少孤家貧,嘉靖進士,官至河南按察使。明代著名詩人,他與王世貞為“后七子”之首,倡“詩必盛唐”之說。
此書一至九卷為古詩,卷十至二十二為唐詩,二十三至卷末為明詩,中間不選宋元詩,每代各自分體編排。這是一個去取很嚴的選本。王世貞說:“今于鱗以意輕退古之作者間有之;于鱗舍格而輕進古之作者則無是也。”因為嚴格,所以此書“得存而成一家言”,體現了李氏論詩觀點。如其論五古則推崇漢魏,竟說“唐無五言古詩”,即沒有李氏所肯定的那種五古,所以他說:“陳子昂以其古詩為古詩,弗取也。”像杜甫“三吏三別”《北征》《詠懷》等震撼千古的名篇都未入選。其論七古則贊美“初唐氣格”,因而批評李白之七古,言其“縱橫往往強弩之末,間雜長語,英雄欺人耳”。如《蜀道難》《夢游天姥吟留別》都被刪去。論七律則認為王維、李頎“頗臻其妙”,對于杜甫卻說“篇什雖眾,憒焉自放”,使人難以理解。李氏復古思想嚴重,論及某種詩體往往以此體最初的名篇為體式風格的標準,不合于此者,便予以否定,這實際上是否認了文學體式的發展,書中以唐詩與明詩接,中間跳過了三四百年,認為宋元無詩,這種做法為后世讀者所不滿。如“四庫”館臣所言:“且以此選而論,唐末韋莊、李建勛距宋初閱歲無多;明初之劉基、梁寅在元末吟篇不少,何以數年之內,今古頓殊;一人之身,薰蕕互異?此真門戶之見,入主出奴,不緣真有斷限。”編者卻很自信,說“后之君子本茲集以盡唐詩,而唐詩亦盡于此”。后來坊間據此選唐詩部分,加以箋注、評論名為《唐詩選》,這純粹是書商所為,李氏未編著是書。
《古今詩刪》有明嘉靖中刻本。
49 《古詩歸》
古詩流派選本,十五卷,明鐘惺、譚元春合編。
惺(1547~1624)字伯敬,號退谷,竟陵(湖北省天門縣)人。萬歷進士,官至福建提學僉事。論詩反對擬古,提倡獨抒性靈,描寫“幽深孤峭”的境界。為竟陵派創始人。元春(1586~1673)字友夏,竟陵人,天啟末鄉試第一,為竟陵派中堅。
鐘、譚論詩,主張詩應寫“真有性靈之言,常浮出紙上,決不與眾言伍”。對于因為前、后“七子”的提倡而形成的“滯熟木陋”的詩風十分不滿。他們說:“古人以此數者收渾沌之氣,今人以此數者喪精神之原。”他們用此選本貫徹詩應在“精神上求變”之宗旨,提倡“幽深孤峭”的藝術風格。目的在求古人真詩所在,以糾正前、后“七子”的膚廓之病。在選詩之后時有評語,但因為其見解不高,往往“點逗一二新雋字句,矜為玄妙”。有時還鬧出笑話,如謝靈運《登廬山絕頂望諸嶠》詩,六句,是殘篇,鐘、譚二氏把它作為完整詩篇選入,并說:“六句質奧,是一短記。”還說:“他人數十句寫來,未必如此樸妙。如此大題目,肯作三韻,立想不善。”據我所知至少還能為此詩補上四句,鐘、譚二人的褒揚,仿佛是廉價的奉迎。對于“連篇之詩,隨意割裂”,“古詩字句,多隨意改竄”,也為后人所不滿。其入選之詩也有不盡適合之處,如焦贛《易林》之語為卜筮文字,列入選本似不妥。
有明萬歷間刻本。
50 《古詩鏡》
古詩選集,三十六卷,明陸時雍編選。時雍字昭仲,號澹我,桐鄉皂林鎮(今浙江桐鄉)人。工詩文,尚氣節,髫年游泮,崇禎癸酉(1633)下詔舉巖穴之士,時雍與之,然終不遇,久留北京,因寄館于順天丞戴澳家,澳因事被劾,拉時雍以為證,下獄,卒于獄中。
陸氏論詩注重“感通”,他說孔子刪詩“存止三百,亦取感通之至捷者耳,后之人必以義斷,則鄭衛何以并存也”。并說:“是非之畛,理義之辯,必附性情而后見。”表現出他對明中葉以來只在格律聲調上下功夫,徒摹聲響,不見才情的前、后“七子”詩歌創作的不滿。他說:“道發聲落,情通神達,靈油油接于人,而不厭鳥之‘關關’,鹿之‘呦呦’,未聞其何韻之遠,何律之調也。”這個選本就是貫徹他的論詩主張的選本。他說:“是選不惟其詞而惟其情,不惟其貌而惟其意。使天下聞聲而志起,意喻而道行。”(皆見《序》及總論)注重情深意遠的作品,選擇較精,去取較嚴,因此,這個選本在明清之際是較好的。但由于其說重于神韻,重視情深意遠的作品,對于敘事詩和以議論為主的詩則評論不當。如把《古詩為焦仲卿妻作》附于“樂府古辭”之后,言其情詞紕謬,稱之傳奇則可,作為詩則稍嫌繁絮。
有明原刊本,常見者有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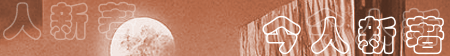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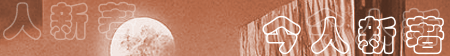
![]() web@guoxue.com
web@guoxue.com ![]() 010-68900123
010-68900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