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詩總聞》
《詩經》注本,二十卷,南宋初王質撰。質(1135~1188)字景文,號雪山,興國(江西省興國縣)人。紹興三十年(1160)進士,官至樞密院編修,為人耿直,為權貴所嫉。出判荊南府,改吉州,皆不行。以奉祠終。
作者力圖擺脫傳統的漢學體系的束縛,廢除《詩序》,不循毛鄭,完全按照自己對《詩經》原文的理解闡釋詩意。其書取詩三百篇,每篇說其大義,后有《聞音》《聞訓》《聞章》《聞句》《聞字》《聞物》《聞用》《聞事》《聞人》共十門,以注解字音、詞義,名物制度,介紹時代背景和點明詩之主旨。每篇又有《總聞》,是對一篇詩的總論。又有《聞風》《聞雅》《聞頌》冠于“四始”(四始:《史記·孔子世家》:“《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之首。此書在廢序解詩時也增添了一些新的穿鑿附會,如書中將情思婉轉,優美生動的《月出》和丑惡的夏征舒、夏姬事件(夏征舒、夏姬事見《左傳·宣公九年、十年》陳國君靈公、大夫孔寧,儀行父皆與夏征舒之母夏姬通奸,君臣以此為戲,后征舒殺靈公)扯在一起,其荒謬可以想見。但其中許多篇章中,注者能結合日常生活感受解釋詩意。如《女曰雞鳴》注者釋曰:“當是君子與朋友有約,夫婦相警以曉,恐失期也。”這就比《詩序》所言“陳古義以刺今,不悅德而好色也”,更合于情理。
此書在寫出之后五十年方能付梓。現有清武英殿聚珍版本,另有商務印書館民國間所編《叢書集成》本。
7 《詩集傳》
《詩經》注本,八卷,南宋朱熹撰。熹(1130~1200)字元晦,一字仲晦,號晦庵,別號紫陽,婺源(江西省婺源縣)人。高宗紹興十八年(1148)進士,歷官知南康軍、秘閣修撰,寶文閣待制,一生講學不倦,著述甚富,為宋代最大的理學家。
注者打破了對《詩序》的迷信,批判了漢學對《詩經》的歪曲;但也繼承漢學的合理部分。特別是在注釋字詞音義之時多采《毛傳》和齊、魯、韓三家詩說,簡明扼要,實事求是。并在訓詁之外,還用平易淺切的文字疏通句意、段意,便于初學者理解。朱氏也注意到《詩經》的文學性質,他對《詩經》的解釋在一定程度上偏離了經學軌道。如他認為“風詩多出于里巷歌謠之作”,其大多數詩篇“乃是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的民歌,并認為“雅”詩中必有一些是文士抒情之作。在對詩的注釋中,他還注意結合篇義、章句、對比、興、賦、詞氣、用韻、篇章結構等藝術手段作了較為中肯的分析和評論。書中將《邶風·靜女》《衛風·木瓜》等二十四篇定為男女淫佚之詩,甚至把青年男女勇敢相愛說成“蕩然無羞愧悔悟之萌”,開王柏《詩疑》刪詩之端。
宋以后理學成為官方哲學,《詩集傳》則成為士子必讀之書,其流傳之廣,影響之大,在《詩經》注本中是少見的。
此書刻本極多,有中華書局1958年排印本。
8 《詩疑》
二卷,南宋王柏撰。柏(1197~1274)字會之,號魯齋,金華(浙江省金華市)人,為朱熹三傳弟子,曾被聘為麗澤、上蔡兩書院之師,為宋末大儒,著作甚富。
此書上卷為《詩說》,下卷為《詩辨》,王氏論詩不信《詩序》,不信《毛傳》《鄭箋》,不信《左傳》記事,也不完全相信朱熹對《詩經》的解釋。他認為《詩經》傳本在文字上有脫簡、錯簡、竄亂等重大錯誤,曾說:“秦法嚴密,詩無獨全之理。竊意夫子已刪去之詩,容有存于閭巷浮薄者之口,蓋雅奧難識,淫俚易傳。漢儒病其亡逸,妄取而攛雜,以足三百篇之數,愚不能保其無也。”因此他把《詩經》中描寫愛情的詩篇都定為“淫奔之詩”,是漢儒據“閭巷浮薄者之口”所傳唱的淫俚之曲而補入《詩經》的。因此,他“律以圣人之法,當放亡無疑”。刪去的名篇有《靜女》《野有死》《氓》《將仲子》《褰裳》《溱洧》《月出》等三十二篇。另外,王氏還毫不理會《詩經》中作品在音樂、聲歌方面的意義,反對以“風”“雅”“頌”分類,主張以義理為歸,把《豳風》中的七首詩歸為“變雅”,主張把《碩人》篇的四章并為三章。這些大膽的主張不僅反映宋代疑古學風達到了頂峰,也表現出理學家文藝觀點的荒謬與迂腐。
此書常見者有清通志堂刻本和中華書局1955年排印的《古籍考辨叢刊》本。
9 《詩經通論》
《詩經》注本,十八卷,清姚際恒撰。恒字立方(或謂善夫),號首源,祖籍新安(安徽省歙縣),長期居住在浙江省的仁和(杭州市),與毛奇齡同時并與之交好。其晚年著《九經通論》共一百七十卷,此書為其中之一。
該書不依傍《詩序》,也不附和《詩集傳》,擺脫了漢學、宋學的門戶之見,指出兩家各有所長。作者“惟有涵詠篇章,尋繹文義,辨別前說,以從其是而黜其非”。他認真研究《詩經》原文,從詩的內容探求詩義;他深入考證書史,逐一檢查各家注疏,然后以嚴謹態度自由立論。如《野有死》一詩則臚列眾說(如歐陽說、朱熹說、毛鄭說以及其他的種種說法)并加以一一駁斥,立論說:“此篇是山野之民相與及時為昏姻之詩。昏禮,贄用雁,不以死;皮、帛必以制。皮、帛,儷皮、束帛也。今死、死鹿乃其山中射獵所有,故曰‘野有’,以當儷皮;‘白茅’,潔白之物,以當束帛。所謂‘吉士’者、其‘赳赳武夫’者流耶?‘林有樸賦’亦‘中林’景象也。”抓住了禮制與原始狩獵相合之處(禮制許多條款起源于原始社會的生產與生活),從而對詩義解釋比較準確。全書除了逐章串講詩句通解全篇意旨外,還有對詩的藝術表現手法的評述。
有中華書局1958年排印本。
10 《毛詩稽古篇》
《詩經》注本,三十卷,清陳啟源撰。啟源字長發,吳江(江蘇省吳江縣)人,精研經學歷時十四年,而于康熙丁卯(1687)成此書。
陳氏以復興漢學,排擊宋學而自命,其論詩以《毛傳》為本,其所辯正者以朱熹《詩集傳》為多,次及歐陽修《毛詩本義》、呂祖謙《讀詩記》、嚴粲《詩緝》。前二十四卷依次說詩,不載經文,但標篇目。其中訓詁依《爾雅》、題解依《詩序》,詮釋內容則參照毛、鄭,由此進而推求詩義,重新解釋毛詩。從二十五卷到二十九卷為《總詁》,其中分《舉要》《考異》《正字》《辯物》《數典》《稽疑》六部分。《舉要》完全肯定《詩序》,他說:“詩有小敘猶《春秋》之有《左傳》,”毛序之有“齊、魯、韓猶《左傳》之有公、谷。”書中“引證之書,必明著于編”“凡有辯證,必述原書”。對于“不知者闕疑”,不隨意妄論。后《附錄》一卷,統論“風”“雅”“頌”意旨,也有所創獲。在書寫時多用篆文,以存古義。此書也有時以佛家和道家之說解詩,如在《附錄》卷中提到“捕魚之器”時說:“俗敝民訛,機巧日滋,肆為不仁之器,殘害水族,是可?也。夫此廣殺物命,恬不知怪,非大覺緣果之文,豈能救之哉!”陳氏著此書標志著漢學與宋學在《詩經》研究領域分道揚鑣,自此清代乃有漢學。
書未能及時出版,清乾隆間收入《四庫全書》。手稿在龐黼廷家,嘉慶間龐氏刊刻出版。
常見者有道光間學海堂《皇清經解》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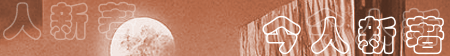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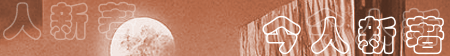
![]() web@guoxue.com
web@guoxue.com ![]() 010-68900123
010-68900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