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東 |
|||
|
[清]
張潮 著
趙曉鵬 李安綱 述論 前
言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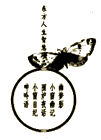 |
|||
|
|
||||
|
|
||||
|
087 詩文與詞曲 詩文之體,得秋氣為佳;詞曲之體,得春氣為佳。 [原評] 江含徵曰:調有慘淡悲傷者,亦須相稱。 殷日戒曰:陶詩、歐文,亦似以春氣勝。 [述論] 言為心聲,文以載道,詩表情思,這是語言和文學之所以產生的根源,也是其根本的目的所在。沒有心聲或者真理、情思,自然也就不需要語言或者文學了。因此,如果要創作詩詞、文章和歌曲,就一定要表現自己的心聲、真理或者情思。否則,文學也就沒有絲毫的價值了。 雖然說文章乃是人類性情之流露,思想之表達,但是詩文體裁不同,方式不同,所要求的風格與手法也都有所不同。曹丕的《典論·論文》說過: 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 這里,明顯提出了四種文體科目的區別和風格的差異。到了陸機的《文賦》,更加明確地提出了文體的風格和手法區別來: 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凄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 的確,我們在寫文章的時候,自然而然地要考慮到文章的內容與文章的體裁。什么體裁合乎什么樣的內容,什么樣的方式能夠創造出什么樣的風格,等等,都是我們要調整和著力的地方。只有這文質并重了,風骨吻合了,才能說你會作文了。 說到詩歌和散文,乃是文壇的正統,因而必須要端莊清肅,所以說宜得秋日的肅殺之氣,簡潔而洗練;詞和曲乃是詩文之別調,談敘的多為細膩之情感,所以應得春天的祥和之氣。如此,才算是到達了佳妙的境地。陳子昂的《與東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云: 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漢魏風骨,晉宋莫傳,然而文獻有可征者。仆嘗暇觀齊梁間詩,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每以永嘆。 就是嫌文章沒有秋氣,而都是繁彩之春氣。杜甫的《戲為六絕句》也說道: 不薄今人愛古人, 清辭麗句必為鄰。 竊攀屈宋宜方駕, 恐與齊梁作后塵。 明確指出詩歌創作應該是清詞麗句,而不是如齊梁的繁文彩艷。到了韓愈,更是"惟陳言之務去"、"詞必己出"等,完全使詩文擺脫了繁艷縟麗的風格,而具有簡潔明了的特色。 至于詞曲,則自然與詩文相異。蘇軾以詩為詞,氣魄大哉大矣,但是卻終究不是本色。有個故事說,他官翰林學士時,問自己的幕僚說:"我詞何如柳七?" 對方答道:"柳郎中(柳永)詞,只合十八七女郎,執紅牙板,歌'楊柳岸,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銅琵琶,綽鐵板,唱'大江東去'。" 這正說明一個問題,詞曲都是歌館青樓女子們唱的。蘇軾盡管有開拓詞境之功,但卻不是詞曲本色,所以遭到了李清照《論詞》的批評: 至晏元獻、歐陽永叔、蘇子瞻學際天人,作為小歌詞,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讀不葺之詩爾,又往往不協音律者。 就因為這"詞別是一家",也就必須具備這種體裁的需要和風格。那關西大漢如何能夠用銅琵琶和鐵板演奏呢?畢竟不是本色啊! 當然,這也是就一般的風格而言的。比如說陶淵明的詩和歐陽修的文章,也都是靠著春氣取勝的。就如陶詩的平淡和溫柔,清麗和明快;還如歐文的歡快和流麗,都不見得就是秋日里的殺氣。而詞、曲盡管表現情感和春意,但一些調子本身就哀傷者,怎么還能夠唱出溫暖如春的歌詞呢?總之,以內容與形式即文與情統一方好!
|
||||
|
|
||||
|
中國社會出版社
|
||||
|
||||
版權所有 首都師范大學中國詩歌研究中心 聯合主辦
Copyright© 2000
北京國學時代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 mailto:web@guoxue.com
mailto:web@guoxue.com
![]() mailto:yyyinxl@sohu.com
mailto:yyyinxl@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