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東 |
|||
|
[清]
張潮 著
趙曉鵬 李安綱 述論 前
言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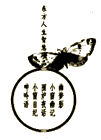 |
|||
|
|
||||
|
|
||||
|
082角度與效果 松下聽琴,月下聽簫,澗邊聽瀑布,山中聽梵唄,覺耳中別有不同。 [原評] 張竹坡曰:其不同處,有難于向不知者道。 倪永清曰:識得“不同”二字,方許享此清聽。 [述論] 音樂講究共鳴,有共鳴才有韻味。松樹之下,清風泠泠,本已具有聲韻,加上琴聲瑯瑯 揚揚,自有一番超然世外的感觸;明月之下,萬物朦朧,原自富于情調,襯以簫韻悠揚婉轉, 定會產生如幻如化的妙趣。在溪澗邊傾聽那遠方傳來的瀑布之聲,澗水嘩嘩,瀑聲洪洪,洪 洪嘩嘩,仿佛是一首協奏曲;在深山中靜聽著寺院發出來的梵唄之聲,山中萬籟俱寂,梵唱 清音入耳,益發顯得清凈妙樂,不是仙佛而勝似仙佛了。 這種美妙的組合,便有超然的境界,可惜能如此領略的人太少了。原因在于人們樂于感 官的逐獵,已經習耽于絲竹之樂,而失去了對自然清聲的鑒賞能力。音樂本身就是對大自然 聲音的模仿,起初簡單,往后則愈來愈繁復,離開原初的樸素淳厚也就愈遠了。 孔子從儒家的角度來認識和觀察世界,強調建立一個以仁義相標榜的社會。而能夠實現 這一理想,就必須讓人們擁有自覺的仁義之心,這就需要禮樂的輔助。所以,他一生為之奮 斗的,就是克己復禮,使音樂成為雅樂,從而使人們得到真正的音樂教化。 他認為鄭國和衛國之音樂歌聲淫蕩,所以要奮力恢復正聲雅樂,以完成其克己復禮的大 業。盡管歷史記載,他自從衛國返回魯國,而后音樂就被更正了。但是,畢竟是潮流所尚, 鄭衛之聲卻終究取代了周文王和武王的高雅音樂,朝著越來越流行的目標發展了下來。 然而,我們應該看到,人們所追逐的聲、色、犬、馬,雖然能夠滿足一時的耳目口腹之 娛,但畢竟使我們自己的心神日益外馳,魂不守舍,勢必會導致我們心理和生理的崩潰和變 異。因此,《老子》大聲地疾呼: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 他要勸告人們閉目塞聰,去掉心智,而返璞歸真。若是我們不去追逐聲色,而歸心于自 然,則如劉禹錫《陋室銘》中說的那樣: 可以調素琴,閱金經,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 自然就會有一份清賞了。 當然,為什么要有這樣的分別呢?能夠明白了這個道理,也就可以說真正知道聲音的奧 妙了。這里,筆者只想談談自己在終南山法華寺聽圓照大師及其他法師誦唱梵唄時的情形, 這一 段在拙著《圓照法師與金剛心法》中: 吃完晚飯,山里已是一片月色朦朧,涼風習習,更增添了山寺的神秘氣氛。…… 我們仿佛置身于紅塵之外,走進了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之中,陶醉在大自然的醇釀里。 晚課時間到了,小尼姑如珠落玉盤、韻味悠揚的梵音,法鼓鐘磬,婉轉鏗鏘,似乎要界 破這朦朧的月和奇妙的夜,去領略那宇宙深處的玄奧和秘密。北屋里,大師那洪亮圓潤的聲 音正諷誦著梵語的秘咒,時不時地一聲法鈴響起,余韻回環,仿佛是一架發射臺,將電波向 四面八方散去,載著那宇宙的真諦和奧秘,傳達到了每一個角落。接收的和發射的,共同交 織起來,組成了大自然中最美妙的奏鳴曲,使人心曠神怡,塵念頓消,飄飄然有欲仙之慨! 這只是我自己的一種感覺而已。當然,人們各自的境界不同,所領略到的也自然不同。
|
||||
|
|
||||
|
中國社會出版社
|
||||
|
||||
版權所有 首都師范大學中國詩歌研究中心 聯合主辦
Copyright© 2000
北京國學時代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 mailto:web@guoxue.com
mailto:web@guoxue.com
![]() mailto:yyyinxl@sohu.com
mailto:yyyinxl@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