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東 |
|||
|
[清]
張潮 著
趙曉鵬 李安綱 述論 前
言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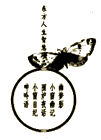 |
|||
|
|
||||
|
|
||||
|
045 詩僧與詩道 詩僧時復有之。若道士之能詩者,不啻空谷足音。何也? [原評] 畢右萬曰:僧、道能詩,亦非難事;但惜僧、道不知禪玄耳。 顧天石曰:道于三教中,原屬第三。應是根器最鈍人做,那得會詩!軒轅彌明, 昌黎寓言耳。 尤謹庸曰:僧家勢利第一,能詩次之。 倪永清曰:我所恨者,辟谷之法不傳。 [述論] 僧、道乃是佛、道兩教的教團和護法。能作詩的僧人往往還有幾個,可道士里 面能作詩的卻絕少。仿佛是空曠無人的山谷響起了腳步聲,不可能。這到底是怎么 回事呢? 當然,要回答這一問題,不僅要從道、僧的本身素質上找原因,關鍵的問題還 出在各家的教旨和為人處世的態度上。 佛教乃古印度迦毗邏衛國凈飯王的王子釋迦牟尼所創立的,以解脫痛苦為宗旨, 建立起了一套完整圓融的有關宇宙和人生的理論體系。尤其是那大乘般若部的經典 如《金剛經》、《心經》、《楞嚴經》等等,加上翻譯的美妙,本身就仿佛是一首 耐人咀嚼的詩篇,境界遼迥,無掛無礙。 而中國古時的出家人多為學者,或者常與儒者相往來,唱酬過從,自然不會庸 俗,能詩者極多。況且“世間好話佛說盡,天下名山僧占多”,山川秀麗,梵剎鐘 磬,的確為他們的詩詞的創作提供了靈感和慧根。 佛經中有許多偈頌,句子整齊,加以韻腳,調以平仄,便是一首妙詩。盡管凈 土宗以念佛為本,但禪宗的旨意還是要參禪悟道,心下直指;或者如天臺、華嚴, 講究心性三千,一念三千;或者如唯識宗,講究三界唯心,萬法唯識等。這種方法, 正與詩人捕捉靈感的途徑一模一樣,所以許多禪僧也正用詩歌來表達自己的悟境, 成為了一種風尚。 比如唐代著名的詩僧就有寒山、皎然、貫休、齊己等,都很有名氣。齊己有一 首《早梅》詩,寫得很有意味: 萬木凍欲折, 孤根暖獨回。 前村深雪里, 昨夜一枝開。 風遞幽香出, 禽窺素艷來。 明年如應律, 先發望春臺。 還如那個對律詩很有研究,并且寫出了《詩式》的僧皎然,有一首《尋陸漸鴻 不遇》的詩: 移家雖帶郭, 野徑入桑麻。 近種籬邊菊, 秋來未著花。 扣門無犬吠, 欲去問西家。 報道山中去, 歸來每日斜。 說這些詩好,主要是說它們都有詩的境界和意味,符合于文人詩家的創作原則。 道教則有所不同。縱然老、莊的著作已像一首詩,比如《道德經》第十二章云: 五色使人目盲, 馳騁田獵使人心發狂, 難得之貨使人之行方。 五味使人口爽, 五音使人之耳聾! 的確已經是很美妙的韻文了。 但是,道教的祖師張道陵等人卻文化修養并不高,沒有佛教那樣的完整理論, 只有借老、莊的理論來立教。直到南北朝時的陶弘景、抱樸子等人,才依據佛教的 體系初步建立了道教的理論傳統。但道教主要借助方術、煉丹術,以求成仙、長生, 所以很少有人去像僧人那樣寄情于山水,或者培養什么境界。 能詩的道士也有,比如呂巖、王重陽等,但卻畢竟還是少數。原因在于他們所 注重的是法術、服食以及后來的內丹修煉,已無精力或者無心再顧及身外的自然美 景和文章詩賦了!即是有,亦是勉而為之,應酬而已。 根據《全唐詩》中的記載,能詩的道士,在數量上遠遠超過了詩僧,但有成就 的卻不多。后來,修行的道士幾乎都能詩,尤其是全真道士。只不過他們的詩詞都 是為了教化的目的而寫的,多講的是宇宙自然生命的大道,并不在乎什么意境之類 的。 從哲理詩的角度看,我們并不能說他們寫得不好。因為詩是言志的,不見得非 要去寫什么外在的風景不可。能夠的把心中的境界或者人生觀、世界觀寫出來,就 是很可以的了。《西游記》中所引的詩詞,都是道教的金丹學詩詞。其中好耐人尋 味的也并不少,就是那些文人們往往都帶著偏見,只認為出言蘊藉的而且是寫自己 的感情的才算詩歌,而那些真正符合了“詩言志”標準的其他詩詞作品就不能算做 詩歌了。 比如宋代的道教南宗祖師張伯端的《悟真篇》就寫得不錯,《西游記》中就引 用了他的很多詩詞。如第十四回“心猿歸正,六賊無蹤”一開篇,就引了他的《即 心即佛頌》,其中說道: 佛即心兮心即佛, 心佛從來皆妄物。 若知無佛復無心, 始是真如法身佛。 法身佛,沒模樣, 一顆圓光含萬象。 無體之體即真體, 無相之相即實相。 非色非空非不空, 不動不靜不來往。 無異無同無有無, 難取難舍難聽望。 內外圓明到處通, 一佛國在一沙中。 一粒沙含大千界, 一個身心萬個同。 知之須會無心訣, 不染不滯為凈業。 善惡千般無所為, 即是南無及迦葉! 如果從文學或者藝術的角度說,也許能夠挑出一些毛病來。但是,從他自己所 領悟到的境界來說,確實是難以企及的。因為到不了他所修行的人生境界,是無法 真正理解那種味道的。他本身就是一首超越了凡俗的詩篇,寫出來的也只是糟粕而 已。 韓愈集中有《石鼎聯句詩序》,稱衡山道士軒轅彌明善詩,與進士劉師服、校 書郎侯喜以石鼎為題而聯句賽詩,而道士的詩卻是高古而出群的。但顧天石認為道 士都不能寫詩,所以說韓愈的序言只是一篇寓言而已,不是真有其人。 反過來說,為僧入道的目的,是要探索人生真正的奧秘所在,所以以修行實證 為目標,絕不把詩歌文字當做追求的事業。往往那些能詩的僧道,只顧去把自己禁 錮在什么格律聲韻的束縛當中,自然也就玩物喪志,如畢右萬說的“不知禪玄耳” 了!
|
||||
|
|
||||
|
中國社會出版社
|
||||
|
||||
版權所有 首都師范大學中國詩歌研究中心 聯合主辦
Copyright© 2000
北京國學時代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 mailto:web@guoxue.com
mailto:web@guoxue.com
![]() mailto:yyyinxl@sohu.com
mailto:yyyinxl@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