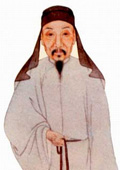
顧炎武
字號:原名絳明亡,字忠清;后改名炎武,字寧人,亦自署蔣山傭
生卒:公元1613年~1682年
朝代:清初
籍貫:江蘇昆山
評價:清學“開山始祖”,清初繼往開來的一代宗師
一、“明道救世”的經世思想
面對當時黑暗的社會現實,顧炎武認為當務之急在于探索“國家治亂之源,生民根本之計”(《亭林佚文輯補·與黃太沖書》)。他在纂輯的《天下郡國利病書》中,首先關注的是土地兼并和賦稅繁重不均等社會積弊,對此進行了有力的揭露,指出“世久積弊,舉數十屯而兼并于豪右,比比皆是”,乃至出現了“有田連阡陌,而戶米不滿斗石者;有貧無立錐,而戶米至數十石者”的嚴重情況。在所撰寫的《軍制論》、《形勢論》、《田功論》、《錢法論》和《郡縣論》中,他探索了造成上述社會積弊的歷史根源,表達了要求進行社會改革的思想愿望。他指出“郡縣之弊已極”,癥結就在于“其專在上(《文集》卷一),初步觸及到了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問題,從而提出了變革郡縣制的要求。他指出,”法不變不可以教今……而姑守其不變之名,必至于大弊“(《文集》卷六)。在《日知錄》中,他更是明確地宣稱自己的撰寫目的就是:“意在撥亂滌污,法古用復,啟多聞于來學,待一治于后王”(《文集》卷六),并強調“君子之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文集》卷四)。
顧炎武在“明道救世”這一經世思想的指導下,提倡“利民富民”。他認為,“今天下之大患,莫大乎貧”(《文集》卷一),因而認為“有道之世”,“必以厚生為本”(《日知錄》卷二),他希望能逐步改變百姓窮困的境遇,達到“五年而小康,十年而大富”(《日知錄》卷二)。他不諱言“財”“利”。他說:“古之人君,未嘗諱言財也。……民得其利,則財源通而有益于官;官專其利,則財源塞而必損于民。”(《日知錄》卷十二)他認為問題不在于是否言財言利,而在于利民還是損民,在于“民得其利”還是“官專其利”。他認為自萬歷中期以來,由于“為人上者”只圖“求利”,以致造成“民生愈貧,國計亦愈窘”的局面。由此,他主張實行“藏富于民”的政策,認為“善為國者,藏之于民”。并且指出只有這樣,才是真知其“本末”的做法(《日知錄》卷十二)。
顧炎武也和黃宗羲、王夫之一樣,從不同的角度對“私”作出了肯定,并對公與私的關系作了辯證的論述。他說:“自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而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以不能免矣。……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此所以為王政也。”(《日知錄》卷四)這就把人之有私看作是完全合乎情理的現象,并且認為“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文集》卷一)他的這種利民富民和“財源通暢”的主張,以及對“私”的肯定,都反映了當時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萌芽狀態下新興市民階層的思想意識。
顧炎武從“明道救世”的經世思想出發,還萌發了對君權的大膽懷疑。他在《日知錄》的“君”條中,旁征博引地論證了“君”并非封建帝王的專稱,并進而提出反對“獨治”,主張“眾治”,所謂“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獨治也。獨治之而刑繁矣,眾治之而刑措矣”(卷六),強調“以天下之權寄之天下之人”(卷九)。他雖然還未直接否定君權,未能逾越封建的藩籬,但他這種懷疑君權、提倡“眾治”的主張,卻具有反對封建專制獨裁的早期民主啟蒙思想的色彩。
顧炎武“明道救世”的經世思想,更為突出的是他提出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響亮口號。顧炎武所說的天下興亡,不是指一家一姓王朝的興亡,而是指廣大的中國人民生存和整個中華民族文化的延續。因此,他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口號,就成為一個具有深遠意義和影響的口號,成為激勵中華民族奮進的精神力量。而在顧炎武的一生中,也確實是以“天下為己任”而奔波于大江南北,即令他在病中,還在呼吁“天生豪杰,必有所任。……今日者,拯斯人于涂炭,為萬世開太平,此吾輩之任也”(《文集》卷三),充分表達了他“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高尚情操。
二、“經學即理學”的學術新途徑
晚明以來,陽明心學以至整個宋明理學已日趨衰頹,思想學術界出現了對理學批判的實學高潮,顧炎武順應這一歷史趨勢,在對宋明理學的批判中,建立了他的以經學濟理學之窮的學術思想。
顧炎武對宋明理學的批判,是以總結明亡的歷史教訓為出發點的,其鋒芒所指,首先是陽明心學。他認為,明朝的覆亡乃是王學空談誤國的結果。他寫道:“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股肱惰而萬事荒,爪牙亡而四國亂,神州蕩覆,宗社丘墟。”(《日知錄》卷七)他對晚明王學末流的泛濫深惡痛絕,認為其罪“深于桀紂”。他進而揭露心學“內釋外儒”之本質,指斥其違背孔孟旨意。他認為儒學本旨“其行在孝悌忠信”,“其職在灑掃應對”,“其文在《詩》、《書》、《禮》、《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處、去就、交際”,“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罰”(同上)。他直分贊同宋元之際著名學者黃震對心學的批評:“近世喜言心學,舍全章本旨而獨論人心道心,甚者單摭道心二字而直謂心即是道,蓋陷于禪學而不自知,其去堯舜禹授天下本旨遠矣。”(同上)既然陸王心學是佛教禪學,背離了儒學修齊治平的宗旨,自當屬摒棄之列。
在顧炎武看來,不惟陸王心學是內向的禪學,而且以“性與天道”為論究對象的程朱理學亦不免流于禪釋。他批評說:“今之君子……是以終日言性與天道,而不自知其墮于禪學也。”(同上,卷七)又說:“今日《語錄》幾乎充棟矣,而淫于禪學者實多,然其說蓋出于程門。”(《文集》卷六)他還尖銳地指出:“孔門未有專用心于內之說也。用心于內,近世禪學之說耳。……今傳于世者,皆外人之學,非孔子之真。”(《日知錄》卷一八)這不僅是對陸王心學的否定,也是對程朱理學的批評。但是,在面臨以什么學術形態去取代陸王心學和程朱理學的氛擇時,卻受到時代的局限,他無法找到更科學更新穎的理論思維形式,只得在傳統儒學的遺產中尋找出路,從而選擇了復興經學的途徑:“以復古作維新”。
顧炎武采取復興經學的學術途徑,不是偶然的,而是學術自身發展的結果。從明中期以來學術發展的趨勢來看,雖然“尊德性”的王學風靡全國,但羅欽順、王廷相、劉宗周、黃道周,重“學問思辨”的“道問學”也在逐漸抬頭。他們把“聞見之知”提到了重要地位,提倡“學而知之”,強調“讀書為格物致知之要”,重視對儒家經典的研究。而在嘉靖、隆慶年間,就有學者歸有光明確提出“通經學古”(《歸震川先生全集》卷七)的主張,認為“圣人之道,其跡載于六經”(同上),不應該離經而講道。明末學者錢謙益更是與之同調,認為“離經而講道”會造成“賢者高自標目務勝前人,而不肖才汪洋自恣莫不窮潔”(《初學集》卷二八)的不良后果,他提倡治經“必以漢人為宗主”(同上書,卷二九)。以張溥、張采、陳子龍為代表的“接武東林”的復社名士,從“務為有用”出發,積極提倡以通經治史為內容的“興復古學”(《復社記略》卷一)。這就表明復興經學的學術途徑,已在儒學內部長期孕育,成為顧炎武“經學即理學”、用經學以濟理學之窮思想的先導。
顧炎武也正是沿著明季先行者的足跡而開展復興經學的學術途徑的。他在致友人施愚山的書札中就明確提出了“理學,經學也”(《文集》卷三)的主張,并指斥說“今之所謂理學,禪學也”(同上)。他認為,經學才是儒學正統,批評那種沉溺于理學家的語錄而不去鉆研儒家經典的現象是“不知本”。他號召人們“鄙俗學而求六經”,主張“治經復漢”。他指出:“經學自有源流,自漢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考究,而后及于近儒之著,然后可以知其異同離合之指。”(同上書,卷四)在他看來,古代理學的本來面目即是樸實的經學,正如全祖望所概括的“經學即理學”(《鮚琦亭集》卷一二),只是后來由于道二教的滲入而禪化了。因此,他倡導復興經學,要求依經而講求義理,反對“離經而講道”。顧炎武認為,只有這樣才能稱為“務本原之學”(《亭林文集》卷四)
此外,顧炎武還倡導“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同上)的治學方法。他身體力行,潛心研究,考辨精深,撰寫出《日知錄》、《音學五書》等極有學術價值的名著。《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在談及《日知錄》時,說:“炎武學有本原,博瞻而能貫通,每一事必詳其始末、參以證佐而后筆之于書,故引據洗繁而牴牾少。”顧炎武的學術主張使當時學者折服而心向往之,在學術界產生了很大影響,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轉移治學途徑的作用,使清初學術逐漸向著考證經史的途徑發展。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說顧炎武開創了一種新的學風,即主要是治古代經學的學風。汪中也曾說:“古學之興也,顧氏始開其端。”(《國朝六儒頌》)顧炎武成為開啟一代漢學的先導。
三、“博學于文”、“行己有恥”的為學宗旨與處世之道
“博學于文”、“行己有恥”二語,分別出自《論語》的《顏淵》篇和《子路》篇,是孔子在不同場合答復門人問難時所提出的兩個主張。顧炎武將二者結合起來,并賦予了時代的新內容,成了他的為學宗旨與處世之道。他說:“愚所謂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于文’,曰‘行己有恥’。自一身以至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文集》卷三)可見,他所理解的“博學于文”是和“家國天下”之事相聯系的,因而也就不僅僅限于文獻知識,還包括廣聞博見和考察審問得來的社會實際知識。他指責王學末流“言心言性,舍多而學以求一貫之方,置四海之困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說明他所關心的還是“四海之困窮”的天下國家之事,所注重的自然是“經世致用之實學”,這也就是顧炎武“博學于文”的為學宗旨。
所謂“行己有恥”,即是要用羞惡廉恥之心來約束自己的言行。顧炎武把“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等處世待人之道都看成是屬于“行己有恥”的范圍。有鑒于明末清初有些學人和士大夫寡廉鮮恥、趨炎附勢而喪失民族氣節,他把“博學于文”與“行己有恥”結合起來,強調二者的關系。他說:“士而不先言恥,則為無本之人;非好古而多聞,則為空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是從事于圣人而去之彌遠也。”(《文集》卷三)因此,他認為只有懂得羞惡廉恥而注重實學的人,才真正符合“圣人之道”。否則,就遠離了“圣人之道”。所以,“博學于文”、“行己有恥”,既是顧炎武的為學宗旨和立身處世的為人之道,也是他崇實致用學風的出發點。
此外,顧炎武“博學于文”的為學宗旨的一大特色,是他不僅強調讀書,而且提倡走出書齋、到社會中去考察。他說:“人之為學,不日進則日退。獨學無友,則孤陋而難成。……猶當博學審問。……若既不出戶、又不讀書,則是面墻之士,雖子羔、原憲之賢,終無濟于天下。”(《文集》卷四)他提倡讀書與考察相結合的方法,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方法。這個方法的提出和運用,開創了清初實學的新風。
摘自步近智、張安奇《中國學術思想史稿》第九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