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生推崇中國文化,推動中德文化交流——海外漢學家見知錄之十三
——德國“漢學三杰”之一傅吾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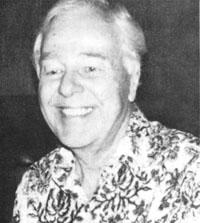
前面我介紹了法國的“漢學三杰”儒蓮(朱利安Stanislas Aignan Julien)、沙畹(Chavannes Edouard)和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其實,在西方當代漢學家中被稱為“漢學三杰”者不僅法國有,其他國家也有,譬如德國就有福格伯(Herbert Franke)傅吾康(Wolfgang Franke)和馬漢茂(Helmut Martin);美國有魏裴德、孔飛力和史景遷(Jonathan D.Spence),本欄目將作為系列文章陸續加以介紹。下面先介紹德國當代的“漢學三杰”之一傅吾康。
一、生活道路
(Franke,Wolfang)原名沃爾弗岡·法蘭克,1912年7月24日生于德國漢堡。傅吾康是德國大漢學家福蘭閣教授的幼子。也是福蘭閣子女中唯一子承父業的漢學家。傅吾康實際上是在一個中國的氛圍中長大的,他的孩提時代的一切好像都是跟中國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的。正是由于受到這樣的影響,1930年中學畢業之后,他毅然絕然地選擇了漢學作為自己的終身事業。
傅吾康1930年至1935年分別肄業于柏林大學及漢堡大學,在校期間他專攻漢學、日語及古、近代史。師從顏復禮(Fritz Jger,1886 – 1957)、佛爾克(Alfred Forke,1867 – 1944)、許勒(Wilhelm Schüler)等著名漢學家從事漢學方面的基礎訓練,并于1932年7月獲得了東方語言學院(Seminar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的翻譯文憑資格。1935年他在佛爾克教授指導下以論文《康有為及其改革派的國家政治改革嘗試》獲漢堡大學博士學位。這篇后來發表在《東方語言學院通訊》上的論文,贏得了眾多的書評。甚至像荷蘭萊頓大學著名的漢學家戴聞達(J.J.L.Duyvendak,1889-1954)教授也親自在《通報》(T’oung Pao)上撰文評論此書,這對年輕的漢學家傅吾康來講無疑是莫大之鞭策。這篇論述中國保守派與西方改良主義思想論爭的專著也奠定了傅吾康在明清史研究中的地位。
傅吾康1937年來華,先后在上海、南京等地訪學,后到達了北平,令他始料未及的是,這一呆就是整整13年(其間只有短期在日本逗留)。在北平,傅吾康主要參與了“中德學會”(Deutschland-Institut)的組織、領導工作,先后在學會中擔任秘書、總干事以及《中德學志》編輯主任等職。從1938年至1944年,共出版《中德學志》六卷(22期),《漢學集刊》(Sinologische Arbeiten)三卷,同時組織出版了“德國文化叢書”等二十余種。1941年夏季,傅吾康跟曾留學德國的胡萬吉(雅卿)先生的千金南開大學生胡雋吟(1910 – 1988)女士相愛,不過按照當時帝國的法律,日耳曼人是不能娶非雅利安人為妻的,否則的話傅吾康就會被迫辭去中德學會的職務。直到1944年9月他們才正式訂婚,1945年3月在戰爭快要結束之前,他們終于結為百年之好。胡雋吟后來隨夫赴德,在法蘭克福大學任教多年。

傅吾康與胡雋吟
抗戰勝利后,經蕭公權(1897 – 1981)先生的推薦,傅吾康被聘為四川大學和華西大學教授,講授“明史”和“德國歷史”等課程,并在中國文化研究所負責漢學研究西文集刊《中國文化研究所集刊》(Studia Serica)的編輯工作。在成都兩年后,傅吾康又接受了北京大學西語系主任馮至(1905 – 1993)教授的邀請,接替去了華盛頓大學的衛德明(Hellmut Wilhelm,1905-1990)出任德語教授。在北大期間,傅吾康與季羨林(1911-2009)等學者建立了終身的友誼。
二戰后的德國是一片百廢待興,漢堡大學此時也在著手重新建立已遭破壞的漢學系。1949年6月,傅吾康得到了漢堡大學的正式任命書,他于1950年回到漢堡,接替了自顏復禮被迫退休后已經空置兩年的漢堡大學漢學系主任一職。來北平時只是孤寂一身的傅吾康,此時攜妻和一女一子回到了闊別十三載的漢堡。在漢堡大學漢學系主任的位置上,傅吾康一直做到了1977年退休。在漢堡大學與弟子林懋(Tilemann Grimm,1922—2002)共同開創了以研究明清史以及中國近代史為主的德國北部的“漢堡學派”,與以傅海波(Herbert Franke,1914-?)為首的德國南部慕尼黑學派,以及以葉乃度(Eduard Erkes, 1891-1958)為首的當時東德的萊比錫學派。
1963年—1966年期間,利用漢堡大學給他的三年學術假期,傅吾康接受了馬來亞大學客座教授的職位。除了學術研究工作之外,他還恢復了多年來沒能夠成立的中文系。也利用各種各樣的方式,盡量多地培養華文人才。退休之后,傅吾康又應聘到新加坡南洋大學以專門研究東南亞華人歷史。
新中國成立后,1972年中德建交是,他是德國代表團特邀代表和顧問,五十至七十年代還先后擔任了美國哈佛大學客座研究員,和檀香山夏威夷大學的客座教授,德國東亞協會主席等職。
傅吾康終生推崇中國文化,積極推動中德文化交流,他主張西方人應該向中國人學習,特別在禮儀方面。他自己就是身體力行:家中中堂掛著中國對聯,書桌上放著“筆墨紙硯”文房四寶,喜歡喝茶并用蓋碗;冬天喜歡穿中式長袍,雙手還籠在袖里;喜歡打躬作揖,喜歡周圍鄰居稱他“傅三哥”或“傅三爺”(排行老三);夫妻倆都喜歡聽京劇,與京劇名伶李少春很熟悉。有次看李少春的《十八羅漢斗悟空》,同行的朋友問他戲后是否去后臺看李少春,他竟忘神地說道:“到水簾洞去也”,結果傳為笑談。
1977年,傅吾康從漢堡大學退休后,與夫人返回北京居住,那時,中國的“文革”還剛剛結束。1987年他又攜夫人在中國居住了一段時間,再圓中國夢。1988年妻子在中國故鄉病逝。二十年后,2007年9月6日傅吾康在柏林逝世,一代大師從德國的漢學長空中隕落。
二、學術成就
傅吾康是國際知名的的漢學家,精通中、英、德文,研究重點是明史,旁及中國思想史和近現代史和東南亞華文碑銘,著作豐富。其主要漢學成就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與福格伯一起,為二戰后西德漢學研究的迅速恢復和重建立下汗馬功勞。
1933年希特勒上臺,納粹興起并主宰國家政治,繼而挑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接踵而至的德國的戰敗,皆使德國學術界受到重大打擊,其中以漢學界損失最大。造成這種大倒退的三個主要原因:
一是持續十二年之久的德意志第三帝國期間的政治迫害以及戰爭災難。1933年希特勒上臺任總理,第二年成為德國元首,納粹興起并主宰國家政治,1933年4月7日,納粹當局頒布臭名昭著的《重建公務員隊伍法》,把種族歧視法律化和國家化,德國學術界受到重大打擊,其中以漢學界損失最大。據有關學者的調查,1933《重建公務員隊伍法》出爐后,至少有43位重要漢學家或因自己或配偶是猶太人被當局開除出大學或驅逐出境,或是不愿與納粹合作而流亡到其它國家,其中包括著名的漢學家子西蒙、科恩、白樂日、哈隆、申得樂、衛德明和埃伯哈德等人[①],離戰火最遠的美國更是首選,這對美國和其它西方國家的漢學研究是個幸事(美國在二戰以后漢學研究后來居上超過歐洲,與此不無關系),但德國漢學卻因此遭到毀滅性的打擊。如巴赫奧芬(1894 – 1976)是一位亞洲藝術史學家,主攻印度和中國研究課題。1921年獲博士學位后,他在慕尼黑大學任教至1935年,其間(1922 – 1926)還擔任慕尼黑民族學博物館工作。因為他妻子是猶太人,1933年,他在慕尼黑大學助教的職位被拒絕。1935年,他移民去美國,成為芝加哥大學藝術史教授直至去世。白樂日(1905 – 1963)1930年在柏林獲得漢學博士學位。其畢業論文《唐代經濟史》引進了中國史研究中社會、經濟的新視角,被其導師福蘭閣認為是他的研究生中最優秀的,1935年移居法國。在法期間推動了法國高等實驗學院中國研究的發展,1945年他的專著《隋書·刑法志》在法獲得儒蓮獎,他還開創并指導了歐洲中國研究中第一個進行國際合作的項目宋代研究課題。
布爾(1900 – 1987)在柏林大學學習中國藝術史和考古,1936年獲以論文《從漢到唐的中國建筑》博士學位,同一年前往英國后移居美國,直到1983年退休。波恩大學著名漢學家、翻譯家庫恩因有猶太血統,也于1933年被驅逐逐移居英國。庫恩流亡到英國后,在牛津大學教授東亞及印度藝術史,并組建和領導牛津東亞博物館,那是這一領域的第一個英國博物館。失之東隅,收之桑榆,這是德國漢學的不幸也是英國漢學的萬幸。科恩-維納(1882 – 1941)生于提爾西特的一個猶太家庭,為藝術史學家。1907年在海德堡大學獲博士學位后,他在柏林大學任講師。1933年被解聘后移居印度,1939年移至美國后被任命為巴羅達州藝術總監。愛伯華(1909 – 1989)是德國中國研究中社會學和文化人類學新領域的開辟者。1937年,在反抗組織成員(后被處決)特羅特的幫助下,移居土耳其,任安卡拉大學漢語教授,是土耳其漢學研究的開創者。衛德明(1905-1990)是著名漢學家衛禮賢之子,1923年,他在柏林大學以關于顧炎武的論文獲漢學博士學位。衛德明是著名漢學家衛禮賢之子,1923年,他在柏林大學以關于顧炎武的論文獲漢學博士學位。1933年納粹《重建公務員隊伍法》頒布后,他來華在北京大學教德語,1948年赴美定居,任華盛頓大學東方學院教授,在華期間著有《中國思想史和社會史》(1942年)、《中國的社會和國家:一個世界大國的歷史》(1944年)等。衛德明曾參與父親德譯《易經》工作,其代表作《〈易經〉中的天、地、人》享譽歐美,西方學者對《易經》的理解深受他的影響。除此之外,還發表了一百篇文章和八十多篇有關漢學的評論。布魯諾·申得樂是《亞洲學刊》》(Asia Major)的創辦人及主編,也是位研究中國古代宗教的學者,有專著《中國古代的巫師》(1919年)。1924年在《亞洲學刊》第一卷上發表長文《古代中國的旅、堙、郊祀典》。還研究過中國的上帝,有《中國的上帝》、《中國上帝觀念的演變》等論文。
這種人才大量流失給德國漢學所造成的傷害也為當時的官方報告所證實,1942年夏天,由柏林的帝國安全中心辦公室應慕尼黑的納粹黨中心的要求撰寫了一份報告,評價德國和奧地利大學中國學的研究處境。該報告承認“年輕才華的缺乏”,以及在德國的中國學研究中顯現出“明顯的危機”,該危機也許會影響對于目前以及預想的遠東重大政治變革的理解。當然,當局的責任幾乎完全被隱瞞起來,報告雖然提到一些人“甚至”離居海外,但沒有提到其背后的政治原因,也未對大批學者事實上是從原職位上被開除有所陳述。報告甚至隱瞞了最有名的德國漢學雜志《亞洲學刊》已經因雜志出版者和編輯申得樂已于1933流亡倫敦而被迫停刊的事實。
二是留在德國的著名漢學家為了生存和過政治關,紛紛加入了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他們在戰后又受到不同程度的懲治,從另一個側面使漢學研究受到打擊。對這些留在國內的德國漢學家要不要作政治傾向上的區分,其中的一些人究竟對社會造成了那些危害,對他們應該如何評價,漢學界缺乏深入的研究,德國學者對此也多諱莫如深甚至刻意掩飾。直到1997年,德國戰后最著名漢學家之一,也是納粹時代的親歷者之一福蘭閣還在一本專書的序言中對此刻意淡化:“納粹時代中國學只受到邊緣化的微笑沖擊”[②]。因此進行這段漢學史研究的多是外國學者,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系的Martin Kern(柯馬丁)就有個長篇考察報告,對這個時段被迫流亡的漢學家身份、學術貢獻、流亡原因以及留在德國境內的漢學家對此的不同態度皆有詳細的考察。其中提到福蘭閣、Fritz J·ger(顏復禮,1886 – 1957)和HansH.Stange(施坦格,1903 – 1978)在納粹統治期間所發表的幾篇研究報告。福蘭格在1939年寫的調查報告雖提到了魏特夫、白樂日、勒辛、布爾、愛伯華、哈隆、馮·梅興-黑爾芬等漢學家,但卻掩蓋了他們已被迫離開德國的事實,更不敢觸及他們離開德國的原因。同樣的,雖提到著名的《泰亞》雜志“不幸于1935年停止發行”,但沒有告訴讀者停刊的原因是由于該雜志的出版者和編輯申得樂是猶太人,已于1933年被驅逐出境流亡倫敦[③]。顏復禮在1937年發表的《德國的漢學研究現狀》一文中對這批被迫流亡的漢學家則完全秘而不談。他提到申得樂的《亞洲學刊》代表了“一戰后德國漢學的巨大發展”,卻掩蓋《亞洲學刊》已經停刊,申得樂也已流亡國外這一事實,說什么政府的“資助將繼續,以保證這一不可或缺的雜志得以不間斷發行”[④]。
施坦格在1941年的發表的《人民生活中的德國文化》一文中只提哈隆、埃伯哈德和衛德明這些“雅利安人種”的漢學家[⑤]。“這兩位作者都沒有提到在他們自己的寫作生涯中任何的學術間斷,沒有言及那些離開祖國的學者們,只有提供那時活躍在德國的學者的名字,他們中的許多人在歐洲漢學研究史上幾乎沒有得到哪怕一個注腳”。
三是戰后東西德分裂也使德國漢學研究受到進一步的傷害。戰后東西德的分裂,使戰爭中受到巨大摧殘的德國漢學人力和資料更加薄弱。戰后柏林分被割裂成美歐和蘇聯兩個軍事控制區域,柏林的普魯士圖書館豐富的中國圖書也分別流散到兩個軍事控制區域。普魯士國家圖書館內中國圖書收藏量當時位于全德國之冠,也因被占領國瓜分而一蹶不振。戰前,柏林的洪堡大學、萊比錫大學的漢學研究都相當出名,柏林科學院的漢學研究也有相當的進展。二戰以后,因這些大學和科學院的所在地在東柏林而劃歸東德,漢學研究受政治因素的影響而起伏不定。民主德國和新中國皆于1949年立國,又同屬社會主義陣營,關系友好密切。就漢學教學和研究而言,若以人口比例計算,東德的中國研究人員和學術機構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中最多的。當時兩國學術交往相當頻繁,中國學者應聘去東德傳播漢學,北京大學也接納了許多東德留學生,如后來成為東德著名漢學家的Eva Mǖller(梅薏華)、Roland Felber(費路)、Klaus Kaden(賈騰)、Thomas Thilo(蒂洛)、Reiner Mueller(穆海南)、Irmtraud Fessen-Henjes(尹虹)等。但到了六十年代初,隨著中蘇進入意識形態冷戰期,中國與東德的關系也急轉直下,此時整個東德的漢學研究處于停滯狀態,一些漢學家放棄了漢學研究,如二戰以前就很著名的漢學家魏勒和韋德瑪耶。即使有漢學著作此時也不能出版,如梅薏華在北大留學時曾將老舍的話劇《茶館》譯成了德文,六十年代回國后由于兩國關系緊張而不準出版,稿本也被搗成紙漿,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中國實行改革開放的八十年代前就是在上述背景下,傅吾康和他的漢學同行們開始了艱辛的德國漢學恢復和重建。當時戰敗后的西德是一片焦土,許多漢學圖書館遭到相當大的毀壞,其中包括法蘭克福的中國研究院、萊比錫、哥廷根等大學著名的漢學圖書館。德國境內的大學漢學系只剩下漢堡大學一家還在苦苦支撐,但在戰爭中也備受摧殘:系主任福蘭閣以其五卷本《中華帝國史》享譽西方,但這部巨著在1930年出版第一卷后就因戰爭而中斷,直到1952年才出齊。此時作者已于1946年帶著遺恨去世。漢堡大學漢學系主任一職自1948年顏復禮被迫退休后已經空置兩年。最大的傷害是在這十二年國內的漢學家喪失殆盡:或是受納粹迫害被迫流亡國外,留在國內的在戰后又被當成與納粹合作而受到清洗,再加上12年間的老死和得不到后續補充,使德國漢學研究人員空前匱乏,有的西方學者指出,當時德國“首先是缺乏研究人員。這種缺乏,不僅單個的學者,而且整個領域和新的學術方法的移徙國外,在中國(和東亞)藝術史、社會史、經濟史、民族學、語言學諸領域尤為明顯,”[⑥],德意志研究協會在1960年發表的《東方學狀況專題報告》中也指出:“1933年后,它(東方學研究)遭到了比別的業更嚴重的人員損失,……西德各大學重新開辦的幾年以來,(研究工作)一直為戰爭造成的科后備人才短缺及大量被破壞的專業和大學圖書館困擾。[⑦]研究人才的匱乏所導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學術研究的中斷和學術雜志的停辦:《亞洲學刊》是德國最早一批也是最有影響的一份以漢學和日本學為主的專業雜志,因雜志出版者和編輯猶太人Bruno Schindler(申得樂,1882-1964)被驅逐出境而于1935年被迫停刊。在此之后,“惟一具國際水準的德國研究中國專業雜志”[⑧]——波恩大學東方語言學院于1898年創辦的《東方語言學院通訊》,也因缺乏學術力量而停刊。據德國有的學者統計:直到1962年,德國漢學家的數目才與1933年前持平。1950年,傅吾康擔任漢堡大學的漢學系主任,一直到1977年從該位置上退休。在此期間,他還出任漢堡大學中國語言文化研究所所長,并與福克斯于1954年在漢堡創立《遠東學報》(Oriens Extremus),這是德國最有影響的漢學雜志之一;并倡導創辦了漢堡亞洲研究所。1953年,他培養的第一批兩名漢學研究生畢業,其中林懋(Tilemann Grimm,1922 – 2002)與他共同開創了以研究明清史以及中國近代史為主的德國北部的“漢堡學派”。
作為一個漢學家,傅吾康在德國的威望,幾近于費正清在美國和李約瑟在英國。他主張德國所有大學都應設立漢學教學和研究機構,甚至說“一個大學沒有漢學系,還叫什么大學”!普通中學也應開設中國文化課程。
第二,漢學研究成果豐富
傅吾康是漢堡學派的開創者和代表人物,可謂著作等身。其主要學術成果是在明史方面,旁及中國近現代史。對東南亞華人史研究也有相當成就。
他的《明代史籍匯考》(Preliminary Notes on the Important Chinese Literary Sources for History of the Ming Dynasty,1368 – 1644)(1948),收集了大量中文文獻和西文資料,是西方公認的治明史重要著作。此外還有《明代時期中國的土地稅》(1953)、《關于明代歷史的最新中文論述》(1954)、《明代史料入門》(1968)、《中國科舉制度革廢考》(1960)等。
傅吾康十分關心中國近代歷史的演變,于1957年在慕尼黑發表了《中國的文化革命:五四運動》(Chinas kulturelle Revolution – Die Bewegung vom 4.Mai1919)論著,1958年又在慕尼黑出版專著《1851 – 1949年間的中國百年革命》(Das Jahrhundert der chinesischen Revolution 1851 – 1949)。在這部專著中,傅吾康敘述了1851 – 1949年中國近代革命的歷史,并采用不同于西方學者的視角來闡釋中國近代的百年革命史,把太平天國以來中國近代史上的事變看成一個連續的發展過程,他把近百年的中國革命分為五個階段,認為這是一個不斷發展、上升和深化的過程。傅吾康強調從整個中國歷史的角度來觀察中國近代史,不是機械地把近代和傳統割裂開來。他從《易經》里的“革命”說起,談到五行學說、漢代緯書、以及孟子的“君輕民貴”的思想,證明了在中國的國家觀念中,革命是作為一種合理的手段而存在的。傅吾康在書中批評西方革命黨人的理想化和政治幼稚以及脫離中國實際的錯誤看法,進而指出,國民黨從政治上背離革命走向反動和衰敗,社會變革任務最終由共產黨人完成。書中,傅吾康如實地記錄了國共兩黨的不同形象:國民黨政府的腐敗到了驚人的地步,共產黨人清貧而廉潔,充滿著理想主義精神。共產黨的軍隊裝備很差,但是指揮有方,戰斗情緒高漲。一切表明進行社會革命的時機成熟了。新中國的建立則標志著中國近百年革命的最后階段社會革命的完成。在這部專著中,作者還批評一些西方人士想把西方的民主制度移植到中國,是不了解中國的國情。也正因為這些觀點在西方學術界富有挑戰性,所以專著出版后受到西方學者尤其是美國學者的批判,認為他是在用中國共產黨人的觀點解釋中國百年革命史。然而,德國當代漢學家斯泰格(Brunhild Staiger)和艾伯斯坦(Bernd Eberstein)等對其人其作的評價為:傅吾康繼承并發展了福蘭閣對中國歷史的研究。福蘭閣研究的是19世紀以前中國在一個相對封閉的東亞文化圈內的發展;而傅吾康研究的是19世紀以后中國通過種種決裂和危機走向現代化的過程。因而該書于1980年又出版了增訂本。傅吾康的另一部關于中國近代史的重要著作是1962年在德國格廷根出版的《中國與西方》(China und das Abendland),該書對近代西方列強在華的侵略行徑持批判態度。他還利用自己的優勢,于1974年在杜塞爾多夫出版了介紹現代中國的《中國手冊》(China-Handbuch)。
傅吾康在60年代曾受聘到馬來西亞大學創辦中文系,在那兒他產生了對東南亞華人史跡的研究興趣。1977年,他退休后再次受聘到馬來西亞大學中文系任教授,期間集中精力研究南洋華人的歷史,在星馬各地搜集了大量的金石碑刻,1978年他與陳悌凡(Chen Tieh Fan)合著并出版了《馬來西亞的華人碑文》(Chinese Epigraphy in Malaysia)。另有《印度尼西亞華文銘刻匯編》《泰國華人銘刻萃編》等論著。1989年在新加坡出版了《傅吾康學術論文選集》,這本大型選集匯編了其關于明史、清史、東南亞華人史和海外中文教育以及日耳曼學的研究論文,大體反映了傅吾康一生治學的歷程。
作為歷史學家,傅吾康一貫重視史料的運用,并將中文文獻與西文資料并重,他的《明代史籍會考》就是在這方面最好的例證。在方法運用方面,他總是力圖以西方的學術思想為出發點,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讓歐洲學界盡可能多地理解遠東的文明。在《中國與西方》一書中,傅吾康便稱:“跟中國人的西方觀相比較,在書中我更深入探討的是西方人的中國觀。因此這本小冊子署為《中國與西方》而不是反過來的《西方與中國》。作者的首要任務是要讓讀者理解中國的立場以及面對西方時的中國態度。”此外,在歷史的梳理方面,傅吾康從其父福蘭閣那里繼承了中國歷史乃是一個連續發展過程的觀點,對于中國近代史中出現的運動和觀念,他總是到中國歷史中去尋找根據。在《中國革命的百年》(1980年修訂版)一書中,傅吾康便強調要從中國歷史的整體去看中國革命的觀點,認為中國近代史只是中國歷史的自然延續。他從《易經》里“革命”的概念及孟子“君為輕”的思想出發,證明了“革命”并非到近代才突然出現的西方觀念,作為爭取平等權利的手段,“革命”在中國歷史中一直存在著。
跟將中國看成是一堆歷史的古典文明這樣的看法不同,傅吾康一直在努力地尋找古代、現代以及當代中國發展的歷史軌跡。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他在上個世紀50年代曾與古典語文學派的海尼士(Erich Haenisch,1880-1966)教授展開過激烈的辯論。他認為,海尼士所認為的近現代中國研究以及漢語口語不具備學術性的觀點,盡管在第三帝國的時候使漢學免遭了政治的影響,但卻割裂了中國歷史的傳承。在這一點上傅吾康依然秉承著他父親的觀點,亦即中國歷史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傅吾康對近現代中國研究以及現代漢語的重視,實際上也開啟了德國中國學研究的先河。
傅吾康的治學態度十分嚴謹,他的專著《中國科舉制度革廢考》是在哈佛大學任客座時的所作的一份學術報告,僅七十頁,但其中所附典故、史實資料竟上百條,做到句句有依據,處處有來歷。
第三,為德國培養了一大批出色的漢學專門人才
傅吾康不僅在漢學研究方面取得了顯著的成就,在長達二十七年的漢堡大學漢學教授位置上,還為德國培養了一大批出色的漢學專門人才。他指導的學生中有22人獲得漢學博士學位,其中如林懋、馬海茨克和什塔格爾已是享譽國內外的著名漢學家。
傅吾康推崇中國傳統文化,主張把它列入普通學校的教學內容中,以普及對中國文化的了解。他還認為,漢學是一門重要的學科,德國所有的大學都應設立漢學研究和教學機構。他曾擔任德國東亞學會主席,亞洲學會副主席,創建了以研究中國和東亞為重點的德國漢堡亞洲研究所,他還主張在著名的德國科研機構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設立東亞歷史研究所,研究商周以來的中國歷史。并與福克斯于1954年在漢堡創立《遠東學報》,這是德國最有影響的漢學雜志之一。
三、年表
1912年生于德國漢堡,從小受其父德國漢學界泰斗福蘭閣的影響,對中國和中國文化有著特殊的感情。
1930年起先后在漢堡大學和柏林大學學習漢學和日本學、歷史學。
1935年以《康有為和他的學派的變法維新運動》(Die staatspolitischen Reformversuche K’ang Yuweis und seiner Schule)一文取得漢堡大學博士學位。
1937年傅吾康只身來華游學,先到上海、南京等地訪學,不久到北京,歷任“中德學會”(Pekinger Deutschland Institut)秘書、主事、會長和研究員等職。
1945—1946年曾任北平輔仁大學講師。
1946—1948年在成都擔任國立四川大學歷史系教授。
1948—1950年應馮至先生的聘請擔任北京大學西語系德文教授。期間,他還先后擔任了《中德學志》、《漢學集刊》和《中國文化研究會刊》的編輯工作。在中國他同畢業于天津南開大學的胡雋吟女士結婚。
1950年傅吾康回德國,接受漢堡大學的聘請,出任中國語言文化研究所教授兼所長,直至退休。
1977年傅教授退休后,復擔任馬來亞大學中文系,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廣州中山大學東南亞歷史研究所客座教授。
2000年6月馬來亞大學中文系畢業生協會出版一本“慶賀傅吾康教授八秩晉六榮慶學術論文集”以表揚他對東南亞銘刻資料之搜集及編纂工作。
2000年6月傅教授授回德國定居。
2007年9月6日逝世于德國柏林。
四、學術著作
- 1、《明代史籍匯考》(Preliminary Notes on the Important Chinese Literary Sources for History of the Ming Dynasty,1368—1644)(1948)
- 2、《明代時期中國的土地稅》(1953)
- 3、《關于明代歷史的最新中文論述》(1954)
- 4、《中國的文化革命:五四運動》(Chinas kulturelle Revolution—Die Bewegung vom 4.Mai 1919)(1957)
- 5、《1851-1949年間的中國百年革命》(Das Jahrhundert der chinesischen Revolution 1851—1949)(1958)
- 6、《中國科舉制度革廢考》(1960)
- 7、《中國與西方》(China und das Abendland)(1962)
- 8、《明代史料入門》(1968)
- 9、《中國手冊》(China—Handbuch)(1974)
- 10、《印度尼西亞華文銘刻匯編》
- 11、《馬來西亞華文銘刻萃編》(Chinese Epigraphy in Malaysia)(1978)
- 12、《泰國華人銘刻萃編》
- 13、年在新加坡出版了《傅吾康學術論文選集》(1989)
注釋:
[①]瓦拉文司 (Hrmut Walravens)《1933-1945年間德國的東亞學及其流亡》,見《書目及報告》,瓦拉文司編,慕尼黑:K.G. Saur, 1990,231-241頁。
[②]馬茂漢編:《漢學研究——德語地區漢學歷史資料選輯:概述,機構的歷史,學者傳記和資料目錄》,第2,波鴻魯爾大學1997年輯,福赫伯“序言”。
[③]福蘭閣《德國漢學》,《研究與進步》1939年第5期,257-267頁。
[④]顏復禮《德國的漢學研究現狀》,《研究與進步》1937年第3期,96-99頁。
[⑤]施坦格《人民生活中的德國文化》,《德國漢學》1941年16期,49-56頁。
[⑥] [美]衛德明《今日德國漢學》,《遠東季刊》1949年8期,319頁。
[⑦] Adam Falkenstein編《東方學狀況備忘錄》,威斯巴登:Franz Steiner,1960﹒2。
[⑧]同[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