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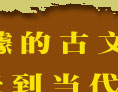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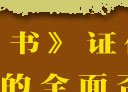

四、《疏證》偽證考略(下)
(4)太甲稽首,伊尹稱字
《疏證》(第六十一):“君前臣名,禮也。雖周公以親則叔父,尊則師保,亦自名于王前,曰‘予旦’,召公亦名之,為‘旦曰’;斷未有敢自稱其字者。或君于臣,字而不名,所以示敬。如‘王若曰父義和’之類,亦未多見。何晚出《書》所載太甲既稽首于伊尹矣,伊尹又屢自稱其字于太甲,豈不君臣交相失乎?君之失,緣誤仿《洛誥》;臣之失,則緣誤仿《緇衣》。何者?《緇衣》兩引《咸有一德》,一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一曰‘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此篇鄭康成《序》書在《湯誥》后,咎單作《明居》前。馬遷亦親受逸《書》者,即系于成湯《紀》內,是必于太甲無涉矣。康成注《書序》于《咸有一德》下云:‘伊陟臣扈曰’,此頗不可曉。要王肅《注》云:‘言君臣皆有一德’,是必當時臣工贊美湯君臣之辭,故君則號,臣則字,不必作于湯前。偽作者止見《書序》為‘伊尹作《咸有一德》’,遂將《緇衣》所引盡竄入于其口,又撰其辭于前曰‘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喋喋稱字不已,不大可嗤乎?或曰:然則伊尹宜曷稱?曰稱‘朕’,《孟子》‘朕載自亳’是也;稱‘予’,‘予不狎于不順’是也;稱‘臣’,若召公‘予小臣’是也;稱摯,若周公‘予旦’是也。至于稱字,烏乎敢?”
這一條先提到兩種制度:“君前臣名”和“君于臣,字而不名”。然后指出《古文尚書》內容(證據一:“太甲稽首于伊尹”在《太甲中》,證據二:“伊尹自稱其字于太甲”在《咸有一德》和《太甲上》)與這兩種制度不符,不符的原因是偽造時“誤仿”《洛誥》和《緇衣》。“父前子名,君前臣名(《禮記·曲禮上》)”的制度與“幼名冠字(《禮記·檀弓上》)”之禮相表里。《禮記·檀弓上》明確提到“幼名冠字”是周代禮制(周道也)。也就是說,在商代初期,這種禮制很可能還沒有出現。“君于臣,字而不名”出自《說苑·臣術》伊尹與商湯一段對話。這樣的小故事戰國中晚期編了不少,禹澇湯旱、伊庖呂屠一類,《說苑》搜集最多。講故事可以,當真事殊為不妥。如此“學問”清代也不多見。
閻氏指控“伊尹稱字”的“靈感”來自《尚書正義·太甲上》孔《疏》下述內容:“《孫武兵書》及《呂氏春秋》皆云伊尹名摯,則‘尹’非名也。今自稱‘尹’者,蓋湯得之,使尹正天下,故號曰‘伊尹’;人既呼之為‘尹’,故亦以‘尹’自稱。禮法君前臣名,不稱名者,古人質直,不可以後代之禮約之。”這里本來沒有什么大問題,孔穎達拘于君臣尊卑之禮提出問題并作了解釋。這位盛世鴻儒怎么也不會想到,如此寥寥數語,會在一千年后給一位叫做閻若璩的考據大師提供了“整材料”的“重磅炸彈”。這是孔穎達十分反感的事情,他所謂“非險而更為險,無義而更生義”,所謂“鼓怒浪於平流,震驚飆於靜樹”。說白了就是無事生非。
稱伊尹為“伊摯”,見于《墨子·尚賢中》《孫子兵法·用間》《楚辭·天問》等書。這些文獻出現較晚,不足為據。除《史記·殷本紀》“伊尹名阿衡”外,先秦文獻并沒有明確提到伊尹何名何字。因此,不存在“尹”是伊尹之字的可靠證據。鄭玄注《書序》于《咸有一德》云:“伊陟臣扈曰”,出自《尚書·君奭》(今文)周公對君奭的訓詞:“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伊陟是伊尹的兒子。伊尹何名何字與此無關。
《疏證》(第三十一):“二十五篇之《書》其最背理者,在太甲稽首于伊尹”,后文提到:“今既證太甲稽首之不然”,說明《疏證》此前已論證過這個問題。考《疏證》全書并無相關論證。而在此條(第三十一)之前,有三條闕文(第二十八、二十九、三十)。所謂“今既證”云云,是剛作過論證的意思。《疏證》目錄第二十八條的題目是:“言太甲不得稽首于伊尹為誤仿《洛誥》”。故閻氏“證太甲稽首之不然”當在第二十八條。按《洛誥》(今文)中有周成王對周公“拜手稽首”之事。即使深文周納,也是為了取信于人。閻氏主動刪掉這部分內容是因為“誤仿”之說過于牽強。這是佞人筆墨的鍛煉過程。
成王之于周公,太甲之于伊尹,二者情況十分接近;周公和伊尹都是長輩,都是主持國政的重臣;伊尹相成湯滅夏立商,輔佐四代五王,其地位之尊,身份之重,要超過周公。殷墟卜辭記伊尹與成湯并祀(《中國通史參考資料·古代部分》),可見其地位之重要。也就是說,在一些特殊情況下,“君而稽首于臣”(太甲稽首于伊尹和成王稽首于周公)合情合理,不足為怪。由于“太甲稽首于伊尹”和“伊尹稱字于太甲”兩條指控都不能成立,不能構成有效的“作偽”證據,也就不存在“誤仿”問題。換句話說,指控不能成立,“誤仿”作為“作偽”事實也就失去依據。閻氏反過來用“誤仿”作為指控的依據,已屬典型的“循環論證”。
上面說過,閻氏此條“靈感”來自《尚書正義》。我曾奇怪,《尚書正義》本有“言君臣皆有純一之德”注語,他為什么不用?細看恍然而悟。原來這是《孔傳》內容。這是他立此一說捉襟見肘之處,注語眼前就有,但不能用。不用又不能實現“震驚飆於靜樹”的效果。我于是查找閻氏所引“王肅《注》”的出處,《尚書正義》沒有,《三國志》本傳沒有,最后在《史記·殷本紀》“書縫中”找到,是裴骃《集解》所引。前面引文“然則伊尹宜曷稱”以下,沒有任何證明意義。亦見翻檢之功。《疏證》類似內容很多,這是拿“學問”當手電筒晃人眼睛。錢穆先生所謂“自炫博辨”。
閻氏“博極群書”,他當然知道“君前臣名”與“幼名冠字”的表里關系,《禮記·檀弓上》“周道也”亦在其視野之中,這些都不能影響他的工作熱情。用《說苑》證殷商制度,純屬無賴行徑。前面已經刪掉“拜手稽首”的無根之論,仍留下一句在這一條中虛張聲勢。為什么?因為他心雄萬夫,屢試不中,只此一途,志在必得。于是苦心孤詣,敷衍造說。在故紙堆中翻云覆雨,字里行間縱橫短長。于“無字處精思獨得”,“證據出入無方”。其學誠博,其智誠狡。如此這般,一代大師橫空出世。《疏證》提到朋友當面夸獎(第六十八):“頃與子游,覺考核之學,今亦有密于古人處。”自謂“予笑而不敢答”。其炫耀自喜之態有些可笑,但讓人實在笑不出來。這是因為中國文明為此人名滿天下而付出的代價實在太大。
北京國學時代文化傳播公司制作
國學網總編室 010.68900123轉808
國學網站,版權專有;引用轉載,注明出處;肆意盜用,即為侵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