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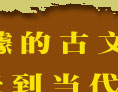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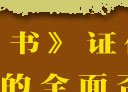

二、《疏證》偽證考略(上)
(1)晁錯傳本與承詔作傳
《詩》、《書》等典籍及百家語在秦火之余喪失幾盡,漢初廢挾書令,“廣開獻書之路”,于是“天下眾書往往頗出”。其中《尚書》大約有三個本子,伏生本、孔壁本和河間獻王本。伏生本是秦博士伏生保存到漢代〔26〕的二十九篇今文(秦漢文字)《尚書》(《泰誓》后得),漢文帝時立為太常博士學官。《漢書·儒林傳》:“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詔太常,使掌故朝(晁)錯往受之。”孔壁本是出自孔壁〔27〕并由孔子十二世孫孔安國整理的古文(先秦文字)《尚書》〔28〕。河間獻王本是河間獻王得自民間的古文《尚書》傳本〔29〕。
建元五年(前136),漢武帝采納董仲舒主張,罷黜百家,專立五經(《詩》、《書》、《禮》、《易》、《春秋》)博士。其中,《書》即晁錯就學于伏生的今文《尚書》。大約在漢武帝即位后十余年之間,由于“書缺簡脫,禮壞樂崩”,于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30〕孔壁本成為皇家“秘府”藏書(所謂“中秘本”),與此有直接關系。這是孔安國《書大序》提到的第一次獻書:“悉上送官,藏之書府”,第二次在“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后:“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后代。”
閻氏《疏證》(第十七)對兩次獻書提出質疑:“是獻《書》者一時,作《傳》畢而欲獻者又一時也。作《傳》畢而欲獻,會國有巫蠱,則初獻《書》時未有巫蠱,何不即立于學官,而乃云以巫蠱遂不及施行邪?”他由此得出結論:“蓋偽作此《書》者知兩漢秘府有古文,而無訓傳。今又并出訓傳,不得不遷就傅會其說,以售其欺耳。”按閻氏《疏證》的前提是魏晉間某人對《古文尚書》“二十五篇”乃至“孔傳”的作偽,上文“偽作此《書》者”指的是魏晉間那個莫須有的作偽者。這里需要搞清兩個問題:即《今文尚書》立于學官的過程以及立于學官需要具備的條件。
《史記·晁錯傳》張守節“正義”引衛宏《詔定古文尚書序》云:“征之,(伏生)老不能行,遣太常掌故晁錯往讀之。年九十馀,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漢書?儒林傳》顏師古注引文與此大同小異)。”伏生撰有《尚書大傳》,據后人輯本觀之,其格制內容與《韓詩外傳》有些相似,講了一些不一定可靠的小故事,并非章句類教材。也就是說,伏生傳授原本只有《尚書大傳》而沒有成文的章句類教材。所以晁錯奉詔“往讀”以及伏生“使其女傳言教錯”者,實為草就一部“屬讀”章句的教材。“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是說晁錯傳本“師說”解讀質量較差。因此,在今文《尚書》立歐陽、大小夏侯三家博士之后,晁錯的傳授就此被取代。
立五經博士的前提條件之一,是要有一個相對完整的經文解讀“輔助教材”,所謂“訓傳”、“師說”、“家法”。由《漢書?藝文志》可知,“歐陽氏學”的“輔助教材”是《歐陽章句》和《歐陽說義》,“大小夏侯之學”是“大小《夏侯章句》”和“大小《夏侯解故》”。由于孔安國二次獻書未果,所以《漢書·藝文志》只有“《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為五十七篇)”。又如《春秋》鄒氏未立學官是因為“無師”,夾氏則“未有書”。《今文尚書》晁錯傳本雖然解讀質量較差,畢竟有書和“師說”,這是立于學官的起碼條件。按《史記·儒林列傳》提到“張生亦為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征,不能明也。”張生是伏生弟子,但他和伏生的孫子并未改觀晁錯傳授的解讀質量。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歐陽生后人(歐陽高)才有必要另行撰寫《歐陽章句》。
《漢書·藝文志》提到,歐陽生(武帝時人)的曾孫歐陽高始為博士,始有“歐陽氏學”〔31〕。“曾孫”是歐陽生后第三代,時間最早也在武帝末昭帝初,武帝末數年間正值巫蠱事起,治獄極酷,殺人數萬,朝野震動,不太可能有立博士之事,故當在昭帝時。立大小夏侯更晚些(在宣帝甘露三年)〔32〕。也就是說,終武帝世太常博士《今文尚書》只有晁錯傳本及其質量較差的“師說”。
上述情況從多個方面呼應了孔安國《書大序》的內容:第一,他只知有晁錯傳本(不知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并指出其解讀質量不高(口以傳授)。按孔氏初為五經博士所學即此。第二,孔氏獻書共有兩次,前次只有經文,后次有經有傳。第三,由于擁有“師說”是立博士的前提條件,所以“承詔作傳”與當時具體歷史情況完全吻合,同時也是“二次獻書”唯一合理的原因。第四,從“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到第二次獻書“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孔氏“研精覃思,博考經籍,采摭群言,以立訓傳”前后用了大約二十年時間。這從一個側面說明孔傳解《書》質量之所以不遜色于馬、鄭諸儒的原因。
閻氏質疑的關鍵是:“初獻《書》時……何不即立于學官”。上面討論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由于初獻《書》時沒有“師說”,故未能立于學官。不僅如此,上面引證史料還提供了孔安國作傳的原因,也是《孔傳》不偽的依據。因此閻氏質疑毫無道理,不能作為魏晉間某人“偽作此《書》”的證據。他由此得出的結論也是捕風捉影。這是從沒有問題的地方去找問題,是“有罪推定”尋找“罪證”的典型體現。關于衛宏(東漢初人)《詔定古文尚書序》的內容,閻氏在《疏證》中多次給予否定,但并未提出相對可靠的否定依據。
北京國學時代文化傳播公司制作
國學網總編室 010.68900123轉808
國學網站,版權專有;引用轉載,注明出處;肆意盜用,即為侵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