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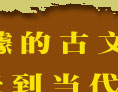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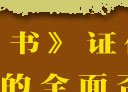

一、引論
(2)閻毛之爭
閻氏撰《疏證》暴得大名,毛奇齡于是作《古文尚書冤詞》力辨其真。此事轟動一時。二人才氣絕高,同是“漢學開山者”〔9〕。歷來評論大多褒貶分明:是閻非毛──前者人品好、學問好,后者反之。錢穆先生則認為,二者至少在人品上“兩無足取”:“(毛)西河(閻)潛邱,其博辨縱橫傲睨自喜之概,讀其書者,固見其呵斥先儒,譏彈前賢,上下千古,若無足置胸懷間,意氣甚盛,而其晚節之希寵戀獎,俯首下心于朝廷圣天子之前,亦復何其衰颯可憫憐之相似耶”〔10〕。
據“疑古派”研究,古文獻“作偽”主要動機之一是“炫名”。閻、毛不是作偽者,而是文獻真偽的辯駁者,但均有“炫名”之嫌。閻氏生平是場多少有些荒誕的悲喜劇。他自負極高,屢試不中,于是以撰《疏證》而成名。晚年則“希寵戀獎”,康熙南巡江浙,他進獻頌詩渴望召見,未能如愿。于是命其子北上,獻所著書及《萬壽詩》多首,希望求到康熙御書一幅字(褒獎其學問)。胤禛手書請他進京設法相助,他臥病在床,得書不勝惶恐榮幸,霍然而起,不顧年老病衰,千里奔波,日夜兼程,趕赴京師。被胤禛請進府邸,不日病情加重,故紙堆中一世雄才因此送命。病重時友人探視,語以老當自重,不知他彌留之際作何感想。享年六十九歲。毛奇齡早年抗清,后應試博學鴻儒科,得翰林院檢討,也曾向清帝獻書獻頌以邀寵,章太炎說他“晚節不終,媚于旃裘”。
閻氏“負氣求勝,與人辯論,往往雜以毒詬惡謔”,毛氏著文亦多“狂號怒罵”。錢穆先生“陋儒(按此評價始出全祖望)”和“才奇行卑”的評語對二人都適用。學術爭論常見一種招術,先將對手人品搞臭,然后乘勝追擊。這場爭論雖“利矛堅盾,逐步斗殺,遂得奇采”〔11〕,可惜雙方均非端士。這里只能就事論事,不去考慮人品問題。據錢穆考據,毛氏《冤詞》凡引《疏證》內容加以駁難者,都隱去姓名而冠以“或曰”〔12〕。《疏證》8卷,128條;刊行本闕29條。錢穆認為闕文原因有二:一是見《冤詞》駁難有據者,自行刪去〔13〕;二是內容調整,移入他卷〔14〕。閻氏見《冤詞》后對《疏證》作了大幅度刪改調整,甚至“本為《冤詞》難《疏證》,今轉成《疏證》難《冤詞》。”〔15〕閻氏刪改調整“全不肯認是見西河《冤詞》后所追改”〔16〕。錢穆所謂“考據家之不德”。杭世駿謂閻氏書多刺譏時賢(凡著名者幾無人能免),“惟固陵毛氏為《古文尚書》著《冤詞》,專以攻擊《疏證》,氣懾于其鋒焰,而不敢出聲,喙雖長而才怯也。”〔17〕
前面提到,大多數學人對閻毛之爭的評論是一邊倒。這里不妨作一“換位思維”:既然西河《冤詞》可以迫使閻氏對《疏證》四分之一內容作大幅度刪改調整,任何人沒有任何理由忽視《冤詞》的價值。既然《疏證》問世之初已經被找到這樣多的問題,也就沒有理由相信《疏證》的問題僅此而已。一邊倒的評論是否有黨同伐異之嫌?或如閻氏所說是“矮人之觀場”?〔18〕“利矛堅盾”之間尚有周旋余地。
北京國學時代文化傳播公司制作
國學網總編室 010.68900123轉808
國學網站,版權專有;引用轉載,注明出處;肆意盜用,即為侵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