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遼金元是中國小說史上一個重要階段。宋代統治者吸取了五代政權不斷易手的歷史教訓,加強中央集權,削弱藩鎮武將的勢力,而優待文臣學士,一再擴大科舉取士的名額,造成一個“右文稽古”的環境,提倡優游文史、整理典籍的風氣。宋太宗即位之后太平興國二年(977)就命大臣集體編纂幾部大書,其中有一部是帶有小說總集性質的《太平廣記》,收羅了許多志怪、傳奇及各種異聞雜說,為宋以前的文言小說作了一次總結性的清理。這對宋代小說的發展有很大影響,不但文人模仿晉唐小說,紛紛寫作志怪、傳奇體的作品,而且民間說話人也從中取材,“幻習《太平廣記》”(羅燁《醉翁談錄·小說開辟》)。《太平御覽》雖然生在史部和子部的典實,但也收錄了不少六朝小說,這對文言小說的創作也有一定影響。
小說觀的發展 歐陽修編纂《新唐書·藝文志》時,把《舊唐書·經籍志》里一部分列在史部雜傳類的書歸并入小說家類,這表明他崇尚紀實,不承認那些紀異志怪的書為史傳,體現了一個史學家的嚴謹態度;另一方面也進一步確認了小說以虛構為特征的觀念。這對小說的發展有積極作用的一面。但稍晚一些的史學家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卻采用了一些小說的資料寫入正文或者附入《考異》而加以辯證。似乎司馬光比較寬宏地重視小說的史料價值,然而客觀上卻混淆了小說和史書的界限,對小說提出了苛刻的甚至不恰當的要求,這并不利于小說的獨立發展。如張邦基在《墨莊漫錄跋》中說:“唐人所著小說家流,不啻數百家,后史官采摭者甚眾。……故予妙此集,如寓言寄意者皆不敢載,聞之審、傳之的,方錄焉。”就是小說作者為抬高自己的身分而依附于史書的說法。此外,古文家如尹洙則以譏笑的口氣稱范仲淹的《岳陽樓記》為“傳奇體”,表示了對唐人傳奇的輕蔑。南宋人趙彥衛對唐代傳奇作了一個分析,說“蓋此等文備眾體,可以見史才、詩筆、議論”(《云麓漫抄》卷八)。這可能只是宋代人的看法,然而宋代小說家真正懂得“文備眾體”的并不多,多數是重史才而不重詩筆,或者竟偏重于議論,如樂史的幾篇傳遍體小說;也有少數作家又過于重視詩筆,堆垛詞章而流于繁縟,對情節結構和人物描寫反面忽視了。
兩宋金元的志怪小說 宋代文言小說的發展,從數量上看,顯然是志怪體作品占了優勢。從宋初徐鉉的《稽神錄》到宋末無名氏的《鬼董》,都是談神說鬼的作品。洪邁的《夷堅志》,更是宋代小說的代表作。題材廣泛,文字條暢,但總的來說,宋代小說好的作品不多,都是“偏重事狀,少所鋪敘”,連《夷堅志》也不免。金代又能元好問的《續夷堅志》,還是恪守六朝志怪的傳統,“粗陳梗概”而已,而用意仍在“明神道之不誣”。元代還有無名氏的《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和郭霄風的《江湖紀聞》等,更是抄摭舊聞,只有刪節而無鋪衍。志怪小說到宋元時代也和雜事小說一樣,崇尚紀實,又往往借以勸善懲惡,逐步走入保守和衰退的境地。
宋、遼、元的傳奇小說 傳奇體的小說,以史官樂史的《綠珠傳》為代表,掇拾史料,改寫歷史人物的傳記,意存勸戒,也崇尚紀實,文學性不強。即使收入《青瑣高議》的一部分宋人傳奇,也有偏重史才與議論的傾向,又有“托往事而避近聞”的風氣,在文采上都不如唐人作品。比較突出的偏重詞章詩筆的宋人傳奇,集中收錄在李獻民的《云齋廣錄》里。此書序于政和元年(1111),代表北宋以前小說發展的最高水平,是唐代以后稍有新意的傳奇體作品。南宋以后雖然還有一些新的作品,但又與話本有融合滲透的趨勢。如見于《醉翁談錄》的《鴛鴦燈傳》和《蘇小卿》(《永樂大典》引),夾雜詩詞而文字淺俗,又為元明的新傳奇體開風氣之先,正如王士衤真《青瑣高議跋》所說的:“此《剪燈新語》之前茅也。”遼代只有一篇王鼎的《焚椒錄》可以算是小說。它屬于宮闈秘史之類,基本上與史籍相合,是一個《奧賽羅》式的悲劇故事,有些情節恐怕是傳述者的增飾。元代的傳奇體小說有一些新的東西,更注重詩筆文采。宋遠的《嬌紅記》寫一個愛情婚姻悲劇,情節曲折,節奏舒緩,詞章華麗,人物性格鮮明,細節描寫的真實懷達到了新的高度,篇幅之長在古代小說里也是空前的。鄭禧的《春夢錄》以第一人稱自述的筆法,寫了另一個愛情悲劇。篇中引錄了大量詩詞,更近似《本事詩》之類的作品。元代悲劇故事較多,與同時代的雜劇有相通之處,似乎是這個時代精神的反映。這種悲劇精神直到明初的《剪燈新話》里還有所體現。以文言小說而言,宋元傳奇體作品上承唐人小說,旁通說唱話本,有一些新的變化。
兩宋的雜事小說和選集 以《世說新語》為代表的志人小說,唐宋以后很少有可以步其后塵者。孔平仲編著的《續世說》輯錄唐五代人的逸事,分門編次,雖續《世說新語》而作,但記事而不善于記言,傳人而不能傳神,缺少的是文采和韻味。王讜的《唐語林》取唐人著作分類編次,比《世說新語》的門類還多十七門,重在倫理教化。宋代較多的是紀實考史的筆記,其中也有一些記載時人逸事的篇章,寫得稍有生氣。如《涑水紀聞》記錢若水平反冤獄的故事,《桯史》記南陔脫帽的故事,《齊東野語》記陸放翁鐘情前室的故事,都寫得比較詳盡真切,富有小說意味,就不止于記事而兼具志人了。至于《清尊錄》、《投轄錄》、《摭青雜說》等富于情節的人世故事,更具備小說的特征。值得注意的是這時期的文言小說,與話本有某些相通的地方。如《青瑣高議》中用七言副標題,近似后世的小說回目。《綠窗新話》輯錄唐宋小說故事,作為說話資料,也是這種格式。至于題材的移植,更為常見。如《鬼董》中的張師厚故事與話本《鄭意娘傳》互有異同,還不易辯別其孰為先后。
兩宋金元的通俗小說 宋元時代話本興盛,正是通俗小說開始發達的時代。說話藝術在唐代已見記載,敦煌遺書中也有不少話本及說唱文學抄本,從廣義上說都是通俗小說。明郎瑛《七修類稿》(卷二十)曾說“小說起宋仁宗時”,不知他的根據是什么。如果說通俗小說在宋仁宗時期有較大發展,則大致可信。因為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詳細記載北宋末年汴梁的“京瓦伎藝”,有講史、小說的專業藝人,包括專說三分的霍四窿和專說《五代史》的尹常賣等,那么在仁宗時期曾有話本流傳是完全可能的。不過當時大概還只以抄本流傳,未必就有刻本。現在所見到的話本,都是南宋或金、元的刻本,而且還比較簡略,只是節本或綱要而已,所以書名稱為《三分事略》、《薛仁貴征遼事略》的。南宋說話的盛況,見于《都城紀勝》、《夢粱錄》等書的記載。同時的金朝也盛行說話。金兵占領東京之后,曾向宋朝索要諸色藝人,其中就包括說話人和小說家(《三朝北盟會編》卷七十七)。金國左丞相顏充曾聽劉敏講《五代史》平話(見上書卷二百四十三),金朝的說話人還有賈耐兒、張仲軻等。《武王伐紂平話》和《薛仁貴征遼事略》開頭有詩說“隋唐五代宋金收”,可能出于金人之手。《五代史平話》也有可能刻于金朝。元代刻的平話較多,有《三分事略》和《全相平話五種》,《宣和遺事》也像是元刻本。小說則僅見《紅白蜘蛛》殘頁,從文字看都是節本。元代小說顯然有較大的發展,因為當時知識分子在仕途上很少有出路,一部分人曾投身于書會,除編寫北雜劇、南戲文之外,也有編小說的。如陸顯之曾寫過《好兒趙正》話本,隨后有傳為《水滸傳》、《三國演義》的加工寫定者施耐庵、羅貫中。前者生平還有疑問,后者確為元末明初人,明人記載說他是《三國志演義》的寫定者,總有一定依據。《西游記平話》大致寫定于元代,見于朝鮮人所著《樸通事諺解》,較為可信。說經、說參請性質的《廬山成道記》(即《廬山遠公話》故事)至元代仍在流傳(《廬山蓮宗寶鑒》卷四)。現存宋元話本,大多都經過明代人的修訂,藝術成就也不平衡。《水滸傳》、《三國志演義》、《西游記平話》及一部分小說家的話本大致定型于元代,這是中國小說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魯迅說白話小說的興起“實在是小說史上的一大變遷”。這個變遷開始于宋代甚至更早,但以現存話本的文獻資料來看,到元代才有較多的實績。
宋遼金元作為一個歷史階段,是中國古代小說新舊交錯的時代,但不是新舊交替,而是并駕齊驅。不僅文言小說和通俗小說同時并行,而且在文言小說內還有新體和舊體的不同,在通俗小說內也有繁簡文質的差別。從整體上說,雖然文言小說呈現出了停滯衰落的傾向,通俗小說也沒有達到完全成熟的地步。然而卻是中國小說史上一個繼往開來的時代。
(程毅中撰)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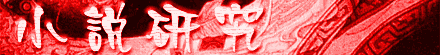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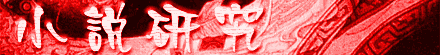
web@guoxue.com
web@guoxue.com
![]() 010-62917824
010-629178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