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14世紀(jì)中葉到17世紀(jì)中葉,繼宋元話本與傳奇之后,發(fā)展和興盛起來(lái)的通俗與文言小說(shuō)藝術(shù)。明代通俗小說(shuō)內(nèi)容豐富,形式多樣,既有長(zhǎng)篇巨帙,又有短小精悍之作。據(jù)明、清兩代著錄及近人搜集,長(zhǎng)篇小說(shuō)有目可考者,不下百種,流傳至今的有五六十部之多;短篇小說(shuō)則數(shù)以百計(jì),形成了中國(guó)小說(shuō)創(chuàng)作的一個(gè)高潮。
明代通俗小說(shuō)空前繁榮之成因
明太祖朱元璋結(jié)束了長(zhǎng)期混戰(zhàn)局面,建立了統(tǒng)一政權(quán)。明初經(jīng)濟(jì)漸趨復(fù)蘇。但是,從明憲宗朱見(jiàn)深起,封建最高統(tǒng)治集團(tuán)驕奢淫佚,政權(quán)每況愈下;權(quán)臣閹宦,結(jié)黨營(yíng)私,矛盾紛起,僅嘉靖一朝,宰相像走馬燈一樣,輪番替換,漫長(zhǎng)的中國(guó)封建社會(huì),緩慢地走向全面崩潰的末世。賴(lài)以這個(gè)經(jīng)濟(jì)基礎(chǔ)而生存的封建制度,以及維護(hù)這一制度的道德倫理、宗法觀念,亦隨之逐漸解體。另一方面,城市經(jīng)濟(jì)的繁榮,市民階層的壯大,紡織、冶鐵、制鹽、造紙、印刷等手工業(yè)的迅速成長(zhǎng),特別是東南沿海紡織工業(yè)中,明顯地出現(xiàn)了資本主義的萌芽的因素,給明代社會(huì)注入了新鮮活力。代表這股新興勢(shì)力的思想家,以王艮為代表的王學(xué)左派應(yīng)運(yùn)而生,造就了一批封建社會(huì)的叛逆者。他們朝著封建禮教,發(fā)起了猛烈抨擊,一切傳統(tǒng)觀念,來(lái)了個(gè)大顛倒,發(fā)生了翻天履地的變化。反映在文學(xué)觀念上,一向被視為雕蟲(chóng)小技的小說(shuō)戲曲,一變而與傳統(tǒng)的儒家經(jīng)典并列,社會(huì)地位空前提高。盡管宋元話本和評(píng)話在唐傳奇之后,已經(jīng)顯示出旺盛的藝術(shù)生命力,形成了另一個(gè)中國(guó)小說(shuō)創(chuàng)作的黃金時(shí)代,并與宋元南戲、元雜劇,雙峰對(duì)峙,在中國(guó)文學(xué)史上蔚為在觀;然而,巨大的藝術(shù)成就,仍沒(méi)有立即改變小說(shuō)不登大雅之堂的社會(huì)地位,仍被排斥在正統(tǒng)文學(xué)之外。只有到了明代--中國(guó)封建社會(huì)史上大轉(zhuǎn)折的朝代,小說(shuō)的社會(huì)地位才真正得以確立。這主要表現(xiàn)在:
一、小說(shuō)與經(jīng)典并列。先是李開(kāi)先指出:“《水滸傳》委曲詳盡,《史記》而下,便是此書(shū)。且古來(lái)更未有一事而二十冊(cè)者,倘以奸盜詐偽病之,不知序事之法,史學(xué)之妙者也”(《詞謔》)。破天荒第一次把小說(shuō)擺到如此崇高的地位。之后,李贄說(shuō)得更為透徹:“詩(shī)何必古選?文何必先秦?降而為六朝,變而為近體,又變而為傳奇,變而為院本,為雜劇,為《西廂記》,為《水滸傳》,為今之舉子業(yè);大賢言圣人之道,皆古今之至文,不可得而時(shí)勢(shì)先后論也”(《焚書(shū)》卷三《童心說(shuō)》)。一變而為“古今之至文”,石破驚天之語(yǔ),聞所未聞。于是,小說(shuō)成為文人案頭必讀之書(shū)(吳道新《文論》),它們的社會(huì)功能與不朽價(jià)值,也逐漸被人們清醒地看到:“歷代明君賢相,與夫君之佞臣,皆有小史,或揚(yáng)其芳,或播其穢,以勸懲后世,如《列國(guó)》、《三國(guó)》、《東西晉》、《水滸》、《西游》諸書(shū),與二十一史并傳不朽,可謂備矣”(崇禎辛未刻本《隋煬帝艷史·凡例》。最終,小說(shuō)戲曲被目為《春秋》,其地位與儒家經(jīng)典并駕齊驅(qū)(單宇《菊坡叢話》)。
二、震撼文壇,反映強(qiáng)烈。明代通俗小說(shuō),風(fēng)靡文壇,深入社會(huì)各個(gè)階層,得到公認(rèn),官僚大吏帶頭刊刻。周弘祖《古今書(shū)刻》已有都察院刻本《三國(guó)志演義》和《水滸傳》;郭勛刻有二十卷回本《忠義水滸全傳》;《酌忠志》卷十八《記內(nèi)板經(jīng)書(shū)記略》,記有《三國(guó)志通俗演義》為二十四本,一千一百五十頁(yè)。同時(shí),小說(shuō)始見(jiàn)著錄于官家書(shū)目。《永樂(lè)大典》卷一萬(wàn)七千六百三十六~一萬(wàn)七千六百六十三,收錄的宋元平話,就達(dá)二十六卷之多;《文化殿書(shū)目》也載有《三國(guó)志通俗演義》。不少作家開(kāi)始把讀小說(shuō)之后所寫(xiě)下的序、跋、文,收到自己的文集里,一時(shí)竟蔚然成風(fēng)。如人們熟知的張鳳翼、李贄為《水滸傳》所作的序。著名書(shū)法家文徵明抄寫(xiě)的《水滸傳》,數(shù)字驚人,計(jì)二十卷,文壇傳為佳話。就連傳統(tǒng)文化薰陶出來(lái)的正襟危坐之士、一生潛心于性命之學(xué)的嘉靖進(jìn)士黃訓(xùn),也寫(xiě)有《讀如意君傳》一文,這都是明代以前從未出現(xiàn)過(guò)的事情。至于通俗小說(shuō)獲得廣大市民的青睞,更不待言。
三、刊刻流布,影響廣泛。隨著印刷業(yè)的發(fā)達(dá),明代小說(shuō)刊刻之多,世人注目。刊刻一部小說(shuō)名著,數(shù)以十計(jì),屢見(jiàn)不鮮。尤其一向被視為范本的選本,也收錄小說(shuō)戲曲之作,前此未見(jiàn)。《花草粹編》據(jù)《水滸傳》收宋江詞,又收小說(shuō)《西湖三塔記》;而藏于美國(guó)國(guó)會(huì)圖書(shū)館佚名選本,所收小說(shuō)篇幅,竟占三分之一。萬(wàn)歷以后的小說(shuō)合刻選集,如《國(guó)色天香》、《繡谷春容》、《最如情》等,雖刻工粗劣,但已把小說(shuō)戲曲放在主要版面,而傳統(tǒng)的詩(shī)文卻被擠在不太顯眼的角落。不僅提高了小說(shuō)的地位,而且擴(kuò)大了影響。
四、小說(shuō)理論批評(píng),勃然興起。閱讀作品而微言大意,是原來(lái)漢儒攻讀儒家經(jīng)典著作的重要手法。隨著歷史發(fā)展,文學(xué)藝術(shù)各類(lèi)體裁的繁榮興盛,才被儒家由經(jīng)擴(kuò)展到史、子、集各部,蕃衍成為中國(guó)傳統(tǒng)治學(xué)的一大法門(mén),后世通稱(chēng)為“評(píng)點(diǎn)派”。明代小說(shuō)理論批評(píng)所以異軍突起,批評(píng)家輩出,乃是在小說(shuō)地位的不斷提高、文人學(xué)士為之傾倒、鄙視小說(shuō)的傳統(tǒng)觀念被徹底粉碎的時(shí)代條件下,才勃然興起的。而小說(shuō)社會(huì)地位的鞏固、確立,又賴(lài)于理論批評(píng)對(duì)它的文學(xué)與美學(xué)價(jià)值的充分肯定,賴(lài)于批點(diǎn)家們對(duì)小說(shuō)作品的深刻剖析。他們或揭明史實(shí),或闡發(fā)主旨,或臧否人物,或藝術(shù)鑒賞,探幽抉微,條分縷析,對(duì)小說(shuō)的審美規(guī)律、形象塑造等重要問(wèn)題,作出探索和總結(jié),不僅對(duì)小說(shuō)創(chuàng)作起了指導(dǎo)作用,而且加快了明代小說(shuō)空前興盛的進(jìn)程,為小說(shuō)的繁榮奠定了理論基礎(chǔ)。
由世代累積型集體創(chuàng)作到作家個(gè)人創(chuàng)作的過(guò)渡
中國(guó)通俗小說(shuō)發(fā)展到明代,處于承上啟下的轉(zhuǎn)折時(shí)期,即由世代累積型集體創(chuàng)作的話本、平話,向文人作家個(gè)人獨(dú)創(chuàng)的過(guò)渡,明代成書(shū)的幾部著名長(zhǎng)篇小說(shuō),都帶有這一鮮明特點(diǎn)。眾所周知,三國(guó)、水滸、西游的故事,都經(jīng)歷了較長(zhǎng)時(shí)間,甚至幾個(gè)世紀(jì)的流傳和積累,匯集世代書(shū)會(huì)人才、民間藝人的集集智慧,創(chuàng)作出各個(gè)系列故事集群,羅貫中、施耐庵、吳承恩,只是在此基礎(chǔ)上加工寫(xiě)定而生。早在《三國(guó)志演義》成書(shū)之前,《三國(guó)志平話》、《三分事略》已經(jīng)創(chuàng)建出三國(guó)故事的基本構(gòu)架;另外,元雜劇中的五十余種三國(guó)戲,場(chǎng)面恢宏,形象豐滿,也為《三國(guó)演義》的成書(shū)打下深厚的基礎(chǔ)。《水滸傳》成書(shū)之前,《醉翁談錄》里已有“石頭孫立”、“花和尚”、“武行者”的話本名目;而元人所輯《宣和遺事》,更保留了大段水滸故事;連同三十種水滸戲,同樣為《水滸傳》描繪出大致輪廓。《西游記》之前,不僅有話本《大唐三藏經(jīng)詩(shī)話》,而且宋元南戲、金院本、元雜劇都有豐富的西游題材劇作,為吳承恩的加工成書(shū),創(chuàng)造出藍(lán)圖。《金瓶梅詞話》究竟是世代積累型集體創(chuàng)作,還是作家個(gè)人獨(dú)創(chuàng),盡管學(xué)術(shù)界看法不一,但僅從名為“詞話”這一點(diǎn)來(lái)看,它應(yīng)當(dāng)和《大唐秦王詞話》一樣,都是世代累積型集體之作。因?yàn)樵挶揪褪窃~話本的簡(jiǎn)稱(chēng),詞話和話本,本是同一藝術(shù)形式,有說(shuō)有唱,唱詞韻文是小說(shuō)的有機(jī)組成部分,現(xiàn)存《金瓶梅詞話》就是明證。
明代的短篇通俗小說(shuō),除了明末文人創(chuàng)作的擬話本之外,也都是在宋元話本基礎(chǔ)上加工寫(xiě)定而成。附刻于明弘冶戊午(1498)《新刊大字魁本全相參增奇妙注釋西廂記》后的《錢(qián)塘佳夢(mèng)》,不僅《醉翁談錄》列在“煙粉總龜”下,而且這部短篇小說(shuō)的引首,全然抄自《水滸傳》的引首“詞曰”部分,除三個(gè)“暮”字外,均步原韻,確系在宋元話本基礎(chǔ)上寫(xiě)定。刊刻于明正德年間的小說(shuō)《如意君傳》,也是在民間流傳的武則天系列故事基礎(chǔ)上加工寫(xiě)定而成。至于《國(guó)色天香》收錄的《龍會(huì)蘭池》、《張于湖誤宿女貞觀記》,其故事也是世代累積而成,本事見(jiàn)南戲《拜月亭記》和《古今女史》。
中國(guó)通俗小說(shuō),由宋元民間創(chuàng)作的短篇話本、長(zhǎng)篇平話,發(fā)展成文人創(chuàng)作的短篇、長(zhǎng)篇小說(shuō),并非一蹴可及,而是經(jīng)歷了一個(gè)循序漸近的漫長(zhǎng)行程,其間也必然有一個(gè)過(guò)渡。關(guān)于這個(gè)發(fā)展過(guò)程,可以歸結(jié)為:世代累積型集體創(chuàng)作話本、平話--文人加工寫(xiě)定--作家個(gè)人創(chuàng)作短篇、長(zhǎng)篇小說(shuō)。文人加工寫(xiě)定,恰處這個(gè)過(guò)渡階段,承上啟下,不可或缺。文人加工寫(xiě)定,不同于改編,特別是篇幅浩繁的長(zhǎng)篇小說(shuō),從簡(jiǎn)單回目對(duì)仗、整齊劃一,到復(fù)雜的結(jié)構(gòu)布局、人物形象塑造,都是一項(xiàng)艱苦的創(chuàng)作性勞動(dòng)。因此,羅貫中、施耐庵、吳承恩、笑笑生、諸圣鄰,以及一大批不知名的加工寫(xiě)定者,都為中國(guó)白話小說(shuō)的發(fā)展,建立了不朽業(yè)績(jī)。他們一方面廣泛吸取民間集體創(chuàng)作的豐富養(yǎng)料,作了創(chuàng)造性的藝術(shù)加工;一方面又為作家個(gè)人獨(dú)創(chuàng),作了有益的嘗試和藝術(shù)實(shí)踐。中國(guó)白話小說(shuō),只有經(jīng)過(guò)這一自身?xiàng)l件的積累和準(zhǔn)備,才有可能在明末出現(xiàn)了一大批擬話本和以《醒世姻緣傳》為代表的長(zhǎng)篇小說(shuō),培養(yǎng)出凌初、李漁、西周生等一批天才的作家;同時(shí),也孕育了吳敬梓、曹雪芹與《儒林外史》、《紅樓夢(mèng)》的誕生和問(wèn)世。
題材廣泛豐富語(yǔ)言通俗易曉
由世代累積型集體創(chuàng)作,經(jīng)文人加工寫(xiě)定而成的小說(shuō),它們歷經(jīng)較長(zhǎng)時(shí)間的錘煉,又在不同地域流布,所以獨(dú)具題材多樣性和語(yǔ)言通俗性的鮮明特色。
就題材內(nèi)容而言,大致可以分兩大類(lèi)。一是非現(xiàn)實(shí)題材,包括歷史、
傳奇和虛的神怪故事,尤以前者居多。這是因?yàn)橹腥A民族歷史悠久,典籍豐富,正史之外,尚有大量的野史稗乘,為它們的創(chuàng)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上自盤(pán)古開(kāi)天辟地,下至明代,下至明代,各朝各代,都以通俗演義的形式相繼出現(xiàn),如《盤(pán)古至唐虞傳》、《列國(guó)志傳》、《兩漢演義傳》、《三國(guó)志演義》《東西晉演義》、《唐書(shū)志傳通俗演義》、《北宋志通俗演義》、《皇明英烈傳》等。對(duì)于這類(lèi)題材小說(shuō)的創(chuàng)作,《新列國(guó)志序》曾作過(guò)概括:“自羅貫中氏《三國(guó)志》一書(shū),以國(guó)史演義為通俗,汪洋百余回,為世所尚。嗣是效顰日眾,大而有《夏書(shū)》、《商書(shū)》、《列國(guó)》、《兩漢》、《唐書(shū)》、《殘?zhí)啤贰ⅰ赌媳彼巍分T刻,其浩繁幾于正史分簽并架。”《三國(guó)志演義》就是它們的代表作。
與七分史實(shí)、三分虛構(gòu)的歷史演義不同,有一類(lèi)小說(shuō),受傳奇小說(shuō)審美定勢(shì)的影響,加之傳統(tǒng)文學(xué)比興表現(xiàn)手法的根深蒂固,憑借歷史人物和事件來(lái)寄寓自己的理想,借古人之形骸,吹進(jìn)作者的思想情感。這類(lèi)小說(shuō)特點(diǎn),是不拘囿于史實(shí),而是擷取一些歷史人物和事件的某個(gè)側(cè)面或片斷,鋪張揚(yáng)厲,虛構(gòu)謀篇,《水滸傳》就是其中典型的一部。宋江,史有其人;宋江起義,也實(shí)有其事,但據(jù)《宋史》記載,宋江起義的規(guī)模有限,遠(yuǎn)不及同時(shí)代的方臘起義。像《水滸傳》所寫(xiě),攻城掠地,兵鋒所向,北至大名(河北),南及江州(江西九江市),西達(dá)華州(陜西華陽(yáng)縣)的起義,在宋代根本未曾出現(xiàn)過(guò)。評(píng)論《水滸傳》是歷史上宋江起義的真實(shí)反映,顯然不符合作品的實(shí)際,同時(shí)也沒(méi)有抓住這類(lèi)題材小說(shuō)的真諦。《水滸傳》主要借用宋江起義這一歷史事件,虛構(gòu)了一系列英雄形象,他們嫉惡如仇的高尚品德,超乎常人的非凡武藝,大無(wú)畏的反抗精神,特別是“官逼民反”這一封建社會(huì)反抗者的至理名言,正是他們世代夢(mèng)寐以求并為之奮爭(zhēng)的理想燭照。《北宋志傳》對(duì)楊門(mén)將的熱情謳歌,也是明代嘉靖以后,延綿不斷的邊患戰(zhàn)爭(zhēng)的歷史折射。這類(lèi)題材小說(shuō)的通病,在于有濃厚的封建倫理色彩。
在非現(xiàn)實(shí)題材小說(shuō)中,還有一種,借歷史事件描寫(xiě)神魔鬼怪之爭(zhēng),內(nèi)容虛幻,風(fēng)格奇特。《西游記》之唐三藏西天取經(jīng),《封神演義》的武王伐紂,在歷史上或可捕捉到身影,而《飛劍記》、《咒棗記》大寫(xiě)道仙、禪師,則在歷史上毫無(wú)蹤跡了。這些故事,毋寧說(shuō)是傳統(tǒng)道教、佛教逐漸世俗化的一個(gè)反映。因果報(bào)應(yīng),輪回說(shuō)教,宗教迷信,俯拾皆是,是其嚴(yán)重不足。
第二類(lèi)是現(xiàn)實(shí)題材,直面人生,可謂明代社會(huì)生活的一面鏡子。諸凡封建統(tǒng)治集團(tuán)的驕奢淫佚、忠奸斗爭(zhēng)、社會(huì)腐敗、政治黑暗、市井生活的蕓蕓眾生,聲情畫(huà)貌,情趣心態(tài),盡入筆端,構(gòu)成了一幅生動(dòng)的明代社會(huì)生活的風(fēng)俗畫(huà)卷。《金瓶梅詞話》發(fā)端,大批擬話本繼其后,間以海瑞、況鐘的斷獄公案,數(shù)量可觀,而以反映愛(ài)情婚姻題材的篇幅最多。愛(ài)情婚姻題材,是傳統(tǒng)小說(shuō)乃至整個(gè)文學(xué)史上的重要內(nèi)容,然而到了明代,卻賦予了新的內(nèi)涵。這主要表現(xiàn)在:伴隨著資本主義萌芽破土而出形成的新興思想影響下,傳統(tǒng)封建禮教受到了猛烈沖擊,反映在文學(xué)領(lǐng)域內(nèi),情與性,就是指向“存天理,去人欲”虛偽道學(xué)的投槍和匕首,而明代小說(shuō)和戲曲,恰是率先作了藝術(shù)反映。它們從肯定人的生存價(jià)值出發(fā),大膽肯定人的性欲為正當(dāng)要求,描寫(xiě)青年男女突破封建禮教的樊籬,追求摯著的愛(ài)情生活,帶有明顯的人文主義色彩,標(biāo)志著一個(gè)時(shí)代的覺(jué)醒。《金瓶梅》、《牡丹亭》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然而,這類(lèi)小說(shuō)也存在兩個(gè)嚴(yán)重的缺陷,即一夫多妻制的肯定和淫穢描寫(xiě)的泛濫。剛剛萌生的新興勢(shì)力,它們重視自身的價(jià)值,要與封建勢(shì)力抗?fàn)帲珔s看不到為之奮斗的美好前景。或者說(shuō),處于封建社會(huì)末世的明代現(xiàn)實(shí),還不能為它們提供一幅美的藍(lán)圖。觸目所及,盡是瘡痍,腐爛不堪,是故揭露抨擊有余,追求建樹(shù)不足。它們寫(xiě)情寫(xiě)性,是為了沖破傳統(tǒng)的封建禮教束縛,帶有那個(gè)時(shí)代的進(jìn)步要求。但是,才子佳人、一夫多妻,或長(zhǎng)篇累牘、恣意刻露的淫穢描寫(xiě),又恰是一次倒退;至于通篇淫亂,“著意所寫(xiě),專(zhuān)在性交”的一批淫書(shū),更是一個(gè)反動(dòng),形成了明代小說(shuō)創(chuàng)作的一股逆流。
明代通俗小說(shuō)創(chuàng)作一個(gè)最鮮明的藝術(shù)特色,就是語(yǔ)言更加通俗易曉,朝著俚俗化方向發(fā)展,使用了大量的市廛隱語(yǔ),切口聲嗽,有時(shí)雖失之規(guī)范,卻有很強(qiáng)的表現(xiàn)力,詞匯豐富,鮮明生動(dòng)。如果說(shuō)明代前期成書(shū)短篇和或長(zhǎng)篇還夾雜著大量文言詞匯的話,那么明代后期之作則洗蕩一空,完全口語(yǔ)化了。《三國(guó)志演義》使用的語(yǔ)言雖然簡(jiǎn)潔流暢,但也半文半白,更多地是淺近的文言。比之《三國(guó)志演義》,《水滸傳》的語(yǔ)言更接近口語(yǔ),洗練明快。《金瓶梅詞話》使用的就是當(dāng)時(shí)的白話口語(yǔ),諺語(yǔ)、成語(yǔ)、歇后語(yǔ)隨處可見(jiàn),隱語(yǔ)、江湖切口,比比皆是,帶有濃厚的市井獨(dú)特風(fēng)格,顯得異樣的生動(dòng)潑辣。這些成就的取得,不能不歸功于它的加工寫(xiě)定者或創(chuàng)作者不再是一些鴻儒雅士,而多數(shù)是長(zhǎng)期混跡于市民的一員,熟悉他們的語(yǔ)言,加工也得心應(yīng)手;或有的文人作家,對(duì)通俗文學(xué)特別酷愛(ài),以畢生的精力為之搜集整理、加工編輯,耳濡目染,吸引他們用通俗語(yǔ)言進(jìn)行小說(shuō)創(chuàng)作,馮夢(mèng)龍正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明代通俗小說(shuō)另一個(gè)藝術(shù)成就,是結(jié)構(gòu)完整嚴(yán)謹(jǐn),細(xì)節(jié)真實(shí)生動(dòng),人物性格飽滿鮮明。由文人作家加工寫(xiě)定而成的幾部著名長(zhǎng)篇小說(shuō),如“四大奇收”,與宋元平話相比,在藝術(shù)創(chuàng)作上有著質(zhì)的飛躍。這些作品對(duì)長(zhǎng)期流傳在民間的,作為小說(shuō)這一仍嫌粗糙的藝術(shù)樣式,進(jìn)行了重要的改造加工。從題目引首的整齊劃一、對(duì)偶勻稱(chēng),到情節(jié)結(jié)構(gòu)的精心安排、巧作勾連,特別是細(xì)節(jié)描寫(xiě)的真實(shí)逼真、細(xì)膩入微,使小說(shuō)這一藝術(shù)樣式在結(jié)構(gòu)上首尾完整,情節(jié)上引人入勝,形象上豐富生動(dòng)。寫(xiě)戰(zhàn)事,鐵馬金戈、氣勢(shì)恢宏。一個(gè)赤壁之戰(zhàn),《三國(guó)志演義》整整用了七回,重在刻畫(huà)人物性格。雖頭緒紛繁,人物眾多,卻處處圍繞著諸葛亭,盡管他未帶一兵一卒,但在魏、蜀、吳三國(guó)間的重大的、驚心動(dòng)魄的政治、軍事斗爭(zhēng)中卻運(yùn)籌帷幄,縱橫捭闔。寫(xiě)天上,神奇瑰麗,想象豐富。《西游記》里的孫悟空大鬧天宮,描寫(xiě)得如火如荼,栩栩如生。寫(xiě)世情,依照現(xiàn)實(shí)生活的本來(lái)面貌,細(xì)心提煉,維妙維肖,給讀者以真情實(shí)感,產(chǎn)生了巨大的藝術(shù)魅力。不同題材,采用了不同的塑造人物方法,藝術(shù)性格飽滿豐富,琳瑯滿目。幾百年過(guò)去了,而四大奇書(shū)里的藝術(shù)群像,仍在人們心目中熠熠生輝。
明代后期,馮夢(mèng)龍、凌濛初、李漁等創(chuàng)作的一大批擬話本小說(shuō),篇幅不長(zhǎng),但精雕細(xì)鏤,玲瓏剔透。一個(gè)故事入筆,揮灑自如,敘得娓娓動(dòng)聽(tīng)。如《譚楚玉戲城傳情
劉藐姑曲終守節(jié)》,在細(xì)致描寫(xiě)戲班演員生活的同時(shí),加進(jìn)傳統(tǒng)的王十朋與錢(qián)玉蓮故事,剪裁得體,獨(dú)具特色。難怪“祭江”這一細(xì)節(jié),到了《紅樓夢(mèng)》里,林黛玉也借以旁敲側(cè)擊,微含譏諷。不難看出,文人作家邁入明代通俗小說(shuō)的創(chuàng)作園地,從他們?yōu)槭来鄯e型集體創(chuàng)作加工寫(xiě)定,到自己匠心獨(dú)運(yùn),獨(dú)立創(chuàng)作,為中國(guó)古典小說(shuō)的藝術(shù),開(kāi)拓了一個(gè)嶄新的天地,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xiàn)。
文言小說(shuō)創(chuàng)作 與明代通俗小說(shuō)空前繁榮相比,明代文言小說(shuō)的創(chuàng)作,相對(duì)來(lái)說(shuō),難以抗衡。因襲傳統(tǒng)的靈怪、艷情題材,多以因果報(bào)應(yīng)出之,示意勸懲,削弱了小說(shuō)藝術(shù)的感人力量,筆記雜俎又多側(cè)重于自然現(xiàn)象的變異,帶有較多的迷信色彩。《剪燈新話》、《剪燈余話》雖不乏故事曲折、文筆凈潔之作,給予明代的文言小說(shuō)創(chuàng)作以深遠(yuǎn)影響,致使仿作迭起,趙弼的《效顰集》、陶輔的《花影集》、周禮的《秉燭清談》、邵景瞻的《覓燈因話》等相繼問(wèn)世,形成了“剪燈系列”,不少篇章也為擬話本和戲曲創(chuàng)作提供了素材,但內(nèi)容上多承唐宋傳奇余緒,較少新意,就其總體而言,成就不高。中國(guó)古代文言小說(shuō)發(fā)展到宋代,衰微之勢(shì),已見(jiàn)端倪,元、明兩代繼之,至清《聊齋志異》出現(xiàn)后,始有改觀。在文言小說(shuō)發(fā)展史上,明代處于創(chuàng)作的轉(zhuǎn)折時(shí)期,承上啟下,為清代文言小說(shuō)的興盛創(chuàng)造了條件,這主要表現(xiàn)在:
一是宋人崇尚紀(jì)實(shí)的小說(shuō)觀,在明代又有發(fā)展。自宋濂以小說(shuō)筆法作紀(jì)傳起,紀(jì)傳體小說(shuō)或帶小說(shuō)性的紀(jì)傳文不脛而走,蔚然成風(fēng)。即便帶有寓言性質(zhì)的《中山狼傳》,也以此體命筆,首尾完整,娓娓動(dòng)人。紀(jì)實(shí)性文言小說(shuō),逐步由虛幻飄渺的靈怪鬼魅,向現(xiàn)實(shí)生活貼近。雖是寫(xiě)鬼怪,卻富于強(qiáng)烈的現(xiàn)實(shí)人生色彩,如《綠衣人傳》的李慧娘鬼魂,采摭史實(shí),寄托了現(xiàn)實(shí)社會(huì)的愛(ài)僧,讀來(lái)親切可信。至宋懋澄的《負(fù)情儂傳》、《劉東山》、《珍珠衫》,則直面人生,有時(shí)有地,徹底擺脫了靈怪的構(gòu)架,改變了文言小說(shuō)“托往事而避近聞”的創(chuàng)作傾向。作者在《負(fù)情儂傳》結(jié)尾,明確無(wú)誤地告訴讀者:“余自庚子秋聞其事于友人,歲暮多暇,援筆敘事”。“丁末攜家南歸,舟中撿笥稿,見(jiàn)此事尚存,不忍湮沒(méi),急捉筆足之,惟恐其復(fù)崇,使我再捧腹也。既書(shū)之紙尾,以紀(jì)其異,復(fù)寄語(yǔ)女郎,傳已成矣。”現(xiàn)實(shí)社會(huì)生活入篇,就為文言小說(shuō)的創(chuàng)作開(kāi)拓了廣闊的天地。《聊齋志異》的作者蒲松齡在其作《老饕》篇末云:“此與劉東山事蓋仿佛焉”。說(shuō)明他的文言短篇?jiǎng)?chuàng)作,就接受了這一影響。《聊齋》中的不少篇章,本身就是作者耳聞目睹的現(xiàn)實(shí)社會(huì)生活的實(shí)錄;即便怪異故事,也與現(xiàn)實(shí)人生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所寫(xiě)陰司,實(shí)際上就是人間的反映,筆下的鬼狐,恰是人類(lèi)的化身。這一創(chuàng)作傳統(tǒng),在文言小說(shuō)創(chuàng)作史上產(chǎn)生的深遠(yuǎn)影響,是不應(yīng)低詁或抹殺的。
二是文言小說(shuō)朝著通俗的方向發(fā)展。先是明代前期之作顯受宋元話本的影響,《嬌紅傳》、《鐘情麗集》,甚至《如意君傳》,已是介于文言和話本之間;次后,通俗小說(shuō)的繁榮,對(duì)文言小說(shuō)的創(chuàng)作,更帶來(lái)了強(qiáng)大的沖擊力。于是,一向?qū)J掠玫洹?biāo)榜古奧的文言小說(shuō)中,也摻入了普通生活的口語(yǔ)、俚俗。特別是小說(shuō)合刻選集,漸趨明顯,至清初之蒲松齡,則集其大成,人物語(yǔ)言,聲口如聞,典雅與俚俗兼容并蓄,而且達(dá)到了和諧統(tǒng)一,形成了古雅簡(jiǎn)潔、清新活潑的語(yǔ)言風(fēng)格。
三是文言小說(shuō)的容量越來(lái)越大,包羅萬(wàn)象,傳奇、志怪、筆記、雜俎,群體具備。這固然為各種形態(tài)類(lèi)型的文言小說(shuō)創(chuàng)作打下了良好基礎(chǔ),但同時(shí)在內(nèi)容上也愈來(lái)愈駁雜。甚或在一部著作中,既有傳奇紀(jì)事,又備寓言小品;既講神鬼怪異,又談逸事瑣聞;既有帶情節(jié)的故事,又載自然界的奇異現(xiàn)象,籠統(tǒng)地把這類(lèi)著作稱(chēng)之為“文言小說(shuō)”,實(shí)不相符。尤其是一些文人筆記,更難以“小說(shuō)”立目。應(yīng)當(dāng)指出的是:在這些筆記雜俎之作中,常載有珍貴的小說(shuō)史料,向?yàn)檠芯空咚P(guān)注,如胡應(yīng)麟的《少室山房筆叢》,屠本畯的《山林經(jīng)濟(jì)籍》、薛岡的《天爵堂筆余》,李日華的《味水軒日記》、張丑的《日記》等,把它們列入小說(shuō)史料類(lèi),更為允當(dāng)。
四是文言小說(shuō)的篇幅愈來(lái)愈長(zhǎng)。明代的文言小說(shuō),筆記仍多短簡(jiǎn),而傳奇體則呈擴(kuò)充為中篇的趨勢(shì)。瞿佑之《剪燈新話》初見(jiàn)端倪,《鐘情麗集》、《懷春雅集》、《天緣奇遇》、《花神三妙傳》、《劉生覓蓮記》、《龍會(huì)蘭池錄》等集、編繼其后,至《輪回醒世》則動(dòng)輒數(shù)千言。篇幅的趨長(zhǎng),使情節(jié)曲折繁復(fù),枝節(jié)層出不窮,便于編織出更加動(dòng)人的故事;同時(shí),也與這種文體小說(shuō)的寫(xiě)法方法密加相關(guān),即作品中插入了大量的詩(shī)詞韻文。究其源,蓋因話本創(chuàng)作的影響,故時(shí)人稱(chēng)之為不文不白的“詩(shī)文小說(shuō)”。總之,不難看出,明代的文言小說(shuō)創(chuàng)作,由于受到通俗小說(shuō)的影響和沖擊,無(wú)論在思想內(nèi)容或是藝術(shù)形式上都增添了新的特色。
(劉輝撰)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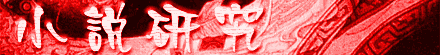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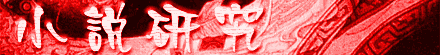

web@guoxue.com
web@guoxue.com
![]() 010-62917824
010-629178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