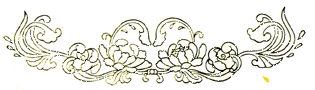| 國學 一說,產生于西學東漸之后,作為西學的對立物在東西方文明沖突中與西方文明對壘。二三百年來,國學是屢戰屢敗又屢敗屢戰,西學則“西風落葉下長安”,歐風美雨滿乾坤。面對如此局面,國學陣營里的戰將們每每悲從中來,時不時地舉起國學的旗幟吶喊一陣。 這些年,社會上一部分人對國學的興趣真是有增無減,理工科大學研究生導師把《論語》列為必修課已經不能盡興,還要將國學引入中學。國學為什么能有如此頑強的生命力,還能在今天博得如此眾多的愛憐?又為何總是振興不起來?
國學是產生于農業小生產基礎之上的一套理論,它規范了人際關系的準則,維護了漫長的封建社會的穩定,對于中華民族的形成、凝聚和發展立下過大功勞。但是,它幾乎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于政治和倫理,而忽視了對自然界的探索;過于注重內心的求索和人格的塑造,缺乏向外開拓的勇氣和興趣;過于注重現存秩序的穩定,而害怕變革。它經過兩千多年的自我改造而臻于完善,成為中華民族堅固的 文化 ———心理構造,滲透進了人們的思維習慣和行為準則。
歐洲 人對自然有著濃厚的興趣,總是不安分。他們能夠擴張,能夠“發現”新世界,能夠發動科學革命、工業革命和政治革命,根子也在于傳統的力量。古希臘 哲學 家們很注意觀察自然。與 孔子 同時的一批哲人猜想萬物的本源,是水?是火?是土?是風?是數?是原子?生活于公元前六世紀、古希臘七大賢人之一的泰勒斯,由于航海生活的需要,居然測定了太陽從夏至到冬至的運行軌道。古希臘的科技之光又照亮了西歐北歐,出現了一大批百科全書式的 思想 家和 科學家 。
哲學的核心是世界觀和認識論,回答精神和物質的關系。我國古代思想家缺乏科學的思辨,沒有回答這個問題,嚴格意義上說不是哲學家。著名美學家李澤厚認為,儒家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政治———社會哲學,而莊、禪則是人格心靈哲學,是很有道理的。據說列寧說過,莊子和禪學是一枝不結果的花。老莊也談到許多自然現象,但那是為了證明他們的社會學、倫理學和人生哲學,并不是他們學說的主體。到了宋朝,理學興起,把古代哲人本來就不發達的科學思考都打掉了,與禪宗相融合,搞打坐悟道那一套東西,專門去琢磨心性,把 儒學 引進了死胡同。
美國當代著名 歷史 學家斯塔夫里阿諾斯分析為什么西歐能順利擴張時指出,當時阿拉伯人和 中國 人都在熱衷于內省,專做心靈的工作,阿拉伯人讓出了 印度 洋, 中國人 讓出了太平洋,都遭受了慘重的損失。他在《世界通史》中這樣評價中國當時的儒學:“它尊重老年人,輕視年輕人;尊重過去,輕視現在;尊重已經確認的權威,輕視變革。由此,它成為保持各方面現狀的極好工具,最終導致了處處順從、事事以正統觀念為依據的氣氛,排除了思想繼續發展的可能。這一點有助于說明為什么中國盡管最初在發明造紙、印刷術、火藥和指南針方面取得了輝煌成就,但后來卻在技術上落后于西方。中國人在作出這些早期的發明之后,未能提出一系列科學原理。”
朱熹講“致知格物”,我原以為是對自然物的研究,后來才知道,他的“格物”是指“格心”。美國著名漢學家費正清在《美國與中國》一書中說:“‘格物'這句話沒有被解釋為科學的觀察,而是對于人生的研究。人類社會和個人關系繼續是中國學問的中心點,其中心點不是對自然的征服。”他還比較了中西古代 學者 的不同。他說,中國古代官員選拔制度使 讀書 人和工匠分離,“這種手與腦的分離與達.芬奇以后的早期歐洲科學家先驅們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對照。歐洲的科學家們往往來自講求技藝傳統的人們,雖然他們同樣是讀書人,可是他們沒有為社會風俗所限制而建立了自己的實驗室。”中國的國學先輩們自然沒有實驗室,只有講授倫理道德的書院。
鉆研外部世界的文化戰勝鉆研內心世界的文化,難道不是歷史的必然嗎?秋天來了,樹葉要落,不要悲傷,不要憂慮。我們不主張割斷歷史,不主張拋棄 傳統文化 。但國學并不等于傳統文化,不能一說到傳統就是國學,以為國學失傳了,就是傳統文化割斷了。
在競爭幾乎白熱化的現代世界,我們的當務之急是發展科學技術,迅速地把生產力搞上去。這關乎國家前途,民族命運。
愛了一輩子國學的錢穆早在80年前就說過:“學術本無國界。‘國學'一名,前既無承,將來亦恐不立。”在全球化的今天,各種文化正進行著前所未有的碰撞、交流和融合,與其戀戀于過去,莫如面向世界,面向未來。我們要借鑒和吸收古今中外文化中一切營養物質,創造出充滿生機與活力的、新的、先進的文化,只有這樣,才能夠“拓寬生命的河流,張揚生命的色彩,舒展生命的個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