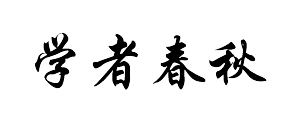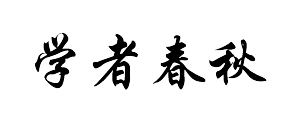采訪地點:北京馮其庸家中
采訪時間:2004年9月27日
采訪人:鄭寒白
鄭寒白(以下簡稱鄭):您畢業(yè)于無錫國專,這所由唐文治先生創(chuàng)立的學校,人才濟濟,如王蘧常、錢仲聯(lián)等,能否談一談他們給您的影響。
馮其庸(以下簡稱馮):這兩位先生確實是我終生難忘的恩師。先說說王先生,我認識王先生是在抗戰(zhàn)勝利后的1946年。這年春季,我考取了無錫國專。當時學校伙食較差,費用還高,另外大家對個別青年老師上課也不滿意,很有意見,就鬧,我寫了篇雜文,貼在墻上,批評學校。當時王先生是無錫國專上海分校教務長,兼無錫本校教務長。在王先生來無錫處理校務時,大家推舉我為代表。我就去見王先生,原原本本地講述了學生的要求,重點是教師問題,當時學生都是認真學習的,有些還很有根底,所以對老師要求很高,王老先生聽了我們的意見,不但不責怪我們,還很同情,認為學生的要求是合理的,他表示要安排調(diào)整,同時又為年輕教師作了解釋,說他們都很有學問,但畢竟年紀輕,口才不好,表達能力不夠,不要去傷害他們。伙食問題他也講了,帳目上如有問題,要清理查看,伙食要改善。王先生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對我也留有印象。那天談完以后,包括學校的老師,都請他寫字,他是大書法家。
鄭:那時他的書法就很有名?
馮:那時已經(jīng)不得了了。大家早已把紙準備好。無錫有一家箋扇店,叫春麟堂,春麟堂的紙全部被學校的學生教師買光了。當我知道大家求他寫字,王先生也答應給大家寫字了,我趕去買,但好宣紙都已賣完,就剩下夾宣,我就買了幾張夾宣帶回來。后來王老先生還是給我寫了幾副對子,我一直保留著。幾十年以后我去上海看望老先生,帶著對子給他看的時候,他看了說你還保留著,當時我寫字還不成樣子呢。他說,這樣吧,我給你在兩邊加一段跋。他就在這個對子上面加了一段長跋,(指著《王蘧常書法集》)這里面有,就是這個,“不妨春秋佳日去,最難風雨故人來。”這是他后來跋的,“此聯(lián)為余四十七歲,歲在丙戌,于無錫……”
鄭:王先生更早的作品您沒見過吧?
馮:更早的可能也就這樣。他后來給我寫了大量的信,但都在這之后了。
鄭:后來您聽過王先生的課嗎?
馮:我聽啊。從此我跟王先生有了交往,他也很關(guān)心我,這是1946年。接著1947年我參加了地下組織的活動,忽然我接到通知說,你不能在無錫呆了,你已經(jīng)上了黑名單,叫我連夜走。我想我到哪兒去呢,我一個農(nóng)村的學生,我就連忙給上海學校的王先生寫了封信。王先生很快給人捎信來說,別的不用管,你先來。我就和另外兩個同學馬上到了上海。上海無錫分校比較小,地名叫“麥特哈斯脫路”,很偏僻,大家都不太注意,所以他就叫我到那里去。當時上海的一些學界名人都被他請到了無錫國專講課。王老先生自己講《莊子》,他當時就講《逍遙游》,整個一學期一篇《逍遙游》沒講完,他講課不帶書,《莊子》原文全靠他自己背誦出來。我們都帶書,他背得跟書上一點兒都不差,然后他把各家的注釋一家一家給你講,最后再評這些家注釋的得失。
鄭:您所用的課本是《莊子集釋》嗎?
馮:那時沒有規(guī)定,選修課的課本都是自備的。老師把前人的注釋一家一家地疏通,最后他有自己的結(jié)論,這句話應該怎么解釋。當時我們都非常尊敬他,有時別的老師講課我們就不去了,遇到王老師講課沒一個缺的。《逍遙游》沒講完,但是他給我們最大的啟示是讀書要專精。當時童書業(yè)先生給我們講秦漢史。
鄭:王先生對秦史也很有研究。
馮:對,但當時童先生給我們講秦漢史,他后來是山東大學的名教授。每位教師都有特色。王先生是從來不帶書,隨便講卻能一字不差。童書業(yè)先生只帶一口袋粉筆,穿了長褂子,里面的褂子比外面長,外面褂子短了一大截他都不在乎,口袋里裝滿了粉筆。他講課時左邊一個學生,右邊一個學生,在他前面給他記錄。他隨口講隨時拿起粉筆寫,所引的古書都是他拿粉筆寫出來的,記憶力讓人佩服。而且他非常有意思,當時他和北京的唐蘭先生在論戰(zhàn)鐘鼎文,每次在講課以前先要講一段他辯論的情況,興致沖沖地說,今天我又給唐蘭先生寫了辯論文章,大公報的文史專欄馬上發(fā)表,我是講某某內(nèi)容,馬上把唐老先生駁倒了。過了一天又說,唐老先生反對我了,他是怎么怎么講的。他們很友好,互相也很尊重。他經(jīng)常這么講,把我們也帶入了這種學術(shù)的氣氛中了。還有顧佛影先生講詩。
鄭:顧佛影是被稱為“大漠詩人”的那位?
馮:對。顧佛影講詩。王佩諍先生講目錄學,他也是有名的大學者。
鄭:朱大可當時也在上海分校。
馮:朱大可也講詩,朱大可在前,顧佛影在后,我去的時候見過朱大可,但我聽到已經(jīng)是顧佛影講詩了。這里面有一個有趣的事,我去上海之前先到了虎丘,我們騎著馬到寒山寺。到上海后,因為有一個學生要被開除,他們叫我去向王先生講情,給他記過不要開除,因為他要畢業(yè)了。當時那個學生不太好,跳舞,老先生們非常生氣。在去講情的路上我被汽車撞了,汽車從我身上軋了過去。王先生知道這個情況非常關(guān)心,那個學生也免于了開除。我在病床上寫了一首詩,在上詩課的時候我把詩給顧佛影先生看,顧先生看了后稱贊得不得了,說“好詩好詩”,這給我寫詩以很大的鼓舞。我的詩是這樣寫的,“大劫歸來負病身,瘦腰減盡舊豐神。青山一路應憐我,不似春前躍馬人”。其實這之前我在中學時就開始寫詩,當時我不到20歲,在紡織學校讀書,無錫大畫家諸健秋和詞人張潮象組織了一個“湖山詩社”,他們要我參加。他們說“你寫一些試試,不要怕嘛,不管你寫得怎么樣,我看了之后我教你。”我就寫了一首詩,題目叫“上湖山社諸、張二公”,詩是這樣寫的,“東林剩有草縱橫,海內(nèi)何人續(xù)舊盟。今日湖山重結(jié)社,振興絕學仗先生。”兩位先生非常高興,稱贊我“清快有詩才”,諸先生馬上畫扇作為獎勵。
鄭:王蘧常先生早年詩寫得就很好,像“百嶺截江回地力,萬濤奔海放天才”、“山過大江俱跋扈,秋來北地亦蒼涼”,但他中年之后,專心學問,很少作詩,這其中有什么原因嗎?
馮:王先生他詩還是寫的,但是寫得不是太多,我問過他為什么不多寫,“反右”的時候他看到別人胡亂解釋,把人家詩解釋得一塌糊涂,而且定人家的罪名,這樣他怎么寫詩啊?但是在這之前他寫過一首詩特別長,是中國歷史上最長的詩之一,是歌頌中國共產(chǎn)黨的,一共2280韻,二萬二干八百四十多個字。寫完后就開始反右了,在這之后就不太寫詩了。但是我有幾首詩拿去給他看,他還是幫我改的。我寫的文章他也幫我改。王先生出書法集的時候,他打電話來讓我寫篇文章,我就寫了,他老先生看了很高興,但又把文章作了些修改。他改了什么地方呢?我當時的文章講,吳昌碩的石鼓文失去了石鼓的原意,何紹基寫漢碑,漢碑的意思盡失,他就把這些都去掉了。他對我說,“你講的話都對,如果是單獨評論他們就可以,但是你的這篇文章是寫你的老師的,寫我,你把古人說的不好,說我好,我心里不好受。”他還告訴我,以后寫文章的時候可以寫出自己的意見來,但要慎重后來我寫文章的時候,就盡量注意到這些。王老是章草大師,是學王的。我也學王,但學的是右軍家書那種,在學習中我也經(jīng)常向他請教,古人講執(zhí)筆要緊,要緊到別人從背后拔你手中的筆拔不了,我覺得沒那個必要,自己寫字誰來拔你的筆?執(zhí)筆過緊便會死板,我覺得在寫字的時候,要不斷地調(diào)整筆鋒,筆要隨時圓轉(zhuǎn),我不知道這樣對不對,他說你很聰明,很能領(lǐng)會,這一點誰也不講的,但都這么做,不會這樣做的字就寫不好,字是死的,不能變化了。他講寫字要用心地學習古人,他學習古人有的帖都臨爛了,我就按照他教的去寫。在他去世前給我寫了18封信,這個信寫完5天就去世了。當時我們在一起的時候,他身體還很好,吃飯比我吃得多,還叫他的女兒照顧好我,我是他的學生,他卻稱我為“馮先生”,說“你要照顧好馮先生”。沒想到18封信寫完交給我?guī)Щ貋恚氐奖本]幾天,電報來了,他去世了。他是個大學問家,但從來不炫耀自己,從來不說自己的學問大,比如這幾幅字(指著《王蘧常書法集》),我們知道他古文字寫得特別好,希望他寫一些古文字,寫完后,我們向他請教字的結(jié)構(gòu)、來歷,他就隨即給我們講哪個字出自哪本書,根據(jù)什么變化來的,交待得一清二楚。我們都大為吃驚。學問這么淵博,如果我們不問,他從來都不講,這對我們也是一個深刻的教育。他一再告訴我們,要謙虛,不要自炫,學問大的有的是。
鄭:錢仲聯(lián)先生教您是在無錫還是在上海?
馮:錢仲聯(lián)先生在無錫教的我。我的一位朋友嚴古津。
鄭:他是夏承燾的學生。
馮:是的,他也是錢先生的學生。嚴古津?qū)ξ艺f“你的詩才很難得,沒有錢先生指教這是一個大損失,王先生當然了不起,‘江南二仲'嘛!但他在上海,你還是先拜錢先生為師吧,我替你介紹。”他先向錢先生介紹了我的情況,錢先生也非常高興,當時(1946年)錢先生也沒什么工作,心境不大好,約好后,我就在無錫公園見了錢先生,拜他為師。那時他才四十歲左右,可詩名已經(jīng)不得了。當時沒有隆重的拜師禮,也就是喝喝茶。嚴古津當時正帶著那幅字(指著墻上懸掛的條幅),這是錢先生剛寫好的給嚴古津的一首詞,嚴古津說“我們都是窮學生,只能請老師喝喝茶,但老師能不能把這幅字賜給其庸作為紀念。”這幅字我從1946年一直保存到現(xiàn)在,前兩年我到蘇州去看錢先生,帶上了這幅字給他看,他還記得,“這幅字當初不是給你的。”老先生說“那時詞填得不好。”其實這是他的一首名作,詞名《八聲甘州》。前些年,葉嘉瑩先生來,看了我掛著的這首詞,還連聲說好。我說“我保存了50年了,這詞寫得多好啊,您能不能再給加個跋?”他馬上又給我寫了跋,后來還給我寫了一首長詩,七百多字,還給我寫成四尺整幅的大幅,寫時稿子也不看,寫完后一個字都不錯,當時我們都想老先生活到一百多歲都沒問題,沒想到后來……
鄭:96歲吧?
馮:是。錢先生是我在校外拜的老師,一般人都不知道。老先生在“文革”中很窘迫,要把他箋注的陸游詩稿賣掉,我反復勸他不能賣。后來到上世紀80年代,這部書終于出版了。
鄭:無錫國專創(chuàng)始人唐文治先生晚年雙目失明,他經(jīng)常參加學校的一般性活動嗎?與學生接觸多嗎?
馮:我1948年到上海,唐先生就在上海,他親自給我們講《詩經(jīng)》。他眼睛都看不見了,他的秘書陸修祜老先生扶著他上課。他的膀胱還出了問題,一個口袋掛在腰上。最近啟功先生也出了這個問題,所以我一直安慰啟先生,我們的唐老先生幾十年帶著這個口袋一直沒有出問題,挺好的,這對你身體不會有什么不好。啟先生后來也寬心了一些。中間更動人的一件事是,1948年解放戰(zhàn)爭打得非常厲害了,上海學生運動也風起云涌,國民黨反動派抓了我們一批同學,大家就推我為代表去找唐先生,陳述學生愛國的心情,不應該把學生抓起來,希望唐先生出來呼吁,把學生釋放。當時我們擔心這么大年齡的老先生,怎么肯卷入政治中呢?我們幾個同學到了唐先生家里,沒想到唐先生大大地表示同意,由他來起草,寫了一封給上海市長的信,請求釋放青年學生。寫好后唐先生還請當時社會名流來簽字。信送上去后國民黨政府受到了壓力,就把學生都放了。
鄭:在書畫界,您和許多大師都有密切的交往,比如劉海栗先生,他早期擅長油畫,以首倡人體模特繪畫教學,人稱為“藝術(shù)叛徒”,而晚年則多作國畫,畫上題詩,很能看到他傳統(tǒng)藝術(shù)修養(yǎng)之深,您認為他晚年的藝術(shù)觀念、藝術(shù)思想乃至性格是否變化很大。
馮:我和劉海老交往有二十多年了。他被打成“右派”,平反后的第——次畫展來北京舉辦,當時我不認識他,他到中國藝術(shù)研究院來找我給他寫序言,是我的朋友介紹的,我不在,他留了個條,我見到條后馬上去看望他。當時美術(shù)界的派系矛盾較重,聽說我要寫序,有人就給我打電話,叫我不要寫,說,如果你寫一篇,我們就要寫10篇來批判他,為了避免爭端我就沒有寫。后來文化部長黃鎮(zhèn)出面清美院的一位老前輩寫了篇序。開始時海老對我還有誤解,認為我膽小不敢寫,后來知道不是那么回事。對我了解后,他對我特別關(guān)心,我們來往20年,我覺得老先生人品很高,從來不說人壞話,文革中他受了很多苦,我們都為他不平。他說不要講這些事,過去的事沒有什么了不起的,都過去了就不要再提了,要看人家長處,不要看人家短處。他的油畫水平很高,但晚年為什么多畫中國畫呢?因為他的中國畫綜合修養(yǎng)是非常高的,他的中國畫都有深厚傳統(tǒng)功力,特別是晚年畫黃山,就是“揚州八怪”也畫不出來這種境界。這位老先生才華橫溢,有一次在黃山,我碰到他在桃源亭作畫,當時我要走了,但汽車壞了,又回到了山上,他說“我說你走不了嘛,快來給我的畫題字。”我想這么珍貴的畫,我怎么能隨便題呢?他說“你題嘛,你愛怎么題就怎么題。”我題過后他很高興。后來他給我畫了一幅《拜山圖》,托人帶過來,但我始終沒有見到,打電話問他,他也沒記住那個人的名字,只是當時那個人說能帶給我,他就信了。
鄭:這幅作品將來在拍賣會上也許能見到。
馮:后來他又特意為我畫了一幅葡萄,并題上了幾句詩。有一次在北京海老要和我會面,但有位要人請他吃飯,派車來接,他說“現(xiàn)在不能去,我已和馮先生約好了,車一會兒到恭王府接我吧。”在恭王府我的辦公室他看了我的畫,很稱贊。車幾次來催,海老才對我說,“今天本來要合作繪畫,留待以后吧。”臨走的時候,夏師母給我一卷紙,原來是海老為我早巳題好的“瓜飯樓”匾額。所以后來我去香港,在九龍見到海老,他邀請我和他合作,鋪開了一張六尺宣紙,他說你先畫,我想起在新疆看到的葡萄,就拿筆畫起了葡萄,我畫完后海老來收拾畫面,又題了兩句詩,落款處他寫道“馮其庸、劉海粟合作”,我說“你怎么把我的名字寫在前頭?”他說“我題當然應該把你的名字寫在前頭。”我給他題的另外一幅畫,后來有一個慈善機構(gòu)拿去拍賣,聽說賣了很大一筆錢,都捐給慈善機構(gòu)了。有一次在北京開畫展,美國人拼命要買他的畫,他堅決不賣。后來是黃鎮(zhèn)部長協(xié)調(diào),他才同意將幾幅畫賣給美國人,所得的一筆錢全部交給國家,他自己分文不取。
鄭:劉海栗、朱屺瞻都是您所熟悉的繪畫大師,對于他二人您能否作一個比較性評價?
馮:兩個人都畫油畫,國畫畫得也都很好,劉海老更傳統(tǒng),用墨畫的東西多,用筆老辣,境界之高都是傳統(tǒng)的精神。朱屺老吸收油畫的東西多,他把油畫的技法都用到國畫上去了,他畫的山水在用色等各方面都吸收油畫的東西。朱屺老畫畫時還喜歡聽音樂,都是外國音樂,一邊聽一邊畫。
鄭:給您影響較多的其他的書畫家,能談談嗎?
馮:前面提到的諸健秋先生,他看到我的畫后很喜歡我,又知道我很窮,就特意允許我看他畫畫,一般畫家創(chuàng)作時是不愿意讓別人看到的,他說看就是學,就這樣看了半年,我初識了一些山水畫的畫法。
鄭:您到北京之后接觸的畫家呢?
馮:我1954年調(diào)到北京,第一個接觸的就是許麟廬先生,他當時開了個和平畫店,我在無錫國專時的老師周貽白先生帶我去許先生那里。我把我的畫帶給他看,是齊白石的風格,許老看了很稱贊,他說我?guī)闳タ待R白石。我想我這樣一個小青年,怎么敢去看齊老先生呢,等以后畫好了再去吧。沒想到第二年,齊老先生就去世了,我懊悔得不得了。以后我再見到劉海老、朱屺老等其他大畫家,就再也不敢輕易放過了。
鄭:除了北京的畫家,您和上海、江蘇一帶的畫家聯(lián)系好像比較多。
馮:上世紀80年代朱屺瞻老先生到北京,他給我打電話說要來看我,我哪里敢當呢,就馬上去北京飯店看望他,冰心和吳文藻也恰好在,雖然我以前曾為老先生題過畫,但這是我們的第一次見面,他非常高興。直到他去世,我們二十多年一直有往來。周懷民先生是我的同鄉(xiāng)前輩,大我十幾歲,他畫山水很出名,深受張大干的器重,我們來往比較多。也是上世紀80年代后期,上海的唐云先生到北京來,就是周先生介紹我認識的。唐先生非常爽快,喜歡喝酒,每次到上海我都要去看他,見面一定要喝酒。唐先生聽說我有一把曼生壺,特地跑到我家,看到壺高興得不得了,他說拿紙來我要畫畫,乘興與周懷民先生合作了一幅山水,命我做個長題,這幅畫現(xiàn)在還保存著,可是唐先生在畫完的第二年就去世了。另外一位謝稚柳先生也是那個時候認識的,第一次見面的時候,閑談中我提起我非常崇拜的常州詞人、書畫家謝玉岑,他說,“哎呀,就是我的哥哥”,我們就從謝玉岑談到錢名山,又談到他也喜歡的《紅樓夢》,非常投機。
鄭:您在繪畫上喜歡哪些人的作品?
馮:比較喜歡董源、巨然,尤其是“元四家”。我現(xiàn)在在認真地學習宋元的作品,最近臨摹了好幾幅,有些在裱。
鄭:您廣覽歷代碑帖,見過許多真跡,而皈依只在王羲之,“平生苦愛古軍書,一帖蘭亭卅載余”,在今天書壇力倡創(chuàng)新,對王羲之顛覆重整、大力改造的作品頗領(lǐng)風騷,您有何看法?
馮:藝術(shù)和市場是兩回事。對現(xiàn)今的書壇,我有兩點看法,首先是后繼有人,很多人能夠?qū)懙煤芤?guī)矩,能夠得古人的風神。第二點,我不贊成現(xiàn)在的有些書風,它不是真正的書法。其實,書法要和傳統(tǒng)學問結(jié)合在一起。古人說詩有別才,其實書也有別才,書法家要先讀書,有修養(yǎng),有學問,眼界要開闊。只有提高了自己的學問修養(yǎng),再勤學苦練,才能使自己的藝術(shù)有所成就。
原載《中國書畫》2006年11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