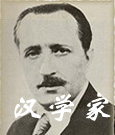|
| 國學網首頁→學人部→海外漢學→漢學家 |
|
||
訪談法蘭西科學院院士謝和耐 |
||
相關專題
|
(法)謝和耐/錢林森
錢林森(簡稱錢):您的大著《中國與基督教》(Chine et Christianisme)從1982年在巴黎出版以來,受到了西方和東方讀者的廣泛歡迎,引起學界的重視。據我所知,法國老資格的比較文學大家艾田樸先生(R.Etiemble)就把您這部著作視為研究中西文化關系的權威性著作,給予了極高評價,在其兩卷集的代表作《中國之歐洲》(L'Europe chinoise;1988-1989;Gallimard)多次加以引述。中國先后有兩種譯本問世,一是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譯本,一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出的譯本,在中國讀書界廣泛流傳。我首先想問的是,您花了多長時間醞釀、撰寫這部著作?為什么要寫這部書?這部書問世后在學術界和宗教界引起怎樣的反響,這也是中國廣大讀者和學者感興趣的問題。 謝和耐(簡稱謝):大約從1970年起,我開始對基督教與中國這個主題發生興趣,那時我正應歷史學家費爾南多·布洛代爾之邀,準備撰寫一部關于中國通史的書——《中國世界》(這本書有一個很好的譯本,開始面向中國讀者,由黃建華先生和黃迅余女士翻譯,《中國社會文化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它也促使我嘗試去更好地了解明朝。我的第一篇文章事實上開始寫于1972年(《關于17和18世紀中國和歐洲的接觸》),(1972年中文翻譯登刊在《國際漢學》,由商務印書館1995年出版),緊接著1973年寫了另一篇文章由《將近1600年前后利馬竇的皈依政策和中國精神生活的演變》,(1973中譯本刊登在《國外中國學研究譯叢》),和1976年寫了《從16世紀末到17世紀中葉的基督教主義和中國哲學》,《尚蒂伊國際漢學討論會文集》。 當我寫這本書時,我的想法是,中國人對傳教士行為和傳授的反應提出一些根本性的問題,由于存在一些根深蒂固的觀念,這些問題在西方并沒有被研究過。西方人仍舊認為世界的歷史打他們的歷史那兒開始,并且從他們自身來判斷別的事物。認為現代西方人是過去所有時代,對所有文化具有價值典范的想法,在我們這里還沒有完全消失,西方原則優越性的偏見也沒有完全消失。因此,仔細研究17世紀中國人對傳教士言行的反應是把這些觀念再次提出來加以審視的途徑,這也是表明,除非人類有所意識,他們是受其時代、階層,尤其是在一個不同于歐洲和中國的氛圍中,以及所有他們繼承的歷史傳統所制約的。社會組織、政治體系、思想、行為,所有的歷史傳統,尤其是宗教傳統,所有這一切在既定的時代和文化中形成相對凝聚的整體。所有這些方面都得予以考慮。相反,如果人們認為一個人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樣的,那就沒有什么可研究的了。(在一段歷史中人們是被設想為一個敘述。這個歷史可能非常艱深、博學,有時甚至具有教育性或娛樂性,但是在歷史和文明過程中它提不出異于其他的根本的思想問題。) 我并不很關心我的書出版后的反響。我相信應該總體反應是好的(除了耶穌會士雜志《學習》中一篇一位耶穌會士寫的惡意的文章。文章影射我不懂中文,因此我不能閱讀我曾譯過的文章)。內容上唯一的批評是基于最后三頁,關于語言和思想的關系問題(這個問題一直使我掛慮。我認為人們不能借口剔除所有的思想和哲學,這一語言與思想的關系問題是可以從一種語言譯至另一種語言的)。 錢:您的這部書有一個副標題:第一次沖撞(La première confrontation)。據此,中國的第一本譯書名干脆改為《中國文化與基督教的沖撞》。表明本書的主旨在于描述東西方兩種不同的文明首次相遇時所存在的差異,所發生的矛盾與碰撞,正像您的導言和再版前言里所強調過的那樣。這是您的書有別于同代人和前輩同類作品的地方。我想請您就這部“充滿深刻智慧的著作”,就其獨特性:構思、選材、論述及主旨諸方面的獨特角度,發表您的看法。 謝:您問及我這本書的特色。我上面剛剛說過,我的觀點是社會組織、政治體系、思想、行為、傳統,尤其是作為這一整體的主要要素的宗教形式,所有這一切構成一體,所有這些方面應該予以考慮。相反,如果人們認為面對的只是可互相替代的個體,如果人們假設一個人在任何地方都是不變的,而大部分情況則首先他不是賴以生存的世界之產物,(即使他個人是獨特的),那么都沒有什么可以研究的。 至于工作方法,在我看來應該以文獻為基礎。在撰寫我的著作時,我最重視的就是中國和西方同一時代的文本比照,中西文本、法文和意大利文文本的對照。可以說,這本書就是中西文獻的雜集。文獻的對照和分析使得我給自己提出問題,就是這樣,一點一點組成這部書的材料。若從先驗的觀點出發,注定只能講些平庸的見解,或者從一開始就走上歧途。正如在我看來是中國最偉大的哲學家王船山所言:“有即事以窮理,無立理以限事”。 錢:就嚴格意義上的中外文化交流通史而言,在促進基督教文化和中國儒家文化真正意義上交融中,利馬竇(Matteo Ricci)無疑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他是近代羅馬天主教在中國傳教的真正奠基人,保羅教皇在1982年慶祝利馬竇到達中國400周年紀念會上稱利氏為“歐洲文明與中國文明之間的真正橋梁”。他的重要嘗試和貢獻在于尋求地球兩端獨立發展的兩個偉大文明首次對話的共同話語,即致力于“合儒”、“補儒”的方針大略,力圖將兩種不同文化進行“調和”和“會通”,從而構成了中外關系史上永恒而迷人的話題。您作為這方面的權威專家,對此有何看法?兩種不同形態的文明,基督教文明和儒家文明能夠“會通”和“調和”嗎? 謝:似乎可以,實質上不可能,利馬竇曾經嘗試過,有其歷史功績,但失敗了。 要想理解傳教士的行為和他們詮釋中國人的反應的方式,就必須按照他們的思想來思考:罰入地獄或靈魂永久得救的思想,在人類生活的所有細節,在皈依和圣跡中都有上帝永恒的干預的思想,在頭腦中有信仰撒旦的干預和著魔的思想,相信洗禮、圣水、十字架和圣象的效力,善與惡的根本對立。傳教士來到中國時是深信自己掌握著由上帝親自默啟的真理的。他們深信基督教應該在世界各地獲得勝利。在他們看來,他們的勝利幾乎是完全的,既然他們進駐到美洲、非洲、印度和東南亞。他們認為正如他們在別的地方所做的一樣,他們是來拯救中國人于永恒的地獄,把他們從魔鬼的束縛中解脫出來,借助上帝的幫助使人們皈依。他們隨時準備必要時去為了證明基督教的真理而獻身。中國人的所言所行應該與這些先存的心理模式相協調。 中國不是一個易被征服的國家。最初的兩個傳教士,羅明和利馬竇因此從1583年開始不得不同時被人們當作外國修道士而萬分小心地推進。中國人在他們身上首先看到的是一種佛教和尚的新面目。但是中國也不同于被征服的那些國家和日本,因為她是一個由國家高級官員統治的疆域廣闊的國家。在中國文化與政治權利之間有著緊密的聯系(這一特點也使其有別于印度,葡萄牙人通過武力定居在西海岸的幾個城市里)。然而,基督徒他們自身是修道士的同時也是一些學識淵博,頗有修養的人。因為他們想使得皇帝改變信仰——他們相信,這樣將會改變整個中國的信仰——最初也是最知名的的基督徒,利馬竇認為首先應該贏得統治階層和文人們的同情。他著名的綏靖政策就是受到這一計劃的啟發。他在進入廣東時的艱難情況逐步令其認識到他以修道士自居的錯誤以及必須以講學的西士身份出現的優勢,因為這是那個時代的潮流。為了能夠深受大學士和高官們的歡迎,為了能夠和他們去討論,他努力去掌握中文知識以及四書五經,并且從1595年起,在他到達肇慶12年后,他改換了服飾,穿著像大學士。這樣他就開創了一種幾乎為其所有同胞和后繼者所使用的方法。他想不僅通過他對古典文學的了解而且通過他驚人的記憶力,他在數學和天文學方面的知識,他的倫理著作,他帶來的新奇的玩意兒震撼和感動中國的精英們。從他旅居肇慶開始,他在居住的寺廟中所繪制的《世界地圖》,或稱《萬國輿圖》引起了極大的好奇。從1590-1591年起,他開始教授歐洲數學。 在閱讀古典文學的時候,利馬竇相信《尚書》和《大雅》中的上帝就是《圣經》中的純潔的神靈,造物主上帝;他相信中國在基督之前的上古時代經歷過一次最初的基督的默啟。利馬竇和他的一些后繼者們認為在任何情況下,他們所關注的是將基督教的意義賦予古典文學作品和孔子的言錄來改造加工這些神靈。但是,這個方法從中國文人方面而言可能與宋朝(基督徒們視之為無神論和唯物主義的時代)評論權威們發生沖突;而另一方面,也遇到一些基督教徒和其他嫉妒基督教的宗教階級(奧古斯丁教派,多明我會,方濟各會修士,在17世紀已自菲律賓進入福建)的強烈反對。這些反對利馬竇策略的人拒絕去適應中國傳統或者懷疑其效力。他們認為他不用這么謹慎,而應該嚴格地傳授教義。這一敵意自然也延及利馬竇及其策略的與會者為贏得中國精英們的賞識所做的事情中(科學和技術的教授,倫理著作或宇宙志)。尤其使那些反對利馬竇所創的如此謹慎的方法論著的人震驚的是,構成基督教精髓本身的東西沒有被傳授,也即基督即上帝的化身,基督教在中國可能會以伊斯蘭教和猶太教的簡單變種出現。然而,對于中國人耶穌被釘于十字架上是一種侮辱性的酷刑,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的圖像令他們不寒而栗。利馬竇很快就意識到這一點。那場應該激起歐洲高漲情緒的宗教儀式的著名論戰正式涉及的只是古典文學作品中的上帝和《圣經》中的相似之處以及對已皈依的中國人仍舊繼續崇拜孔子的許可。事實上,這觸及一個更加根本性的問題:想知道是否基督教確實被傳授給了中國人。 但是,在謹慎派和堅定派之間,歸根究底,只是策略的不同而已。對于他們所有人來說,目的就是改變中國。盡管今天我們很自然會說到這是傳教士頭腦中的“兩個文明的對話”,但這并不是對話的問題,而是知道要使得中國信奉宗教怎樣去行事:給中文文本一個新的意義,滲透入文人的思想中去,暫時允許對祖先、孔子、與其所聯系的大學士的崇拜,被人當作文人或者從一開始就表現其是什么,也即想修道士來中國宣揚福音書?利馬竇的嘗試在于混淆基督教和中國人的概念的范圍里可能允許一些“宗教信仰的改變”,因為改宗一詞所隱瞞的事實從沒有那么簡單。但是借助古典文學,并想說服他們并不完全理解的文人階層,利馬竇與他的信徒們走進了一個死胡同。此外,從中國人的觀點出發,一方面不能接受其以文人自居的方法混合;另一方面也接受不了耽于那些驅魔法中。 我認為,不應該把這“兩個文明沖撞”的結果看得太重要。基督徒的確使得一些西方傳統得以傳播(尤其是技術和科學),但是應該睜大眼睛,分析一下這些東西帶來的后果《幾何原本》(《歐幾里得數學基礎知識》的前六個章節)就是通過利馬竇的講解,由徐光啟翻譯的。這本書非常不適應中國傳統,中國人又以其自己的方法重新詮釋過。該書有一些影響,但不是以其最初的形式。從普遍的方法看,許多中國人欣賞那些以“求問和探索”為主的他們稱之為西方方法論的東西(諸如質測),要看的不是理論的方面,而是適用于那個時代的方面,在那個時代經過東北方面的威脅和16世紀的佛教偏移之后,人們想回到一些具體的事物上(諸如史學)。當人們研究利馬竇主要著作《天主實義》時,會看到他在書中鋪呈了一系列的抽象論據。這些論據完全不同于中國傳統,被中國人認為是人為的(中國人喜歡的是利馬竇那有著與中國道義人為的相合之處的道義)。利馬竇的論據是基于亞里士多德理論上的11至16世紀的中世紀經院派論據。這一極其貧乏的經院派理論已經被那個時代正在發展從伽利略到牛頓的古典主義理論的學者所摒棄。這里我并不想花時間談論這些細節。歸根結底,之所以基督徒帶來的革新在中國的影響不可能十分深遠,是因為思維模式、歷史傳統、知識基礎是大不相同的。大體上,我認為尤其存在著對兩根肋骨的鄙夷和錯誤解釋——對于宗教、天、上帝和道義尤為如此。而就傳教士本身,為了促成他們所構想的“轉變”也有著一些故意的歪曲。 來源:中華讀書報 |
|
北京國學時代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Copyright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