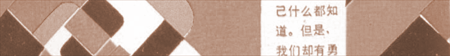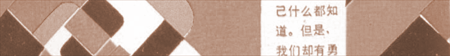歷史文學史序言
在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中,歷史與文學始終有著不解之緣。無論哪種形式的文學,總是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說起具有悠久歷史的中國文學,我們也總是習慣于按朝代或時代來對其進行劃分,如先秦文學、兩漢文學、唐宋文學、近代文學等等。中國人早就認識到了文學的發展和時代變化之間的關系,劉勰在《文心雕龍·時序篇》中說得好:“時運交移,質文代變”,自“昔在陶唐”到“皇齊馭寶”,“蔚映十代,辭采九變”,于是,“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的說法,就不僅僅是人們描述中國文學發展史的常用話語,同時也成為對其進行研究的重要思想指導。
但是要說起文學與歷史的關系,還遠遠不是如此簡單。文學的產生與發展不但受制于歷史的變化,其內容和形式有時竟也與史學不分,亦文亦史,亦史亦文。在中國的上古時期亦即先秦時期,以《春秋》、《左傳》等為代表的中國早期的歷史著作,同時也被我們稱之為“歷史散文”或曰“史傳文學”;反過來,像《詩經》這樣的文學作品,也被歷史研究者視為最珍貴最可靠的上古歷史文獻,其中有些作品就直接被后世稱之為“史詩”,正所謂“六經皆史”、“六經皆文”。到了漢代以后,雖然隨著學術的分化而使中國的正統史學與文學的關系越來越遠,但是用文學來演繹歷史或者把歷史作為文學題材的現象并沒有消失。從遠在先秦的《穆天子傳》、《晏子春秋》開始而形成的雜史雜傳傳統,到漢代以后則蔚為大觀,出現了袁康、吳平的《越絕書》、趙曄的《吳越春秋》、佚名的《漢武帝故事》、劉向的《列女傳》等一系列著作。由此而往,魏晉南北朝有軼事類小說;隋唐以后有歷史人物傳奇;宋代有講史話本;元代有歷史戲劇;明代有歷史演義小說;清代有歷史題材的說唱;現當代有歷史回憶錄、歷史題材的電影和電視劇等等。它們的內容是“歷史”的,形式是“文學”的,“文”與“史”在它們身上如水乳交融一般,永遠也不可能分開,這無疑是一種重要的中國文化現象。
遺憾的是,多年來我們雖然在斷代文學史和分體文學史的研究中不斷地涉及這種現象,其中一些作品,也是傳統文學研究的重要對象,可是我們并沒有把它們當成一種特殊的文化現象來認識,自然也沒有人來揭示它的藝術特質,對它的發生發展過程進行詳細的考察。這對于全面地認識中國文學傳統來講,不能不說是一個缺陷。樹增教授以其敏銳的學術眼光,看到了這一文學現象的重要性,并率先對它展開了系統的研究。他把這一類型的文學統稱之為“歷史文學”,第一次對它的特質進行了具有科學意義的界定,對其發生發展的歷史進行了粗線條的描述,并寫出了第一部中國《歷史文學史》(先秦兩漢卷),這無疑是一項具有開創性意義的工作。
“中國歷史文學”是中國歷史與文學的完美結合,它既是以文學的筆法書寫的歷史,又是以歷史事件、歷史人物為題材的文學作品。它在先秦時期就達到了相當的高度,這正體現了中華民族的文化特征:由于自夏商周三代以來中國就逐步進入了“理性社會”,原本十分豐富的中國神話傳說被過早地湮滅;而史官文化的發達則使中國人很早就形成了重史的傳統。這使先秦時期的中國沒有產生像古希臘那樣長篇的史詩,可是卻產生了希臘人無法企及的歷史著作。如果說,正因為古希臘的神話與史詩的出現才會給西方文學提供了“豐富的土壤和武庫”,從而奠定了西方文學的文化傳統;那么在中國,也正因為史官文化的發達,才使得先秦的歷史文學成為中國后世小說、戲曲等的重要文化源頭,使歷史文學成為中國文學的一種主流。我以為,樹增教授以此為切入點來研究中國文學,其意義是相當重要的。他不僅為中國歷史文學的本質給予定性,寫出了第一部具有開創意義的中國歷史文學史,而且還從一個新的角度揭示了中國文學獨特的發生過程、發展規律,有利于從世界文化的范圍內來更好地認識中國文學的內容形式以及其鮮明的民族特色,確立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中的獨特地位。
我們知道,中國文學史作為一門新的學科,是在西方文學史觀的影響下發展起來的,因而對中國文學史規律的認識,在不知不覺中也受到了西方文化中心論的影響,這使得我們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習慣于按西方文學史的發展之路來評價和衡量中國文學史的發展。例如關于史詩,曾經有許多學者以古希臘的長篇史詩為標準,認定中國古代沒有史詩,這甚至被看成是中國古代文學不發達的標志。這種論斷自然是錯誤的,因而也引起了一些學者的強烈反對,他們認為,《詩經》中的《生民》、《公劉》、《玄鳥》、《長發》等詩,就是中國古代的史詩,它們雖然沒有古希臘史詩的長度,但是卻具備史詩的全部要素。這種解釋自然是有道理的。但不容諱言,《生民》、《公劉》等史詩在規模的宏偉和內容的豐富上遠不能與荷馬史詩相比,若以此來進行比較,仍然不能說中國的古代史詩與同時期的古希臘的史詩一樣偉大。但我們并不能以此作為評價中國古代文學是否發達的標準,這是不公平的。因為在這種比較中,人們還是在不自覺中受制于西方文學的評判體系,仍然沒有脫離西方文學中心論的偏見。而樹增教授的研究則完全立足于中國文化傳統的實際,他以充分的事實說明,中國文學是在一種完全不同于西方文化傳統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有著獨特的發生發展之路。這正如同樹增教授所說:我國古代神話史詩的不發達,“這與其說是我們民族文化的‘短處’,不如將它視為我們民族文化的一個特點。中國文學有自己獨特的發展道路,中國不曾發展出繁榮的神話文學、在荷馬史詩的時期也沒有產生出具有大型規模的敘事詩,但中國在當時卻找到了一種新的表現形式,它那種全面、詳盡地反映歷史大變革的能力,甚至超過了荷馬史詩。”因此,我們不必要為中國沒有產生古希臘那樣的長篇史詩而自卑,而應該為中國有如此悠久的歷史文學傳統而驕傲。這對于站在世界范圍內全面而又正確地認識中國文學特色,其啟示意義是極大的。
中國歷史文學史是把“文”與“史”融為一體的具有綜合形態的一種新的文學史,它包含著蓄積久遠的文化內容,有著旺盛不衰的生命活力,因而對它的研究也就必須從民族文化的大背景方面著眼,從中國文化特征的早期探源開始,從文學與史學以及其它意識形態的網狀聯系中理出頭緒,從紛繁復雜的中國文化現象中去把握其發展脈絡。可以說,中國歷史文學史的撰寫既是一個全新的課題,也是一個較大的系統工程,其難度可想而知。樹增教授經過四年的勤奮研究,數易其稿,終于寫出了這部五十萬字的巨著。全書分為“中國歷史文學的萌生”、“中國歷史文學的發達”、“中國歷史文學的成熟”三編,并在“導言”中就中國歷史文學的特質及其發展脈絡進行了科學的界定與簡要清晰的描述。書中的許多問題,都是樹增教授首先提出來并在歷史文學史的框架下第一次展開論述的。如樹增教授認為:“歷史文學的基本特質是既有歷史科學的真實性與概括性,又有文學的典型性與藝術性。它是藝術地表現歷史,同時又在表現歷史的過程中體現出作者對歷史以及現實的思想情感與審美觀。”這一定性既講明了什么是歷史文學,同時也界定了全書論述的范圍,并為其進行史的表述和理論的分析打下了良好的基礎。樹增教授還指出:“中國歷史文學發展的內在脈絡是中國歷史文學特質的形成及其演化,只有把所握了這一點,才能清理出一條清晰的中國歷史文學自身發展的軌跡,這條軌跡要合乎中國歷史文學內在的發展邏輯。當我們將中國歷史文學特質的形成、演化置于中國社會歷史進程中去加以觀照時,便會發現:中國歷史文學特質的形成不僅與社會的發展相聯系,也與中國文學形體的演進相聯系。”以此為線索,樹增教授把中國歷史文學的發展大致劃分為四個大的歷史階段:從上古到漢為第一個階段,從魏晉到宋為第二個階段,從元至清為第三個階段,“五四”運動以后至今為第四個階段。并根據每個階段的不同特點,分別把它們稱之為“文隱于史的階段”、“文史偏流的階段”、“史隱于文的階段”和“文史兼容的階段”,我以為,樹增教授的這一論述和歷史分段是符合中國歷史文學發展規律的,其概括也是相當準確簡明并具有學術啟發意義的,它有助于我們認識中國歷史文學的發展過程,并為以后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礎。有了這樣的理論指導和史的框架,樹增教授自然就把過去文學研究中難以涉及到、或者雖有涉及卻因為難以納入傳統的文學系統因而不可能進行深入研究的一些著作,如《山海經》、《穆天子傳》、《晏子春秋》、《燕丹子》等納入了一個完整的中國歷史文學的范疇,并給它們設定了一個準確的文學史位置,同時得出了一些前人所未發的結論。此外,全書豐富的內容、翔實的資料,析理的深刻透辟,以及一些富有理論創見的論述,都會給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它的出現,是近年來中國古典文學研究領域里可喜的新收獲,也是著者獻給21世紀學術界的一份厚禮。
樹增教授是我的師兄。1984年底,我們共同考入東北師范大學楊公驥教授門下攻讀博士學位,并同處一室。樹增兄不但在學業上給我以巨大的幫助,在生活上更如同親兄長一樣給我以熱情的關懷。我們共同讀書,共同討論問題,共同跑步和打球,也共同去欣賞長春五月的飛花和十月的瑞雪。三年多的朝夕相處,結下了無比深厚的友誼,也留下了許許多多難忘的回憶。博士畢業后,我先去了青島,又來到北京,他則去了大連。雖然兩地相隔,但我們之間一直沒有中斷學術上的合作與互助,一起參予策劃并編寫了《先秦大文學史》、《兩漢大文學史》,共同撰寫了《二十世紀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史》。在青島和大連美麗的海濱,我們數不清有多少次的長夜漫談,共訴別后的相思,共析學問上的疑難,共話人生中的困惑,也共同在海邊撿拾美麗的貝殼,追逐那雪白的浪花。在這些年中,他在學術上的勤奮,更給我樹立了很好的榜樣。十幾年來,除了我們共同的合作之外,他自己還撰寫了多部學術著作和教材,為部隊院校的建設做出了重大貢獻。自然,在這些年的學術研究中,他最投入的還是關于中國歷史文學的思考。早在攻讀博士學位之時,他就把自己的學術主攻方向定在了以《春秋》、《左傳》和《史記》等為代表的先秦兩漢的歷史文學上。這部著作,正是他十多年來在中國歷史文學方面研究和思考的結晶。多年的辛勤耕耘終于結出了豐碩的成果,做為他最親密的學弟,我怎能不為他的豐收而感動!
在新世紀的第一年,在一個明媚的春日,樹增教授托人給我捎來了這部書稿,并矚我寫幾句話為序。 全書中豐富的內容和精辟的論述,已非我這支拙筆所能盡言,相信它能夠經受住讀者的評判和歷史的考驗。在此,僅能寫幾句贅言,以表達我先睹為快的感受和心情,一來為我的學兄所取得的成果表示祝賀,二來也為學術界在新世紀的開始就產生了這樣具有創新意識的新著而高興,并愿樹增教授再接再厲,寫出一部貫通古今的歷史文學史。
趙 敏 俐
2001年3月15日于北京花園村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