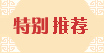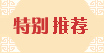【總序】
可以用參考資料來代替教科書么?
編纂一套哲學史或思想史的參考資料集,并不算什么新的舉措,以前的學者,陸陸續續也編過不少種。在國內,像過去中華書局出版過《中國哲學史參考資料》若干冊,曾經是過去幾十年里學習中國哲學史的重要參考書。在國外,很有名的,比如狄百瑞(W.de Bary)編《中國傳統研究資料集》(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和陳榮捷(Wingtsit Chan)編《中國哲學文獻選編》(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前者與《印度傳統研究資料集》、《日本傳統研究資料集》構成一個系列,1960年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影響相當大,我曾經看到日本學者福井文雅相當推崇的書評,后者1963年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按照臺灣的黃俊杰教授的說法,它“一直是歐美各高等學府講授中國哲學或中國思想史等相關課程的必要教科書或參考書,其地位一直屹立不搖”,而近年更由一些臺灣學者聯手回譯成中文,1993年在臺灣巨流圖書公司出版兩大冊。
不過,盡管有這些書在前,我還是希望重新編一部新的《中國思想史參考資料集》。為什么?因為現在有了一些重新編撰的條件。首先,經過這些年的世事變更,中國大陸的學術界不僅開始走出意識形態的局限,而且有了將思想史與哲學史區別的自覺,更有了來自本土的問題,思想史研究已經有了相當大的變化,漸漸形成了新的研究思路和敘述立場。其次,思想史有了豐富的新資料,除了眾所周知的考古新發現,像簡帛文獻等,使得先秦兩漢思想史不得不重新考慮自己的范圍之外,由于思想史觀念的變化,也使一批過去很少被納入思想史視野的資料,特別是過去的邊緣資料,開始進入了思想史關注的焦點。再次,思想史研究的背景視野,也從過去的單一的漢族中國,放寬到全球,至少像明清以后,中國的思想與文化背景由“天下”變成了“萬國”,它的思想史,就已經不再是一個孤立的思想線索,于是它也有了很多諸如“交往”、“影響”、“沖擊—反應”、“世界體系”、“現代化”等框架,這使得原來的資料不敷使用。
更主要的是,很久以來,我一直在想一個問題,就是“是否可以用參考資料集代替教科書?”思考這個問題的原因很簡單。作為一個教師,首先,我常常遇到的一個困惑就是,當我們大學里面那些集歷史敘述和歷史解釋為一體的教科書,把所有的歷史事實和歷史解釋好像都已經完滿地總結和論斷了以后,那些教科書的讀者還需要,或者說還可以做什么、想什么?其次,經由那些教科書中權威解釋了的內容,如果它已經可以充當考試的標準答案,可以使閱讀者獲得需要的分數,那么,除了一些自己對歷史有興趣的人以外,學生們還會去讀有關歷史的原始文獻么,這樣,歷史就不再是原來的歷史,而成了被咀嚼過的飯、被皴染過的布了。再次,這些教科書是否會成為,或者已經成為歷史研究的范本或者模仿的文本,如果是,那么接受了這些現成答案以后的歷史研究將如何進行?
因此,我總覺得,代替教科書,更多地閱讀和使用那種解釋成分較少、文獻資料較多的參考資料集,可能會在某種程度上修正過去依賴教科書的弊病,也可以使讀者少一點后設的結論,多一點自己的理解。這就是我提出編纂一套資料集的初衷。
但是,我得承認,編起來還是很不容易,并不是說,新的一定比舊的好,現在來編一套參考資料就一定比過去人編得好,其實,在還沒有開始編撰的時候,我就已經察覺到面臨的困難。
第一個困難是,思想史是一個學科邊界至今也還不很清楚的領域。雖然它作為一種歷史著述被歐美歷史學界普遍接受和使用,從十九世紀晚期已經開始,但是,盡管西方人對于如何是“觀念史”(History of Ideas)、如何是“思想史”(History of Thought或Intellectual History)、如何是“哲學史”(Philosophy History)有過種種討論,可它的領地邊界至今也沒有一個被共同認可的說法。而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中,它也和哲學史很難分清,所謂社會思想、政治思想、哲學思想之類的詞語,常常在哲學史和思想史中混用,特別是近年來思想史與社會史、思想史與知識史的互相結合,一般知識、思想與信仰史被普遍重視,更使得這種原來期待的學科邊界被瓦解于無形。于是,這使得我們現在重新編纂一部《參考資料集》發生了很大的困難,如果我們不想漫無邊際地擴張思想史的領地,以至于思想史本身都被瓦解,我們應當如何小心翼翼地、有節制地選擇文獻資料?
第二個困難是,如何合理地確定文獻資料的章節安排,使它能夠擺脫過去思想史編寫的舊格局?在拙著《中國思想史·導言》中,我曾經說過,在以往的各種《思想史》中,習慣的編纂法是,按照時間的順序安排著思想家們的章節,大的思想家一章,小的思想家一節,不夠等級的可以幾個人合起來占上一節,再不夠格的也可以占上一段,而這些思想家的組合就是思想史,大多數《思想史》都是這么寫的。但是,我總覺得,這種方式并不能體現歷史的連續性,也常常使思想史變成“學案”,而不是“歷史”,它忽略了那些作為“背景”的合唱聲音,更容易忽略在社會生活中真正影響人們的一般知識、思想與信仰,那么,我們如何在有限的篇幅中,通過文獻選編盡可能地呈現更廣泛的思想世界?
第三個困難是,過去各種哲學史或思想史的參考資料選編,其實,背后都有一個相當完整和固定的理論和歷史在,他們是按照一種既定方針和思路,在有目的地選擇文獻資料的,但是,這樣的參考資料實際上是對某個《思想史》進行解說或提供證據,因此,讀參考資料集的時候,其實就是在讀擴大了的某個思想史著作的論據,那個思想史著作始終明里暗里在約束著閱讀者對思想史的理解。我不否認每個參考資料都有自己的歷史理解在支持它的選擇思路,但是我們能不能使參考資料變得更開放一些?套一句熟語,就是使參考資料集的閱讀者在這些資料的閱讀中有“可持續發展”,他們能否從這里面進一步發展出自己對思想史的看法?過去我們的教育常常是“教”,居高臨下,用考試、答案和分數制約思想,盡管常常說“教學相長”,卻總是忽略了“學”如何對歷史進行理解,那么,我們能否采取某些形式,使閱讀者能夠自己從中得到理解的自由空間?
我設想的參考資料集,本來應該包括三種,一是《中國思想史參考資料集》,主要是按照時間與專題的順序收錄參考文獻與論著,二是《海外中國思想史研究資料集》,我希望以原文收錄,因為這既可以讓學生領略國外的思路和方法,又可以閱讀外文的專門著作,三是《中國思想史參考圖集》,這是我一直在琢磨的一種形式,我總覺得,思想并不止在文字表述中,也在圖像之中,因此可以收集一些有意味的圖片為思想史資料。
但是,現在呈現在各位面前的只是第一種。關于這一種《參考資料集》,我理想中的結構應當是這樣的:
首先,由簡明的“編者按語”或者“引言”開頭,對每一節的內容提綱契領進行說明;
然后,有若干“關鍵文獻”,因為這些文獻可能是了解這一部分思想史的關鍵,因此需要加上較詳細的注釋,以幫助理解,而注釋又最好能夠進一步提供深入探討的線索,所以在可能的情況下多引用資料;
再后面,是為了進一步擴大閱讀面而安排的“參考文獻”,我希望這些文獻能夠超過過去教科書的范圍和數量,使讀者能夠自己在原始文獻中理解,并想象那個時代的思想與文化狀況;
最后,是經過選擇的“參考論著”,當時我建議應當廣泛搜羅中外文的論著,仿佛提供一個挑選過的論著索引,為愿意更深入研究的讀者提供信息的空間。這里所有的意思,就是三點:
一是少一些固定的敘述和結論,免得它成了限制思想史空間的緊箍咒;
二是多提供一些文獻,讓讀者接觸一些應當自己讀的資料,免得在第二手的敘述中接受現成的答案;
三是盡量提供一些論著,讓讀者知道還有更多的深入的探討,不要以為這點兒教材就已經窮盡了思想史。
但是,盡管編撰一套《中國思想史參考資料集》的設想和計劃,在我心里已經反復考慮過好多遍了,盡管我可以不自量力地獨自寫了一部《中國思想史》,但是編撰一套《中國思想史參考資料集》,我卻覺得必須要邀請同事來一起合作,而合作,就不能完全依照我個人的想法,如今的集體項目,常常要將就、要妥協,總是取最小公倍數或最大公約數,因此呈現在讀者面前的這一套參考資料集,仍然是半新半舊,半是理想,半是現實的一個雜拌兒,這是我要向讀者預先道歉的。